书里书外“弼马温”
编者按:近日,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广雅出版夏婷婷《表象背后:文艺作品中的法律小史》,该著立足法律史视野,由中外代表性艺术画作、文学小说切入,挖掘表象背后具有现实意义的法律问题,展现古今中西不同的社会文化及法律制度的演变。经出版方授权,中国作家网特遴选其中《书里书外“弼马温”》部分,以飨读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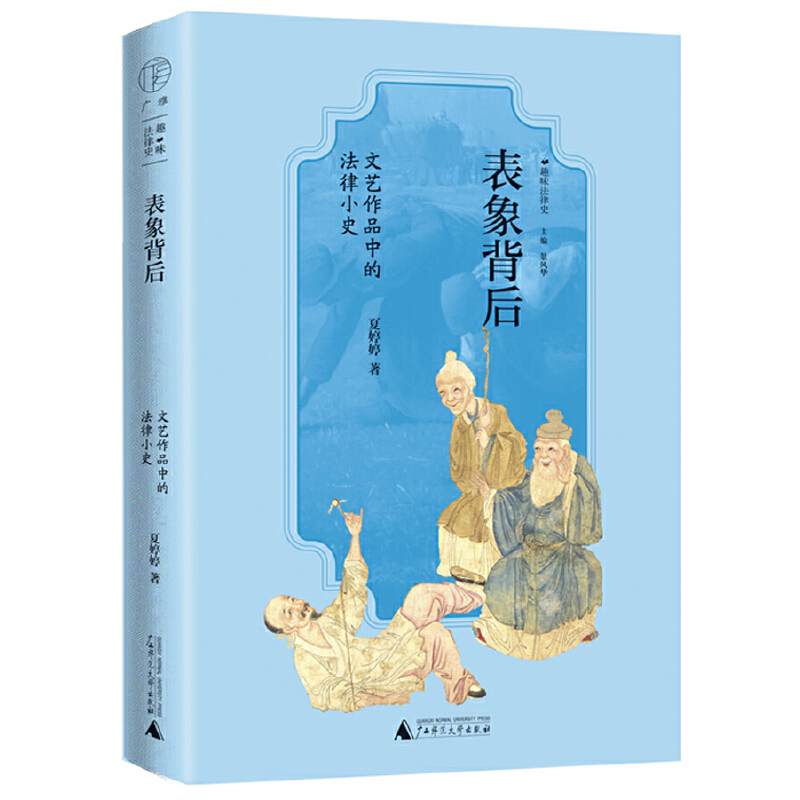
《表象背后:文艺作品中的法律小史》,夏婷婷 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广雅,2025年2月
一、《西游记》中众所周知的弼马温
在《西游记》中,“弼马温”一词成为神仙鬼怪对孙悟空的专用嘲笑和贬损之词。而齐天大圣被封为弼马温的故事情节主要发生在第四回“官封弼马心何足 名注齐天意未宁”。得官后的猴王起初还是欢欢喜喜的,到任后也是非常爱岗敬业的。但在接风酒席上,猴王忽然问道“我这弼马温是个甚么官衔”时,得到的回答却是“没有品从”。众道的解释是:“不大,不大,只唤做‘未入流’。”“末等。这样官儿,最低最小,只可与他看马。”自称“齐天大圣”的猴王到了天宫却被封了个不入流的末等官,这是何等的羞辱!所以才引出了猴王搅乱蟠桃宴、偷吃仙丹的报复故事。被天宫羞辱过的猴王,在取经道路上遇到知道他过去底细的神怪,在情急之下都愿意揭他的伤疤,指他的痛处。十万天兵讨伐花果山时,二郎神就当面骂过孙悟空:“你这厮有眼无珠,认不得我么!吾乃玉帝外甥,敕封昭慧灵王二郎是也。今蒙上命,到此擒你这造反天宫的弼马温猢狲,你还不知死活!”揭孙悟空伤疤最多的当然要数猪八戒了,每次受到孙悟空的戏耍时都会骂上一句“弼马温”。嘲笑孙悟空做过弼马温的,当然少不了来自天庭或佛界,像骗取袈裟的黑熊精、广寒宫里的玉兔精、文殊菩萨的坐骑青毛狮子怪等一干神妖精怪。
回到我们要讨论的主题,当大圣问到属下此官是个几品时,得到的答案是不入流,没有品从。属下接着还说弼马温的主要职责就是饲养天马,马喂得膘肥那是本分,如果马儿稍有羸弱,就会受到责怪,如果马儿有了损伤,甚至会被罚赎问罪。很明显,玉帝给孙大圣安排了一个吃力不讨好的职位。《三晋石刻大全》中对现存石刻“西游记华表”上的记载进行了拓印,其中有一句提到:“唐设楼烦监牧于此养马,典记系猴于马厩可避马瘟。”明代谢肇淛在《五杂俎》中也曾提到:“(弼马温)置狙于马厩,令马不疫。”看来因为在中国古代有民间传说,认为猴子可以避马瘟,所以吴承恩在《西游记》里取其谐音杜撰了“弼马温”这个官名。
“弼马温”遭到了大圣的嫌弃,只因其被告知弼马温是一个不入流、没有品从的官职。那么,“弼马温”真如书中所言是个极其低微的职位吗?在中国古代,马被看作重要的交通运输工具,还是衡量战斗力强弱的重要标志,那么有没有跟养马相关的官职?官品又是几何?同时,古代人讲的“不入流”是什么意思,与其相对的又是什么群体?
二、历史上的御马监
按照武曲星君启奏的原话,天宫里的御马监缺个正堂管事的,于是玉皇大帝便除授给孙大圣“御马监正堂管事”一职。再从御马监的人员构成来看,还有监丞、监副、典薄、力士等一干人等,也就是说这管天马的御马监人员组成完备,是个标准的职能机构,所以也不能简单地认为弼马温就是一个马匹饲养员,低贱而不入流。那么,为什么孙悟空本人甚至是普通读者都觉得弼马温是个没有官品的、最低最小的末等官呢?这样的灌输自然来自御马监中众人之口。所以有些专门研究《西游记》的学者从行政管理学的角度给出了一个解释,认为孙悟空上任御马监最初其实是有着励精图治之心的;但是他工作狂的作风使得手下的这些监丞、监副、典薄、力士都招架不了,再加上这些人在孙悟空出现之前一直是消极怠工的,甚至还有捞点草料钱的油头,但在新官到来之后一切都起了变化。这种情况下,只有架空新官或逼走新官才能维护他们小集团的利益,于是有一天,这些人逮到了机会,告诉孙悟空他担任的是个末等官,是给玉帝做奴才的。在这些属下的挑唆下,官场菜鸟孙悟空一怒之下返回了花果山。回过头来,在玉皇大帝设朝之日,这些御马监的监丞、监副在丹墀下拜奏时却是另外一种说法:“新任弼马温孙悟空,因嫌官小,昨日反下天宫去了。”由此可见,粗读之下,《西游记》中对弼马温官品的描述确实容易让人产生错误认识。
事实上,古代对马的重视,从其专设官职即可见。例如,在明代确实存在过御马监这样的属衙,它属于宦官二十四衙门之一,《明史·职官志三》中记载:“御马监,设令一人,正七品,丞一人,从七品。”“御马监,掌印、监督、提督太监各一员。腾骧四卫营各设监官、掌司、典簿、写字、拏马等员。象房有掌司等员。”可见,明朝御马监无正堂管事一职,其最高长官是掌印太监,官职为七品或从七品官(明初则是四、五品级)。总之,明代的御马监为官署名,由太监执掌担任,掌理御厩、兵符之事,历史上像汪直这样的宦官也曾担任过掌印御马监之职。宦官在明代组成二十四衙门,掌印太监在各部门均有,并各司其职,御马监属十二监,在御马监内,掌印太监一名和监督太监、提督太监各一员一起,共同职掌御厩诸事,禁军下有监官、掌司、牵马的人等。
清代《称谓录》卷十九中记载:“顺治初年设御马监,十八年改为阿敦衙门,以大臣侍卫管理。康熙十六年改为上驷院。”在《清史稿·兵志》中亦有介绍:“清初沿明制,设御马监,康熙间,改为上驷院,掌御马,以备上乘。畜以备御者,曰内马;供仪仗者,曰仗马。御马选入,以印烙之。设蒙古马医官疗马病。上巡幸及行围,扈从官弁,各给官马。”清初承明制,仍然设有御马监,虽名称有变,但其职能并未有实质性变化。
在冷兵器时代,马的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历朝历代统治者都对其重视有加。《宋史·职官志》中提到过“掌国马,别其驽良,以待军国之用”。马除了用于战争,平时还是非常重要的一种交通运输工具,其用途甚广。马饲养得好坏,关乎国运,这样说并不为过,若是皇帝的御马,那就更显珍贵和重要,统治者自然也会给予足够的重视。如辽代掌管御马的机构为尚厩局,宋朝有群牧司,唐代有太仆寺,高宗龙朔二年(662)改为司驭寺,武后时叫司仆寺,中宗神龙元年(705)又复旧称。唐太宗曾任命太仆少卿张万岁掌管马政。此外,唐代还专门设置东宫九牧监,正八品以上,掌牧养马牛,供皇太子之用。武后设置闲厩使、飞龙使,渐夺马政权利。可见历朝历代,御马都深受统治者重视。
《明史》中说御马监令为正七品,从古代官员的品秩上看,官品确实不高。从俸禄的发展变化看,御马监官的所得俸禄也确实不多。但如前所述,皇帝的御马都是精挑细选出来的良马。若是战时,御马监还是掌管作战工具的重要军事机构,战马的好坏直接关系到骑兵的生死和战争的成败,岂是小事!所以说,御马监其实是一个官小权重的机构。
三、“流内官”与“流外官”
《西游记》中的弼马温据称是未入流的末等官,但事实上明代的御马监令官品最低时为正七品,七品官属于流内官,相当于今天地方基层官员的品秩,并非“未入流”。《明史·职官志》中对“未入流”有解释:“文选掌官吏班秩迁升、改调之事,以赞尚书。凡文官之品九,品有正从,为级一十八。不及九品曰未入流。”由此可见,明代的官品共分为十八级,而九品外的官才就被称为未入流,官秩低微;而九品之内叫作“流内官”。
对“流内官”与“流外官”的区分并非始于明代。我国封建社会官品选拔、考核体系的形成可追溯到秦汉之初,官职的具体品级在历朝历代都有严格规定,并有所沿革。西汉将官职分为二十级,曹魏时以一品至九品定分为九级,形成九品官人法。九品官人法是魏晋南北朝时期将人才评价与官员任用相结合的一种人才选拔方法。
“流内官”“流外官”是从北魏的人才选拔中开始出现的。鲜卑政权通过氏族详定制度,确定每一个家族的地位,然后以九品中正制为基础,对官员进行“乡品”的认定。“乡品”是指根据乡里公众的评论评定的品级标准,“乡品”高的被称为“流内官”,“流内官”的升迁速度非常快。与之相对应的就是“流外官”,“乡品”低,升迁速度相对也慢。“流内官”还被称为“清官”,“流外官”又被称为“浊官”。
官品性质的发展与转变是一个渐进的过程,但它也有突变的时候。公元5世纪末、6世纪初,南朝梁武帝在天监二年(503)、天监七年(508)进行了两次重大的官制改革:“使九品官人法向两个方向分张,一个是向官阶制的分张,一个是向官班制的分张,九品官人法被改造成为两个内容,一个是九品官阶制度,一是官班选用制度……官班制中的流内十八班与流外七班间的巨大鸿沟,二品资品者可以进入官班制的十八班,不具有二品资品者,不能进入十八班,这就在二品以上与三品以下之间划出了深刻的界限。”从这一思路着眼梳理官品与俸禄之间对应关系的变化,秦以前官爵合一,以爵定官;秦汉以秩定官,即以官吏俸禄来确定官阶;汉袭秦制,以石为单位论俸禄并最终定型;魏晋时以品定官开始出现。
隋朝的官品制度与职官制度的联系就更为紧密了。隋朝职官是由流内官和流外官两部分组成的,而流内与流外皆有官品。流内的官品分为九品,品各有从,由正四品开始到从九品,每个正、从品又分上下阶,一共三十个等级。流外官官品也有“流外勋品、二品、三品、四品、五品、六品、七品、八品、九品之差。又视流外,亦有视勋品、视二品、视三品、视四品、视五品、视六品、视七品、视八品、视九品之差。极于胥吏矣,皆无上下阶云”(《隋书·百官志下》)。从整个官僚体系考查,隋代的官品设计,是比较复杂的。但也遵循一个大的原则,就是官品的高低是与官职、爵位的高低相对应的。
隋以后,将不入九品的职官称为流外官,流外官通过考核可升级为流内官,此时称为“入流”。唐袭隋制,因贵族政治向官僚政治的过渡,与三省六部为主体的行政格局相适应,确立了完整的职官制度,并为宋朝以后历代职官制度奠定了基础。唐代,文官自正四品以下,武官自正三品以下,还分为上下阶,因此,唐代文官的散官实际上有三十个等级,武官散官等级是三十二等,这些等级总称为“流内官”,为正式文武官员。
依唐代官制,以低级散官而任较高职务者称守某官,反之为行某官,可以看出当时散官具有一定的独立性。流外官也有九品,实际上属于吏员,不在正式官员的范围内。唐代的流外官作为中央集权政治制度的组成部分,在中国封建社会的职官制度发展中,起到了承上启下的作用。唐代数量众多的流外官如令史、书令史、府、史、亭长、掌固、典事、谒者、楷书手等,广泛设置于中央到地方的各级行政机构中,同样担负着重要的行政职能。与流内官的管理制度相当,唐代政府对流外官的管理,在选任、置品、督课、酬劳、入流内叙品等方面有其完备的制度。
同样到了明代,散官成为官品的附属,称官阶不到从九品的职官为“未入流”。但在明清的司法实践中存在“百官者虚名,而柄国者吏胥而已”的奇怪现象,这些未入流的衙门吏员们“品卑权重”,异常活跃,架空地方长官、左右案件成败的情况并不鲜见。例如,清代阎文介公在户部掌职时,因琐事得罪了库吏。库吏便私藏其红顶阻碍其上朝,以此来报复。后又整蛊文介公数次,方才收手。文介公得知是库吏所为后,便对胥吏的管理更加严格。可谁知不久之后,文介公不知因何事触怒了孝钦皇后,出户部。后来方得知是那库吏贿赂内监,故意中伤文介公。清代胥吏为了自身利益,可以要挟长官,架空长官权力,以行贿之手段拉拢权贵。不仅如此,索贿之事也是频频发生。光绪时,浙江候补知县某,到了浙江后当补某缺,部吏贻书告知曰:“某缺,君依例当补,然须予我千金。”某自然是不愿打点,认为这是循例之事,为何还须贿赂一个胥吏。结果可想而知,补缺结果出来之后,已补他人。鲁迅先生在《中国小说史略》中谈及《西游记》时,说过“神魔皆有人情,精魅亦通世故”这样一句话。的确,《西游记》作为一部神怪小说,谈仙说佛、恶魔毒怪只是它的表象,吴承恩在描写神仙佛怪时,也脱离不了当时中国各种社会现象的影响。这些社会现象、社会问题以神怪为依托,在我们的大脑中由于幻想的作用,呈现为一种光怪陆离与人情世故的结合体。大多数的经典文学作品都会给我们提供这样或是那样的时空背景,在不同的场域下,我们可以在虚构的作品中寻找真实,印证历史,挖掘与自己专业领域的契合点,也许会有思路大开、高见立现的效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