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扬:论夏衍的《上海屋檐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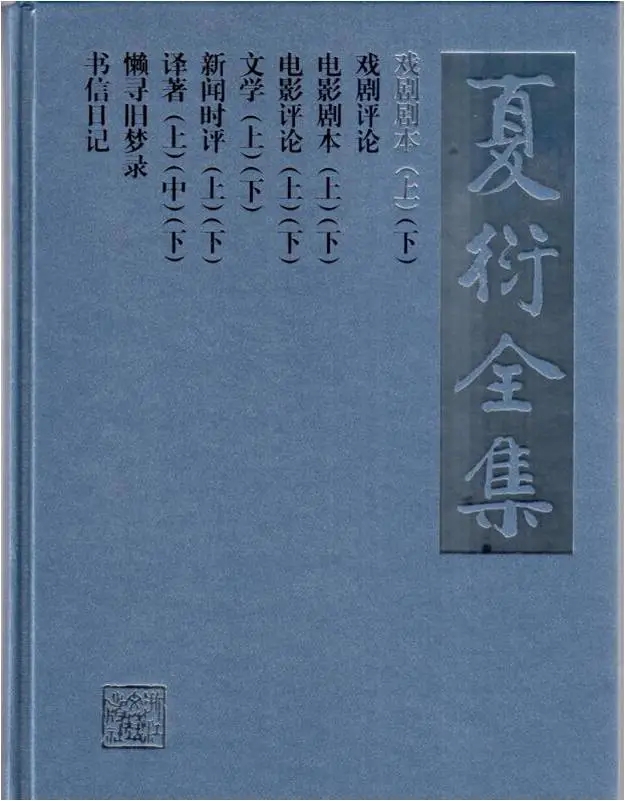
《夏衍全集》(全16册),浙江文艺出版社,2010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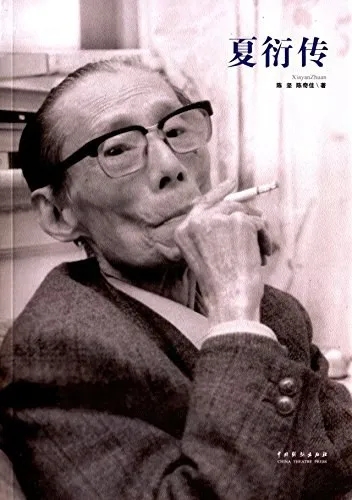
陈坚、陈奇佳《夏衍传》,中国戏剧出版社,2015年
2020年10月30日,是夏衍先生一百二十周年诞辰。上海话剧中心为表达对首任院长的敬意,排演了他的话剧《上海屋檐下》,这是新世纪以来,上海话剧中心出品的《上海屋檐下》的第三轮演出,其间,还邀请有关学者对该剧进行了讲解①。这部诞生于20世纪30年代的话剧作品,经过了半个多世纪的考验,成为中国话剧舞台的保留剧目,同时也成为很多评论家和研究者心目中公认的经典海派话剧作品。但与曹禺的《雷雨》《日出》《原野》《北京人》《家》,以及老舍的《茶馆》相比,夏衍的话剧作品在公众的视野中似乎曝光率没有那么高,一般的普通观众说起中国话剧代表人物,对曹禺、老舍是耳熟能详,但对别的剧作家作品,就有点印象模糊了。这种状况,从一个侧面体现出人们对中国话剧艺术的认知水平,还达不到像对小说、诗歌、散文这些文学类型的认知水准,人们随报刊宣传聚焦于一两位剧作家的作品,而不能像阅读小说那样,自由选择,广泛阅读,依据个人的阅读兴趣和独立判断来选择自己喜欢的作家作品。所以,包括像《上海屋檐下》等一系列话剧作品,尽管观众观剧后都觉得不错,研究专家的评价也很高,但最终的传播始终只能在一个有限的范围里流转,不能像《雷雨》《茶馆》那样在一个广阔的社会空间中持久传播,获得高度聚焦和持续不断的社会影响力。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并不完全是由夏衍剧作本身的不足造成的,而是体现出研究者和社会公众受诸多条件限制而对话剧艺术的整体面貌缺乏了解。

《上海屋檐下》,上海国民书店,1940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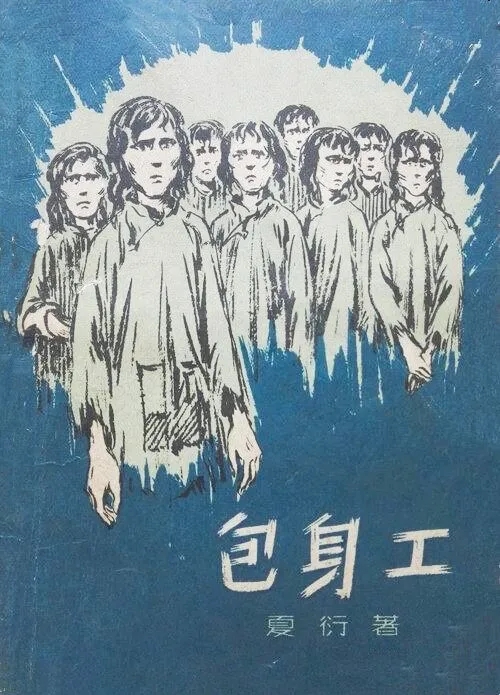
《包身工》,工人出版社,1959年
一
夏衍晚年对自己的创作有过一个评价,他认为一生所完成的七百多万字的作品中,文艺只占五分之一,绝大部分是新闻、杂论和社论之类的东西。所以,他愿意称自己是报人。而在文艺作品中,他认为《包身工》大概还传得下去②。可能很多研究者和熟悉中国现代戏剧、电影的人不会赞同夏衍这样的说法,因为从他对中国现代话剧、电影所做的贡献看,很多作品已经是公认的优秀之作。以话剧作品《上海屋檐下》为例,它在1937年6月完成、11月出版,1939年初演后,很快得到社会的好评,像评论家李健吾多年后依然赞叹“《上海屋檐下》是夏衍的杰作之一。他写了好几出关于上海的好戏,几乎碰到所有的角落,对我特别意味隽永的,要以《上海屋檐下》为最”③。夏衍同时代的朋友吴祖光、唐弢、于伶等,对该剧也有很高的评价。中国话剧史研究者陈白尘、董健先生在《中国现代戏剧史稿》中,称之为“现实主义杰作”④,田本相先生在《中国话剧艺术史》中,称《上海屋檐下》是“诗化现实主义的杰作”⑤。新中国成立后,《上海屋檐下》在话剧舞台上,多次复排演出,是夏衍话剧作品中复排最多的作品,至今没有中断过。如果说,夏衍的剧作是能够传世流传下去的话,毫无疑问,《上海屋檐下》是最具代表性的作品之一。
既然《上海屋檐下》具有这样良好的社会声誉,为什么无法获得像《雷雨》《茶馆》这样的社会影响?这是一个非常值得思考的问题,牵扯到剧作本身,也牵扯到与剧作相关的诸多因素。20世纪末,就曾有话剧研究者在学术会议上对中国话剧研究仅局限于曹禺、老舍等剧作家作品的研究现象,演出推广上也仅集中于一两位剧作家的作品现象,提出过批评。这些意见应该是合理的,具有建设性。
《上海屋檐下》是一部杰作,其杰出的成就表现在对上海1930年代都市生活的独特开掘之功力,以及戏剧艺术的多种新探索上。与曹禺和老舍这些剧作家相比,夏衍的戏剧创作特色鲜明,这种鲜明不在于他创作的文本拥有契诃夫式的“淡淡的忧伤”,而是他的戏剧从根本上区别于曹禺、老舍的写作方式。如果说曹禺、老舍是职业作家,从事的是一种职业写作的话,那么夏衍的社会身份首先是一位职业革命家,他的写作服从于他的革命事业需要,是一种业余写作。这种写作方式差异,对于有的研究者,以及职业写作者而言,很容易忽略过去,或者轻视下去,认为这样的创作政治宣传色彩太浓;或者认为非职业身份的写作,对文学创作的深化是一种限制。但事实上,写作者的身份问题,对于创作者而言,是一个非常值得探讨的问题。没有人会否认,文艺创作者可以彻底脱离自己的社会经验和生活体验。至于文艺职业之外的业余写作,如果稍懂一点戏剧史知识的人,都会知道世界戏剧史上,不少优秀剧作家和优秀剧作,是职业戏剧之外的某种非职业的戏剧写作。他们不是靠戏剧职业来圈定自己的事业影响和贡献,而是从流动的社会人生中寻求自己的戏剧理想和人生价值。夏衍的戏剧创作就属于这一类。读夏衍晚年所写的回忆录《懒寻旧梦录》,人们一定会对他的职业革命生涯印象深刻。透过他的回忆文字,人们了解到夏衍1927年从日本留学回国后,始终是在中共的隐蔽战线从事文化工作,并且长期担任要职。文艺创作对他而言,不是职业,而是工作需要。所谓工作需要,就是中共党组织指派给他的任务。夏衍说,地下党组织起先是让他参与到左翼作家联盟工作,后来扩展到左翼电影、左翼戏剧者联盟。在这一过程中,他开始学习电影剧本的创作以及话剧创作⑥。所以,他的话剧创作,不像曹禺、老舍等,是出自情感的冲动或文艺创作的需要,而是从现实斗争出发,配合中共党组织的宣传需要,具有鲜明的政治立场和现实战斗力。他最初的几个话剧,像《都会的一角》《秋瑾传》《赛金花》和《上海屋檐下》等,现实针对性非常强,以至于在南京演出时,国民党的要员看到一半,起哄砸场子,拂袖而去。这种鲜明的政治色彩,始终是夏衍话剧创作的基本色调和突出风格。抹去了它们就难以把握到夏衍戏剧的核心内容。夏衍在总结《上海屋檐下》的写作经验时说:“我写了几个戏以后,自己颇有些感触,特别是看了曹禺同志的戏之后。我学写戏,完全是‘票友性质’,主要是为了宣传,和在那种政治环境下表达一点自己对政治的看法。写《赛金花》,是为了骂国民党的媚外求和,写《秋瑾传》,也不过是所谓‘忧时愤世’。因此,我并没有认真地、用严谨的现实主义去写作,许多地方兴之所至,就不免有些‘曲笔’和游戏之作。人物刻画当然不够。后来很有所感,认识到戏要感染人,要使演员和导演能有所发挥,必须写人物、性格、环境……只让人物在舞台上讲几句慷慨激昂的话是不能感人的。写《上海屋檐下》我才注意及此。”⑦夏衍的这一说法,非常明确了他的创作与曹禺创作《雷雨》的动机和情形有所不同。曹禺说:自己创作《雷雨》“并没有明显意识着我是要匡正、讽刺或攻击什么。也许写到末了,隐隐仿佛有一种情感的汹涌的流来推动我,我在发泄着被抑压的愤懑,毁谤着中国的家庭和社会”⑧。如果说,夏衍的戏剧创作与曹禺等文艺色彩比较突出的戏剧形成对照的话,那么,其与1930年代流行于上海左翼阵营的宣传戏剧,也是有所不同的。像阿英、阳翰笙、于伶、陈白尘等,尽管这些左翼剧作家革命热情很高,宣传性、鼓动性、针砭时事的现实性非常强烈,但夏衍的剧作与他们的作品相比,似乎另有一种色彩,这就是江南色彩,尤其是上海的地方色彩,时常超越了作品的革命风采。
夏衍出生在浙江杭州,除了到日本留学的七年,早年的记忆中,杭州和上海是他生活、学习和工作时间最长的地方,也是印象最深最持久的。夏衍对故乡的记忆和对江南的留恋之情,有散文名篇《旧家的火葬》和电影《春蚕》等,这些作品有着左翼文学的反抗姿态,但同时带有一种浓浓的挥之不去的哀江南的婉约和缠绵。夏衍对上海的都市生活不仅熟悉而且适应。他长期从事地下工作,职业习惯使他对都市的环境和周围人物有着一种特殊的敏感和警觉。譬如他对家庭住址的选择,有着非常独特的要求,体现了一个地下工作人员的职业特点⑨。1932年秋,中央特科在东京设立由陆久之负责的情报站,随后,夏衍受命实地考察。夏衍看了陆久之的驻地之后,认为陆久之的选址有问题⑩。这些都是地下工作经验培养出来的对周围环境的职业敏感。对于人物观察和性格特征的考察和把握,夏衍也兼具一种特殊本领。从职业角度讲,他是1930年代以来中共在上海从事地下工作的重要人物中少数几位没有遭遇逮捕的。除幸运的成分之外,与他特殊的警觉力和超常的识别力有关。就像他自己在回忆录中所说的,凭借着出众的观察力和职业敏感,在最危险的1935年,夏衍几次躲避危险,免遭逮捕的厄运⑪。夏衍把他这种职业敏感转移到文艺创作上,尤其是对都市生活的把握上,更凸显出他的个性风格特征。李健吾在评价《上海屋檐下》时,称颂夏衍对上海城市生活角角落落都熟悉,认为其中的人物、故事让人想起那个“低气压时期”上海的生活状态⑫。对于像李健吾这样一位在上海生活了二十多年之久的文化人而言,能有这样的阅读感受,应该说是感同身受吧。但夏衍剧作中的这一特色,并不是为制造某种戏剧效果而刻意设计的环境和情节,而是他自己长久地生活在上海这座城市,对生活于其中的人物性格、环境气氛,太熟悉的缘故。以至于一提笔书写,那些熟悉的景观和人物说话的腔调神情,就会源源不断地浮上心头。像《上海屋檐下》基本上就是在避难期间,花了两个月时间完成的⑬。这种快速写作的背后,是作者对于所选取的创作材料的熟悉,几乎不用费太多的心思,那些熟悉的东西就被呼唤出来了。


《上海屋檐下》1940年首演剧照,主演:赵丹、赵慧深
二
《上海屋檐下》作为夏衍式戏剧写作的经典代表,体现了一种独特风格的戏剧写作样式和戏剧风范。其基本范式是戏剧创作与剧作者的人生理想和生活状态处于同构形态,剧作者不是将写作作为一种职业,与其生活处于不同状态的分隔之中,而是将生活与写作处于同等重要,甚至是无缝对接状态。他的工作性质要求他以笔为戈,对敌斗争。他是非写不可,而不是可写可不写,或是为了谋生而不得不写。夏衍从不放弃自己的左翼立场,也不讳言自己作品的宣传功能。在他的思想意识中,戏剧与宣传在功能上有很多一致的地方,一部有力的戏剧作品不会因为宣传上是有力的,而在艺术上反倒是虚弱的。戏剧的强大,包含了作品的感染力和宣传鼓动性。如果说左翼戏剧有什么鲜明的特色,战斗力就是它的特色,而且这种特色是写在左翼的旗帜上,被很多文学家、艺术家自觉表现出来的。夏衍作为中国左翼文学的开创者和组织者,他的身上洋溢着创业者开天辟地的理想精神和勇往直前的探索勇气。他是革命者,但不是那种被教条捆住手脚的口头革命派,而是有创造能力、有人格魅力和文化自觉意识的前行者。《上海屋檐下》说它是戏剧作品也好,说它是左翼文化也好,说到底,是一种文化上的新尝试和新样式。它拓展了戏剧的边界,赋予戏剧以一种新的生命形式与战斗力。我们不妨想象一下,在1937年之前,是否有过类似《上海屋檐下》这样的话剧作品?如果说没有,就应该追问为什么从话剧在中国诞生以来,数十年的创作、演艺探索,唯有到了1930年代,才具有《上海屋檐下》这种形式的话剧作品?《上海屋檐下》如果单纯从戏剧构造的角度来考虑,有几个要素是非常突出的,一是左翼的品格;二是舞台空间处理;三是市民题材。左翼色彩的话剧并不是从夏衍手里开始,但在夏衍作品中成熟。这种成熟,表现为剧作家能够在一个较为完整、充分的话剧格式中,艺术地呈现人物性格和故事情节。《上海屋檐下》在一天时间内,将上海下庙路的弄堂房子中的五户人家的故事和不同身份地位,交代得清清楚楚。让观众从这些戏剧人物的生活状态中,反思自己的生活。关于舞台空间的处理,《上海屋檐下》在中国话剧史上也是独树一帜的,一栋石库门房子内五户人家的五个小空间,随着剧情的发展需要,彼此凸显、表演,形成了多重复合的立体表演效果。空间参与剧情叙事的潜能被大大地激发出来,形成了中国话剧表演形式上的大胆创新。对于市民题材的戏剧展示,《上海屋檐下》雅俗兼顾,化腐朽为神奇,有一种诗一般的远致和余韵。一般处理市民题材的作品,无论小说还是戏剧、电影,都容易陷于日常生活的平庸陷阱。对平常生活细节津津乐道,而对理想性格缺乏追求,这在表现上海都市生活的文艺作品中并不少见。夏衍《上海屋檐下》的市民们,尽管都很平常,但都有一种向上努力的心愿,他们都曾努力过,不愿意糊里糊涂地生活,也不甘愿沉沦。但周围世界的无望和压抑,让他们处于极度的苦闷之中。革命者匡复的出现,犹如黑暗中浮动的一丝亮光,尽管匡复自己刚刚从监牢中出来,尽管他面对自己的妻子改嫁表现得那么痛苦和不能接受。但最终他没有沉沦下去,而是离开了亲人们,去寻找自己的人生之路。这剧本中的一丝亮色,并不是夏衍随意添加上去的乌托邦梦想,而是他从自己的革命信念和社会斗争磨炼中获得的经验和识见。所以,看夏衍的《上海屋檐下》你不会觉得虚无缥缈,而是现实感非常强。这种现实感不是指向戏剧编剧技巧的软润熟练,不是编戏编得好,而是作者呈现的分寸和指向,实实在在,好像剧中一切的东西,都像是与观众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你不是在欣赏戏剧,而是以戏剧的方式参与到对当代生活的思考和讨论中去。
当代英国戏剧家彼得·布鲁克在戏剧理论著作《空的空间》中,论及戏剧史上四种戏剧类型时,曾列举出僵死的戏剧和粗俗的戏剧两种类型。这两种戏剧不能说不是戏剧,而是这两种戏剧脱离了戏剧原创的生活基础,没有自己独特的思考和灵魂,成为某种庸俗的摆设,供少数人附庸风雅或遣兴娱乐⑭。夏衍的戏剧作品从其写作之初,就没有把它仅仅当作供观众轻松观赏的戏剧作品,而是当作激发广大观众观照自己生活状况的一面镜子。所有的剧中人物都是普通的日常生活中能够遇见的,他们努力工作,希望过上安稳的日子,但最终的结局却是生活无望。这样的结果说明,这个社会出了问题,个人的不幸已经不是个人努力能够解决的,而是需要社会一起努力来改变。所以,夏衍戏剧的最后落脚点是要唤起民众一起来改变这一不合理的黑暗现实。这种左翼的政治立场,在夏衍初期的作品中,常常是直露的,也就是他自己所说的,是一种宣传。但到了《上海屋檐下》这种直露隐退到人物的行动和命运的背后。通过这五户没有出路的上海小市民的生活展示,很多观众明白了一个道理,不革命这个社会就不可能从根本上改观。这是戏剧让人明白的道理,也是夏衍戏剧区别于很多同时代剧作家作品的地方。夏衍的《上海屋檐下》改变了市民剧的格调和品格,在庸常而灰色的市民生活中,注入了革命的理想的色调和元素。相比之下,曹禺的话剧创作比较倾向于人物命运的宗教与情绪的表达,一旦触及革命等实际问题,作品的局限性就显得比较明显。事实上,曹禺是希望在表现革命理想方面能够有所突破,但尝试的结果却不理想。譬如1950年,曹禺曾检讨自己的创作,认为“《雷雨》中的周朴园自然是当做一个万恶的封建势力代表人物而出现的,我着力描写那些被他压迫的人们。当时我认为这种看法是‘大致不差’的。但在写作中,我把一些离奇的亲子关系纠缠一道,串上我从书本上得来的命运观念,于是悲天悯人的思想歪曲了真实,使一个可能有些社会意义的戏变了质,成为一个有落后倾向的剧本。这里没有阶级观点,看不见当时新兴的革命力量;一个很差的道理支持全剧的思想,《雷雨》的宿命观点,它模糊了周朴园所代表的阶级的必然的毁灭。”⑮1951年,借重印《曹禺选集》时,曹禺修改了《雷雨》,他自己当时认为自己的戏剧人物提高了觉悟,寄希望作品“对读者和观众产生有益的效果”⑯,但直至曹禺逝世,观众和研究者的评价更多的还是倾向于原来的《雷雨》。老舍对《茶馆》的创作,也遇到与曹禺修改《雷雨》相近似的情况。老舍非常坦率地承认,“茶馆是三教九流会面之处,可以多容纳各色人物。一个大茶馆就是一个小社会。这出戏虽只有三幕,可是写了五十来年的变迁。在这些变迁里,没法子躲避政治问题。可是,我不熟悉政治舞台上的高官大人,没法子正面描写他们的促进与促退。我也不十分懂政治。我只认识一些小人物。”他拒绝了一些人要求他以康顺子的遭遇和康大力参加革命作为主线⑰,坚持以表现小人物为《茶馆》的主要内容。以戏剧的方式表达政治,在夏衍《上海的屋檐下》可以成为一个亮点,但在曹禺和老舍的剧作中,却成为制约创作的一道障碍。问题的关键可能还不在于政治本身,而是剧作者在现实生活中对政治题材的熟悉程度以及在剧作中如何表现的问题。夏衍是通过戏剧人物行动和剧情变化来展示这种政治的合理性和政治诉求的现实性,相比之下,曹禺的修改是硬贴上去,这种硬写的结果是政治游离于作品结构之外,犹如身体外额外长出了一个果实,成为一种累赘,其表演的舞台效果当然也是可想而知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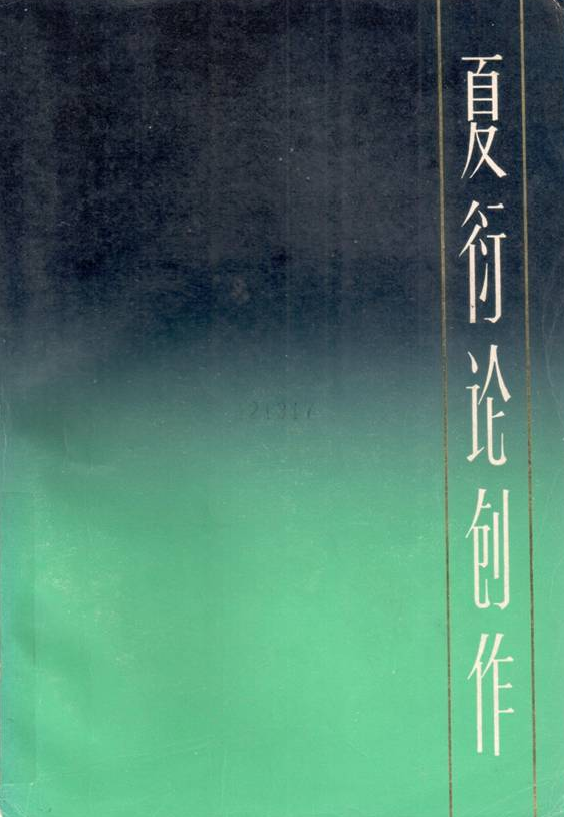
《夏衍论创作》,上海文艺出版社,1982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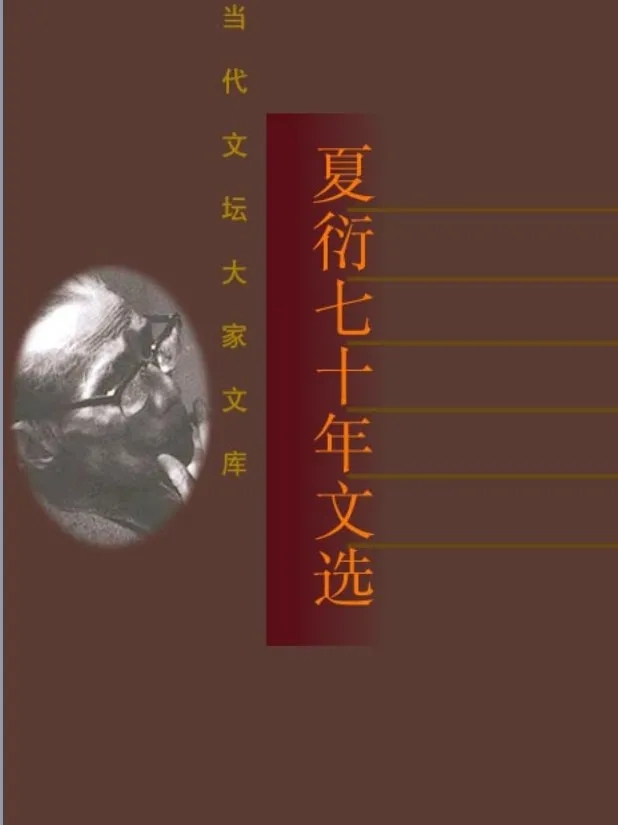
李子云编选《夏衍七十年文选》,上海文艺出版社,1996年
三
夏衍的《上海屋檐下》与曹禺的《雷雨》《日出》《北京人》《原野》《家》以及老舍的《茶馆》相比较,另一个值得关注的差异是曹禺和老舍的话剧作品都曾有过国外巡演的机会,有着海外积极的响应和回声,而夏衍的《上海屋檐下》似乎从来就没有海外巡演的记录。这种差异说明了什么,与我们论述《上海屋檐下》这一剧作有什么影响?如果海外巡演不是单纯看作是一种话剧的海外传播,而是从文本的世界影响和接受的角度来思考问题,能够走出去与不能走出去的确包含了某种区别。不是说能够走出去都是优秀之作,而不能走出去就不是优秀之作。不能走出去从某些方面看,总有自己的约束和规范限制。
那么,是什么使得夏衍的《上海屋檐下》产生了自我约束和限制呢?我想与政治的规定情境过于具体有关。真所谓成也萧何,败也萧何。革命和政治,在夏衍作品中是一个标识物,构成了他与曹禺、老舍等职业剧作家的创作区别。唐弢先生在《夏衍剧作集》序言中,以“政治抒情诗”来概括夏衍剧作的艺术风格,他认为“也许有人会说,抗战爆发前后,没有一个作家的笔簇不蘸上一点政治,夏衍在这个时候开始写戏,对政治有所渲染,不过是适逢其会而已,算不得特色。但我说的不是这个。我想提请评论家们注意,应当研究夏衍的政治抒情诗如何在戏剧创作中具体表达,他的富有个性特征的艺术风格怎样通过创作实践体现出来。在我看来,要说明夏衍的戏剧艺术风格的特点,这才是重要的关键”⑱。脱离了政治因素,就无法认清夏衍剧作的意义和价值。这是唐弢作为中国现代文学研究者提出的意见和建议。对于政治因素在创作中的表述和影响,在夏衍和同时代人的创作中,有时是非常明确,有时又显得非常含混,常常与题材选择、社会压迫、现实生活不如意等当下社会问题混在一起。对于夏衍而言,政治首先是反抗国民党压迫和统治,宣传中共的政治主张。这样的思想意图,在特定社会氛围和环境中会因为题材的敏感性和尖锐性产生特殊的社会效应。以《上海屋檐下》为例,它创作于1937年上半年,正是抗战即将全面爆发的时期,在这样一个“低气压”的氛围中,夏衍选择了上海杨树浦一栋石库门房子里的五户住家的日常生活状况,来表现某种压抑的生活感受和思想情绪。事实上,大战前世界各国的都市生活都沉闷,小人物生活的动荡和无望,也比比皆是。如果说,欧洲有像茨威格那样的作家,对人类前景感到绝望而自杀的话,那么,1930年代初上海都市生活在茅盾的《子夜》中已经展示为一种至暗。夏衍的戏剧创作只不过是在此时此刻加重了一种艺术表述的节奏和分量。它让人们在此前的各种感受之外,又一次在剧场的特定场景中以镜像的方式,看见了都市生活的窘困与灰暗。五户住家不是上海最底层的工人或外来讨生活的,而是职员、小学教师、大学毕业生、海员的妻子和卖报人,但在某一天因为一个偶然事件,大家突然间似乎都意识到原来自己的生活竟是如此的绝望。这变故是一位从牢里释放回家的革命者匡复来找自己的妻女引发的。匡复找见了自己的妻子与女儿,但她们已经与他的朋友林志成结成了新的家庭。匡复平息了内心的痛苦,留下妻女去寻找新的生活,而这一出走照见了这一石库门内五户人家的绝境,这些拖家带口没法子出走的人们未来的生活该怎么办?话剧留给人们的问号,也是夏衍心头的问题。他以革命者的姿态揭示了都市社会的灰暗和无望,也明确了只有革命才有出路,但面对一群不太可能革命的小市民,他也没有底气来鼓动他们起来革命。他只能用革命者的出走来照见小市民生活的战战兢兢、抖抖索索,但这样的表达也仅仅是起到揭露和引导作用而已。在1930年代末的上海和1940年代初的重庆,这样的戏剧作品具有很强的现实针对性,也很容易让普通观众产生此情此景的现实联想。像话剧史上所回忆的此剧产生的各种社会反响,应该就是社会情绪与剧情所传递的情绪的相互激荡。但此情此景过后,尤其是1949年天地玄黄、历史翻转一页之后,《上海屋檐下》所针砭的现实、所揭示的小市民灰暗生活,还有价值和意义吗?事实上,在1950年代针对新中国有没有悲剧、要不要写悲剧,的确有过一些不同意见。一些意见认为,新中国成立,人民当家做主,旧社会的悲剧已经一去不复返了,所以,不用也不要再写悲剧了。在他们眼里,悲剧与旧社会是同等概念,悲剧的戏剧形式也是与暴露旧社会的黑暗这一特定社会内容连接在一起的。为此,老舍先生写下《论悲剧》一文予以回应。老舍先生指出:“是不是我们今天的社会里已经没有了悲剧现实,自然也就无从产生悲剧作品,不必多此一举去讨论呢?我看也不是。在我们的社会里,因为人民生活的逐渐改善和社会主义的建设等等,悲剧事实的确减少了许多,可是不能说已经完全不见了。”⑲1957年上海电影演员业余剧团复排了《上海屋檐下》,作为观众的唐弢先生“恍如进入了一个久已逝去的梦境,那么现实,又是那么遥远”。而与之一同观剧的青年观众“不能够理解,从生活到感情都显得陌生”⑳
为什么会有陌生感呢?在新中国的舞台上上演具有悲剧性质的话剧《上海屋檐下》,连夏衍本人都有点吃不准适合不适合。1956年11月,夏衍在与中国青年艺术剧院《上海屋檐下》剧组座谈时,曾说过:“这个戏,今天二三十岁的人不一定都能够了解了,他们缺乏这种生活感受,今年二十五六岁的青年,那时只不过是阿牛的年纪。所以结尾处要掌握得好,不要让人看了觉得暗澹。应该为着革命为着前途继续下去,不要造成悲惨的分离,造成没有希望没有前途的分离。”㉑如果说剧作最后的处理比较悲惨,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是合适的,是能够理解的,为什么到了1950年代就显得不那么适合,甚至于夏衍本人也担心不容易被观众理解了呢?这不仅仅是时代政治的问题,某种程度上也体现了剧作者对于戏剧观众期待视野的某种误读。对于像同时期中国舞台上上演的莎士比亚戏剧中的悲剧以及俄罗斯戏剧中的悲剧,似乎没有什么人觉得不适合,也没有人担心因为时代问题观众会有陌生感。为什么一旦涉及类似于夏衍《上海屋檐下》这样的剧作时,就会有此担忧呢?如果不是因为经历了“文革”的“十年动乱”,或许很多人还会继续担忧观众会不会有一种不了解、有一种陌生感。这种来自夏衍的担忧,其实也体现出《上海屋檐下》的戏剧创作意图的困局。戏剧无论创作还是表演,都不用回避政治,这是世界现代戏剧史上公认的铁律。有很多现代世界戏剧史上的杰作,正是因为在剧本创作和戏剧舞台上直面当代政治而赢得了持久不衰的声誉。但为什么中国的戏剧舞台会因为表现政治而多少年之后常常需要采取规避和讳言的姿态呢?说到底,这不是因为表现了政治的原因,而是表现政治时缺少一种真正的政治风度。谈政治要像伟大的政治家那样触及人的思想和灵魂,表现政治也要像政治家那样面对社会的每一个普通百姓,不能把政治理解成做手脚、鬼鬼祟祟,或是妖魔化、丑化对象。对照夏衍1937年出版的《上海屋檐下》,尽管在剧本里作者不能放言高论,而只能采取曲曲折折的隐晦表达,但戏剧人物的个性和思想情绪,依然是那么清晰而真切地传递给每一位观众,剧作者的感情和思想情绪也是直抵人心。半个多世纪后的今天,上海话剧中心复排这出戏、呈献给广大观众时,观众们并没有产生年代久远的“陌生感”,反倒是对夏衍这样的革命者表达了由衷的敬意。因为在久远的1930年代这个“低气压”时期,怀抱理想激情的三十七岁的夏衍用话剧《上海屋檐下》告白天下:这个社会不公平,生活在这个社会中的普通百姓没有出路。不革命不行!相比之下,在中国现代话剧史上,很多人对于话剧《上海屋檐下》的解读和理解,是置于一种非常狭隘的党派政治的含义上来进行解读。正是因为过分拘泥于这种狭义政治的理解,一旦形势变换,就觉得再上演这样的剧目与形势不合拍,《上海屋檐下》的舞台命运就不得不终止。但为什么曹禺的《雷雨》、老舍的《茶馆》就可以超越这些,没有让人担忧与当前形势“不合拍”呢?我的感觉,这是一种习惯养成的文学共识,也就是一种艺术的崇高声誉和社会舆论。没有人认为上演曹禺和老舍的剧目需要考虑政治形势问题,因为上演经典戏剧是任何时代的荣耀和光彩,即便从粉饰太平的角度出发,也需要经典。所以,相比于曹禺和老舍,1950年代以来,一些人包括夏衍本人对《上海屋檐下》持有一种深深的怀疑态度,这一现象表明对一部经典作品的认识,需要时间来回答。
(杨扬,上海戏剧学院)
注释:
①《看话剧·上海屋檐下》2020年10月号,上海话剧中心内部交流出版物。
②李子云编选:《夏衍七十年文选》,上海文艺出版社,1996,第993-994页。
③⑫李健吾:《论〈上海屋檐下〉——与友人书》,载巫岭芬编《夏衍研究专集》(下),浙江文艺出版社,1999,第945、945页。
④陈白尘、董健主编:《中国现代戏剧史稿》,中国戏剧出版社,1989,第423页。
⑤田本相主编:《中国话剧艺术史》第三卷,江苏凤凰教育出版社,2016,第292页。
⑥夏衍:《忆阿英同志》,载李子云选编《夏衍七十年文选》,上海文艺出版社,1996年,第423-424页。
⑦㉑夏衍:《谈〈上海屋檐下〉的创作》,载夏衍《上海屋檐下 法西斯细菌》,人民文学出版社,2007,第80、84页。
⑧曹禺:《〈雷雨〉序》,载王兴平、刘思久、陆文璧编《曹禺研究专集》上册,海峡文艺出版社,1985,第16页。
⑨有关1932年夏衍在爱文义路选择家庭住址时的描写,见陈坚、陈奇佳:《夏衍传》,中国戏剧出版社,2015,第146页。
⑩陈修良:《梦里依稀哭夏公》,载《陈修良文集》,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9,第535-538页。
⑪夏衍:《懒寻旧梦录》,中华书局,2016,第180页。
⑬夏衍:《〈上海屋檐下〉自序》,载夏衍《上海屋檐下 法西斯细菌》,人民文学出版社,2007,第74页。
⑭彼得·布鲁克:《空的空间》,王翀译,中国友谊出版公司,2019,第3-4页。
⑮曹禺:《我对今后创作的初步认识》,载王兴平、刘思久、陆文璧编《曹禺研究专集》上册,海峡文艺出版社,1985,第60-61页。
⑯曹禺:《〈曹禺选集〉序言》,载王兴平、刘思久、陆文璧编《曹禺研究专集》上册,海峡文艺出版社,1985,第63页。
⑰老舍:《答复有关〈茶馆〉的几个问题》,参见北京人民艺术剧院、《艺术研究资料》编辑部编《〈茶馆〉的舞台艺术》,中国戏剧出版社,1980,第183-184页。
⑱唐弢:《沁人心脾的政治抒情诗——〈夏衍剧作集〉序》,载《唐弢文集》第9卷,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5,第430页。
⑲老舍:《论悲剧》,《人民日报》1957年3月18日。
⑳唐弢:《二十年旧梦话“重逢”——再度看〈上海屋檐下〉的演出》,载巫岭芬编《夏衍研究专集》(下),浙江文艺出版社,1999,第953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