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见证者到亲历者——2020年巴西文学叙事转向研究
内容提要 2020年,巴西文坛延续了前两年的变革趋势,严肃文学与娱乐文学的壁垒被进一步打破,对现实困境的观照依然是文学创作的核心。由于疫情引起的社交隔离与网络“曝光”运动兴起,巴西社会越来越习惯于从个人视角出发参与公共讨论。因此,本年度的巴西文学在探讨社会议题的同时,叙事视角也变得更为主观与内倾,以第一或第二人称叙事的作品明显增多。作家或者站在受害者立场,以独白或追问引发读者共情;或者同时展现多种视角,全面反映巴西当前的对立与冲突。
关键词 巴西年度文学研究 叙事视角 主观化 社会议题
自2018年以来,受社会冲突加剧与出版业危机影响,巴西文坛的评价体系与创作趋势都迎来了持续转向。具体来说,以往将“文学性”凌驾于“通俗性”之上的评价标准正在被打破。越来越多的评论家认为二者只是侧重点不同,并无高下之分。许多作家也开始有意识地将二者结合起来,在传统文学中吸收大众文化,在通俗作品中探讨严肃主题。与此同时,为化解当前极端化的对立倾向,号召巴西民众团结起来共同应对当前困境,文学作品也不再一味进行谴责与批判,而是致力于让读者更为全面地了解巴西现实,唤起共情,促进理解。在2020年的巴西文坛,上述重要特征不仅延续下来,而且得到进一步发展。作为巴西国内最重要的文学奖项,雅布提奖组委会在3月发布本年度的评选章程,宣告在传统的“长篇小说”“短篇小说”“杂文/散文”“诗歌”等类别之外,新增“娱乐长篇小说”(Romance de Entretenimento)这一文学奖项,并将原有的“长篇小说”更名为“文学长篇小说”(Romance Literário)。章程公布不久,雅布提奖负责人佩德罗·阿尔梅达(Pedro Almeida)专门针对这一变更做出解释。他提到纯文学或严肃小说强调叙事形式,而商业或娱乐小说则侧重于情节推动,这两方面本来就无法相互比较,但此前的评委都只善于对“形式”进行评价,从而导致以情节取胜的作品无缘大奖。然而,就在奖项评审承认后者价值的同时,严肃文学与通俗文学的界限也变得愈发模糊,因此,在实际评选中,将由作者本人决定参评“文学小说”还是“娱乐小说”,以最大限度地保证公正性。
鉴于近年来巴西文学在变革趋势上的一致性,2019年最受好评的新作也相继成为本年度各项文学奖的赢家。就雅布提文学奖而言,最佳娱乐小说与最佳文学小说分别由《一个黑暗中的女人》(Uma Mulher no Escuro)与《歪犁》(Torto Arado)摘取,后者还同时获得葡语海洋文学奖的第一名。而同样收获诸多赞誉的《棕色与黄色》(Marrom e Amarelo)则夺取了亚速尔文学奖最佳长篇叙事大奖。不仅如此,这些作品中所探讨的暴力、性别、阶级、种族等议题也依然是2020年巴西文学创作所关注的焦点,部分新作甚至可以看作是上述作品的延续或回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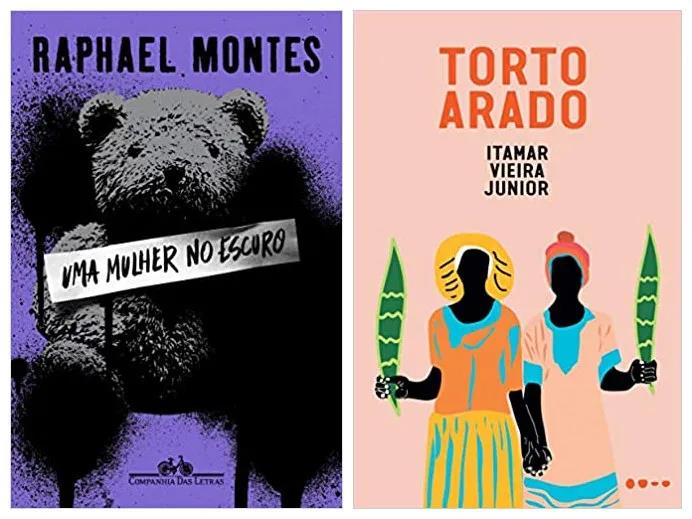
《一个黑暗中的女人》与《歪犁》,图片源自Yandex
一、叙事人称变化:以主观视角关注社会议题
即使2020年巴西文坛在很大程度上承袭了前两年的评价标准与创作理念,本年度出版的作品仍显现出新的特点,尤其是在叙事视角上,存在明显的主观化倾向。全知全能的叙事声音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讲述自己亲身经历的人物本身。尽管在此之前,巴西文学中也不乏第一人称叙事甚至自传体作品,但每年高质量的作品数量毕竟有限,且其关注点大都聚焦于个体情感或自我身份,致力于探讨如成长、孤独、衰老、死亡等存在主义话题。而在2020年,第一人称叙事则一跃成为巴西文学的主流,第二人称叙事的比例也大幅增加。无论陈述的主体是“我”还是“你”,这些作品都有意从个体感受出发,以参与者的姿态反映与反思在巴西现存的社会问题。
上述变化的发生与2020年的巴西现实有密切关系。作为世界上新冠病毒感染数与死亡率最高的国家之一,巴西在经济、政治、民生等方面均遭遇重大打击,人与人之间的近距离接触也降到最低。对于巴西人而言,私人交往与群体聚会都不可或缺,疫情引起的社交隔离也对他们造成了更大困扰。在这种情况下,网络媒体成为个人情感宣泄的重要出口,也成为群体声浪形成的源头。这种个体与群体之间的呼应看似矛盾,在当前特殊的时代背景下却并不令人意外。一方面,由于独处时间增多,每个人对自身的关注度提高,人们的思考叙述自然会更加贴近个人生活;另一方面,肆虐的疫情却又将所有人的命运以前所未有的方式连接起来。每个人都陷入相似的困境,面临同样的风险,个体层面的讲述也自然能够反映群体焦虑,从而成为时代精神的重要参照。
除全球肆虐的疫情之外,另一个事件也同样在巴西引起轰动并余波不断,那便是2020年5月开始的“曝光”(“Exposed”)活动。这项活动最早由推特账号“尼特洛伊妇女之声”发起,旨在通过被害人的个人叙述,曝光并谴责她们所遭受的性骚扰与性暴力。尽管乍看起来像是近几年#Metoo运动的变体,“曝光”运动的范围却迅速扩大化,从控诉前男友的背叛,到举报家庭暴力与种族歧视,这些都可以归于这一标签之下。因此,在声势浩大的“曝光”运动之下,体现的并不仅仅是对于单一社会问题的关注,而是对普通个体遭遇的重视。无论曝光的问题在于性别、种族、穷困还是暴力,个人真实的自述都能在网络空间赢得同情与支持,并鼓励更多的受害者继续发声。
一边是重重危机让人们拥有更强烈的倾诉欲望,一边是网络技术令陌生人之间的交流互助变得更为便捷,二者的聚合让大家意识到,他们无需将自己的故事交由少数“专业人士”描写报道,而是可以亲自回忆讲述。他们并不缺少呼应者,因为在每一个发声的个体背后,都站着更多有着相似境遇的人。即使在追求真实性与感染力的同时,难以保持中立客观与面面俱到,但在多种声音的共振中,仍能谱奏出反映这个时代的独特乐章。正是在这一背景下,巴西文学的叙事立场产生了明显变化。
二、单一视角下的独白与追问
在2020年巴西出版的作品中,最受关注与好评的莫过于《皮肤的反面》(O Avesso da Pele)。作者杰斐逊·特诺里奥(Jeferson Tenório)于1977年出生于里约热内卢,少年时便移居至南大河洲。由于那里的欧洲移民人数更多,深肤色的他感受到更为明显的种族歧视。因此,在创作主题上,《皮肤的反面》与上一年度的《棕色与黄色》有许多相似之处,而且后者也同样出自于一名南大河洲作家之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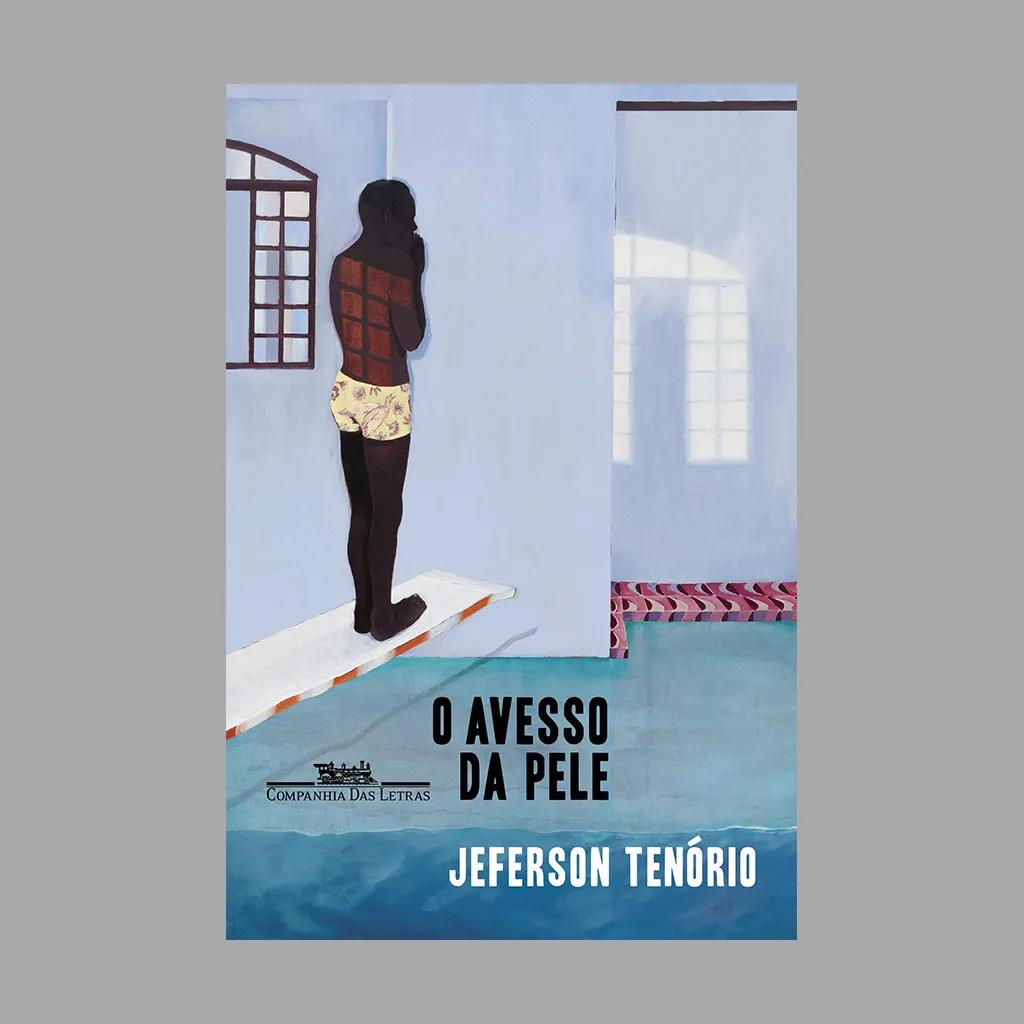
(《皮肤的反面》图片源自Yandex)
然而,与其将特诺里奥的成功看作上一年热度的延续,倒不如将其归功于作家本人多年的积累。事实上,在两年前出版的《没有上帝的斯特拉》(Estela sem Deus)中,特诺里奥已经讨论过种族问题。而除文学创作外,特诺里奥也在攻读文学批评方向的硕博士学位,其研究对象均为非洲作家或是具有非洲血统的作者,这也使他对族裔身份的处理更为细腻,不至于让文学作品沦为生硬的道德说教。正如保罗·斯科特所称赞的那样:“[特诺里奥]并非仅仅在国家普遍的不幸中做一场社会巡游,不会将对不平等的批判变成一种取巧手段、一种吸引眼球的廉价途径……”
如果说,在五年或者十年之前,这种廉价的批判还有些许市场的话,最近几年的文坛趋势已经宣告了此路不通。一切“置身事外”的文学都难以赢得认可,“真诚介入”比任何时候都更为重要。《皮肤的反面》恰恰满足了巴西读者与评论家对于“真实”的追求,因为其中所有的反思都由内而外自然发生。在这部具有自传色彩的小说中,特诺里奥采用了口语化的叙事策略,仿佛当事人就坐在读者面前,将所思所想娓娓道来。
《皮肤的反面》情节并不复杂。故事的叙述者名为佩德罗,是一名黑人。他的父亲本是一名公立学校的教师,但在警方的街头盘查中被误杀。悲剧发生后,佩德罗回到父亲生前居住的房子,通过整理旧物,重拾父亲的回忆。可以说,这部小说就是佩德罗的个人独白,而其倾诉的对象正是已经离世的父亲。由于他的倾诉中还交织着对于母亲等人的回忆,使得这部小说在第一、第二与第三人称叙事中交替变换。其中,第一与第二人称占据了核心地位,奠定了整部小说真切而又悲伤的基调:“有时你有了一个想法,便住在里面,远离人世。你建造了一栋这样的房子,远远的,在你自己心里。这就是你的行事方法。今天,我更愿意认为,你的离开是为了回到我身边。”在这个开启全书的句子中,特诺里奥不仅表达了叙事者对父亲的思念,也暗示了记忆与空间的关系。已逝的父亲将自己的思想打造成远离现实的房屋,儿子则借助他居所中的日常用品,一点点拼凑、重塑父亲生前的故事。如此一来,父亲房间中简单凌乱的陈设——没有墨水的钢笔、不成对的袜子、笔记纸张、学生的试卷、作文以及坎东布雷宗教的神像——便透露出了他生前的身份特质:一位公立学校的语文老师,收入微薄,信仰巴西非洲宗教(具有黑人血统)。
对于巴西社会而言,这三种身份具有极强的关联。因为相较于白人而言,黑人的平均收入更低。而巴西公立基础教育极为薄弱,基本只有穷人才会选择。于是,公立学校集中了更多的黑人儿童,他们无法得到足够的教育资源,更难通过学习实现阶级跃升。值得一提的是,这种教育、文学、种族、阶级的结合并非仅仅来自于特诺里奥的创作巧思,更因为他本人便是一名公立学校黑人语文老师。因此,当书中的佩德罗以第二人称的口吻叙述父亲的遭遇时,读者很容易感同身受,并为他所遭遇的种族歧视愤恨不已。
事实上,在最终被警察误杀之前,这位语文老师已经数次遭遇警察盘查,原因无疑在于他的肤色与穿着。当年少的他与同伴踢球,当他去富有的同学家玩游戏,当他在富人区等待女友,甚至当他在公交车上读书,都会有警察突然出现,询问他的身份。这种歧视无处不在,如果没有最后夺取他生命的悲剧,也许并不会引人注意,然而,《皮肤的反面》最打动人心的便是对这种细碎日常的描写。尽管没有任何情绪化的宣泄或是戏剧性的冲突,特诺里奥的文字却令读者相信,身为一名黑人,必须时刻配合警察无理的盘问,承受商店保安怀疑的目光,理解路人从旁经过时的紧张情绪,因为他一旦像主人公的父亲一样,为了奢侈的理想而选择反抗,便可能在警察慌乱的枪击中丧生。
在2020年巴西出版的长篇小说佳作中,《皮肤的反面》并非唯一一部从单一人物视角出发,对社会问题发起反思与追问的作品。其他作家也采取了相似的策略,如巴西南大河洲作家杰佛逊·亚松桑(Jéferson Assumção)在年初出版了《犹大的地狱》(O berço de Judas),借一名搏击者的口吻来展现巴西日常生活中的暴力问题;而在巴西著名作家克里斯托旺·泰扎(Cristóvão Tezza)发表的新作《时间的表面张力》(A tensão superficial do tempo)中,一切情节都在化学老师兼盗版视频制作人坎迪德的叙述中展开,探讨的核心则是博尔索纳罗执政时代的社会与政治。

克里斯托旺·泰扎与《时间的表面张力》,图片源自Yandex
除长篇小说之外,2020年最受关注的诗歌作品也体现出相同的特点。诗集《恐吓之歌》(Canções de atormentar)是本年度巴西文坛的一大惊喜,因为它以最具独创性的隐喻,表达了当前巴西人内心的普遍感受。这是安杰丽卡·弗雷塔斯(Angélica Freitas)自2012年出版经典诗集《子宫如同拳头一般大小》(Um útero é do tamanho de um punho)之后,历时八年才最终问世的新作。在上一部诗集中,弗雷塔斯以冷静精确的笔触,对女性形象及女性境遇进行描述,突出性别的社会构建过程与自我认同。而在本年度的新作中,诗人则毫不掩饰其叙述视角的主观性,通过童年回忆与日常观察,明确展现出她对于巴西以及全世界现存社会问题的焦虑、不解与疑惑。
《恐吓之歌》开篇回顾了诗人生长的土地与亲眷的生平,并以孩童的视角写到:“我居住在瓦维尔德/那里是文明的尽头”“你想知道/什么是文明的尽头吗?”然而,这一对文明的追问却并不限于天真的童年,而是串联起整部诗集,暗示我们所处的时代就像是文明的终结。因此,从第三首诗《蜜蜂》(“Abelhas”)开始,诗人便将目光直接转向了现实问题:“如果/这个国家/苛待我们/是因为/……/……/没用的/从未见过/有蜜蜂/能够退休/就算是蜂后/也会被断腿断翅/被工人/带去远方。”作为这部诗集中最短的一首诗,弗雷塔斯以蜜蜂比喻巴西的劳动者,几乎是对巴西养老金改革及劳工保障缺失的直接批评。而在接下来的《愉港市,2016》(“Porto Alegre,2016”)里,弗雷塔斯则选择了第二人称叙事,展示了当代人对于现实问题的无动于衷。在这首诗中,“你”是电视机前的观众,看着远方战火连天,但“你”却并不在意,只会起身取出冰箱里的食物,却不曾想同样的悲剧也可能很快降临到自己身上。
在自我的表达之外,弗雷塔斯还致力于说服他人也参与其中。在与诗集同名的诗中,作者写道:“凡是因条件所限/而无法成为水手的人/凡是无法在船只中/周游世界的人/都应当/立即考虑/成为塞壬。”在弗雷塔斯看来,塞壬代表了广义上的受害者,因为她们半是女人,半是猎物。但与此同时,她们只要发声便足以使水手惊惧,这也正是“恐吓之歌”的由来。
三、多重视角下的辩解与对峙
无论在《皮肤的反面》还是《恐吓之歌》中,叙事者主要站在受害者一方与读者对话,力图引起大众的共情、理解与支持。但在2020年,还有更多作品虽然同样采用了第一人称叙事,却并不满足于展示单一视角,而是着力塑造一组组立场相悖的人物,赋予他们交替发声的机会,在双方叙事的矛盾与冲突中,表现巴西各阶层、团体之间的撕裂与对立。这些作品虽然探讨的主题不尽相同,展现的方式也有所区别,但内核都是要通过不同视角的切换,号召大家跳出既有的思维定式,仔细聆听其他的观点与声音,以促成不同团体的相互理解,或是进行更为全面的揭露与批判。
在《东京套间》(Suíte Tóquio)里,小说家乔瓦娜·马达洛索(Giovana Madalosso)便凭借其对两种叙事声音的细致刻画,获得了普通读者与学院派评论家的一致好评。这部小说的主人公是两位女性:保姆玛露和女主人费尔南达。全书共分为35章,其中奇数章节均为玛露的个人陈述,而偶数章节则为费尔南达的独白。小说的故事发生在一天之内,因为在这天早晨,当玛露带着费尔南达的女儿科拉离开公寓楼时,便已经做好了拐走孩子的准备,之后便与科拉开启了不断颠簸的旅程。而费尔南达在得知保姆与女儿失联的消息之后,陷入了对自我、婚姻与亲密关系的反思之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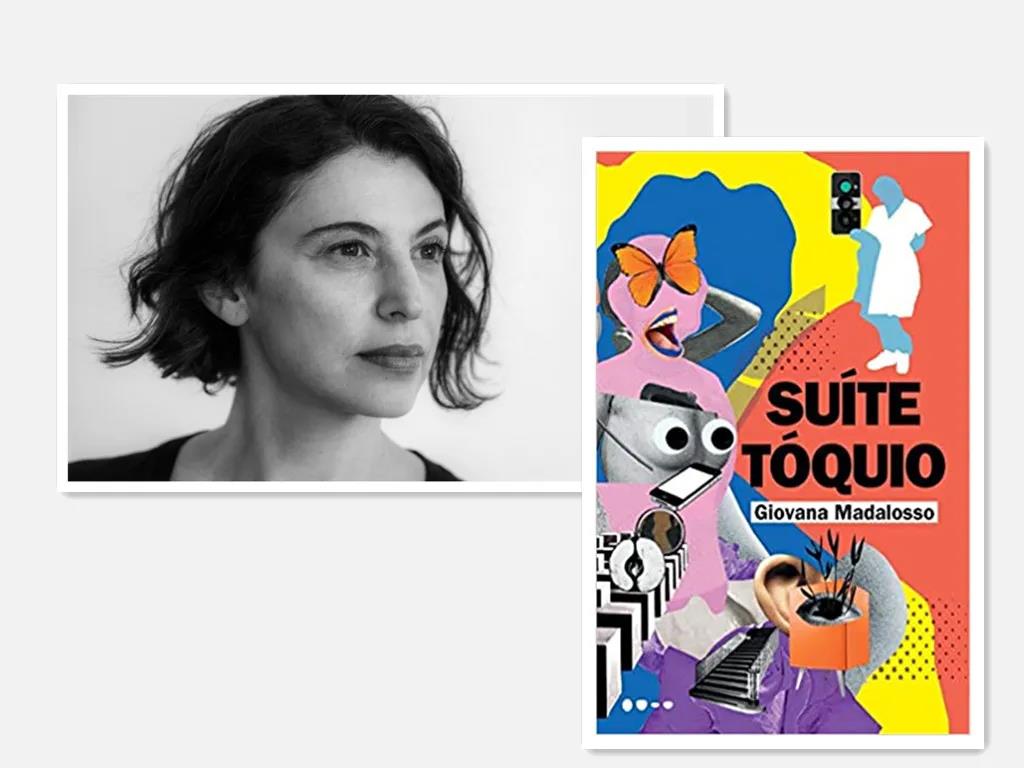
乔瓦娜·马达洛索与《东京套间》,图片源自Yandex
倘若将单数章节串联起来,读者会看到一个细心、慈爱、迷信而又明理的女性。玛露当了多年保姆,照顾过许多幼童。科拉两岁那年,费尔南达竭力劝她成为住家保姆,并精心布置了一间保姆房。费尔南达认为这个房间就像是东京酒店的套间,这也正是本书标题的由来。在接下来的两年中,玛露对科拉精心照顾,两人建立起极为亲密的情感联系。然而,在一次与女主人的争执之后,玛露无意间听到费尔南达想将她辞退。只因不愿与精心照顾的孩子分离,玛露才萌生了将科拉带走,当作自己女儿抚养的想法。
而在费尔南达的叙述中,呈现的则是一个独立要强却又缺少关爱的女性形象。作为影视团队的负责人,费尔南达收入颇丰,在结婚后依旧承担起赚钱养家的责任。然而,费尔南达的丈夫却并未履行照顾家庭的职责,尤其是在女儿科拉出生之后,便寻找各种借口逃避。正是在一次独自带领年幼的女儿旅行之后,费尔南达决定说服玛露留在家里,并将女儿完全交给保姆照看。与此同时,她对丈夫的感情也越来越淡漠,反而与影视公司的一位女领导发生了婚外情。
就客观事实而言,玛露和费尔南达在道德上均有瑕疵;但看完她们的自述之后,又会觉得她们都情有可原。作为保姆,玛露擅自将科拉带走足以构成犯罪,但她对小姑娘的爱却远胜于其亲生父母。而费尔南达在生育之后,工作的压力、婚姻的不幸、母亲的疏离、同性的爱恋几乎把她压垮,使她再没精力去关照女儿。然而,即使读者对她们二人均抱有同情,却无法忽视她们之间的冲突与敌对。拐骗发生前,女主人利用阶级优势,对保姆颐指气使、极尽压迫;之后,女主人又成为受害者,因女儿的失踪而承受巨大的痛苦。在书中,两人的叙述交替进行,却从未能进行对话,也未能理解对方。但在书外,乔瓦娜却为读者带来了双重视角,让我们放弃盲目对立,寻找解决问题的新路径。
值得一提的是,并非所有的自白都能够引人同情。马尔塞洛·维森廷(Marcelo Vicintin)的小说处女作《昨日的余烬》(As Sobras de Ontem)尽管也采取了双主人公交替叙事的写作手法,其最终的结果却是通过两种不同的视角,让读者看到了更多巴西上流阶层的自私与腐败。这部小说的主人公分别是埃吉迪奥和玛利亚·路易莎,前者是巴西一间大公司的继承人,因在巴西反腐行动中获罪而被监视居住;后者则来自一个破产的中产家庭,自少年时便致力于借助美貌、一步步进入上流社会。
这是巴西近年来罕见的以富人为主角的作品,里面呈现了丰富的生活细节,只有如维森廷一样的商业精英才可能了解,这也是令许多读者与评论家对这本书产生兴趣的原因。埃吉迪奥从小含着金汤匙长大,无需担忧生计,但他却因为无聊、贪婪与权欲,不惜官商勾结,即使被捕也毫无悔意。在玛利亚·路易莎的叙述中,如埃吉迪奥一般的富人尽管拥有一切,却极度自私,对自己拥有的特权毫无意识。当然,她也毫不掩饰自己的贪婪与虚荣,只是在谈及与富豪的恋爱时,依然暗示自己付出了真情,而这一点也在埃吉迪奥对前女友的回忆中遭到瓦解。
与《东京套间》的两位主角不同,埃吉迪奥与玛利亚·路易莎对于对方所属团体的批评,并非源于忽视或误解,而是因为太过了解。借助他们的观察与自省,大众得以窥见部分上层精英的行事逻辑,也更加确信改变现有权力格局的必要性,因为巴西上流精英与普通大众完全生活在两个不同的世界。当底层人民发现仅凭努力与才华,越来越难以实现阶级跃升时,只有像玛利亚·路易莎一样的新贵,才能依靠美貌与钻营,侥幸进入上流圈子。与此同时,处在社会金字塔顶端的人却在其内部建立起另一个金字塔,为了登顶而不择手段。
无论是借助间接对话寻求共情与和解,还是通过隔空对峙揭露更多的细节,多视角叙事的重要性都不言而喻。而在2020年出版的作品中,将这一技巧运用得最为新颖、娴熟的当属米歇尔·劳布(Michel Laub)的小说《两国方案》(Solução de Dois Estados)。本书标题原指让巴勒斯坦与以色列和平共存的政治方案,而在小说中则是德国女导演布伦达所创作的纪录片标题。布伦达曾在巴西生活了八年,直到其丈夫在里约热内卢被劫匪杀害,她才回到欧洲,开始到各国拍摄与暴力相关的纪录片。在2018年的一次活动中,巴西艺术家拉盖尔被弟弟的朋友当众殴打,掀起了轩然大波,布伦达因此重返巴西,将这里作为她下一部纪录片的主题,并说服这对姐弟接受采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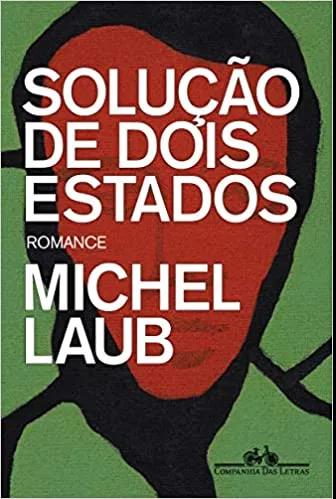
《两国方案》,图片源自Yandex
《两国方案》便是集合这次采访素材的文字转录稿。按照劳布的设计,这些素材主要分为三类:预先剪辑的材料、未经剪辑的材料与补充材料。其中,预先剪辑的材料剔除了采访者的提问与引导,只留下姐姐或弟弟的个人陈述。而在未经剪辑的材料中,读者则能够看到导演与姐弟二人分别的对话。补充材料占据的篇幅很少,主要由公众人物的演讲发言或者新闻报道构成。从表面上看,《两国方案》也是在两个人物视角的不断交替中展开叙事的。然而,即使就剪辑过的素材而言,德国导演的身影也未能完全隐形,而是作为对话对象,出现在姐弟两人的叙述之中。事实上,在小说前半部分——也即采访初期阶段,此时的大部分材料已经过剪辑——姐弟两人都在积极争取导演的支持,导演也在一定程度上扮演了两人对话的中介角色,引导他们对对方的辩驳做出回应。而在小说的后半部分,导演本人则不得不面对两人的质疑与挑衅,被迫做出解释与反击。
与本年度其他从主观视角出发的小说相比,《两国方案》独具特色,探讨的主题也更加深入多元。这首先是因为,在这部小说中,三名主人公都有丰富的媒体经验,深谙话语的重要性。德国导演曾拍摄同类题材,提问专业老道;姐姐年少时便在欧洲学习表演,活跃于艺术与文化活动之中;而弟弟是一家连锁健身公司的老板,并与一位新教牧师关系甚笃,深知如何进行布道与宣传。因此,他们的问答有来有往,措辞谨慎,观点犀利。与此同时,每个人的叙述过程都可能被随时打断并开启新的话题,也使这本书讨论的主题变得更为广泛,从姐弟之间的家庭冲突延伸到对巴西经济政策、选举制度、男权文化、暴力犯罪的全方位辩论,更涉及诸如福音派崛起、外来文化操纵等新问题。
在小说最后,每位人物的立场观点都逐渐清晰,却没有任何一个人能够真正说服对方。因为在当前巴西社会中,他们所分别代表的右翼保守势力(弟弟)、左翼身份政治(姐姐)与反政治化倾向(导演)根本难以调和。正如在国际舞台上,和平解决巴以冲突的“两国方案”仍是一个设想,劳布也无力为祖国的困境开出良方。但他仍相信文学的力量,这点从他年底的采访中可以看出:“我能保持的乐观就是出版一本书,相信有人会对它感兴趣。……我相信艺术仍然可能构成一个讨论的空间,让我们能够摆脱教条。这本书的圆满结局正在于此——在于我写出了它。”
结 语
受疫情影响,2020年巴西的各种社会问题愈发严峻,巴西文学不可避免地会有所回应。然而,正如米歇尔·劳布借书中主人公之口所表达的那样:“你以一个黑人、一个印第安人、一个一百三十公斤的女人的名义说话,这与你就是一个黑人、一个印第安人、一个一百三十公斤的女人是非常不同的。”在这个受疫情及社会不公困扰的时代,人人都渴望发声,又因互联网技术的发展,人人都能够发声,这就要求作家反思自己的创作方法,重新审视作者与大众、文学与社会之间的关系。正是在这一背景下,2020年的巴西作家更倾向于站在书中人物的立场,以亲历者的姿态进行创作。通过大量的独白或对话,他们的作品不仅能够更加清晰地展现书中人物的内心世界,更能够揭示出不同的思想理念如何构建出当前现实,引发读者的共鸣与反思。
(原文载《外国文学动态研究》2021年第3期,“年度文学研究”专栏,由于篇幅有限,省略了原文中的脚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