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缘身在此山中——怀念傅璇琮先生
编者按:学者俞宁的散文集《吾爱吾师》近期由人民文学出版社正式出版。俞宁先生是当代著名语言学家俞敏先生之子,现执教于美国西华盛顿大学英美文学系。这部散文集汇辑了作者近年偶尔撰写的文章,这些文章有些是回忆其父亲事迹,有的是回忆父亲挚友启功、柴德赓、李长之等事迹的,有的则是回忆自己的师傅曹士元、导师周珏良等文章,内容都是作者所闻所见。中国作家网经出版方授权,特遴《吾爱吾师》中部分文章发布,以飨读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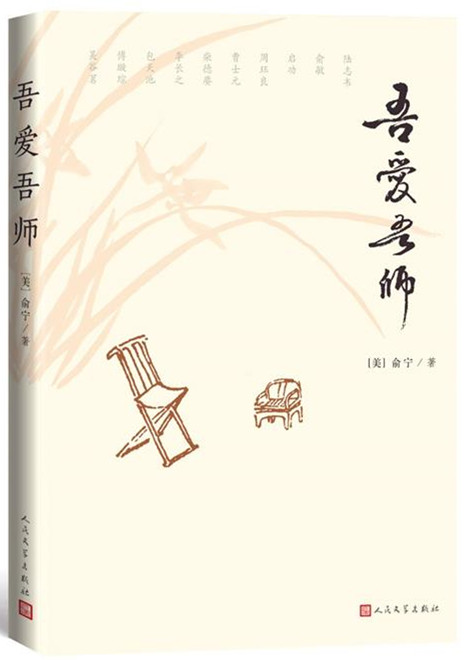
我认识傅璇琮“叔叔”已经四十年了。我认识傅璇琮“先生”才四年。
20世纪五六十年代,我岳父家住北京西郊翠微路二号中华书局宿舍的西北楼,和傅璇琮先生住对门。70年代大家同去湖北咸宁的五七干校,同吃同住同劳动,按男女有别之古训,各住在一个大屋子里,直到自己盖起房屋,条件才有所改善。那时我妻子的妹妹不但和徐阿姨住同一宿舍,而且是上下铺的紧邻。后来中华书局搬到丰台区的太平桥,这时两家人不住对门了,改住隔壁。两家都姓傅,都是浙江人。我岳父年长,所以他的三个女儿都把傅璇琮先生称作叔叔。傅叔叔和徐阿姨自己有两个女儿,却长期寄养在上海外婆家。大概是想念自己的孩子心切,他们夫妇从早年起就视我岳父的三个女儿如己出,把相当大一部分长辈对下一代之爱,移情到这三姊妹身上。1976年地震以后,我和现在的老伴确定了恋爱关系,自然常到她家走动,自然认识了近邻的叔叔阿姨。听我妻子讲,她们姐妹三人小时候去叔叔家,常常是推门而入,连敲门的礼节都省略了。回家因失礼遭父母训斥,但在对门却受亲热的招待。傅璇琮先生忙,只是年节时偶尔到我岳父家里来坐坐。听他和我岳父在一起说浙江老家话,又听到妻子姐妹三人直呼叔叔,我没想过他不是那姐妹三人的亲叔叔。不知什么原因,徐阿姨似乎没有使用过我的学名,却一直呼为“宝宝”。听她的口气,好像不是半开玩笑,仿佛真的以为我永远长不大。我1986年出国,每次探亲回家,总要到岳父岳母家住一段,以尽半子之责。于是常常见到傅叔叔和徐阿姨。徐阿姨总是很亲切地说:“哦,宝宝回来啦?住多久呀?过来坐坐吧。”这个称呼沿用到我耳顺之年。
我受家中长辈影响,一直对中国古典文学感兴趣。但“文革”结束、恢复高考的时候,不愿意受父辈的学术荫庇而失去自我,就选择了英美文学专业。直到过了知命之年,可能是人生进入老年的信号,我渐渐地被一种负罪感压得难受,觉得父辈从小给我灌输了一些中国古典文学知识,我一生不为中国古典文学做点什么,实在没法和良心交代。于是我发狠,把《全唐诗》通读了两遍,从中选出四百多首和自然环境关系密切而微妙的唐诗,把它们翻译成英文。翻译诗歌是自讨苦吃的事情,一遍又一遍地琢磨涂改,折腾了好几年。终于算是勉强看得过去了,就动手给各位诗人写小传,向美国读者解释诗歌的创作背景。查阅资料时找到了傅璇琮先生的《唐代诗人丛考》和《唐才子传校笺》,刚读了两三个诗人,就已经为作者的缜密认真的治学态度和广博深入的知识所倾倒。由衷地对妻子感叹,说:“有位叫傅璇琮的学者,真是让人佩服。他的材料,翔实可靠,使用起来让人特别放心!以后有机会的话,回国时去拜见人家一次,好好地感谢人家。”妻听了这番话,神情怪怪地盯着我看了半天,说:“这个学者呀,你叫叔叔都叫了三十多年了!你这个呆子!”说完还狠狠地踩了我脚背一下。我张口结舌站在那里,嘟嘟囔囔地说不出囫囵话来。难道我真是如此之不可救药?怎么能闹出这么大的笑话?仔细想想,根本不可笑,反而十分可气、可悲!妻批评我“生在福中不知福”,我完全接受。
妻要在中国出版我的书稿。我觉得不可思议——哪个中国人不直接读唐诗,反而要看我的英文翻译?这比买椟还珠还荒唐。可是她的决定,我是无力逆转的。只好按照她的要求,把英文的引论翻成了中文,然后又编了一个中文目录,一共二十几页稿纸。中国的春节,美国的学校里是不放假的,老伴儿已经退休,所以就自己回家过年。她陪我岳父参加中华书局的春节招待宴会,紧挨着徐阿姨坐,借机把我的引论和目录交给了徐阿姨,马上又转到了傅璇琮先生的手里。不久老伴探亲归来,带来了我最爱吃的果丹皮,还有一封傅叔叔的亲笔信,用的是清华大学中国古典文献研究中心的稿纸。节录如下:
现在中国大陆有关唐诗选注,出版已有不少,因此出版社肯定要求有一定特色,才能考虑出版。现在编著唐诗选注中文、英文,当有特色,我可以向有关出版社介绍。目前选目已有,也有特色,可以确定。现在希望提供一二篇样稿,即选译一二首诗,先录中文,后录英文;英译之要求,一要准确,二要有一定艺术性,有美感。
诗原文后,不必详作注释,可用500字左右,介绍每首诗的内容及艺术特点。同时介绍著者情况,字数也不必多,100字左右即可。这也都有中英文。请提供一二首样稿,我可以向出版社介绍,出版社确定后即可全面按计划进行。
傅璇琮
2012.2.22
我手里捧着信,放下咬了半截的果丹皮,读罢对妻说:“老伴儿,老伴儿。你使劲儿踩踩我的脚。”妻说:“你要干什么?”我说:“我要悔过。你说这么多年,我守着这个当代鸿儒,还是很亲近的叔叔,怎么就有眼不识泰山呢?早点儿读了他的书,不早就拜师学艺了吗?当面错过泰山北斗级的人物!你说该踩不该踩?”这话把妻气得笑了起来。她马上转身给徐阿姨打电话。我听见听筒那边也是笑得不可开交。
当年暑假,我回到北京,恰巧傅叔叔在我岳父家的客厅里坐着,我赶紧行礼、道歉。平时和气而严肃的傅叔叔也忍不住笑着摆手说:“没想到你还真能心无旁骛呀,连我是谁都不知道。”他这是为我开脱,反而弄得我更加无地自容,只好把话题岔开,向他请教。《唐才子传》里说天宝三载贺知章退休,请求皇上把周宫湖数顷赐给他做放生池。玄宗虽然答应了,却没有给他周宫湖,反而给了他更大一些的鉴湖一角。我问傅叔叔周宫湖是哪个湖,在什么地方。他毫不犹豫地说,这个他也不知道,做《校笺》时没弄清楚就存疑了。这给了我一定的安慰,同时我心里也佩服,这么大的鸿儒,有弄不清楚的事情就存疑,坦坦荡荡,虚怀若谷,值得我学习。几天以后,我专门跑到浙江去找,也没找到任何线索。傅叔叔听说后对我岳父说:“你这女婿还算实在,真的跑去找。”顺便说一句,2016年夏天,绍兴文理学院的俞志慧先生帮我解决了这个问题。据他考据文献和实地踏勘,认为周宫湖当地人又叫周官湖,就是禹池。详情说来话长,须另文再谈。
我回到美国后又找一位诗人朋友帮忙,在酒吧间、咖啡馆里对饮,论诗、改诗,终于完成了美感较强的一稿。我从西雅图电邮回去,请妻妹帮忙打印出来,送到隔壁。据徐阿姨说,傅叔叔看完笑眯眯地说:“我给宝宝写个序吧。”我听说后亦喜亦惧,喜的是傅叔叔这个许诺是对我工作的肯定,惧的是自己真的配不上如此殊荣。可惜傅叔叔写的时候用笔而非电脑,我得等上一段时间才能看到。序文纯是傅氏风格,平实而细致,使我最高兴的是他老人家夸我的工作也是“平实”和“有特色”。他的肯定对于我这个刚刚回头的学术浪子来说,是极大的鼓励。我由此坚定了信心,决定今后的职业生涯就是把西方文艺理论中一些实用的东西,介绍给国内同仁,让他们能更好地认识唐诗本身的魅力。我曾不止一次对傅叔叔和徐阿姨讲,就唐诗研究而论,国内随便找一个学者都比我功力深,我介绍的这些新工具,他们一旦掌握了,就肯定比我做的好得多。那时,我就完成了自己的历史使命,该退休了。傅叔叔说:“你能有这样的学术心愿,很好。我介绍一个伙伴给你。”我的书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之后,傅叔叔让他的大弟子,南开大学中文系的卢燕新教授为我写了书评,指出拙著里面一些可取之处,在《博览群书》杂志上发表,引起了正面的反响。后来燕新到美国哥伦比亚大学访学,顺便到我家来玩,我向他请教了许多问题。如果像傅叔叔说的那样和燕新做学术伙伴,我还不够资格;但在燕新的帮助下,我总算走上正路,能用国内学者通用的文体和他们交流学习心得了。后来,燕新还介绍我参加了在成都召开的唐代文学年会,并获得在大会上发言、和国内学者交流的机会。这些机会是在燕新的帮助下获得的,但究其根本,还是在傅叔叔的关心下才得以实现的。对于他们师徒二人,我心中充满感恩之情。
2016年新年伊始,我正在为拙文《杜甫〈秋兴八首〉的形式美发微》收尾,突然接到燕新的电信,说傅叔叔仙逝了。噩耗传来,我悲痛不已。一方面伤心我们夫妻二人失去了亲人,另一方面感叹学界遽失泰山北斗,同时也悔恨自己四十年来身在庐山而不识其巍峨的学术面目。刚刚亲承謦欬四年,就失去了良师,怎一个“悔”字了得!怎一个“愧”字了得!然而,世上没有卖后悔药的。唯一的办法,就是沿着傅叔叔给我指出的路走下去——在西方文论中排沙拣金,去其浮躁虚华的部分,取其实用、适用的部分,为国内同仁们贡献一个工具箱,让他们在里面任选所需,使其工作起来更方便,更顺手。只有为唐代文学贡献自己的绵薄之力,才能对得起傅叔叔的在天之灵。先父的学生们曾经为怹出了一本论文集,先父为其拟题为《薪火编》,意寓“学如燃薪,薪尽火传”。傅叔叔他们那一辈的学者,都有这种献身精神,值得我辈学习。众人拾柴火焰高。只有越来越多的有志者为学术献身,才能把前辈的事业承传下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