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黑一雄《克拉拉与太阳》:书写与凝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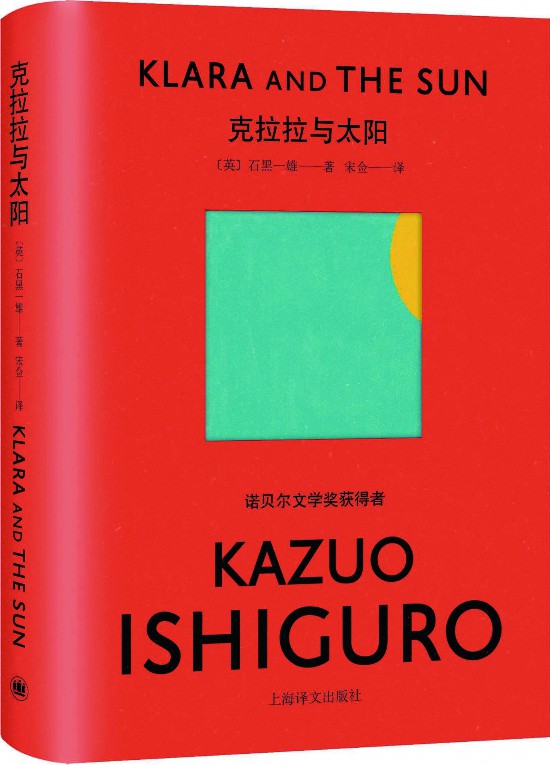
很长一段时间以来,我总是对石黑一雄那张留着披肩长发、身穿背心、抱着吉他弹唱的老照片无法释怀。很难想象,这位喜爱深色休闲西服,拥有一张东方面孔,说着纯正英式英语的优雅男子30年前迷恋过摇滚乐,是个地地道道的嬉皮士。虽然做音乐的梦想破灭后,他随即开始小说创作的职业生涯,且一路几乎没有遭受过什么大起大落。加之包括诺贝尔奖和布克奖在内的光辉获奖记录,人们委实难以把他与非主流音乐热爱者的出格与极端联系在一起。诺奖组委会赞赏他作品中有“巨大的情感力量”,这评价仿佛将作家归置在了以情感描写取胜、表达细腻而柔和的那一类中。确实,石黑一雄的风格有这个面向,但我们常常忘记了这一评价还有下半句,那就是这一情感力量最终所指向的——“我们与世界联系的幻觉之下的深渊”。当一个人敏锐到足以发现自我和一切他者之间无可回避的裂隙,并且深深地迷恋这个难以弥合的精神上的创口时,是作家还是嬉皮士已经没有那么大的不同了。因为无论他是什么,他都已经抓住了一切艺术创作最初的脉动:对深渊的执迷。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说《克拉拉与太阳》只是作家对人类伤口的又一次呈现,只不过它被披上了一件由后现代社会生产出来的“外衣”,如果确实需要的话。
一
石黑一雄在某次采访中坦言这小说脱胎于一个悲伤的童话故事,本来是写来送给女儿的。张怡微也在一篇文章中分析了克拉拉这个人物与小人鱼的相似点,它们都不是人类,按“种属”的划分原则,它们的属性、地位和能力等等都低于人类。但它们都对人类充满了好奇与向往,最后也都为了保住人类的幸福而牺牲了自己,都通过放弃自己的存在而成就了自身的价值。但克拉拉显然比小人鱼更为复杂,这不但表现为它不是“自生”的,而是“被造”的,在与人类的关系方面,克拉拉所要面对和处理的内容也比小人鱼显得更加庞大和纠结。作为人类的“旁观者”和“陪伴者”,这个特殊身份首先就具有强烈的内在矛盾。基于它的观察常常是全景式的,且伴随着对人类生活的不懈观察和思考,这仿佛使克拉拉与人类可以建立起一种赤裸敞开的亲密关系。但同时,旁观者本身也构成了一种局限,这表现为克拉拉自我意识的软弱乃至缺失。作为一个AI,一个模仿者和替代品,它到底不是真正的人类,无法成为一切情感和认知的中心。而这种强烈的矛盾性,也是构成克拉拉悲剧命运的根本因素。此外,克拉拉和乔西一家的关系也是绝对不平等的,因为它本质上是个商品,虽然乔西母女对她很好,甚至做好了让她代替乔西的准备,但这仍然不足以使其摆脱这种本质上绝不对等的权力关系。然而正如作者借着小说所感慨的:“人心是一栋奇怪的房子,里面房间套着房间……”乔西一家在感情上又非常依赖、接纳克拉拉,这与很多文艺和影视作品中出现的人工智能与人类由于权力不对等而导致的彼此毁灭全然不同。表面上看,作者似乎已经接受了AI作为未来社会的一份子而存在,然而事实上,这种存在对一个真正渴望融入人类的AI来说,又是极为残酷而屈辱的。正如现代人对待宠物的感情,那种貌似的极端付出和无私关爱不可避免地存在自我中心的一面,这种爱可以被理解为是一种单向的爱,一种一厢情愿的寄托,甚至还有许多幻觉,其真实性必然会受到质疑。反而从克拉拉身上体现出来的那种对人类的理解和向往却显得特别单纯,甚至表现出一种无目的性。这是因为对它进行价值预设的恰恰就是人类,它的全部意义都是人类,也只有人类才能赋予它。
因此,克拉拉在观看和理解人类时始终带有一种困惑,但系统又要求她必须带着“理解和认同”的预设来进行思考,这就是说,当克拉拉还未曾真正深入地熟悉并了解人类以前,她已经被要求需要尽可能,甚至完全地理解他们、认同他们。这显然是对人类之间认知过程的某种悖反,在通常的情况下,我们习惯的是先认知后认同的思维方式。这种由强烈的悖谬感而产生的反讽效果使得小说始终带有一种重审人伦的特质,通过对人工智能所寄予的深切期待,它指向的是人类自身的匮乏及愿望,是深藏在我们强烈欲求之下的,那种可悲的矛盾性和荒诞感。这一点在乔西母亲的身上表现得尤为淋漓。这位被公认为极度自私与自我中心的母亲,一个深陷进化升级的“幸福迷局”从始至终执迷不悔的后现代冷酷女性,却又极其看重甚至依赖她的“女儿”,无论是已经去世的姐姐萨尔,还是重病的妹妹乔西,甚至是可能将会替代乔西的克拉拉,这位母亲一边榨取着传统的血亲人伦能带给她的一切情感需求,一边又试图利用高科技将这种情感放置在能够与自我满足够成完美平衡的天平秤上。当她绝望地发现两个女儿都因为“提升”技术而死亡或即将死亡时,她仍然顽固地寄希望于从克拉拉对女儿的“模仿”中获得一份可以被“模仿”的亲情。
其实“提升”技术到底是一种怎样的技术,小说自始至终都没有展开说明,这使得《克拉拉与太阳》与一般的硬科幻小说有了本质上的不同,后者将未解锁普及的前沿科学作为叙事得以成立的基石,而石黑一雄却甚至都不关心科技发展本身。他只着眼于科技对人类可能产生的后果,它是表现在伦理层面上的,就如安徒生也并不关心小人鱼是如何变身成为人类的,对他来说这是一个魔法就能解决的问题。那么就石黑一雄而言,可能新兴科技也就是和魔法差不多的存在,他宁可从一条类似于“神秘主义”的通路去理解它,也不希望将它理解为人类工具理性之下的某一种必然结果。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认为作者仍然是一位传统作家,其价值取向中仍然存留浓厚的人文主义色彩。面对高科技下的人与人之间扭曲的情感关系,以及对作为悲剧来源的阶级跃层的残酷性,他的否定态度是明确的。但也像克拉拉贯穿始终的困惑一样,作者不愿意以批判的视角和书写方式去对抗这些问题,他的有节制的反讽和不尖锐的对抗,最终是为了赋予这困惑一些更丰富的内容,即为什么人类需要这些东西,在人的深渊一般的内心世界里,究竟隐藏着什么样的欲望和罪恶,使得人甚至愿意成为自己的试验品和牺牲品。
二
小说名叫《克拉拉与太阳》,侧面说明“太阳”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意象。克拉拉的生命需要太阳的能量来维系,太阳就成了克拉拉心目中的神。当知道乔西的生命即将消逝时,它向它的神祷告,希望神能以一种神秘的力量挽救乔西。这种告求的方式其实是非常古老的。但克拉拉的祷告行为本身,却让我们看到了它第一次不再只是一个旁观者,一个替代品,而是变成了一个主体。通过“祷告”这一方式,克拉拉成为了一个有意志、有独立思想、有情感和愿望的行动者,它跃出它本来该有的被动属性,跃出了它作为AI的“种属”,被赋予了“人”的属性。如果把太阳理解为一个永恒的自在的存在物,是一切能量、力量和价值的来源,而把克拉拉理解为一个在任何处境下都绝对需要它、依赖它的被造物,那么当后者在向前者祈求的时候,它们彼此“相认”,并产生极为亲密的一对一关系。而作为太阳神秘力量的受惠者,乔西及她代表的人类,虽然在“种属”方面是绝对高于AI的,却因为退到了故事的次要位置,他们看似强大、丰富,但在克拉拉和太阳面前,却仍然是软弱的。
然而小说最使人哀伤之处亦在这里,克拉拉完成了她的使命,被理所当然地丢弃,等待回收,其实也就是它作为一个AI的死亡。读者理应读得出克拉拉的全然献身,它的原型曾多次出现在经典的文学作品中,比如安徒生的《海的女儿》或王尔德的《快乐王子》。和这些童话故事一样,克拉拉也并不是一个真正的“人”,但却被赋予了人类所不具备的灵魂的纯净性。而这纯洁,可能恰恰是人们一直追求却无法获得的。当我们厌倦了这个乌七八糟的现实世界,厌倦了连自己都无法解释清楚的各种让人窒息的欲望时,我们并非对这种被捆绑和压抑的不自然状态完全没有警惕与反省,以克拉拉为代表的一系列AI的被造,不正是出于人类想要弥补自身纯净性的缺失这样一个无奈而悲伤的目的吗?在这个意义上,任何的“进化”与“提升”也都可以被认为是一种对缺陷的弥补,它们共同指向一个亏缺了具体内容的“乌托邦”。而那些用来陪伴我们的AI,它们就像一块块被女娲用来补天的石头,因为这个世界的堕落与丧失反而具备了灵性。小人鱼为了追求不灭的灵魂变成泡沫,快乐王子则因着那颗无法熔化的铅心得以回到天堂。当石黑一雄和他的前辈作家们不得不用这些低于人类的造物来构建“乌托邦”的具体内容时,我们所感慨的其实并不是这些非人的灵魂的可贵,而是人类自己灵魂的虚空。
但也因此,石黑一雄的深刻得以同时覆盖看上去是处在被批判和讽刺位置上的人类社会,这与他自己作为“旁观者”的一贯视角是分不开的。在某种程度上,他和克拉拉一样,都不具备完全融入到一个具体的社会历史阶段的能力。在一则访谈中,他坦言:“我既不是一个英国化的英国人,也不是一个非常日本化的日本人。因此,我并没有清晰的角色定位,既没有要代言的社会,也没有要为之书写的国家,正因为如此,我才不得不选择一种国际化的写作方式来进行写作。”这可以说是跨文化视角的必然矛盾:没有办法纯熟地使用传统的创作价值维度,比如国族、民族、社会、历史等。但这也使得石黑一雄为自己开拓出了新的价值领域,使他对当代社会的虚无性具备更深刻的洞察力。所谓的“国际化写作”,其实就是一种“彷徨于无地”的写作,将写作者自身的现实负担降到最低,将写作的“介入性”和“功能性”降到最低,从而产生一种疏离乃至漠然,而这,同样也可以导向一种类似的怜悯与同情。事实上,在之前的布克奖得奖作品《长日留痕》中,石黑一雄已经借由管家斯蒂文斯这个人物将那种在场同时不在场、介入同时不介入的悖论感发挥到了极致。和克拉拉一样,斯蒂文斯观看一切,但同时,他止步于观看,止步于自己旁观者的身份与职责,以一生之力坚守不越雷池一步。由此,他几乎完美地做到了将整个20世纪的历史拒之门外,从而完整地把持住了自己的内心,即其作为一名管家的职业价值。在克拉拉身上,我们同样可以看到这种悲情,它只是陪伴、观察、理解和模仿,却从根本上无法真正介入人类的世界。所以,无论克拉拉对人类的爱与理解是多么细致而深刻,它的献身和代赎行为最终只能以间接的方式惠及到他们。它怜悯他们,爱他们,恰恰是因为它有限、疏离,是一个并不重要的角色。
而黑石一雄自己又何尝不是在旁观者/参与者这一充满了悖论色彩的角色中游弋呢?这或许也是当下这个时代所应有的一种写作姿态吧。作家从旁审视,同时把握自己的创作,看上去他不再成为自己作品的强势掌权者,他的叙述语言低沉、忍耐,带着一点点漠然;但同时,他又对人类的存在抱有极深切的灰色情感,比起被极大浪漫化了的红色和充满绝望色彩的黑色,灰色是充满了现实感的颜色。显然,作家不愿意对人类可悲的堕落处境再踏上一脚,但因着一种不合时宜的人道主义的清醒,他也不再可能反身拥抱。于是,他选择自我放逐,逡巡在人类的现实与太阳的神秘之间,在人性之暧昧与爱之纯粹的复杂性中为自己留下一个不起眼的观众席。而书写,成了最终的驱动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