露易丝·格丽克与阅读的政治
2020年诺贝尔文学奖颁给美国女诗人露易丝·格丽克(Louise Glück),出乎不少人的意料。这是诺贝尔文学奖在十年内第三次颁给诗人(前两次分别是托马斯·特朗斯特罗姆,2011年;鲍勃·迪伦,2016年),并在五年内两度授予美国诗人。引发争议的另一个重要原因或许是:许多人压根没听说过露易丝·格丽克。

露易丝·格丽克
除了世纪文景在2016年推出过两本格丽克诗歌合集外,中文世界对格丽克其人其诗的介绍寥寥。这与她在大洋彼岸获得的殊荣显得很不相称:在荣膺诺贝尔文学奖之前,格丽克已经包揽了包括普利策诗歌奖、美国国家图书奖、华莱士·史蒂文斯奖在内的几乎所有重要诗歌奖项, 2003-2004年还被授予年度美国国家桂冠诗人。
中国读者仍然需要去了解这位新晋诺奖诗人。11月15日,新京报·文化客厅联合世纪文景,专门邀请到作家、诗人、宗教与文学学者倪湛舸,与读者一同走近露易丝·格丽克,解读其诗歌的美学和阅读的政治。

倪湛舸,作家、诗人、宗教与文学学者,北京大学英语语言文学系学士,福德姆大学神学系硕士,芝加哥大学神学院宗教与文学专业博士,弗吉尼亚理工大学宗教与文化学系副教授。著有文集《黑暗中相逢》《人间深河》,小说《异旅人 》,诗集《真空家乡》等。
个人化的古典主义者
格丽克1943年出生在纽约长岛的一个匈牙利裔犹太移民家庭,家境优渥。父母育有两女,格丽克是家里的长女。17岁时,格丽克患上厌食症,导致她无法继续上学。为此,她接受了长达7年的精神分析治疗。厌食症让格丽克对死亡有了早熟而清醒的认识。她曾提到,“我认识到,从逻辑上,85磅,然后80磅,然后75磅是瘦了。我知道,在某种程度上我正在走向死亡。我内心深处清楚地知道,我并不想死。即使那时,死亡仍然是一个悲痛的隐喻。”
厌食症对格丽克的一生,乃至她的诗歌追求都产生了重要影响。据格丽克自己讲,这种心理障碍和她早夭的姐姐有关。原来在格丽克出生之前,父母已先育有一女。女儿的去世,让母亲大受打击。而格丽克似乎一直生活在姐姐早逝的阴影下,个体的创痛使得她早期的诗作接近“自白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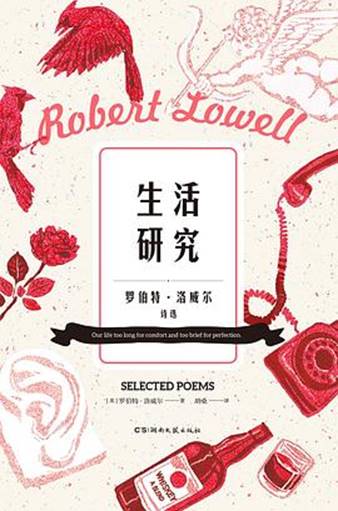
《生活研究:罗伯特·洛威尔诗选》中文版书影
作为诗歌流派,“自白派”肇始于罗伯特·洛威尔的诗集《生活研究》。这部诗集大胆揭露诗人内心的思想活动,涉及隐私、性爱和心理创伤,由此引发了一场“自白派”运动。同时,格丽克步入诗坛是在上世纪六十年代,正是“自白派”风头正劲的时候,格丽克不可能不受到影响。
1968年,格丽克推出第一部诗集《初生子》(Firstborn),结束对厌食症的心理治疗。诗集涉及家庭生活中的亲密关系,围绕着生与死、爱与性等主题展开。此后,格丽克两度结婚,又两度离婚。破碎的婚姻在某种程度上使得格丽克的写作一直延续着“自白派”的主题。
“自白派”女诗人如西尔维娅·普拉斯(Sylvia Plath)、安妮·塞克斯顿(Anne Sexton )等经常被拿来和格丽克比较,三人在诗歌写作上颇有相似的地方:比如经常书写女性在父权社会中的痛苦经历。但也有不同的地方,格丽克的诗歌风格更加偏向低调和冷静。倪湛舸认为,“格丽克并不看重受难者痛苦状态的宣泄,也不事无巨细地描绘痛苦。她虽然借助个人经历,但往往将其藏着掖着,很多话不愿意明说。早期作品中已经有了后期的倾向,更愿意去寻找一个原型”。
倪湛舸援引伊丽莎白·卡罗琳·多德(Elizabeth Caroline Dodd) 1992年出版的《遮蔽的镜子与女诗人》(The Veiled Mirror and the Woman Poet),称格丽克是后自白派的“个人化的古典主义者”。《遮蔽的镜子与女诗人》是最早研究格丽克诗艺的专著之一,多德在书中研究了四位女诗人,其中之一便是格丽克。多德在书中提到,格丽克的文风具有斯多葛主义的特征,喜欢使用无夸张的修饰手法,采用大量留白,运用沉稳冷静的语气。这种风格往往被认为是古典主义的特点。
融合自白与思辨的神话重写
格丽克从小熟读西方古典神话,经常借助重写神话来书写个人经历和反思现代生活。她的诗里大量出现了希腊神话、圣经神话、民间传说和历史故事。她在1981年接受采访时说,“我的倾向——这是显而易见的——是非常迅速地建立神话结构,看到当前时刻与原型结构的相似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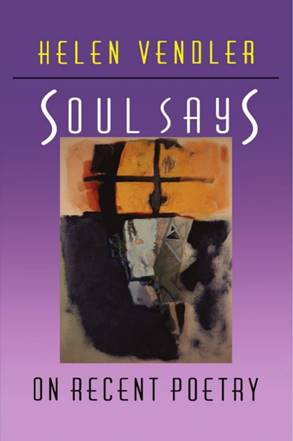
《灵魂说:近期诗歌论》英文版书影
海伦·文德勒(Helen Vendler)1995年出版的诗论专著《灵魂说:近期诗歌论》(Soul Says : On Recent Poetry)里有专门研究格丽克的章节,她认为格丽克在自白派的直抒胸臆和智识派的智力游戏间,成功开辟出神话结构这种独特的个人风格。她称”路易丝·格丽克是一位有强大存在感的诗人。在过去的二十年里,她出版了一系列令人难忘的诗集,达到了不同寻常的辨识度,不是通常意义上的‘自白’或‘智识’,这两个词往往被认为代表了诗歌史的两大阵营。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格丽克拒绝传记式或思辨式的书写,而喜欢一些人们称之为神话的或神秘的陈述。”
通过重写神话故事,格丽克将自白和思辨相融合。“文德勒解释了格丽克为什么做大量的神话重写,因为她需要在自白派和智识派之间找到第三条道路,她既不想单纯地依赖自传性素材,也不想上升到一种概念游戏,她需要在两者之间找到平衡”,倪湛舸说。
在倪湛舸看来,格丽克重写神话的举动标示着一种双向运动:一方面是神话对日常经验的整合,另一方面是日常经验对神话故事的激活。读者在阅读格丽克诗歌的时候,可以借助她的经验上升到神话经验,并且不被她的个人经验所限制。同时,作为女性主义诗人的格丽克通过重写神话,让在神话中缺席的女性角色发出自己的声音。“格丽克在她的诗歌中给日常经验赋予了一种神话原型的力量,把日常经验提炼并升华到神话原型的高度,这也是诺贝尔文学奖颁奖词里提到的,‘以朴实的美感使个人的存在变得普遍’。”
倪湛舸提到,另一位美国女作家玛丽莲·罗宾逊(Marilynne Robinson)同样喜欢重写神话,称其为“写小说的格丽克”。“玛丽莲·罗宾逊的代表作《家园》重写了浪子回头的神话故事,语言极为简练,去除任何修饰,冷峻朴素的语言达到了强烈的情感冲击力。同时,《家园》中加入原神话故事中被忽视的女性角色,与格丽克类似。”
多声部复调书写
除了书写日常生活中创伤性的个人经验、重写神话故事,自然也是经常出现在格丽克诗歌里。因此,有人把格丽克与以书写自然著称的玛丽·奥利弗(Mary Oliver)相提并论。不过,两人的倾向性有很大不同。正如倪湛舸所言,玛丽·奥利弗诗里的抒情主体往往是一个观察者,诗歌出自人对自然的观察。而在格丽克的诗中,抒情主体并非总是人类生命体。在这个意义上,格丽克的诗歌超越了传统意义上的抒情诗,对抒情诗这个概念做了一定拓展。

玛丽·奥利弗
“进一步说,两人相似的地方在于都把外在的自然世界当作诗人内心世界的投影。在格丽克的写作中,这种投射不是简单的由人到非人的投射,而是人与非人之间互动的关系。从这种意义上讲,她们诗歌中任何自然景物的描写也属于诗人内心活动的描写。”
格丽克的诗歌显得更加“亲民”。在一次访谈中,一位诗人曾调侃格丽克,说如果阅读不同诗人需要支付不同入场费的话,格丽克的入场费只需一美元。这话的意思其实是说,格丽克写诗喜欢用简单的词汇和流畅的短句,诗歌往往“缺乏”意象和音律之美。不过,作为读者的格丽克就从没被悦耳的音律和漂亮的意象打动过。她认为,诗人写下的每个词都应该非常关键,不需要增加修饰。在写作过程中,她便尽量回避华而不实的东西。她称诗歌最重要的是获得一种类似原型的力量,直达本质。倪湛舸称这种风格与东方美学有共鸣。
倪湛舸以《野鸢尾》为例认为,格丽克在这部诗集中塑造了三重抒情声音,这是她对传统抒情诗概念的又一突破。如果让格丽克来写花园里的花,会怎样呢?按照惯例,花可以是一种声音,诗人是另一种声音。但在花和诗人之上,格丽克还能增加另一重声音:那就是神的声音。在某种意义上,格丽克的诗歌达到了类似巴赫金所说的复调小说中的多声部风格。“超验性的神,其实也是格丽克诗歌中的一个重要的角色。”
《野鸢尾》
在我苦难的尽头
有一扇门。
听我说完:那被你称为死亡的
我还记得。
头顶上,喧闹,松树的枝杈晃动不定。
然后空无。微弱的阳光
在干燥的地面上摇曳。
当知觉
埋在黑暗的泥土里,
幸存也令人恐怖。
那时突然结束了:你所惧怕的,作为
讲话,突然结束了,僵硬的土地
略微弯曲。那被我认作是鸟儿的,
冲入矮灌木丛。
你,如今不记得
从另一个世界到来的跋涉,
我告诉你我又能讲话了:一切
从遗忘中返回的,返回
去发现一个声音:
从我生命的核心,涌起
巨大的喷泉,湛蓝色
投影在蔚蓝的海水上。
这种多声部的写诗方式,适合创作“组体诗”。自《阿勒山》(Ararat)开始,格丽克的每一部诗集都属于“组诗”的体例:由单独的诗歌篇章按照某种逻辑组织在一起,形成完整的长诗。因此,格丽克的每本诗集都应该作为一个整体来阅读。倪湛舸将这种多视角的叙述比作电影摄影。“从不同的视角出发,抒情的声音一直在变。这就好比电影里的摄影机,采取不同的视角,把这些视角放在一起,最后呈现出来完整的生活。”
不过,一位叫丹尼尔·莫里斯(Daniel Morris)的学者在2007年出版了一本研究格丽克诗歌的专著《露易丝•格丽克的诗歌:主题研究》(The Poetry of Louise Glück:A Thematic Introduction),里面提出一个有趣的观点,认为格丽克多声部的抒情诗写作,其实受到犹太教释经传统的影响,也就是米德拉什(Midrash)的影响。米德拉什原义是探索和研究,是一个旨在注解《希伯来圣经》而发展出来的诠释传统,通常涉及三个彼此相关但又应予以区分的含义。
倪湛舸介绍说,“《希伯来圣经》里往往有争议性的片段,犹太教的学者会针对这些片段做出解释,不同的学者往往得出不同的解释。这些不同的观点在同一张纸上罗列出来,算得上古代的一种多声部学术,和巴赫金说的多声部复调小说有异曲同工之妙。”格丽克做的尝试是把简单的抒情诗写成一个多声部的“米德拉什”,进入原初的神话故事,但不是简单的引用,而是对经典重新阐释。
阅读的政治学
至于今年的诺贝尔文学奖为何颁给格丽克?倪湛舸认为这与格丽克的写作风格有关。“格丽克的诗歌表现出了强烈的精神追求,愿意突破个体,强调抒情诗的普遍性,看起来非常符合诺贝尔文学奖的一贯审美。诺贝尔文学奖颁给格丽克,对格丽克来说是锦上添花的事,对诺贝尔文学奖则是一以贯之的精神传承”。同时,2020年作为多事之年,全球疫情暴发,世界格局动荡和重组,格丽克的诗歌在某种程度上提供了一条精神性的艺术拯救之路。

格丽克两本中文版诗集书影
格丽克不愿意承认自己的风格是阴沉的(grim),她认为自己一直都在追求精神性的超越。她诗歌里的“自白”风格,其实是一种见证。格里克最终所追求的是一种修复和救赎。“格丽克的诗歌风格从早期的相对阴暗,到后期的越发开阔,其间有一个很明显的脉络,即艺术的拯救之路。诺贝尔奖今年发给了她,对全人类而言,可能也是希望能够给深陷于瘟疫之中的我们以一点所谓的希望吧。”
倪湛舸认为,格丽克的诗歌可以在三个方面为当代汉语诗歌提供有力的借鉴。一方面是格丽克素朴的写作风格,与东方美学中的留白有一定的呼应性。“在我的印象中,现在对美的理解可能还过于单一,我们可能还在追求音律悦耳或意象丰富等,还在寻求一种比较程式化的美。我觉得格丽克的作品向我们展现了美的多样性。如果把美看成巅峰的话,通往巅峰的路不是只有一条,而是有很多条。”
从作者层面看,格丽克写诗已愈半个世纪,现今70多岁的她还在继续写作。“这提醒我们诗歌其实不是一种所谓的青春书写,作为一个诗人,你要不停地寻求变化,寻找自我突破。当我们阅读一位比较长寿的诗人,我们要注意他不同阶段的风格变化。”同时从读者层面看,格丽克的诗歌在读者群体中广泛传播,在研究者中也有很高的流传度。这说明格丽克的诗歌能够激发不同理论框架下的阐释和讨论,似乎也在间接提醒我们为诗人建立诗歌阅读和阐释体系的重要性。
“我觉得比诗人更稀缺的是好的读者,读者其实是诗人生长的土壤。” 倪湛舸总结道,“建立诗歌写作和阅读的女性群体更是我们的当务之急,也许这样的群体早已存在,我们要努力地让更多人听见她们的声音,也就是我们自己的声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