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愚人沙利》:读懂美国底层民众的挣扎与人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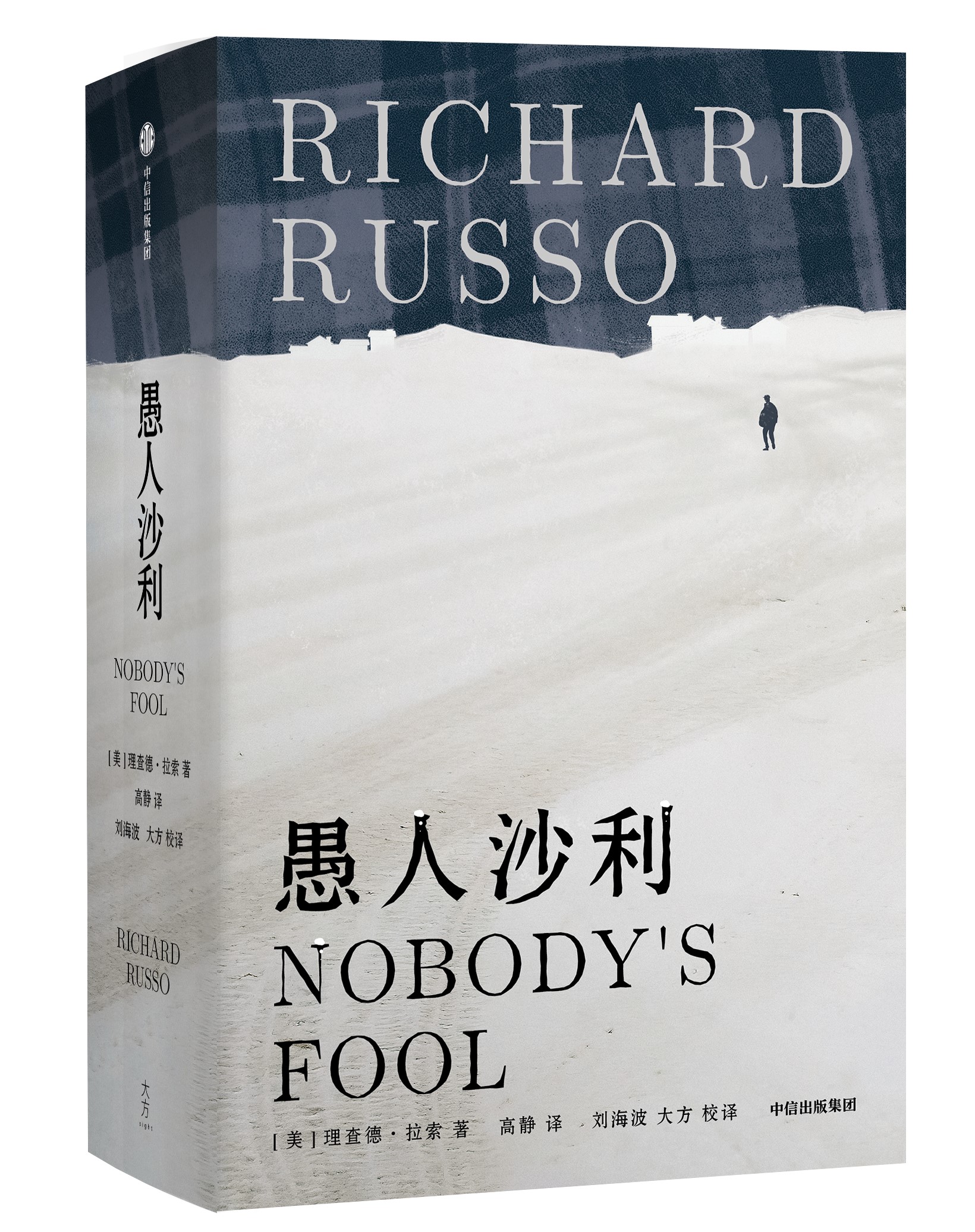
多年前,当我感到不堪生活重负时,我曾梦想隐居到纽约北部的某个偏远小镇中,作为永久住客入住一间荒凉破败的旅馆。这样的小镇在我的想象中位于地图的边缘,而这正是理查德·拉索笔下的故事展开之地。他将雄心勃勃的新作《愚人沙利》设立在纽约州的北巴斯镇,这小镇比其前作《莫霍克》和《危险泳池》中所描述的蓝领穷途之地稍显生机。
北巴斯是那种我们驾车穿过时不会停留的小镇,仅对自己在其“如果是在佛蒙特州还能值点钱的老旧维多利亚式房子和希腊复古式居所”中可能度过的舒适生活稍作幻想。但拉索先生邀请我们停下脚步,四处看看。他展现给我们平静表象下的暗涌。我很快意识到,有理智的人是不会到北巴斯镇来隐居的,因为这里的生活,就像巴尔扎克说的那样,是完全暴露在公众视线中的。
也许这就是为何小镇的设定,如同远航船只,总是小说的理想选择:像高压锅一样可控,有固定的一组人物,而缺乏隐私和被迫近距离接触让情节具有沸腾的潜力。在北巴斯,让事件升温的是一个叫“终极逃亡”的主题乐园的投资项目,在小镇居民严重,这可可能会给垂死挣扎的小镇带来一线经济生机……
1984年秋,北巴斯“仍然在等待转运的一日”,你能感知到,只有靠小镇转运才能影响到沙利的命运,他是小说难以分割且不可改变的主人公……这六十年间,沙利从他暴力的父亲家搬到了上了年纪的中学老师贝丽尔家的楼上,贝丽尔曾经是沙利的老师。疼痛难忍的膝伤让沙利不得不接受奇怪的工作——只有用现金支付酬劳的零工。
沙利就像一头半驯化、半疯狂的熊,向书中那些倒霉的人物不断发起佯攻或猛戳,组成了书中的许多次要情节。沙利疏离的情人露丝有一个让她蔑视的丈夫,以及一个差点死于自己丈夫之手的女儿。沙利的儿子彼得婚姻不睦,有两个难缠的孩子,一个疯狂且占有欲旺盛的母亲,和一个患病的继父,而他自己又被所在的大学拒绝聘用。贝丽尔开始在小镇附近的出行中迷路,不得不避开她那贪婪、自私且擅自插手的银行家儿子小克莱福——“终极逃亡”项目的主要推动者之一。就连沙利最好的朋友罗布(他傻到不会给自己找麻烦)也受妻子牵连,后者新近染上盗窃癖。
我要祝贺拉索先生成功避免了一些缺点。《愚人沙利》从未陷入在关于小镇生活的小说中常见的那种乡巴佬式的矫揉造作,在那种小说中,乡村设置如同一张沃克·埃文斯的照片。那些书中人物说话的方式就好像他们正为亨利·方达在《愤怒的葡萄》中饰演的角色参加试镜。对话恰是拉索先生的强项,这本小说的有趣之处在于听那些男人(和女人)讲话,互相刁难——他们幽默、反应迅速且别出心裁。(小说的氛围和其低调、自作聪明的角色一样。)
这些人物都有内心生活(在被巴斯,你不得不有),且一专多能。他们能把苦工和形而上的思考融合在一起:“也许铺夹板并非沙利最喜欢的工作,但和大多数体力劳动一样,它有着一种若你用心寻找就会发现的节奏……多年来,沙利所依靠的就是这种节奏,以及知道无论一份工作有多吃力不讨好、愚蠢或辛劳,都有完成的一日。时钟不会停止。”
和他笔下的人物一样,拉索先生触及到一些有趣的主题:改变与停滞,自由意志与义务,运气,责任,连结社区、友谊的情感纽带,以及家庭的宽恕。他带给我们对不同种类的人和人类行为恰如其分的观察结果……
在赞扬了这部小说后,我不得不说,阅读它并不总是愉快的体验。一些人物设置是个错误——例如彼得的花痴女友。临近结尾,我们感觉到拉索先生剪段并串接起情节线索。我们知道正确的节会打在何处。主题公园最终会建在别处,因为北巴斯的居民“看起来很奇怪,就像失败的基因实验”。但除小克莱福之外,无人在意。当苦乐参半的音乐在父子重聚的感人场景背后响起,我们即将退出这些人物的生活。最后的装饰音甚至把这种善意延伸到一只半瘫的杜宾犬身上:“它的小尾巴抽动着,带着——谁知道呢——也许是一丝满足”。
更有问题的是小说的长度。它并非不值得阅读,也确实包含许多情节:有人打架,有坏掉的卡车与破裂的婚姻,还有官司和死亡。但有时候这书要把人逼疯了:你想要用根大头针戳穿书页,然后看着那些次要情节漏出去。那些观察性的旁白和具有强烈效果的片段是书中最棒的部分,因此需要足够缓慢的节奏来容纳它们。尽管如此,好东西仍然太多了一点——太多关于次要人物的半自传式叙述,太多观点表达,太多在赌马投注点和小餐馆里虚度的时光。你会希望拉索先生在编辑他的书时能更狠心一些。
这使得阅读《愚人沙利》的体验有点像在北巴斯度日。大多数时候,你好奇且愉快,很高兴有机会偷听并审视这些人的生活。一段时间后,你开始担心自己不能活着离开这里了。但随着你离开的日子临近,你开始感到一种还未到时候的思乡之情——你会想念这座小镇,尤其是沙利——一边怀着爱意和遗憾四顾,一边加速驾车离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