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烨:小说最难的部分,恰恰在开始写作之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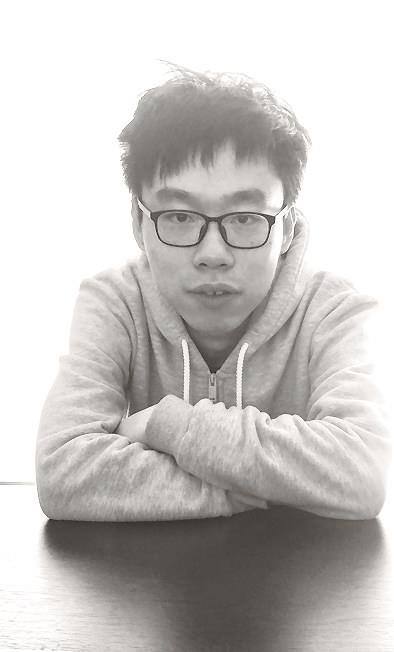
魏烨
在小说里编造故事、扭转现实,对某些写作者而言是一种巨大的乐趣,《西湖》杂志2018年第四期的新锐魏烨正是如此。“我之所以写小说,是因为我非常喜欢虚构。虚构的取材显得自由开放乃至混乱,小说涉及的经验漫布在作者人生的细碎角落里,藏匿在创作冲动之下,甚至构成创作冲动本身。”这一切吸引着他。
但魏烨的虚构并不是凭空想象,“无论你如何虚构,都需要材料的支撑,而这些材料不可能先验存在于你的大脑里——要么是从你的生活中直接萃取,要么是对其他文本的二手转化”。他的所有作品都基于现实,尽管很少在作品里挪用现实经历,但大多会从生活经验里提取某个元素,构成小说的起点。现实经历提供了他小说创作的一个口子。
因为如此偏好故事情节的发展,甚至是叙述下去的某种动力,魏烨的小说常常在一些关键情节上反复推演甚至推倒重来,有时甚至不得不停下来重新思考方向性的问题。魏烨自陈,这一切的缘由只有一个——“在写作中探索未知的事情”。
记者:不妨从虚构谈起。你说自己之所以写小说,是因为非常喜欢虚构,而你写小说的一个习惯则是只写想象出来的事情。这和很多基于生活经验的写作不同。为何是这样的?由此而来的一种担忧是,源于想象的写作何以持久?
魏烨:想象并不是空想,从我个人的认知来看,想象力是有很大局限的,经常会依赖已有的经验。只是我们平常在讨论这个问题的时候,往往会有所侧重,比如有些作家会用最切身的经验作为素材,甚至直接挪用记忆里的故事情节,让人可以从他的作品里直接窥测他的人生经历。这种写作侧重的就是经验。而侧重想象的写作,也只能从经验出发,只不过它更多的是去推导去试验,就好像我在打一个开放世界的游戏,我可以尝试各种各样的玩法,而不是走过去触发一段剧情。它的优势在于未知,时常会有超出意料的惊喜;而缺点也在于未知,我可能会推导出自以为是或索然无味的情节。
当然,你提到的担忧也是存在的。当我准备开启一篇新小说的时候,我往往得耗费大量时间,在脑子里做测试,就像爱迪生试灯泡的传说,试试这个元素有没有意思,那个人物能不能触动我,直到试出属于这篇小说的灯丝,然后天就亮了。至于说何以持久,就像我上面说的,再怎么想象也需要生活经验作为支点,毕竟灯丝也是客观存在的,如果我想要能够持续地尝试、持续地创作,那可能还需要收集更多的零件,这一点和注重经验的写作并没有太大区别。
记者:《西湖》上的三篇小说,从某种程度上可以窥见你小说的一斑,尽管熟悉种种理论及小说技法,但你似乎不以结构、叙事的炫技为要,小说的面目清晰、直接、敞开,更多的是在情节设计、故事本身上着力。
魏烨:因为炫技其实并不炫。我所能想象到的所有结构、叙事上技巧,都是别人原创的,经过二三四五手的转用之后,流入到我手中。
但我不是在否认结构叙事的重要性。巴尔扎克那一代就已经穷尽了所有情节套路,我们现在也是在不断重复,而重复的价值,在于你是否给套路注入了新的内容。结构和叙事也是如此,只要它能把内容本身的价值发挥到最大,它就是有效的。换句话说,炫技本身是为内容服务的。就我目前所写的内容,我看不到玩结构和叙事的必要,直接简单的呈现反而要更真诚一点。
记者:何焜说你小说的两座桥梁是幽默和荒诞,《虚度七种》可能更明显一些,但可能《热垫圈》更有代表性,因为它显得更含蓄一些。换句话说,你是在看似正常的故事里暗藏着这些玄机,由此就更意味深长一些。
魏烨:应该说不仅是特质,这些东西本身就是我写作的理由。就拿《热垫圈》来说,我之所以写这篇小说,就是因为经常听到人抱怨说冬天马桶圈太冷坐下去屁股凉飕飕,当时我就想,如果一个人早上起来坐到马桶圈上,发现马桶圈是热的,那是一种怎么样的感觉。我觉得这种感觉非常有意思,所以才有了写作它的冲动。接着我想到,这个人必须是独居者,否则一个热马桶说明不了什么。情节就开始向外延展了。
记者:这种幽默与荒诞之下,似乎隐隐有一种对人的生存的疑问,无论是《故居》里的一件微不足道的事情在网络发酵变异之下人被逼到绝境,还是《热垫圈》里的人的命运的偶然性,或是《虚度七种》里直接显示的人如何虚度时间,你小说兴趣的落脚点似乎还是人的生存问题。这和你对自身处境的思考是否也有关联?你想在小说里怎样解释人的生存本质?
魏烨:对我来讲,情节最根本的推动力,就是人的焦虑。我其实没有能力去写那种不痛不痒温吞水的故事。我写小说的时候,人物必须处于强烈的焦虑当中,他必须遇到问题,这个问题可能很小(就像垫圈发热),但却直接牵扯到他生活中某一个具体且坚硬的困境。而这个困境,很可能就直接来源于我自己的生活观察,比如说《故居》,它的直接来源就是互联网上弥漫的对于熊孩子的厌恶情绪,本来这可能只是一个很小的情绪,但在网络的煽动下无限放大。前段时间网上就有一些案例,有网友直接把网络上热传的那些对付熊孩子的方法付诸实现,结局可想而知。
但我得说,我并没有想在小说里面解释什么,这好像不应该是小说的功能。我之所以会写这些东西,纯粹是我觉得这些东西应该是吸引人的,起码是吸引我的。看到一个小孩往文物马桶里撒尿,作为管理员的我应该怎么办?这个念头一浮现,我就立刻代入了进去,并处在一种持续不断的焦虑当中。之后所涉及的网络传媒等事物,就是自然而然的事情。所以我没有在小说里解释什么,我写小说,反而更像是在寻求一个解释。
记者:这三篇小说其实是你研究生时期的作品,虽然这个时间也没有过去多久,但你暂时没有新作了。当然小说写作的断续都很正常,却有一种感觉,似乎你并不是不想写,只是在探索未知的路途里还没有下一个目标。
魏烨:其实并不复杂,就是过了一段时间总要暂停,整理一下。过去创作比较随性,冒出什么点子就写,有时候并不太好的点子也会尽量完成它,好处是练了笔,坏处就是永远处在一个很不稳定的产出状态,作品时好时坏。我现在觉得有必要沉淀一下,稍微在前期准备上下功夫,给自己摸索和建构一套稳定有效的写作思维方式。最基本的,就是如何寻找点子,如何判断一个点子能否诱发一个相对完整成熟的故事。我不想或者说不擅长直接挪用人生经验,所以有时候一篇小说最难的部分,恰恰在开始写作之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