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棣:我们欺骗了生活

导演、小说家唐棣短篇集《遗闻集》新书分享会“文字中的时间戏法”在南京文化地标——先锋书店五台山店举行。小说家曹寇、江苏文艺出版社编辑部主任李黎、《钟山》杂志副主编何同彬作为嘉宾与其畅谈了真实、虚构、时间、电影、现实等话题。唐棣在现场毫不回避写作的困境,并称所有没有困境的写作更值得怀疑。任何艺术的起点都是疑问。所以,这本书也可以叫“疑问集”,好像这就是他对与其诶事物的看法。
多年以来,他被大众认知的身份都是拍先锋电影的导演。3年前,电影处女作《满洲里来的人》一经推出就引来争议,很多人都在猜测这个不顾一切法则的家伙是谁?很多人也不屑于中国电影又多了一个“先锋派”。39届香港国际电影进行完世界首映之后,这种诡异的作者表达引起了《好莱坞报道》等媒体和电影节选片人关注。从此,唐棣被认为是国内最受期待的“作家导演”之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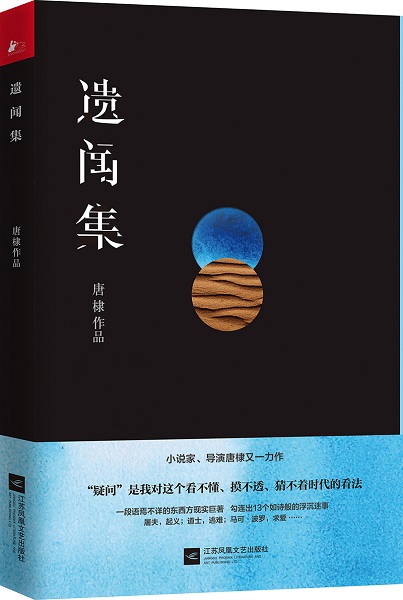
其实,他还有一个身份是作家。他从2003年开始写作,曾入选日本《火锅子》杂志评选“百名华语人物”,并且坚持与众不同的写作观念。在作者群体中,他也属于钟情于研究词语,以及语言的意义,诗人、散文家于坚欣赏其对语言的想象力,说他的“不同凡响之处在于,他的写作朴素而诚实,散发着土地、地方的灵气。与周围的时髦而媚俗的现代主义修辞不同。”
这些年,他在拍摄之余,不疾不徐地写作,不但成了香港知名文学杂志《字花》首位开设专栏的内地作家,还把自己工作中对电影的体会写成随笔,刊登在《人民文学》《书城》《南方周末》《新知》等报刊上,对新电影人影响力巨大。同时,他还出版了两本口碑不俗的小说集,他的小说和电影比起来一样,兼具现代与古典气质,难以界定。
关于电影与小说是不可回避的问题,他说得很轻松:“很多时候,都先把想拍的东西写成小说,我希望打破边界,没有谁规定小说怎么写,电影怎么拍。”
《遗闻集》里的作品都是唐棣从日常阅读和游历的生活里,采撷下来的片段,融历史、传奇、新小说、新闻调查与神话为一体,有东方的神秘,也有西方故事的诡异……创作时间最早的一篇写于2006年。著名作家孙甘露还记得当年这本小说的雏形,因此他说:“时间证明了他是一位致力于制造独特风景的作家”。
在南京先锋书店5月12日的分享活动后,我们坐下来,有了这次难得的会面,访谈内容围绕新作《遗闻集》以及他从事导演的各种故事。
Q:从你的故乡谈起,你是河北唐山人,对大地震有什么感觉,有写过这种大题材的东西吗?
唐棣:外界对我老家的认识是大地震,我对大地震的感觉来自身边的人,现在我们家那边也经常有小地震,年轻人逃跑时,老辈人通常没反应,泰然自若。有意思吧。这就告诉我们,经历过灾难的人很不一样,因为他们懂得如何度过灾难。
Q:如何对待虚构与真实?
唐棣:老家有个上班的朋友过年聚会时跟我说,部门领导让总结去年的工作,然而大家去年都没干啥事,于是他和这个领导玩笑说,我就写咱们坐了一年。部门领导平时和大家相处不错,他说,你要是写这个就别想干了。朋友反问,我说的不是真的么?同事们都知道事实就是如此。你看,我们从来都是欺骗生活的,我们想要活下去是靠某种意义上的谎言。在我们的世界里没有什么真实和虚假,我觉得好像都一样?
Q:你在小说里会植入这些思想吗?
唐棣:小说不是炫耀思想的。我们的真真假假就摆在那里。其实,谁都会想一些事,称不上思想,你那就是感受。我觉得,(写作)借机会抒发感受,大家还不觉得你烦(笑)现实生活中好难敞开心扉啊。
Q:很多作家的写作会创造一个“故乡”,那么这对你是一个什么概念?故乡对你的写作有何影响?
唐棣:其实就是图个方便,要不也要编其他名字,这个没有很多评论家说得那么有深意。这次的新书我就有意离开了马州啊,离开和不离开都没有深层含义。离不开,创造一个地方,不丢人,离开也没什么骄傲。所有的情绪、或文字,或人都在“故乡”背景上活动而已。其实,笔下的故乡无论是不是有意虚构,都和真实的不太一样了。
Q:童年,或者成长中的经验,对于写作者来讲,特别重要,很多细节都处于成长中的记忆和经验。但有些作家可以根据社会新闻去写作,你在写作过程中,您是如何在小说中处理生活中的间接经验的。
唐棣:之前,总面对这种可笑的质疑。八十岁就能写得好吗?我生长在一个塌陷区,很多湿地,各种各样的鸟,各种模样的鱼,我从小跟住在江南水乡没什么区别。我周围的人是纯北方人,比如我们这的人寻死一般都说跳水,而不是上吊,你说奇怪不奇怪?
Q:你说故乡人不避谈死亡,你有没有考虑过有关死亡的命题。
唐棣:我老家这边一般说“使了几个死”,在他们看来,死是可以使用的,功利而具体。我命大,溺水、被蛇咬什么的都遇过。采煤塌陷有很多地缝,时间一长,地缝会涌出水,然后形成湖泊。虽然,我没亲眼见过有人掉进地缝。但我想过很多次,是不是有人掉下去过?地下是否有很多失踪人的遗骨呢?母亲见过有人在田地浇水,不小心一脚落进地缝,然后用铁锹一撑就跳上来了。我从小活在冥冥中很多死亡的边上。
Q:你的小说和电影是否互相影响?
唐棣:我是有感兴趣的事物先写成小说,在找些人聊是否拍电影,但有时候写完,兴奋就过去了。经常这样的。这才让很多人觉得我还在写作,其实目的已经不是写作了。
Q:新书的创作初衷是什么?
我有个习惯是现在拍片,都经常想把感兴趣的写成小说,然后才和编剧聊剧本。对我来说,我必须把事物具体到我个人有快感的领域。有的小说就这么来的。有的后来写完小说就干别的去了,兴趣在写作中消耗光了。电影也没拍。
Q:这本书给人的第一感觉是学术研究,阅读之后才发现,一方面有严肃的知识,一方面又不断解构这些东西,造成一种有趣的故事。
这本书单篇来看写的时间很早,有的是将近十年前的作品,有的是后来慢慢写的。第一篇我记得是写西方故事,后来在阅读战争档案时发现有意思的点就逐步扩充,东方故事与西方故事本质上都是我在档案文件中挖掘到的一种“现象”。对我而言,它们很有趣,很神秘。
Q:你对短篇小说比较钟爱,短篇小说因为篇幅有限,艺术的爆发力要大等,我觉得短篇小说写好更难。
唐棣:看上去容易,做好都难。短篇是最包容的文体,我可以实验自己的想法,我没那么多耐心,可能是拍电影这个工作的原因,环境的问题?我的阅读很大程度上都毁了……也就是我没有具体项目很少看小说。这次的新书是文学的东西,我做了很多指东打西,指鹿为马的东西,挺知足。
Q:我看你的小说越来越强调先锋性,但这些小说如果从文学史中的技术角度来看,前辈也用过这种方法,也就是说,你的写作也受到过之前先锋作品的影响?
唐棣:我大部分读者可以读到的作品都很难懂,选刊和评论基本无视它们,所以基本上我会被误解成一个高深的人,影响无处不在吧,不仅是先锋小说。
Q:先锋小说在很多人看来,把路已经走死了,一方面先锋小说的技术创新很难,前辈几乎都练过了,另一方面,先锋小说的读者已经萎缩的很小了。小说会不会走到尽头?
唐棣:故事的话也许会讲到尽头……这个话题可能有点大,不过你想想,灵魂属于人,而人写了小说,小说连接了这些我们看不见,但的确影响我们的东西。小说的未来,媒介可能会变成别的,而不再是纸。这个问题也是在说书籍的消亡问题。不是先锋小说读者少了,是看书的人少了。这样做的人现在就被认为是傻。傻得可爱。有什么办法呢?这是阅读的困境。
Q:你是否承认自己是一个形式主义者?或者说有时候形式有点大于内容了?
唐棣:形式对我来说就是内容,或者是走在内容前面的,形式也就是结构,如何安排句子与词语是我写作的动力,而故事我并不可能完全剔除,如果可以的话,我不希望写任何事。但往往有了人物就有了故事。我如何把这个故事告诉你就是一个技巧问题了。
Q:你这本新书创作受过什么作家或者书籍的影响吗?或者给大家推荐几本书。
唐棣:我们平时被人牵着鼻子走的地方太多了,读书就是读自己的吧。如果非不相信自己,也不要相信我这种作者说得话。对一本书的影响肯定不是我说得上来的,有人说它像《看不见的城市》之类的,听听就算了。我觉得说不清、也可能是太多东西,不仅仅是书籍影响过我(写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