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佳楠:教创意写作,就像工程师把家电拆解再组装起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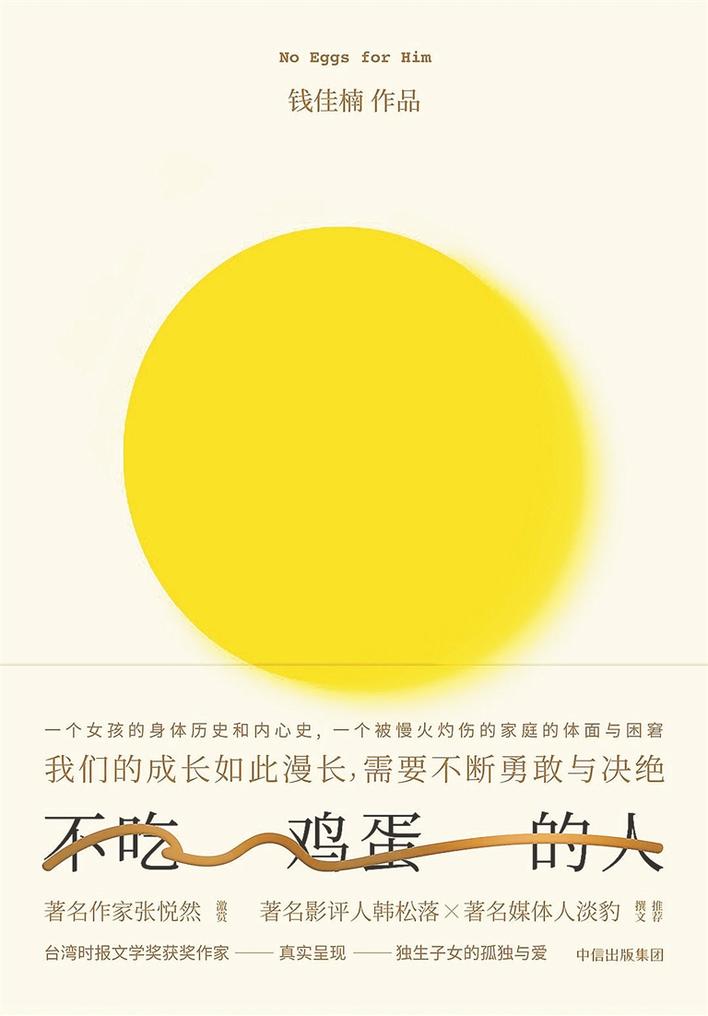
钱佳楠作品两种 《不吃鸡蛋的人》 大方·中信出版集团 2018年1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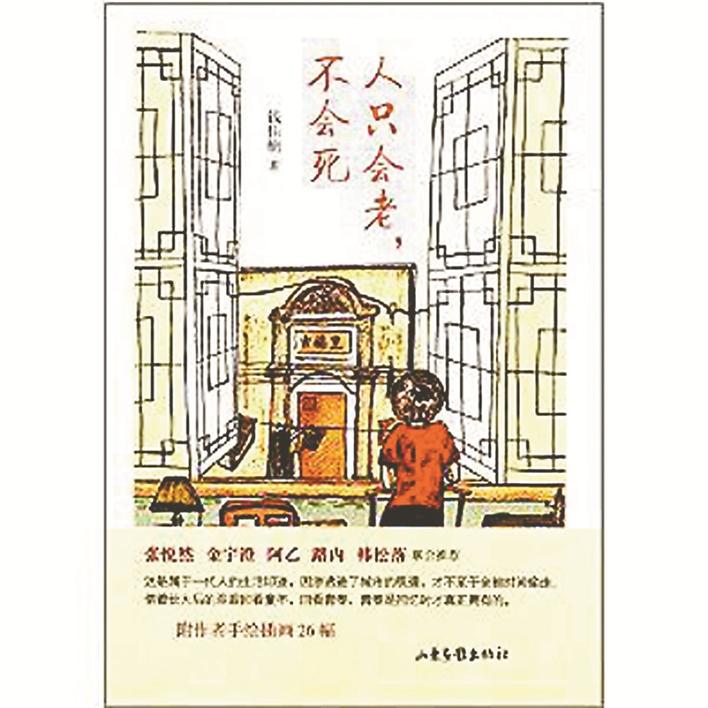
《人只会老,不会死》 山东画报出版社 2014年8月
钱佳楠,1980年代末出生在一个再普通不过的上海工薪家庭里。那个时候还没有显著的贫富差距,读小学的时候,钱佳楠最羡慕的是一个同学可以有自己的房间——其实不过是一楼的天井被同学爸爸封了起来,便算是有了一间独立的卧室了。
和大多数中国家庭一样,钱佳楠从小就被父母告知读书可以改变命运,虽然当时并不懂得改变之后会是何种模样。但钱佳楠算是比较幸运的读书特别好的孩子了,所以相对而言在学校和家庭里都得到了充分的自由度。
说到文学的启蒙,钱佳楠最感念的是她的爷爷。
其实在读大学以前,她从没有想过自己会写作,会成为作家(虽然她的作文常常是语文老师拿来评讲的“范文”),即便进了复旦中文系,她在大一那年都还在忙着转学去新加坡读商科(结果因为微积分成绩低得可怜而失败)。
而爷爷的书房成了埋在钱佳楠心里的一粒文艺种子。钱佳楠的爷爷是整个家族里唯一的大学毕业生,他从事物理学研究,他的书架上有很多科学类书籍,但爷爷又是一位狂热的“文艺老年”,他有《芥子园画谱》,有各种诗话,唐宋八大家文集……钱佳楠记得,小时候只要一去爷爷家,就会找一本将唐诗与唐代绘画联系起来讲解的《诗与画》的书来读,这对小佳楠的心灵是难得的文艺滋养。除了阅读,爷爷还教她习书法、国画、舞剑,这样的“艺术之旅”无论最终能走多远,都将影响她对文艺的感受。
或许正是有了这样的启蒙,钱佳楠开始对事物的本质有所观察,进而理解。当年她所获得的复旦大学望道传媒奖的作品《西村外》,便是她自己对于家族关系与人性的一次反思。今年新出版的长篇小说《不吃鸡蛋的人》也同样展现了一个家庭的体面与困窘下的个体命运。
目前,钱佳楠正在美国爱荷华作家工作坊学习,我们的访谈也从这个工作坊开始。
用英语写作
让我重新变成孩子
晶报:你目前正就读于美国爱荷华作家工作坊,能介绍一下这个工作坊吗?
钱佳楠:这是全美国(也是全世界)首个创意写作项目,因为历史悠久,所以众多杰出的美国当代作家都毕业于这个工作坊,弗兰纳里·奥康纳、雷蒙德·卡佛、丹尼斯·约翰逊等等。所谓的“作家工作坊”得名于我们评议小说的方式,就是我们每周都需要阅读一两个同学的作品(有时是我们自己提交),然后给出意见和建议,再在课堂里讨论。引领讨论的老师本身都是出色的作家。
我的经历迥异于我的同学,这个项目非常美国,而我,作为非母语写作者,无疑是工作坊里英语最烂的人。我不知道该怎么介绍自己学习的情况,研究生没有成绩等级,当然成绩也是非常中国式的衡量学习的标准。我有了很多内心的收获,因为用英语写作,我了解了很多东西方文化以及审美的细微差异。
晶报:在这个评议小说环节里,你所提交的作品是否会区别于你目前的风格?或者说仍然会有中国的元素。譬如上海的家庭关系。
钱佳楠:美国人喜欢说每个作家都会发出自己独特的“声音(voice)”。按照这个表述,我在英语中的声音和我在中文里的声音完全不同,我几乎不写上海的家庭关系——正是因为我希望自己触碰多样的题材才会做出要用另一个语言强迫自己改变的决定。我该如何形容我用英语写的小说呢?这么说吧,在我的第一个短篇集《人只会老,不会死》里其实有异常丰富的元素,既有写实的作品,也有天马行空的狂想,而后批评家以及读者都选择性地看到前者,而我也不知不觉地丧失了“实验”的勇气。用英语写作的我因为重新变成了一个孩子,也重新拥有了玩的热情和愉悦,所以我目前没有固定的风格,我有写实的作品(但不再是写上海),也有奇幻的小说。它们有一天会出来见人的,只是现在还不是时候。
晶报:创意写作课程目前是你研究的项目,你会如何定义创意写作?
钱佳楠:其实所谓“创意写作”,只是和“学术写作”区别的“文学性写作”而已。从这个角度看,我所有喜欢的文学作品都应该是创意写作的好例子。
晶报:你在这个作家工作坊里,还有教书任务,你是怎样教书的?
钱佳楠:我教书面向的是从没有过文学性习作基础的本科生,所以我会每周要求他们阅读小说和诗歌,而后我们从一个文学维度(比如叙事角度)来讨论。同时,学生也要求提交他们的作品,而后我们一同品评。
晶报:如果让你给中国的读者讲一堂创意写作课,你想教给他们什么?
钱佳楠:我会教如何从写作者的角度从文学作品中汲取营养,这个过程就像工程师把家电拆解再组装起来的过程,其乐无穷。
晶报:说说你在美国的生活吧,是否和你期待中的一样?
钱佳楠:说实话,我没有期待。两年前决定去美国读书,更大的原因在于我迫切知道自己必须离开,所以爱荷华提供给我一个机会。
我有过很多对于创意写作项目的怀疑,对于写作技巧的怀疑,这些怀疑仍然在,但我更明白怀疑是可贵的,尽信书,则不如无书。也明白不应因为怀疑就抗拒学习的过程,因为不去学习,不去实践,自己只会停留在一个美化了的肥皂泡里,成天做着白日梦。我喜欢美国的生活和用英语写作,它将罩在我身上的肥皂泡无情戳破,我必须看清自己的渺小与简陋,然后告诉自己必须通过学习和实践取得进步。
晶报:用英语写作更容易融入美国文化,听说《纽约时报》刚刚推荐了你的一篇文章。
钱佳楠:这篇文章是我谈东亚与西方叙事模式差异的长文随笔,从谷崎润一郎的小说《钥匙》和同类型西方小说的差异谈起,东亚并没有西方那样讲求人物的“觉醒”或“转变”,我们倾向于将冲突内化,同时谈到这如何影响了东西方小说的结构和审美。《纽约时报》的编辑说,虽然题目很大,但因为作者精心选择了例证,所以不仅有趣,且发人深省。
反复摸索反复确认的成长是亲情很难给予的
晶报:来谈谈你的作品吧,你的新书《不吃鸡蛋的人》讲到了中国家庭关系,它既有家庭伦理的反思,也有爱情的元素,两者间你更看重哪一个?
钱佳楠:对我来说,复杂性是小说应当具备的美德。我看重这本书中爱情的部分,仅此而已。
晶报:书中主人公周允的爱情观对一代人来说是否有代表性?她对待爱情的态度和方式是消极的吗?
钱佳楠:我不知道,我所知道的仅仅是我们生活经历上的重合点,比如都收集过奇多圈,吃过小浣熊干脆面,都被父母带到城市的地标性建筑前比出“剪刀手”拍照片,至于这些相仿的生活经验会如何作用每个个体,我无法一概而论。我写的时候,只考虑周允个人,她的爱情经历,而她的爱情故事有多大的代表性,那或许需要社会学学者来谈论。
第二个问题,若只谈周允,我不会用积极或消极这种二元对立的方法来看待她的选择。我写的时候只是关注她的难,难一方面来自她的家庭企图操控她的人生,另一方面来自她对这种操控的忍让和默许,在这个过程中很大程度上她没有爱情。而小说中的爱情真正到来的那部分实际上也促成了她的改变。
晶报:说到“80后”这代人,你觉得亲情、友情与爱情,哪一个更能影响自身的成长?
钱佳楠:很难说哪一个,每一个都会给个体带来不同的影响。C.S.路易斯曾经说过人类有四种形式的爱:亲情是联系相似人群的感情,友谊和爱情则是个体与个体之间的联系(也被路易斯视作最高尚且难得的情感),此外还有身体欲望和邻居之间的关怀。
借助路易斯的分类,我会认为亲情在某种程度上给予一个孩子最初的爱的可能,他可以从父母之爱那里懂得他作为一个个体是值得被呵护和疼爱的,也是这种爱给了他勇气去面对这个世界。当然,因为是相似人群之间的纽带,且是非个体所能决定的天然纽带,这种爱时常会变相延续这种“相似”以及“自然法则”,从而成为了阻止个体成长的强力。
友情和爱情,我会放在一起看,这是个体与个体的碰撞,是和陌生人建立联系的过程,这个过程是双向的,也就是说,我在交朋友的过程中也通过朋友确认自己——我喜欢什么,我是什么样的人,我和他人打交道的时候什么是能够被接受的,什么不是……这种反复摸索反复确认的成长是亲情很难给予的。
晶报:当你写到母亲在做脑手术的前一晚,女儿周允在神面前提出交换条件一节时,很感人。这里的神是否也映衬了个体的无助?
钱佳楠:对。这是一个人在最无助的情况下的最后一搏,倒不是周允有什么信仰——其实她并没有,和不少中国人一样,她对神的理解充满功利色彩。正如我们常看到类似的报道,某个高校教授为了治妻子的恶疾竟然会相信江湖郎中的骗术,这样的故事本身不符合现实逻辑,但是一旦人陷入绝境,情感的逻辑会发生很大的转变,就使得这样的故事比现实逻辑更“真实”。周允也是,小说前面已经铺垫了,她别无他法,亲戚是靠不住的,父亲是没办法指望的,她实际上也一无所有,她看到的就是家里摆着的一张卧佛照片,想到自己拥有的也就是才华和爱情。
晶报:拥有才华与爱情不应该是件幸福的事吗?
钱佳楠:我不相信一个人因为个体成长,找到自我,就一定会幸福,又或者一个人永远生活在亲人和爱人的庇护里,就很可怜。不是这样的,后者可能会比前者活得更顺心,更快乐。命运有很多无法解释的东西,简直像黑黢黢的深渊,我们常常说“碰上了就是碰上了”,没道理可言,一个一直顺风顺水的人可以在人生的某一刻一无所有,这可能就是命运。
我思考更多的可能还是,既然命运很大程度不可控,为何还要成长,要找自己?这更多的是我对自己的要求,我从来不以此要求别人。我会敬畏命运的不可知,敬畏人生的有限,个体的有限,从而希望自己在自己尚能腾挪的空间尽可能舒展,成为自己想要成为的自己。
晶报:在小说里,亲情关系是功利的,并且父母对于子女都有掌控欲。这也确实是一代人正在面对的伦理问题。
钱佳楠:亲情,尤其是小市民的情感是很真实的一部分。或许我们时常有一种呼声,希望感情要单纯,希望人与人之间要真诚,但是现实不可能这么纯粹的。我记得我的高中时代曾一度风靡张小娴的情感书籍,有一篇文章是她反驳“爱一个人不需要理由”,她说不是这样的,已经有无数先在的条件(相貌、文化背景、相似的爱好等等)决定了爱情的发生,拿掉了这些之中的部分,爱情会摇摇欲坠。类似的,亲情也避免不了掌控欲,避免不了功利心,因为人本就有自利的趋向,人的情感自然也有。
晶报:所以才有周允这样一位乖乖女的形象,有对家庭的隐忍?
钱佳楠:周允的性格决定了她的屈从——但我们不要用好坏来界定,她的隐忍里面有她体察母亲辛苦奔波的善良。
我认为儿女去体谅父母的难,去照顾父母是特别好的,闪烁着人性的光辉。只是这种爱或许也需要有一些个体的边界,孩子毕竟是独立的个体,他们有他们不同的人生轨迹,这一点也应当被理解。
“失败”的经验让我意识到自己的局限与浅薄
晶报:从你的上一本短篇小说集《人只会老,不会死》中,就能读到你的语言冷静的风格。你在生活中也是个冷静的人吗?
钱佳楠:关于作品里的“冷静”,是一下笔,自然而然形成的。是的,我的温度本来就是低的,可能和我这个人的性格有关,热络不起来,更喜欢隔岸观火,觉得这样安全,舒适,久而久之,文字也成了这副模样。
晶报:从短篇到长篇,你做了哪些转变与努力?
钱佳楠:我有做很多努力,但这些努力或许需要在我以后的作品里才能体现出来。
短篇集出版之后,我最大的恐慌就是自己把生活经验消耗殆尽了,今后写什么?这种恐惧混合着当时生活的安定和狭隘让我更感到必须去探索更广大的社会场域。所以我有去采访和我有相似经历的世纪之交的下岗工人的孩子,原定要采访一百个人,结果就采访了约四十个人,我尝试给“网易·人间”写非虚构作品,之后参与一个在地的艺术实践项目——定海桥,这是上海市区内最破敝的社区,我在那里试图开一个老年人的创意写作工坊,结果意识到自己脱离实际的理想主义。但是这些“失败”的经验于我有益,都是让我意识到自己的局限与浅薄的方式,也促发我做出彻底出走的决定。
晶报:这样的长篇写作,又给了你哪些体验?
钱佳楠:这个长篇还是很不同的,因为这个作品源于迫切的情感抒发,所以看起来我写了一个小长篇,其实我的写作方式还是短篇的方式——希望一鼓作气写成。只不过因为篇幅长,所以我必须夜复一夜地重复这个过程,依靠着内心的激情烧灼年轻的身体,写成,修改,然后文稿搁在抽屉里三年。
如果让我回头做一个小结,我会说因为我的写作方式没有完全区别于短篇,所以有了这本书中不少的遗憾,比如情绪没有得到遏制,比如节奏过快,比如“十年前”和“十年后”叙述口吻的差异。所以这个作品并不奢望艺术上的完美,而只在用这种情感“动”人,无所谓“化”人。
晶报:你也是从复旦大学中文系毕业的,那里培养了许多青年作家,你会阅读他们的作品吗?
钱佳楠:进入复旦中文系是件很幸运的事情,我在那里得到了雨露滋润。但我不会因为“复旦”这个共同的身份,就会对其他作家更青睐或者更苛刻,作家还是凭作品说话。就我有限的阅读经历,我非常喜欢周嘉宁和张怡微的作品,两个人的风格是迥异的,周嘉宁的世界更像是对现实的抽离,而张怡微则从不避让对人情冷暖的直面。
晶报:哪些作家对你产生过影响?
钱佳楠:在我刚开始写作的时候,日本作家芥川龙之介完全颠覆了我对人性的固有看法,现代作家废名则一度让我探索诗、散文、小说共融的可能。之后可能是墨西哥作家胡安·鲁尔福,他为我展现突破人类世界边界的方式,以及日本作家川端康成,他为我重新定义了“美”作为小说超越性的价值。而最近,作家带给我的震撼似乎不再是美学意义上的,而是他们的思想,眼界以及实践,我再次迷上了法国作家加缪,他对人类命运的观察和见解不仅是深刻的,而且给后来人无尽的力量。
晶报:在一部作品完成之后,若让你送给自己一句话,你会说什么?
钱佳楠:我目前仍然想继续用英语写作,在另一种语言里,因为困难重重,我会更希望用黑泽明的话来提醒自己:登山的人不问峰顶在哪儿,只盯着脚下的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