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批评:困境与微光——从“微光”丛书谈开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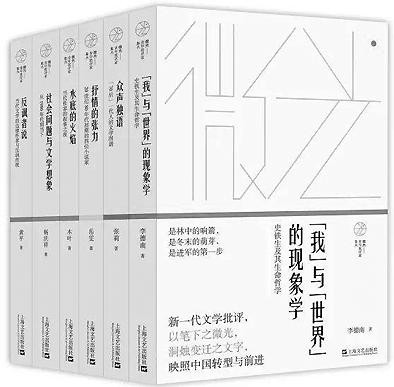
出版提要:“微光”丛书最大的特点,就是收录了很多不是文学批评的文学批评。就像“总序”里引用韦勒克的说法,把文学理论和文学史研究,都包罗在广义的文学批评之中。这是一个开放性的文学批评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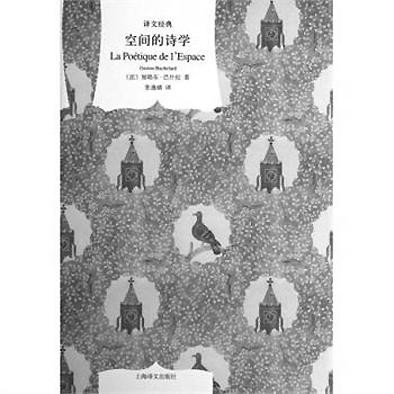
加斯东在《空间的诗学》里营构出来了一个震撼人心的画面:在城市的沥青地面上,清道夫挥舞着扫帚,收割想象中的麦子。在今天的语境下,以文学为志业者大概也有点这位清道夫的感觉。
主持人:陈华积
参与人:杨庆祥 金理 黄平 王德领 杨晓帆 赵天成 李蔚超 樊迎春 陈若谷 朱明伟 刘欣 邵部 周晓
一
陈华积:非常荣幸可以主持这么一场阵容强大的文学批评会议。先请这套“微光”丛书的策划人金理为我们做一个介绍。
金理:虽然不是东道主,但作为策划人,还是感谢各位捧场。我希望大家给我们一些真挚的建议,在往后继续操作体例、入选人员上都可以给我建议。所以,一是表达感谢,二是听听大家的建议。
赵天成:回到我们的主题“文学批评:困境与微光”上来谈。当前文学批评的困境,不是一个内部性的问题,而是一个外部的,比如文学批评与社会问题的关系问题。所以,文学批评的问题,实际上无法从文学批评本身看出。“微光”这套书给了我们一个很好的启示。这套批评集最大的特点,就是收录了很多不是文学批评的文学批评。就像金理在“总序”里面为这套书所做的逻辑维护,他引用韦勒克的说法,把文学理论和文学史研究,都包罗在广义的文学批评之中。所以这套文学批评集,也是一个开放性的文学批评集。这一点很有意思,而且我发现,这六本书里让我印象最深的文章,都不是严格意义的文学批评,至少不是现场批评。我意识到,从事当下批评的人,需要用文学史的作品和问题作为对象,才能够形成有效的对话,这一点可能是上世纪八十年代出生的批评家和活跃在八十年代的批评家的最大区别,而且这种区别是根本性的。我们看八十年代的批评家,李陀、黄子平也好,程德培、吴亮也好,他们当时的争论和对话,都是以正在发生的文学作品和问题来展开的。而且他们这么做的时候,是有强烈的尊严感和幸福感的,他们相信他们所做的批评的意义。而我们八十年代出生的人,包括我,需要退回到文学史中才能开展对话,这里面已经透射出当前文学批评的某种困境,就是我们很难在当下的现场中直接对话。这是批评的困境,但一定不只是批评的困境。那么我们如何找到“微光”去穿越这种困境,我想这套书里的每位作者,都以他们各自的方式指认了困境,并积极寻找改变的方式。他们尝试性的解决方式,是以自身携带的问题,来激活他们的阅读,用杨庆祥一篇文章的题目来说,就是他们“似乎都有余力再造一个世界”,就是他们会把阅读的对象拉到自己的世界中去,而不是像传统意义上的文学批评那样,进入到文本自身的系统中去评价和阐释。我认为这套丛书给予我最大的启发,就是它提示了不一样的一种批评姿态,出路可能恰好就在于此,在于“似乎都有余力再造一个世界”的“余”上面。竹内好曾经借用芭蕉的话评价鲁迅,说争论之于鲁迅,是终生之余业,它的悖论性,也是现代性(或说未来性)在于,它既与生之根本相关,同时又随时都可以放弃。严格意义的文学批评,对于这套丛书中的作者来说,可能也是一种“余业”,是有“余力”的时候才去从事的事业。而如果说“以文学为志业”是一种姿态,“以批评为余业”可能也是一种姿态,就在这种既与根本性相关,又随时可以放弃的悖论之中,可能产生出一种不同于传统,又可开启对未来的想象的文学批评。
金理:我先回应一小点,从编辑体例上来说,刚才天成确实很敏感,我在策划人语中有那么一句,“为什么在一套以批评为名义的丛书中收录了那么一些不那么合乎我们对现代批评认识规格想象的文章”,其实从我个人来说,我自己心目中所认定的文学批评,应该是“同代人”公众号上面的那些,就应该是站在第一线的批评。那我为什么在以批评为名义的书里面收录很多史论方面的文章,是因为我想为第二辑做一点铺垫。
王德领:我从宏观上来谈谈批评的现状。八十年代的批评在我们现在看来可能会存在一些问题,但是它的“激情”,和对当前作品的一种热情,是值得我们关注的。而我们当代的批评往往是对作品有一种知识化的处理,引用了大量的材料和大量的知识来进入文本,对自己生命体验的呈现较少。我所理解的批评,既是对作品的发言,又是对个体生命的介入,而且和我们自身生活和自身生活以外的社会相联系。为什么从新世纪以来,没有一个作品中的人我们能够记得住?因为主人公消失了。即是因为有一种主体性没有建立起来,一个虚无的人走到现在还是虚无的。如果我们从一个建构的主体来说,我希望可以看到这种有力度的批评。再则从批评的文体来说,我觉得,鲁迅的题材有很多我们可以借鉴的,比如童话体、寓言体、广告体、书信体、人物志、演讲文章、标题连在一起的文章等。我们的文学批评缺少趣味,可能和个体写作有关,这会影响到行文风格。我们现在的批评还是应该有文体化、风格化的,从其行文风格就能知道是出自谁之手。一个优秀的作家是这样,一个优秀的批评家也应是这样,应充分风格化。因为借鉴西方理论太多,容易将论文写成一种非常程式化的东西。文学批评的文字也可以超出我们常规的批评文字,让读者读起来酣畅淋漓,而又不缺乏思想、形象、生动。大批评家应该是有气魄、有格局的。为什么说现在的批评面临困境呢?因为我们的批评家还没有展现出极大的才华。为什么有的作家对批评家不以为然呢?如果文字中自己的思想、热力、生命、观点、穿透力不足的话,就不会让作家服气。现在的作家是很有水平的,高学历的,读过很多书,如果我们的批评家对对方没有征服力的话,我们的困境就很难走出来。
杨庆祥:现在的批评面临的问题主要是体制化,C刊有严格的标准,博士论文也有严格的规范,许多条条框框去规训你的文章风格,最后,好文字都是非体制内的批评家写出来的。八十年代的时候规训没有这么严格,出来许多好文章,现在的规训越来越严格,制度化层次化,做不到不能发表,不能评职称。
李蔚超: 我年初正好看了贺桂梅的《批评的增长与危机》。她梳理了九十年代文学批评的转型,九十年代是一个批评的时代,2000年以后,大家就开始做史料的研究。现在,金理很敏感地抓到了文学批评的变化。这套丛书收录进的评论家,不管是在学院,在刊物,还是在一些体制,有多重的面向,写出来的东西,意识也不同。“微光”真的扩展了这种可能性。
有一个比较特别的命题是回到文学本身,这是我们八十年代的一个口号。而回到事物本身是现象学的口号。所以从李德南《“我”与“世界”的现象学》这本书,我重新意识到“重回文学本身”这个八十年代口号的策略性和目的。现象学鼻祖胡塞尔有一句特别经典的话,你一旦用现象学的眼睛来看待世界,世界的一切都会是新的。我们重回文学本身,也是为了去除一切偏见,来重新看待。所以我从这里看到了回到文学本身的一个有益的目的和这个目的本来的可能性。
二
樊迎春:谈及困境,我个人觉得当下批评的问题在于所阐述内容、所表达问题的重复和单质。我们常用的方法是对名词与概念的谱系追溯,对传统与既有风格的全面铺陈。比如讨论一部作品的写法,清新自然的必说沈从文汪曾祺传统,闲适流畅的必说笔记体小说小品文,讽刺酷烈的必说鲁迅精神;讨论一部作品中的某个人物,必定要找出文学史上的对应者,农村青年进城必说《创业史》里的改霞,青年困惑与时代问题必说《人生》里的高加林,民族性格或批判必说鲁迅的阿Q……当然不是要完全否定这样做的意义,这种文学谱系的勾连有其重要的价值,但这更多的似乎是作家的工作,对批评工作者应该有另外的要求。我们谈论反讽传统、抒情传统、史诗传统,文学史的创作中有这些传统吗?当然有。重要吗?当然重要。但同时,我们应该认识到这也始终是批评者的建构。我们在当下做批评,在追溯概念与谱系之外,是不是应该更多地观照“当代性”?观照文学的叙事主体与当下现实的互动关系,观照他们对于此时此刻的人类精神与困境?单纯地将作家作品放进某个传统某个谱系,这可能是一种文学史研究的焦虑,焦虑之外我们或许可以问一句,批评的“问题意识”在哪里?做谱系梳理与概念溯源的诉求是什么?我们如何在文学作品与此时此刻此情此景做有效的勾连,如何完成文学批评本身的价值构建?与其重复概览文学史的概念和风格传统,批评本身的知识谱系,其定义、价值、发展、旨归或许更值得关注。
另外可以讨论的问题是“可能性”一词。我们在批评现场和批评文章中经常见到批评家说“某某的写作带来了某某创作一种新的可能性”,“某某问题是当下文学创作某某方向的一种新的可能性”。之前曾关注另一个常用批评话语,即“这不是某某一个人的问题,而是某某一代作家的问题”,我们在梳理和总结问题时,总是特别容易被“总体性”的概念诱惑,代际的问题、共同体的想象、文学史的定位等等,我们已然共享了时代的荒诞与虚无,该做的不是继续放大和总结这种共享,而是在个体的经历和守望相助中寻求出路和突破。在文学批评中,批评的任务也应该是试图去打破“共名”的魔障,为作家与作品寻找新意,与当下互动。所以同样可以问的问题是:“这种可能性是什么?”当然,文学的魅力更多的时候在于不确定性,即我们永远没有正确答案,永远不知道文学能呈现怎么样的多样性与丰富性,但值得追问的是批评在既往的话语中如何为“可能性”找到能够打开和阐释的空间?比如岳雯这本书中具体写了四位作家的抒情:王蒙的抒情与革命的关系,张洁的抒情与现代化想象的关系,张承志的抒情与人民的关系,汪曾祺的抒情与人道主义的关系。我们能否在“革命”“人民”这样的大话语之外给岳雯自己总结的“可能性”找到位置和空间?这种“可能性”具体是什么?或者这种可能性代表的方向与着力点在何处?我们当然不是要具体的答案和表述,而是希望对批评做更为有力量的推测和展望。
当下批评何在,当下批评何为?当下批评应该承担更多的责任,应该更多地回应我们这个时代的创作困惑与人们的精神召唤。
杨庆祥:这确实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我最近在写梁鸿《梁光正的光》的评论时,就犯了迎春的“错误”。不是说犯错误,而是说我没有办法处理这个人物。当下批评有两个问题,一个作家如果真的提供了一个全新的人,批评家就必须创造或发明一个新词来命名,但是如果他没有提供这样的人,那我们就只能做谱系式研究了。比如我把梁光正的谱系追溯到梁生宝,算一下年龄,梁光正恰好就是梁生宝的“儿子”。但我想讨论的是现代性对农村的想象,我觉得我们对农村的想象一直是程式化的,没有把中国农村的变迁写出来,从鲁迅、赵树理一直到《创业史》的谱系其实有问题。最近十年我们怎样重新想象农村,这是个很重要的问题。
我觉得我们有一些很重要的传统被放弃了,比如我们会从尼采、海德格尔或福柯的谱系去谈作家,但我们从来没有想过从俄罗斯的文学传统去谈。比如别林斯基、车尔尼雪夫斯基、赫尔岑,你看看他们对俄罗斯的评价,他们的评价是带着血的,真的是鲜血淋漓的那种东西,它和他的命运是勾连在一起的。知识性的东西在今天被我们强调得太多,而生命性的东西太少了,生命性的东西没有就会唯谱系和史料是从,谱系和史料对于文学研究和文学史的书写来说是非常必要的,但对于批评来说就会有问题。
黄平:关于这一点我有不同意见。我觉得我们应该回到历史,有时候看不出来是因为没有真正回到历史中去。如果我把我的孩子关在门后,问你他未来会成为什么样的人,你肯定要说把门打开看看孩子才能知道。这是一个基础性的东西。
陈若谷:作为处在知识获取和学术生产生态链条底端的博士生,我还真觉得我们的文学批评是过于热闹了。我自己不喜欢评论者以展望某种“超越的”“可能性”做结语。就好像一个人自我介绍说爱好是旅行、美食、阅读,这几乎说明他一无所长。因为没有一个词被落在了实处。在当代文学和批评里,我们讲述的是自己的生活和命运。举个极端的例子,看古代小说里有张竹坡、金圣叹的点评,批注式的,写一个“极好”,这个主观性太强,会写字的人都会,我还会呢。我们的当代文学批评涵盖了诸多视野,有充分的学理性。批评就是要先进入浩如烟海的文学作品里,还要浸润过各种文学史以后,才能和它们较劲,这就是批评的当代性和切己性。
我觉得文学史压抑了批评的活力。或者说,我接受的大学教育有问题。我们先学了各种文学史,然后学批评理论,然后才开始作品精读。而文学史,刚才金理也说了,记录的都是十几年前文学创作和文学批评互动的过程和结果。我们的文学史关注的是十几年前的现场,文学史为了全面会刻意让自己滞后。比如陈思和先生提出的“共名”和“无名”打开了一个新的视角,成为了许多新研究的增长点,但1999年出版《中国当代文学史教程》之后,他的一些基本框架却面临不断被颠覆和修正,成为了一种新的遮蔽。所以我的思考是,这套丛书,出齐以后可能也会形成新的文学史叙述框架,有些书目已经显示了构建意图,比如讲反讽传统的、抒情传统、社会问题与文学形象。进入到了“传统”里,也几乎要具有新的文学史的面目了,其实并不是更安全,而是可能面对更多的重新评价甚至批判。理论上说来,这几乎是一种宿命吧。
朱明伟:首先我不觉得文学批评有困境,而当代文学史研究才有困境。文学批评的困境只是文学史研究焦虑的投射。无论是刚才各位对当代批评的争论,还是杨庆祥老师谈及的自己写梁鸿的批评,我们发现文学史的谱系都是渗透在他们的无意识中的。所以文学批评的“困境”是:好的文学批评必须与现在的、未来的文学史研究发生对话。我要重提徐刚的一个发言:“文学史研究要有文学批评的锋芒,文学批评要有文学史研究的后路。”我认为如果“困境”的判断成立的话,那它其实是任何时代都存在、无法解决的、批评者对于同时代人创作回应的焦虑。
三
杨晓帆:回到自己对于困境的理解,我觉得参与型的危机有两个方面。其实“70后”和“80后”在时代中的位置是相似的,我们并没有登场就已经没落了,在社会中找不到自己的位置。我之前说过最大的危机感是意义感的危机,一方面是我特别认真地活着想找一个意义却找不到,我从所有作品中得出的一个感觉叫做“败而不溃”:这个失败是注定的,只是溃烂的姿态不要显现出来,尽量有尊严地败下来。但如果不从这个时代中的位置来讲,另外一个参与性的危机,就是庆祥说的体制的问题,我们这一代人的文学教养和背叛。我们这一代的文学教养是从体制里规训出来的,在文体知识方面会有很多束缚,我现在从这个规训里进入到我的工作状态上,我会对整个学科专业化的东西极其不满,它的悖论就在于我不能融入它教养我的这一套东西,今天我又想在这里完成一个背叛,这个背叛的过程是很困难的,要怎么找到自己的一个突破点?我特别喜欢金理在序里说“微光”是两个很有悖论性的解释,一个是黎明前划破黑暗的那一束光,预兆着这一天会慢慢地亮起来,但另一个是烛火,烛火是慢慢在熄灭的。我们最基本的方式还是怎么突破个人,到个人之外去又想避免抱团取暖,那我们怎么样到个人之外去寻找怎么样的方式?可能我们进入的角度不一样,但我们在做的都是希望把个人困扰变成社会公共性议题,这两者之间的中介是文学,还是像庆祥说的“文学想象与社会问题”,只能通过文学想象的方式去触碰社会问题,但这个困境本身就已经决定了我们现有的途径。
所以现在我不喜欢的批评其实大都是现象式和症候式的,这会带来困境,伟大的理论家都是以作品为中介,当然这个作品要能给你中介的可能,所以这不见得是一个好作品,我们当下没有那么多可以承受如此思想重量和社会公共议题的作品。如果没有,那么批评家就只能借助它去谈自己要谈的事。所以不是作品问题而是理论建树可以打开多大的视野。一个问题是我们现在没有独创的理论出来,我们很难说我们的批评里创造了什么新的词。有些词我们用得太多:日常生活、共同体、诗意,但这些词背后有很强的社会议题性和理论性,但是回收得太快,就没那么有分量了。另外一个就是词汇,我们在用西方的甚至是20世纪西方的一套词汇,很容易用一个理论框架找到中国的参照形成对话,但其实我们对于理论本身的原初意义是不太明白的,我们用词用得太快,反而把它背后的历史机理和个人的部分抛掉了,可我们到底了解多少?怎么去创造新词汇,如果不能创造,我希望把“陈词滥调”重新打开。
还有一个焦虑,我作为一个中国的现代人,我中国的部分在哪里,中国特色我没有特别明确地体会到,中国的情感状态和伦理状态到底有怎样的特别,文学能够提供的比社会学哲学思想史更多的在哪里,我们用的很多词都是从它们来的,同时又不能贡献出文学的一套思想。我觉得这很难突破,是文学所谓的困境。
金理:在八十年代,批评家不用做什么就可以引起轰动,现在我们用理论反倒被人看不起。上次去瑞士开会,一位学者讲中国的科幻小说,讲得很好,有人提问中国科幻文学的中国性在哪里?只有中国才会被这么问。我们面对中国文学,确实也一直在焦虑。
杨庆祥:中国文学不被视为世界文学。中国学者才会焦虑。换作其他国家就不会被问同样的问题,比如法国科幻小说绝对不会被问法国科幻小说的法国性在哪里。
刘欣玥: 杨庆祥与黄平两位作者一再提醒我们,一些作家、文学事件,恰恰构成了他们生命经验中许多绕不过去的“问题原点”。用文学的方式面对和解决这些问题,就是以自己的智识和力量,有效地发现、重启、调动他们的成长经验。作为一个批评的初学者,这两本书令我时时反顾,许多时候自己所缺乏的,恰恰是走出自身,走到个人之外,站到历史的取景框里,把自己投掷到更大的社会潮涌和人群中的眼光与勇气。
阅读两位作者关于“80后”写作的批评,使我想起黄子平教授这几年极力强调的观点:批评总是同时代人的批评。无论在生理年龄与社会学意义上,还是在阿甘本的意义上,他们都是“80后”作家的“同时代人”。在黑暗中探照、刺穿同时代人的写作与历史困境,或许正是批评家不同于普通读者的判断力、思想力所在。他们的批评实践,一直在超越个人趣味和狭隘的文学审美,找寻一种更具有生产性的同时代对话。这样的文学批评或许最终得以逃脱“踏空”或“速朽”的命运,因为它们与实实在在的历史和现场生长在一起,朝向“80后”乃至更大的人群。借用鲁迅先生的一句话说,大概是“无穷的远方,无数的人们,都与我有关”。
邵部:如何理解今天的主题“困境与微光”?批评就是“微光”丛书作者面对这个时代的虚无的方式。谈到“微光”,金理用了加斯东的话作为阐释。我想到的则是他在《空间的诗学》里营构出来的另一个震撼人心的画面:在城市的沥青地面上,清道夫挥舞着扫帚,收割想象中的麦子,真正大自然的硕大麦子。在今天的语境下,以文学为志业者大概也有点这位清道夫的感觉。
第二个层面来理解“困境和微光”,是将视野集中在批评本身。我觉得需要辩护的是应该区分谱系和套语这两个不同的概念。前段时间,网络上有一个帖子很流行,叫《人文学术套语偶拾》,作者把我们常用的术语罗列了出来,很反讽。我有个感觉,罗是经过规范的学术化训练之后,我们想写出一篇批评文章是很简单的。这样的批评多的是穿针引线的功夫,把词汇串起来,把对象知识化,套在文章的结构里,就成立了。迎春所指的应该是这一种。但是谱系的方法不是这样。黄平谈到,要在历史能量涌动的地方做研究。这应该是一个寻找谱系应有的态度。谱系就是一个火山喷发的过程。我们此刻面对的问题不仅仅是一时的流行病,而是其来有自,有历史的根源。是历史深处爆发的能量,把它们呈现在我们面前。谱系的方法,是以一种追溯历史的方式来面对问题,其实就是在“问来路”。像火山一样,从地表迎着炽热的岩浆,回到问题产生的那一刻。
最后,我想谈的是批评之于个人的意义。去年杨庆祥给同代人年选写的序言很感人,其中写道:“当初‘怂恿’他们办同代人公号,无非是担心他们在博士期间无所事事,最后寻章摘句,白白耗费几年青春。以做事来抵抗人生的虚度和虚无,这算是我一直以来微弱的自证吧,如果这种抵抗又能让生活变得有趣一些,那自然是更好的境界了。”我感觉“微光”也是这样一种以做点事情来抵抗虚无的自证,即要在时代、批评和“我”之间建立起联系。“我”通过批评介入这个时代,而时代反过来通过批评,融入到“我”的生命体验之中。以此时代中便有了个体的“我”,“我”也便有了抵抗这个时代的虚无的可能。
周晓:文学批评不应以作品的题材大小论高下,而应该看作品的“完成度”。阅读不仅是为了现实政治需要,也是为了精神需要。现在的文学批评需要去关注更多生命性的东西,而非知识性的话语,批评的温度是我们所需要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