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娟:“我很满意写作的命运” 携最新文章结集《遥远的向日葵地》来深举办分享会并接受深圳商报专访

李娟来深举办新书分享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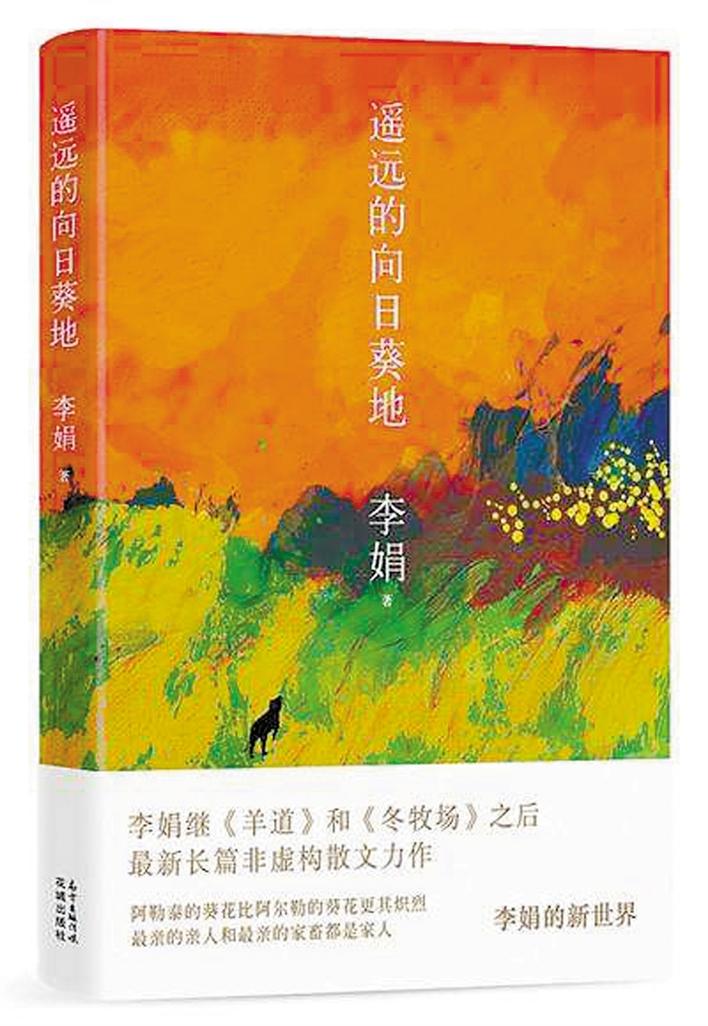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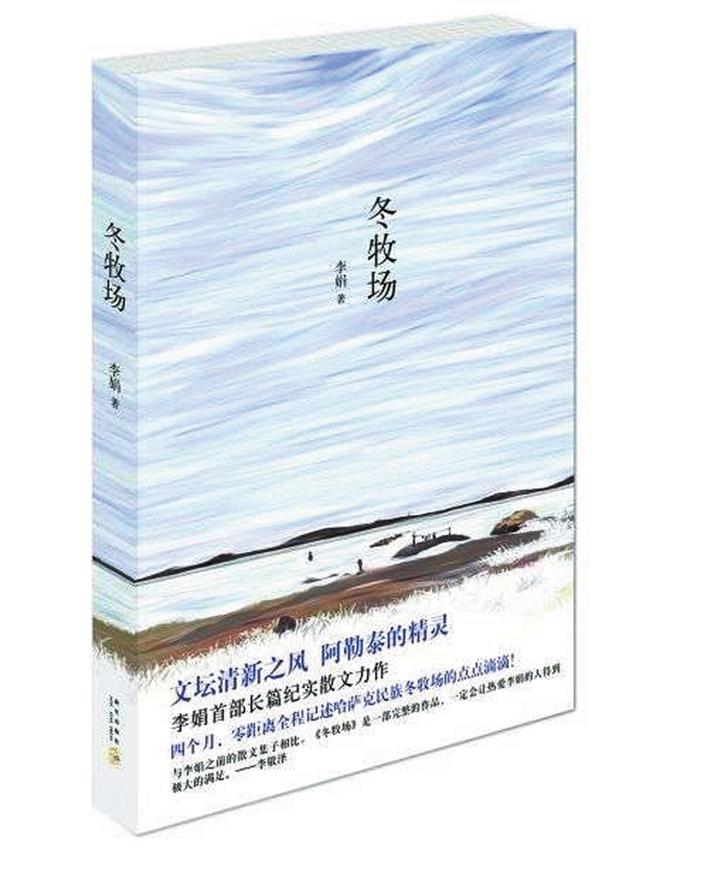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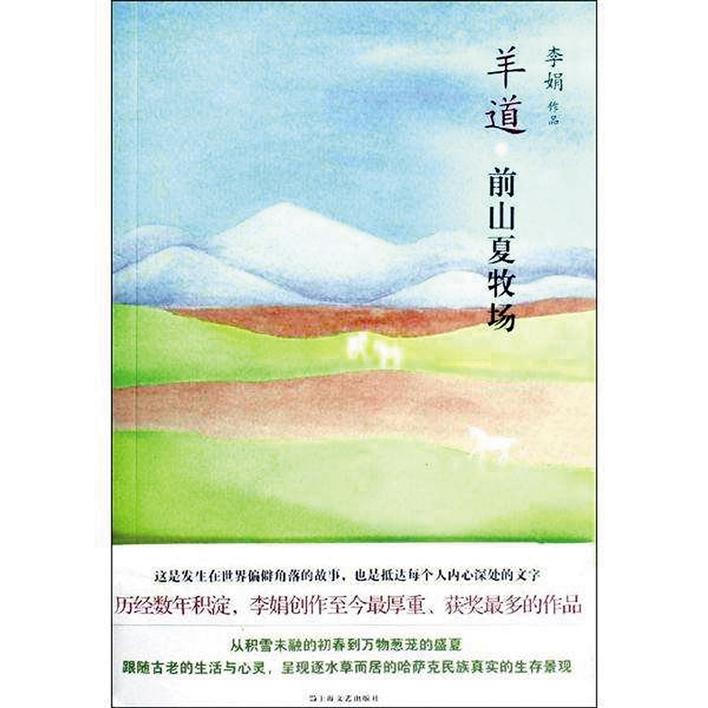
从深山牧场到向日葵地,作家李娟的文字笔调一如既往明亮细腻。近日,李娟携最新文章结集《遥远的向日葵地》前来深圳举行新书分享会。鲜少公开露面的李娟,扬起一派率真朴拙之气质,与读者谈写作,谈文学,谈生活。现场读者如潮,难掩对她的感动和喜爱。“向日葵地”在阿勒泰戈壁草原的乌伦古河南岸,是李娟母亲多年前承包耕种的一片贫瘠土地。在《遥远的向日葵地》一书中,李娟记录了劳作在这里的人和他们朴素而迥异的生活细节。她刻画的不只是母亲和边地人民的坚韧辛劳,更是他们内心的期冀与执著,也表达了对环境的担忧和对生存的疑虑,呈现出一种完全暴露在大自然中脆弱微渺的,同时又富于乐趣和尊严的生存体验。
在新书分享会开始之前,李娟接受了深圳商报《文化广场》专访。她说:“写作的过程像是挖掘的过程,甚至是探险的过程。很多次,写着写着,就‘噢’地有所发现。曾经一直坚信的东西,往往写着写着就动摇了。以为已经完全忘记的,写到最后突然完整地涌出笔端。我依赖写作,并信任写作。很多时候,我还是很满意写作这样的命运的。”
向往纯粹的自然环境
深圳商报《文化广场》:《遥远的向日葵地》写的是大约十年前的事情,但我们读来并未感觉到某种陌生。除了时间意义,这种“遥远”还有其他意涵吗?
李娟:是地域上的遥远和时间上的遥远,是我再也回不去的地方。
深圳商报《文化广场》:人和自然的关系向来是您书写的核心,但在《遥远的向日葵地》中,您似乎对大地万物有一种更加尽情的倾诉?
李娟:我在写其他书的时候,可能会涉及一部分,但都只是点到为止。而这部分特别想有强烈的倾诉欲望,关于很多万物生长,自然奇迹,人和土地矛盾等,可能是一个区别。
深圳商报《文化广场》:您对自然万物的认识理解经历了一个怎样的过程?
李娟:从《冬牧场》《羊道》开始,我的文字的背景都是自然环境,写得多了就觉得对这些东西认识太少了,太有限了。人跟环境的关系的思考不仅是因为写作上的原因,还是我自己的需要。生活在那样的地方,我会比一般作家更关注这些,而且对人和环境的矛盾冲突也更加敏感,感到无能为力和痛苦,我就想写这些。
深圳商报《文化广场》:传统的乡村生活文明正在加速式微,从乡村到城市生活,给您带来了怎样的差异感?
李娟:城市和乡村是截然不同的,可是我觉得人就应该在城市里生活,人就应该聚居,以减少对环境的破坏,除非你是过着最传统地道的乡野生活方式,比如现在还在农耕放牧,我和环境息息相关,那么我在自然中生活基本是没问题的,否则,我生活在那儿就是对环境的消耗和破坏,所以我在城市里生活其实应该是一个本分。
深圳商报《文化广场》:您现在享受城市生活吗?您有一个心灵的角落是属于城市的吗?
李娟:我习惯城市生活,但是享受还谈不上。我就是一个城市人,我就应该在城市里生活。我向往乡村,向往纯粹的自然环境,但向往仅仅只是向往,我跟乡野现实是毫无联系的。
深圳商报《文化广场》:您现在城市生活,以后也会写下这些经历吗?
李娟:以后可能会提及吧。
城市也有永恒不变的东西
深圳商报《文化广场》:都市文学写作如今也浮现了一些问题。在您看来,都市文学写作最重要的东西是什么?
李娟:城市写作往往让人越看越浮躁,我觉得是作者的原因,他们写作的时候关注的是那种转瞬即逝的东西。而城市也有古老的,有它永恒不变的东西,但很少有人去关注这种永恒不变的东西, 比方说《繁花》,读后你会感觉它跟任何一部写故乡、写童年的文字不同,所以还是关注点不一样。
深圳商报《文化广场》:您说到您至今仍有“耕种的梦想”,这种梦想要实现有多难?
李娟:我无力耕种,也无法更好维护它,我连一个普通的农人都赶不上。耕种一块地不人需要热情和理想,更需要许多现实的东西,比如需要一家人都生活在那里,需要子孙后代的共同维持,需要对现代物质享受的约束。不是说你喜欢大自然,喜欢“隐居”,就能做到。搞不好两败俱伤。
深圳商报《文化广场》:相信很多读者都挺向往您母亲多年前承包耕种的“向日葵地”,现在母亲还在耕种劳作吗?您认为母亲的劳作是快乐的吗?
李娟:她还在农村独自生活,应该是快乐的吧。
深圳商报《文化广场》:农人的劳作虽然单调辛苦,但他们的心却“和千百年前的古人一样宁静”,您也感受过这种“宁静”吗?在城市您也能感受到“宁静”吗?
李娟:我从来都不是一个宁静的人,无论在城市还在山野乡村。踏踏实实、平平安安的生活是我终生的向往。
我的散文和小说没什么区别
深圳商报《文化广场》:除了散文,您也写小说、诗歌,但散文是否仍是最适合自己的表达的?
李娟:散文目前已经满足了我的写作需要,我想写的东西完全可以通过这种题材体现,暂时没必要改变,还有,我觉得我的散文其实和小说没什么区别。
深圳商报《文化广场》:无论是《遥远的向日葵地》,还是之前的作品,您都比较喜欢用一种讲故事的语言对族群或乡村的生活方式、历史伦理等方面作出细节化描写。您觉得您对这里面的东西是否已有足够的认识?现在您还想试图去寻找更新的东西吗?
李娟:写完《羊道》的时候,我觉得好像意犹未尽,还有最纠心的一部分没有提到,所以心心念念写了《冬牧场》,有时候写得越多,不了解的东西就越多,你要真的完全写透了的话,要付出的努力、代价、精力是很大的,你要像一个学者一样,但我是一个作家,我不是搞研究的,不是搞田野调查的,我还是更想写更轻松自由的东西,随心所欲。
深圳商报《文化广场》:您的生活经验已经是难以复制的鲜亮,而您在写作中会特别重视语言问题吗?
李娟:当然会额外重视了, 这是必须的。
深圳商报《文化广场》:您怎样看待这些年来写作给您的生活带来的改变?
李娟:改变肯定是好的改变,但它滋养了我,也可能磨损了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