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写地址的“明信片”

视觉中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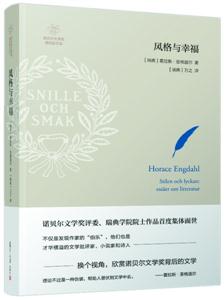
诺贝尔文学奖评委霍拉斯·恩格道尔的文学评论集《风格与幸福》,新近由复旦大学出版社出版。
作为一部“诺贝尔文学奖背后的文学”,这部评论集更激发读者阅读兴趣的,或许还是诺贝尔文学奖本身。因为,这本书很容易被读者视为一条逶迤通往理解诺奖文学世界的路。在不久前举办的一场读书会上,《风格与幸福》一书译者万之和复旦大学教授陈思和对此进行了解读。
评选:更注重面向整个世界
主持人(复旦大学出版社副社长李华):新近出版的诺贝尔文学奖评委霍拉斯·恩格道尔的文学评论集《风格与幸福》,是复旦大学出版社“诺贝尔文学奖背后的文学”系列丛书中的一册。这一丛书旨在让读者换个视角来理解诺贝尔文学奖背后的文学。诺奖评委们的文学品位如何?他们如何解读文学文本?他们自己的创作是什么风格?今天的读书会,我们邀请了《风格与幸福》一书译者、翻译家万之和复旦大学教授陈思和,共同对《风格与幸福》一书进行解读,走进诺贝尔文学奖视角里的文学世界。
万之:我作为译者来说,实际上就是把作者的声音传达出来。为了今天的读书会,霍拉斯·恩格道尔准备了这份 《转型期的世界文学》的讲稿,其中特别介绍了世界文学概念的来历。他甚至提到一个细节说,当初诺贝尔写下设立诺贝尔奖遗嘱的时候,他的书桌上有一本法文杂志《国际杂志》的创刊号,这是由几个国家的艺术家协会组织共同创办的。那时候,在欧洲就有一批作家、艺术家要想创办一种国际性的杂志。
在杂志封面上,诺贝尔读到了歌德与艾克曼的一段对话。其中,歌德认为一种新的世界文学的观念出现了。读过文学史的人都知道,当时歌德提出世界文学的观念,和中国文学也有着一定的关系。因为,他读了一篇翻译成德文的中国小说《好逑传》。读到《好逑传》的时候,他非常吃惊,觉得书里所写的内容与情感都引起了他内心的共鸣。这种内心的感觉让歌德觉得,世界上的文学是可以相通的,可以共鸣的。
诺贝尔是有国际主义精神的,所以,他设立奖项的时候,没有一个字提到这个奖是要颁给某个国家的作家。他所指的文学,实际上也是一个世界文学的概念。所以,霍拉斯认为,将来的诺贝尔文学奖的评选,会更注重面向整个世界。毕竟,诺贝尔文学奖的出发点,是为了寻求优秀文学。何谓优秀文学?我记得霍拉斯曾经这样解释过:优秀的文学好像一张没有写地址的明信片,它是可以寄到世界的各个角落的。
评委:关注迪伦好多年
陈思和:《风格与幸福》是一个文学评论集。读这本书的时候,我的第一感觉是好奇,霍拉斯·恩格道尔作为一个评论家,他怎么评论那些不同时代的经典?我想看看作为一名诺贝尔文学奖的评委,他站在那样一个文学的高度,如何来看待、理解那些作品。因为,他的文学审美观肯定会影响他的评论标准。诺贝尔文学奖到底为什么评这部作品不评那部作品?对此,一直以来读者非常感兴趣,但评委们总是非常严格地遵守着保密制度。
早期诺贝尔文学奖的评选争议很大,因为,早期的评选非常倾向于精英文学。所谓精英文学,就是跟大众“过不去”,大众认为好的作品他们不评,他们评出来的大众也不知道。二战以后,这种情况慢慢在改变,评委们开始关注世界上流行的作家的作品,萨特获奖了,加缪也获奖了。
上世纪80年代,我刚刚大学毕业,那个时候诺贝尔文学奖已经开始在中国产生很大影响了。马尔克斯的《百年孤独》得奖以后,中国文学界是一片赞好。很多作家发现,原来这样的作品可以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于是,开始对它进行模仿,就出现了莫言这样的写作,出现了张炜这样的写作,出现了一大批“寻根作家”。
“诺贝尔文学奖背后的文学”这套书的价值在于,告诉读者这些评委的美学观是什么、文学观是什么、文学标准是什么。这对我们把握诺贝尔文学奖得主的文学创作、了解他们的得奖原因,会有直接的帮助。因为,评委们的爱好与品位会对评选产生影响。
万之:确实,参与评选的人,他们的个人爱好和品位会对评选有很大的影响。比如,至今很多人还在争论2016年诺贝尔文学奖为什么要颁给鲍勃·迪伦。我给大家回顾一下当时的经过,2016年5月,瑞典学院诺贝尔文学奖评委会每年筛选候选人的关键阶段,瑞典知名的文学批评家和作家乌拉,他是鲍勃·迪伦的粉丝,出版了一本书 《分叉轨道——为什么应该授予鲍勃·迪伦诺贝尔文学奖的八条理由》。这本书就像是一封独特的提交给诺贝尔文学奖评选委员会的公开提名信。
后来,乌拉对《瑞典日报》记者透露说,在《分叉轨道》出版之前,他就把书稿用电子邮件发给了老朋友霍拉斯。“不过,霍拉斯从来没有回复我。”在迪伦获奖消息公布之后,就有记者问霍拉斯是不是受到了乌拉的影响?霍拉斯回答说,我关注迪伦已经有好多年了。
所以,我们也就不奇怪了,为什么是霍拉斯在2016年颁奖典礼上宣读了授奖词。通常撰写和宣读授奖词的任务,是由瑞典文学院里最理解、最支持这个得主的评委完成的。毫无疑问,霍拉斯是迪伦得奖的主要推手,所以,当仁不让地起草和宣读授奖词。
埃斯普马克曾经写过一本书《诺贝尔文学奖内幕》,其实不是谈什么内幕,就是解释了这么多年来诺贝尔文学奖评选的变化。这本书可以解释为什么早期像托尔斯泰、易卜生这样的作家没有得诺奖。因为,对诺贝尔遗嘱里一句关键的话,评委们不知道怎么解释。诺贝尔说,这个奖应该给那些有理想主义倾向的人。评委们认为,诺贝尔是信仰上帝的,是爱国的,这即理想主义的价值。因而,那些对上帝有了怀疑的人,像托尔斯泰和易卜生就无法得奖。
到上世纪二三十年代,辛克莱·刘易斯得奖了,而西奥多·德莱塞没有得奖。那个时候,他们又有新的解释。他们把理想主义倾向解释为能够影响的人越多越好,就是看这本书的发行量是多少。结果,当时一些搞现代主义实验的作家就没能得奖,因为他们作品是小众的。德国作家黑塞,在上世纪30年代几次被否认,1945年,新的一批院士进去了,他们喜欢这种现代派,所以,1946年,黑塞就得奖了。由此,大家可以看到,评委自身的爱好对评奖的影响。
现在的瑞典文学院有一个很明显的变化,三位老院士去世以后,连续选出了三位年轻的女院士,一个小说家,一个是评论家,还有一个是神学家。这让我觉得,未来诺贝尔文学奖的评选中女作家得奖的比例会大大增加。
翻译:使语言的障碍被瓦解
陈思和:在读这本书的时候,我很佩服这位诺贝尔文学奖评委掌握了很多欧洲的语言,他可以用德语欣赏德语文学,用法语欣赏法语文学,用意大利语欣赏意大利文学。否则,要谈一部小说的语言风格是很难的。
如果是一个关注语言风格的评委,他要从一个翻译语言中把握一个文学作品的语言风格是很难的。比如,我们读巴尔扎克的小说,读来读去读的都是傅雷的意思;读莎士比亚的作品,我们关注的其实都是梁实秋的语言。
歌德的世界文学的观念,我很熟悉,因为,比较文学的起点就是从世界文学而来的。歌德强调一个“同”,就是说全人类的文学根本上是一样的。来自中国的才子佳人故事他们也可以理解,因为德国也有这个,他自己写的《少年维特的烦恼》也是才子佳人的故事。所以,他认为世界上的文学将来会趋向于大同。
我想,诺贝尔文学奖提倡的是一种人类的文学。它表现在文学作品中,就是鼓励人们为和平、为人类的精神生活去创作。这种文学理想,可能比世界大同的概念还要大一点。
世界文学的概念也好,人类文学的概念也好,我认为,它们的本意是“异”,就是要包容越来越多不一样的文学。所以说,每一个国家,每一个民族,它的语言本身就是世界的。而不是我不是世界的,或者别人才是世界的;我们要走向世界,或者让世界承认我们。
我举一个例子,印度的泰戈尔1912年就得诺贝尔文学奖了。印度人都很开心,认为这是印度文化的光荣。但泰戈尔说,我是一个“奴隶”,我是用别人的语言在写字。泰戈尔写诗是用英文来写的。所以,他得奖的时候就有两种意见。一种意见认为泰戈尔用英文写作,这证明了英国殖民政策的胜利。另外一种意见说泰戈尔的英文比英国人还好,说明我们印度人很聪明。泰戈尔是用英文写作得的奖,而不是用本国的文字写作得的奖。这说明,诺贝尔文学奖的评委们可能关注到欧洲大陆以外的作家,比如泰戈尔,可是,他们理解的是他的英文作品。
有一年的诺贝尔文学奖推荐,汉学家觉得中国作家也应该推荐,就找到了留法的刘半农,刘半农说鲁迅不错。当时,鲁迅的《阿Q正传》已经在罗曼·罗兰主编的杂志上用法文发表了,罗曼·罗曼看了以后非常感动,“这部小说让我看到的不是中国,是欧洲,是法国,我们闭着眼睛都可以看到到处都是阿Q”。
然后,刘半农通过国内的一个朋友去找鲁迅,让他报材料。但鲁迅拒绝了。“我觉得中国实在还没有可得诺贝尔赏金的人。瑞典最好是不要理我们,谁也不给。倘因为黄色脸皮人,格外优待从宽,反足以长中国人的虚荣心,以为真可与别国大作家比肩了,结果将很坏。”
诺贝尔文学奖作为一个世界级的文学评奖平台,对中国和中国文学其实是一直关注的。但因为语言的问题——要翻译成英文、瑞典文来显示中文作品真正的魅力,显示中国文化的优秀,是非常困难的。所以,翻译非常重要,翻译就是使语言的障碍被瓦解。
万之:目前各国对文学翻译都比以前更加重视了。就瑞典来说,他们设立了很多文学翻译奖,瑞典作家协会还特别设立了翻译委员会。毕竟,要建立一个世界文学,没有翻译就无法沟通。(本报记者 黄玮 整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