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书为赢 利在千秋——访深圳出版发行集团总经理、出版人尹昌龙

深圳出版发行集团总经理、出版人尹昌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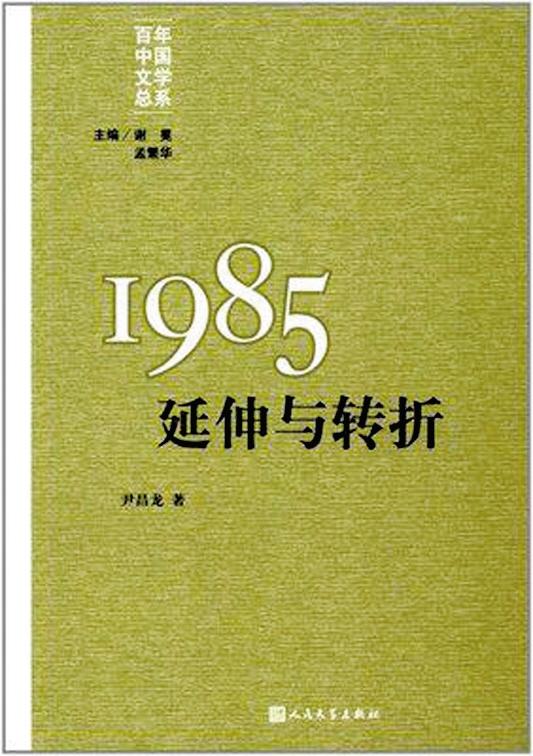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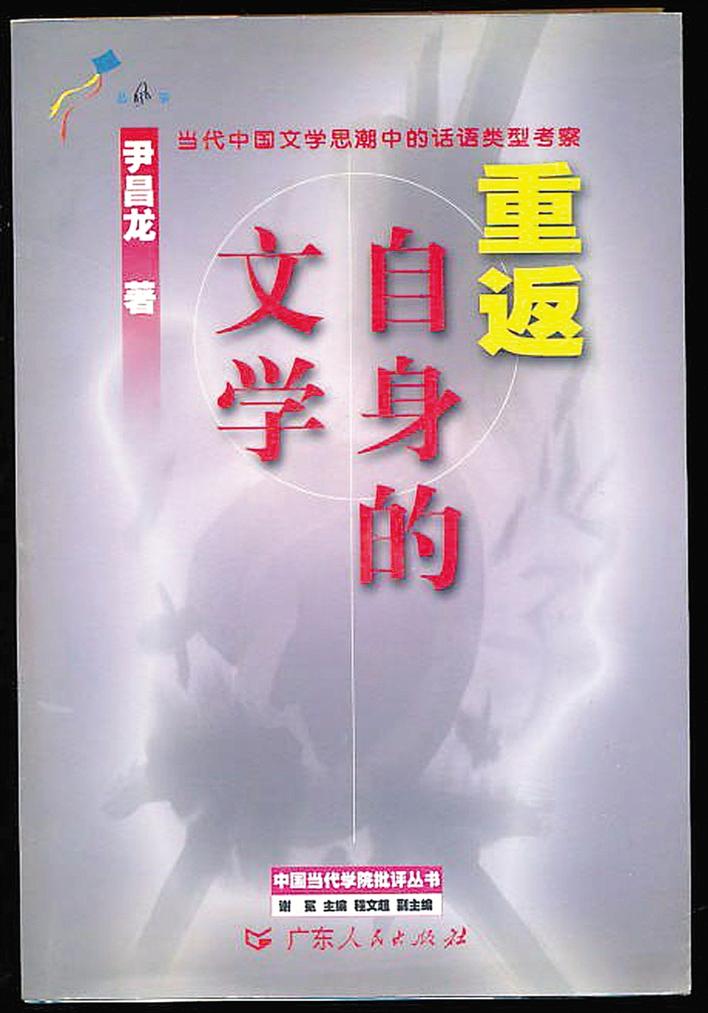
大概十多年前,尹昌龙提出一个概念——“以书为赢”。他认为不读书无以自立,不读书无以自强,读书才能真正赢得未来,对个人而言如此,对一座城市而言也是如此。尹昌龙现任深圳出版发行集团总经理、深圳读书月组委会办公室主任,他由一名学者转型为城市文化的管理者,也是“以书为赢”的践行者。近日,尹昌龙接受深圳商报记者专访,在回顾自己在北京大学求学和治学的经历时,他认为自己从谢冕教授身上学到了宽容和勇于担当的精神。在回顾深圳读书月18年来走过的道路时,他认为这是一种高贵的坚持。读书月给深圳注入了一种文化基因,使它有了延续发展的动力,深圳的前景会越来越美好,未来会越来越强大。
从导师身上学会了宽容
深圳商报《文化广场》:您是北京大学文学博士,您的博士生导师是谢冕教授。上世纪80年代初开始,由朦胧诗等引发的文学潮流席卷整个中国,文学成为社会主流,成为社会中心,谢冕先生是诗歌评论和文学批评的一面旗帜。谢先生对您的人生道路和学术研究有何具体影响?
尹昌龙:我想谢冕老师对我的影响不仅仅是在知识和学问上,他教我的最主要的是道路和方法。一个好的老师对学生的影响主要是在精神上,包括态度和价值。
谢老师为人特别宽容,能容忍各种不同观点。我记得当时我们重读文学经典,包括路翎的《洼地上的战役》,大家在讨论的时候,对作品中班长王顺这个形象颇有微词。整个讨论过程都是开放的,而且轻松愉快,只是在结束的时候,谢老师开了一句玩笑:你们不要看不起班长哦,我就是班长转业的。他不告诉你结论,而是开放了一种通往结论的可能性,对一个学生来说,通往结论的方法和道路比结论本身更重要。
深圳商报《文化广场》:您的专业是当代文学批评,因此采访您绕不开当代文学这个话题,绕不开您的作品《1985:延伸与转折》。这部著作是“百年中国文学总系”之一种,请您谈谈这套书系出版的背景。
尹昌龙:当年谢老师组织撰写“百年中国文学总系”,是基于重写文学史这样一个宏大的构想,他希望这套书在文风上灵活多变,不要像教科书那样呆板。当时这套书借鉴的典范是勃兰兑斯的《十九世纪文学主流》和黄仁宇的《万历十五年》。谢老师说,他喜欢“手风琴式结构”。什么叫“手风琴式结构”呢?选取相对长的一个时间段,将其压缩到一个点上就是一年,拉开了就是横贯的历史长河。
我选择1985年,是因为上世纪80年代是我们这一代人的成长故事,就像青春小说一样。中国经历了近百年的积贫积弱,到上世纪80年代才真正进入改革开放的节奏,中国的强大和崛起,中国进入20世纪下半叶的所有巨大转变都是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的,可以说上世纪80年代开启了5000年未有之变局。我书中的第一章叫“从《人生》开始的人生——眺望城市的灯火”,就谈到农村城市化的进程,其实最早是高考带来的变化,大量农村学子进入城市,他们的人生命运得以逆转,以及他们的情感亢奋和困惑。
特区文化研究中心是介入的旁观者
深圳商报《文化广场》:深圳市特区文化研究中心是一家综合性研究机构,是政府文化决策的智囊,当时有一句口号是要把它打造成中国的兰德公司。您是文化研究中心承上启下的关键角色,怎么看当年的这一定位?
尹昌龙:我记得大概是1995年底,王京生作为时任深圳市文化局副局长分管特区文化研究中心,他在年终总结时提出要将它打造成中国的兰德。深圳市文化局原来有一个调研处,在机构改革时被裁撤,后来深圳市跟文化部合作成立了特区文化研究中心,使原来调研处的功能得到保留,又增加了新的研究功能。特区文化研究中心不同于纯粹的学术机构,它是政府部门主管的一个研究机构,对体制运作方式非常熟悉,同时又有相对独立性,用雷蒙·阿隆的话来表述,它是介入的旁观者。它的优势在于利用体制和观察体制,一方面是介入者,它的观点和成果可以成为政府或文化部门的文件,可以进入政策层面;但同时它又是一个旁观者,不直接进行文化管理。
当时大家关注“特区文化”这个新概念,深圳特区随着经济改革和社会发展产生的新的文化现象,也可能是中国未来社会发展中的新内容,这种研究具有前瞻性和启示意义。当时从中央到各省市的文化研究部门都叫艺术研究所或研究院,而我们叫特区文化研究中心,因为我们的研究是跨领域的,不局限于文化和艺术,这种文化不同于博物馆式的静态文化,而是随着市场经济而起的鲜活文化。
深圳商报《文化广场》:事实证明,深圳市特区文化研究中心对深圳文化产业政策的制定和文化市场的发展起到了重要的决策和参考作用,对此您如何评价?
尹昌龙:深圳市特区文化研究中心的重要意义和贡献至少包括以下几个方面:一、它最早关注伴随着市场经济产生的新的文化,也就是我们今天耳熟能详,国家又非常重视的文化市场和文化产业;二、在政府和市场边界比较清晰的情况下,研究如何对文化资源进行管理和合理调节,形成成熟的分类管理的公共文化政策;三、一座年轻的城市文化发展需要战略决策,研究中心成立以来一直将战略置于研究视野中,使文化成为动词,让文化运营城市、改变城市,让文化成为城市的意志;四、关注移民文化生态,保持文化的共生共荣,多样发展,同时关注创新型文化,从传统文化过渡到跨界文化,比如文化与科技、与金融、与旅游相结合,从而触摸到并开始解读文化创新的密码。
如果说它存在不足的话,我觉得它对国外公共文化政策的关注还不够,因为我们是开放型文化,应该多借鉴发达国家的文化经验。另外,它还可以对一些个案多作发掘、研究和分析。
深圳读书月是一种高贵的坚持
深圳商报《文化广场》:深圳读书月至今已经走过了18个年头,它如今已经成为深圳的一个文化品牌,也可以说是深圳文化的一个代名词。您在深圳市特区文化研究中心和市文化局任职期间,对这个品牌的打造立下了汗马功劳,对此您有何感想?
尹昌龙:回顾深圳读书月这18年来走过的道路,我还是想用一句话来评价:这是一种高贵的坚持!在市场经济时代,当许多地区都在抓经济抓政绩,我们却没有急功近利,在缓慢地培养读书的种子。十年树木,百年树人,一代人的读书习惯需要十年二十年的培养。好事即使寂寞也要坚持,这就显示这个城市的价值追求,功在当代利在千秋,争千秋而不争一刻。
读书月给深圳这座城市带来了令人可喜的变化。我刚来深圳时,感觉不到它的书香氛围,现在深圳读书人口剧增,深圳书城每到周末人头攒动。我有一次陪同一位大学校长参观莲花山,下午5点回到深圳书城中心城,看到有那么多读者,他非常感慨地说:中国任何一座城市都很难看到这种场面,由此可见这个城市的竞争力和希望。确实,读书月给深圳带来的是一种生活方式的改变,使这座城市令人尊重,同时也给它注入了一种文化基因,使它有了延续发展的动力。这座城市如此年轻,又如此热爱学习,它的前景会越来越美好,它的未来会越来越强大。
深圳商报《文化广场》:您提过一个口号:以书为赢!当时您好像还没有到深圳出版发行集团任职。深圳的人均购书量在全国一直排在前列,但应该清醒地看到,纸质书阅读量在降低。现在回过头来反思“以书为赢”这个口号,您有什么感想?
尹昌龙:书与输同音,做生意的人以为不吉利,所以罗湖书城改名金山大厦,其出处大概是“书中自有黄金屋”。所以我提出“以书为赢”,不读书无以自立,不读书无以自强,读书才能真正赢得未来,对个人而言如此,对一座城市而言也是如此。深圳人均购书量一直高居全国第一,应是不争的事实。深圳一般图书(除教材教辅外)的销量超过很多内地的省份;全国十大书店销量排名,深圳至少有两座书城位居其中,到高峰时甚至有三座;深圳书城中心城、罗湖城和南山城的销售总额超过全国任何一家书城;深圳读者买书都是一捆捆、一筐筐地买,这在内地城市甚至在香港都难见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