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鸿:梁庄是别人的故事却是我的世界

梁鸿 文学博士,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教授。致力于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乡土文学与乡土中国关系研究。 著有文学代表作《出梁庄记》《中国在梁庄》《神圣家族》等;学术著作《黄花苔与皂角树——中原五作家论》《新启蒙话语建构:〈受活〉与1990年代以来的文学与社会》《外省笔记:20世纪河南文学》《“灵光”的消逝:当代文学叙事美学的嬗变》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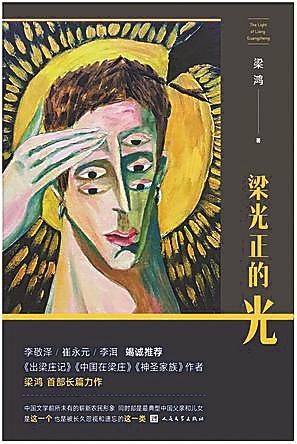
梁鸿作品三种 虚构 《梁光正的光》 人民文学出版社 2017年10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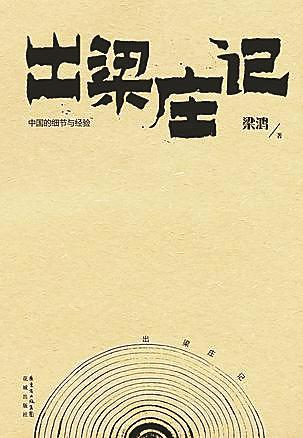
非虚构 《出梁庄记》 花城出版社 2013年4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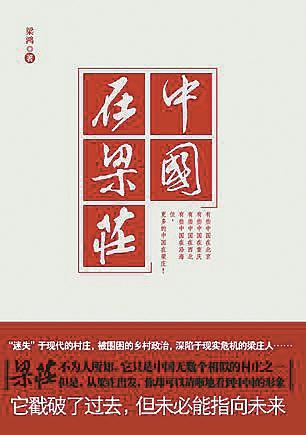
《中国在梁庄》 江苏人民出版社 2010年11月
作为一个写非虚构作品成名的作家,梁鸿的两部作品《中国在梁庄》《出梁庄记》因纪实性、社会性获得不少赞誉。她通过田野调查、口述实录的方法,记录下在“梁庄”和走出“梁庄”的一个个农民的故事,成为非虚构写作领域的典范之作。所谓典范,并非是一个书评性质的赞誉,而是在这两本书之后,梁鸿俨然成了“农民问题”的代言人,甚至有不少读者希望梁鸿给出解决方法。这种赞誉像一把双刃剑,一方面,“梁庄”和“农民”成了梁鸿的标签;另一方面,它让人忽略了梁鸿的作家身份和她写小说的能力。
这一次,梁鸿拿出了虚构文学作品——小说《梁光正的光》,虽然主人公梁光正依旧是生活在“梁庄”的农民,但这一次她笔下的农民不同以往,而小说所讲述的故事,更是“见自己、见众生”。读罢掩卷,深感每个人的身边都似乎有这么一个“戏精梁光正”。
日前,梁鸿来到深圳,接受了晶报记者的专访。在她看来,写《梁光正的光》得益于之前的非虚构写作,给了这本小说大量扎实的细节,作为文本的“地基”。而主人公梁光正虽然是个失败的人物,但是你依然会被他的故事吸引。
把这个故事落地在梁庄可以让我更自在
晶报:读者对您写的“梁庄”太熟悉了,这次写虚构小说又是放在梁庄,不会担心被读者认为您走不出梁庄吗?
梁鸿:我写的时候既没想过要沿着梁庄的路子走,也没把梁庄当成一个IP,而是在写的过程中我发现,梁庄对我已经不单单是一个词语了,而是一个内部空间。我开始不想用梁庄,想用杜庄,梁光正也不叫梁光正,写到一半的时候觉得还是不顺,就索性把杜庄变成梁庄。当我把杜庄改成梁庄的时候有一种开阔之感,也有一种自由的感觉。因为你太熟悉它了。就像我们熟悉一个人,我们可以随便拿捏他。那个度会把握得很好,别人也不会说很假,因为你还在逻辑之内。用梁庄作为小说背景,我不会觉得紧张和拘谨,不会觉得难以把握。所以,梁庄对我来说是一种内部空间,而且内部是有东西的。
晶报:其实这本书和之前的梁庄是完全不一样的。
梁鸿:在别人看来,可能会觉得梁庄是一个系列,但对于创作者来说,这样处理让我感觉更自在。因为如果拿捏不定,那么小说的空间肯定是把握不好的。这种自在的状态其实是可以传达给读者的,你读的时候就会发现,它不是为了梁庄而写的,梁庄就是梁光正生活的一个地方。至于此梁庄与彼梁庄,我并不在乎别人怎么去看这本书,也许别人看的只是一个故事,但对我而言是在创造一个世界。
梁光正的理想在现实中是不合时宜的
晶报:您谈到,写梁光正的故事灵感来自于您的父亲。
梁鸿:这些年我写梁庄,一直是父亲陪着我拜访梁庄的每一户人家。其实,在《中国在梁庄》这本书里面,梁光正已经出现过了,这里的梁光正是我真实的父亲,我以梁光正之口谈了梁庄的历史往事,也谈到1970年代个人的生活和整个村庄的状况。而在《出梁庄记》里,梁光正也非常重要,书中的我和实际生活中的我,对村庄的人是不熟悉的,梁光正作为非常重要的村庄老人,他一出场,村庄往事就打开了。可以说,没有父亲就没有《中国在梁庄》和《出梁庄记》。
晶报:但是在这本小说里,梁光正是一个虚构的人物。
梁鸿:前年我的父亲去世,但他乐观自嘲、夸张煽情和孩童般的无畏形象时时浮现在我的心中,心里慢慢生长出一个叫做“梁光正”的老年男性形象。
梁光正是一个极其乐观的、幽默的、一个不合时宜的人,生活中会被别人嘲笑。他不是本分的农民,他的做法超越了生活给他的规定性。一个人试图超越生活秩序和文化秩序的时候是非常艰难的,他会处处碰壁。这个梁光正就像堂吉诃德,堂吉诃德拿着长矛对风车作战,这是可笑的、荒诞的,但又让人尊重的。但我们说这个人是堂吉诃德的时候,也是因为他坚持某种理想,这个理想在现实生活中是不合时宜的。
晶报:所以,小说中的梁光正充满了戏剧性,一开场就要去寻亲,然后还要去找年轻时候的女朋友,一味奉献,让子女家人不胜其烦。
梁鸿:我是从梁光正的老年写起的,60多岁要去寻亲戚,不顾家人反对去找女朋友。他的女朋友在他家呆过,出了大的事故就走了,这是伤痛。所以梁光正说要寻女朋友,大家就明白了,他其实是不断在跟俗事作战。
梁庄从实在的梁庄变成虚构的梁庄,但它跟我内心深处对梁庄人的认知有关系。我在《出梁庄记》里提到了一个年轻人,他在河北打工,不仅挣到了钱,还捐了很多钱,但他捐钱的动机不光是为了表现自己,而是想获得一种认可。他曾看到一则新闻,新闻报道了一个打工青年在当地获得了“十大务工青年”的称号,得到了政府的奖赏。当这个青年站在电视上被称颂时,这位在河北打工的青年就特别为之羡慕,他希望自己也能获得这样一种认可和身份。但想获得这种身份是非常艰难的,相当于是堂吉诃德的梦想,不过他不放弃,他说我想在我那个地方得到认可。人们会觉得这个人不切实际,但却是值得尊重的。梁光正就有这样的因子,一生都在折腾,一生都在失败,一生都在因为说真话被批斗,哪怕浑身流血、老婆生病孩子受伤他都不改旗帜,这样的人身上有我们生活内部缺乏的东西。
这不只是一个农民的故事而是一个“人”的人生
晶报:如果说之前非虚构的梁庄是一个群像,那么虚构的梁光正更像是梁庄群像中的一个切片,感觉他身上容纳了很多人的生活和个性。
梁鸿:当你在塑造一个人的时候,并不单单是哪一个地域的人的切片,他可能是一个集合体,至于他是哪里人并不重要,但你总要把他落实在一个现实的地域里,比如他生活在哪儿、他说河南话还是山西话、他家里有几口人,他种北方的麦冬还是南方的枇杷等。梁光正并非只是梁庄的切片,我其实更想把他作为这一类人的切片。出于写作的自由和对场景的熟悉,我把他放在了梁庄的背景里。
晶报:读完这本书,有很多人认为您写出了不一样的农民形象。但我发现这本书并不只是在讲农民的故事,梁光正的性格、他与子女的冲突、家庭纷争,是会出现在每一个中国家庭里的。这其实是普遍家庭里存在的问题。仅仅把这本小说理解为讲述的是农民的故事,反而把这本书说小了。
梁鸿:对,我写的是一个人的故事,只不过这个人恰好是农民。这个次序是非常重要的,我不是在写一个农民发生了怎样的故事,而是在写一个人的故事。他的家庭关系不仅出现在农村,同样会出现在城市里,甚至在世界范围内的多子女家庭中都会出现这种情感纷争。我在这方面下了很大的工夫。但说这是一个农民的故事也不是不对,因为梁光正确实是一个农民,只不过是我们没见过的农民,他非常任性,他追求理想,追求光,可能被子女怨,甚至是恨,生活中有很多这样的亲人。
晶报:这本书取名《梁光正的光》,有直面痛苦、黑暗的部分,但是又能从黑暗中看到光。尤其是梁光正的名字,让人想到“伟光正”。
梁鸿:我希望通过梁光正的事件展示我们应该怎么生活,一个人想过“人”的生活非常艰难。在我们的生活里面,梁光正这样的人为什么一生都过不好,他想创业,失败了;他想找女人,没有找到;他想过好日子没有过好;他爱他的老婆,他跟他老婆是娃娃亲,他无怨无悔照顾他老婆七年,他一生都非常真诚,但也没有得到爱情。梁光正一生都在奋斗,想过“人”的生活,但一生都没有过成。读过这本书后,我希望大家能有更深的思考,为什么过成一个“人”这么艰难,他不本分,也不认命,这因为我们的文化生活不允许他这样,虽然梁光正失败了,但是你会被他吸引和震动。
写《梁光正的光》我得益于非虚构
晶报:记得早几年我在采访您时,您说过自己是学文学出身的,自己的工作也是教授文学的,对小说的创作非常了解。但后来您用了非虚构的方式来写作,而现在您从非虚构写作又转向了虚构写作,这中间您有什么感想?
梁鸿:用非虚构还是虚构,在写作时我其实没有特别的规划。而是直觉上,觉得这个题材适合虚构就用虚构的形式。对于梁光正的故事,只能用虚构来体现他的戏剧化,矛盾冲突更容易呈现,也更能高度集中去描写一个人。至于写作中有没有非虚构的成分,这个是写作方法的问题,但当你选择这种文体时,是直觉决定的,当然这个直觉背后有着知识的积淀和职业的敏感。
晶报:您在从非虚构转向虚构写作时,会不会不习惯?
梁鸿:经常有人说非虚构、虚构之间有特别大的障碍,我自己一点都不觉得。写《梁光正的光》我得益于非虚构,因为写非虚构的梁庄,在我脑子里面活了太多的人,我能把人随便捏在一起。《梁光正的光》非常有戏剧冲突,感觉这个人太人性,是一百个人捏在一起的人。你对每个人的性格有非常清晰的把握,当你把他们捏合在一个人身上的时候,并不冲突。有时我们写缺点是为了反衬人物的优点,但写梁光正这个人物不会,你会恨他,你会进入到他儿女世界里面。家庭容易产生个人性,你会非常认同子女的眼光,但读到后面又不会那么恨他,在我们的生活内部,这才是真正的人性存在。当你把他高度细致化的时候,你是在写真实的人性,人不可能只有光,这个光是驳杂的,光背后一定包含阴影。对于梁光正的缺点、梁光正的优点,我是在走微妙的平衡,一个充满矛盾的平衡,好像走钢丝一样。
晶报:这两种写作带给你什么不一样的感受?李敬泽形容写虚构与非虚构就像“骑摩托车与骑自行车的区别”。
梁鸿:非虚构的魅力在于你面对真实场景的时候,你要进入无限深远的地方来看到真实的背后,虚构在于它是飞扬的,它可以让你创造一个人,你就像造物主一样,你要承担全部的责任,虚构有虚构的快乐。因为有前面的两本梁庄,所以有了梁光正。两本梁庄里面写了非常多的细节和人物,读过之后很难忘掉,我对每个人的面貌和精神做了非常精确的推敲,哪怕一个词,哪怕形容一个表情,我也想用最精确的语言表达。比如书中的一个细节,我写梁光正寻亲时,写到他外婆的村庄在1950年代的南水北调工程中被淹掉的,村民在野地搭棚弄窝的情景。尽管呈现在我的书里面只是那四五百字,但是这个细节很扎实,它能构成文本的“地基”,哪怕是虚构的。
所以,梁光正这个人之所以会这么鲜明,是跟我当年的非虚构写作训练有关的,不管是骑摩托车还是自行车,我觉得我是开了电动车。
晶报:所以在这本书里,您关心的不只是一个家庭的故事,更是人的命运、整个城市的集合体。
梁鸿:写《梁光正的光》是写一个人,一个家庭,一个读者能读到家庭内部的纷争,同样也是读出了重点,中国式的亲密关系,它是非常纠缠的,在这个过程中每个人的人性都是委屈的、妥协的,但又是相爱的,这是特别中国式的存在。如果你是一个更深入的读者,你能够读到我在背后的历史信息,那也很棒。梁庄的写法是整体性的,我就要展现尘土飞扬的广阔生活,但这种生活是破碎在家里面的,没有关于社会大背景的书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