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天心:你在场而且真实地看到了,你就有责任去说
正如名作《古都》开篇第一句那著名质问:“难道,你的记忆都不算数……”,遍历错愕,岁月水系的急迫漫漶中,朱天心命笔追记自一九七零年代末随“胡爷”胡兰成踏勘京都风物以来,三十余载落花梦缘京都行旅的世事烟尘、所见所感、“不缺页的日记”,更荡开逸笔,秉持胸次内“士”的良知,书写当时当地的不认同、不畏缩、不否弃、不更易——她称之为,“捍卫微缈的一己记忆”。那许多细数、漫述,正色辩难,浓愁耿耿,雾中沼泽般无力无可挣脱,挥之不去的昔时关键之谜,在在明示朱天心“记忆书写”中最可宝贵的“直”,直见,直面,直现赤诚的灵魂时刻,直言不可言说的言说。——阿城有言:天心的强悍,即在于不绕。
不迂回游离、伪饰雅格的朱天心,自《时移事往》、《昨日当我年轻时》、《我记得……》,到《想我眷村的兄弟们》、《古都》,就一直将“记忆”作为自己文学“言志”的重要命题,张大春以老灵魂的“时间角力”命名之,詹宏志则在"时不移事不往"的命题写下关于化境的定言:"到了那境界,一切现象、新闻、社会事实都会沉淀下本质"。而在《三十三年梦》书中,她的执拗与执着就更是淋漓发挥,浩荡的、博渊的、文学森林星光烈焰般的,唐诺、朱天文、侯孝贤、杨德昌、张大春、詹宏志、骆以军、吴继文、林俊颖、张万康、初安民、钱永祥、林燿德、朱高正、陈宜中、费滢……樱花曼舞的幽邃古都,亦是华语文事的究极处、酣畅处。“不够熟的人,不够喜欢的人,是不会与之一起同游京都的。”简简单单一句话,简单的一声“同游”,其中多少况味,就要读者自书里书外,各自凭阅历经历,拧眉索解了。

朱天心,台湾作家
问:天心老师,《三十三年梦》在《印刻文学生活志》上的连载始于2014年年初,繁体版成书于2015年下半年,到理想国这次推出简体版,就又隔了两年才出,可否先请您简单介绍一下这个书的源起,以及您现在是怎么看《三十三年梦》这本书的?
朱天心:写这么一本书,有大背景,也有小背景。大背景是我一直在想要写的那个长篇,《南都一望》。这个长篇准备了很久,也试过开笔,但一直写不成。写的时候其实一直犯的是初学者的毛病,很急着把自己的想法一直一直塞到里面去,人物还没活起来,就强迫他们当你的代言者。当然这是一场失败,也许别人看不出来,但是我自己知道因为自己心急把这个小说给毁了。在这样的情况底下,我觉得好像该先做一点什么,把我自己的个人所有的意见想法,现实面上先把它做个了断,算是“清理战场”,大的背景是这样。那一般我很怕人家说写成了回忆录,自己觉得是后中年状态的时候,我起码自己觉得还在往前冲的时候,怎么会掉头去看呢?我并不会希望用回忆录来定义它。所以我就选了一个比较轻松的形式,我20岁的时候胡兰成老师带我们去京都,那到开笔写的时候算起来正好33年,这一路走来京都我去了超过30次以上,由此我就像,不如用京都当一个舞台,把我每一次舞台上发生的事情,还有这个舞台(京都)和那个舞台(台北)之间的事情都做个交代,大致是这样。
问:那么,这本书现在达成了你的想法了吗?
朱天心:本来就是对自己交代,写的时候也不会去顾虑到任何人,这是我的记忆,我不会考虑到会不会跟集体的记忆,跟他人选择性记忆、选择性遗忘的结果有任何的扞格,这不是我要考虑的。对我自己来讲,求仁得仁,可以说有做到我当初想做的。
问:所以当初它的两层意思,一层是要自己清理思路,清理之后可能为后面的写作做一个铺垫,这后面一层的效果呢?
朱天心:目前看起来,因为下一个阶段迟迟到现在还没有开笔,我还没被考验出来,可是最起码我是觉得我的行囊会轻松很多。还是那句话,“求仁得仁”。
问:您过往的写作一直在纪实与虚构之间,以“记忆”与“时间”作为主题,代表性的像《我记得……》、《时移事往》、《未了》,在这一次的创作,是不是有意地将这个主题做进一步的深化?
朱天心:倒是没有很自觉地意识到这一点,因为觉得写的时候只能牟足全力如实落笔,感觉好像这是一个归终的整理,所以这次要是没有把它搬出来做好归档,对我个人来说是永远就不存在了。在写的时候,因为它是散文而非小说,只能够如实再如实,无法再意识到还可以去做一些作为小说技艺可以炫技的,或者必须做虚化处理的那个部分。在写的过程中,像某些部分,有些或短或长,有些一年去个两三次,有些是三四年才去一次,这三四年中间的变化也非常大。我自己就完全是很随性的,觉得哪些会对我印象最深刻或者意义最大的,就这样写出来,完全是以自己为主。
问:那您的这种以“自己为主”的写法,也会关联所谓“文学场域”的问题,所以在连载的时候,《印刻》总编辑初安民先生有提出什么要求吗?比如要怎样不要怎样之类的,还是完全由着您“自己为主”地写作?
朱天心:他完全没有,没有要求过,有时候看到会倒吸一口气说,天心你这样写会惹祸。可是他没有任何别的意思,依旧照样会登出来。初安民跟我的关系始终是朋友重过出版者跟作家的关系。
问:在刚刚结束的香港书展上,您有讲到关于文学盛世已逝这样的话题,但是如果有的时候可以有这样好的编辑者,至少还是为文学在保留某些机会和可能。
朱天心:台湾文学市场的大萎缩,我觉得我个人、还有唐诺都很幸运,像初安民,尤其是我们一代之人,在台湾所谓的四年级。安民大我一岁,在价值信念上或者对文学的信仰上,都更接近,台湾的下一辈会说我们说的都是“大话”,就是所谓“言志”,现在不行了,都是小确幸。但我跟安民聊,我们确实是一代的文学中人,他会比较理解你的写作态度,写的这么少,或是有时候好比上一本书,市场热热的,你不赶紧趁胜追击,偏偏停下来,放个五六年,如果作为一个出版人,急都急死了,可是作为一个朋友,他是很理解,我自己倒不敢讲他会说欣赏,可是他会理解,还会持续出版。包括他当时在做《联合文学》总编辑,我的那些旧书也都交给他去处理。
问:顺着这条线其实我们就能想到,您经常在书中会讲到几家人同游京都或者在日本的情形,我们会在书中看到早年的张大春、骆以军、詹宏志和他们的家人,都是大陆读者很熟悉的一些面孔。可以感觉在“同游”的情形下,其实我想那也是一种几近失落的氛围和状态。
朱天心:那其实很像是周杰伦或者谁谁哪个明星,谈恋爱的时候喜欢把当时秘密恋爱的女生带到国外没有人认出来,有时候我觉得好像是那种气氛一样。一个你很喜欢的地方,有很多很丰富的记忆,当时最好的朋友,就是好东西跟好朋友分享,你很希望好朋友可以看到你,就是很单纯的。
问:在整个交流的过程中,您写到了非常多有趣的场景,比如海盟讲“不存在的骑士”来戏弄大人们还有天文逛街东看西看故意走很慢的那些东西,其实这个可能对不那么熟悉台湾的文坛和政事的大陆读者来说,很有效的切入文本的角度。
朱天心:实际下笔的那刻,就像书打开的第一个篇章一样,每次觉得京都对我来讲是鬼影重重的,你每次去的时候,其实就很像是蒙太奇的手法,你仿佛真的会看到海盟还躺在婴儿车的时候,也会看到长到跟你快一样高的时候,我们开始第一次感觉到哥们儿感情,那也是在京都。家人也好、朋友也好,我一去那个地方就好像身处在异次元空间。
问:我也能看到您在写到2005年之后,同行者的部分,就写成了“海盟”,而不是之前的“盟盟”,这应该其实也是您感觉到她成长的状态。包括像骆以军、吴继文,第一次同去的时候,写的是全名,之后就写成“以军”、“继文”。
朱天心:是,你看的真细。可能这是最自然的呈现,所以我说你读的细,而我自己都没有这样的自觉。在回忆的每一刻,都是尽可能贴着真实走,可能很自然就会留下这样的轨迹在。包括后来不再来往的,这些轨迹也都保留。
问:当然这也可以延伸到您对散文创作的观念,因为总体来讲您还是以写小说为主,像《三十三年梦》里面这种对真实的“时移事在”的轨迹的把握,包括对于“不方便的记忆”的记录的方式,其实是您过往的创作中比较少呈现的,那这是不是您所认为的散文书写的关键所在?
朱天心:散文有它很不方便的地方,作为一个小说创作,会小说创作这门技艺的人,写写可以偷懒,这个地方好难写,或者碰到困境就飞走了,所谓的虚构,就可以飞走。当然也有你不耐烦那个现实,或是你受不了这个现实,或者你讨厌极了现实,我去虚构我的黄金国度,很多作家都是这样做,像陈映真就是这样。可是你选择散文文类,你只好咬紧牙关,你碰到再讨厌的现实,再不想面对的都得去选择直面。它也可以去到小说去不到的地方,那小说可以逃走,散文就是得贴着现实走,走到多么无趣、多么残酷、多么平庸的地方,你都得跟着去。所以我也很喜欢看小说作者写散文,看他不逃的时候老老实实写到最后一刻时候,你也会看到小说看不到的地方。我最近很吃惊有一个朋友前两天跟我聊天还讲,《三十三年梦》到底是小说还是散文?我听了非常吃惊,她小我两岁,是跟我一辈的,怎么会问这个问题?《三十三年梦》里面没有一言是假的,也许可以说有些对人对事的看法是不对的,或者是有偏见、有偏颇的,可是绝对不至于说是会脱离我认为的真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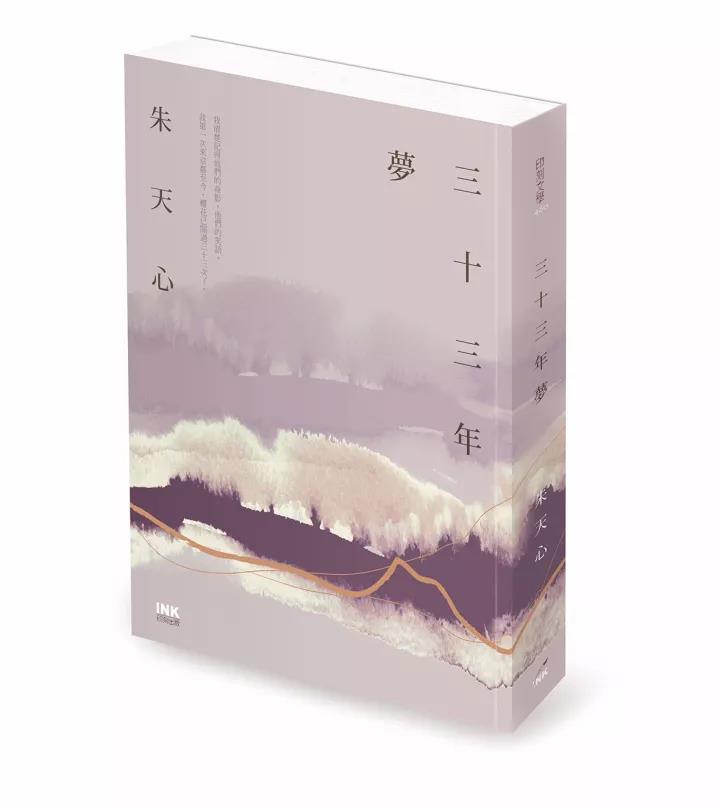
问:但是也正是这样的对“真实”的态度,您直面真实的方式,会让人不舒服,仿佛在催促着要转过身不看这一切的“不愿意面对”。
朱天心:没错。尤其你意识到同代的人或者是众悠悠之口,绝大部分的人有意一起不去“看”某些事情,因为那些你不方便面对的真相,有意遗忘或是真的无意,因为那些被标识为太不重要,太卑微或太缈小,就不再看,乃至当它不存在。尤其你在面对时更是觉得,你是在场的而且真实地看到了,你就有那个责任:你再不说没有人会说。虽然那些讲出来的东西,对很多人来讲或许是杂音,但对我来说,却非常的重要。
问:其实从您上面的论述,很容易就会呈现出大陆读者对您的习惯印象不同的一面,这也其实就体现了大陆在引进您的作品(当然也包括其他海外作家的作品)时,所一直忽视的那一面,就是您刚毅的、诤言的,被阿城老师称为“纯阳的”书写,就比如收在《小说家的政治周记》、《我记得……》里面的篇目,您在现实政治中的“参与”等等,而这一切您其实也都写在《三十三年梦》里面,可以说让您的大陆读者——他们可能是在通过《击壤歌》认识您的、停留在八十年代浪漫化的“文学往事”想象之中——必须对您有个认识上的转变,甚至是有一些突然的。
朱天心:在大陆的出版上,我其实都是很被动的,并没有刻意要做什么的(经营),当然如果现在有出版社要做重新的整理,我会给他们建议。我记得,最初是苏伟贞找到我和天文,说有大陆的出版社要出华文女作家的书系,后来知道是广州的花城出版社,像《方舟上的日子》,就有机会跟大陆读者见面。再之后世纪文景、上海译文都有一些,是大陆的编辑重新编选过,顺序上有调整,再后来是到理想国。当然如果能够按照我自己作品集的顺序,一本一本看起来,就比较可以清楚看出我的脉络,从一个年纪很轻胆大妄为写东西的人,怎么会发展到后来《想我眷村的兄弟们》、《古都》,包括再之后的样子,那就可以很明了:其实那个关注和关怀是一直在的,我觉得跟我那一代人受的教育有关系,甚至跟家庭教育也有关系,就是觉得人不能这么“自活”,要能够看得见世界、看得见社会。还有很多会像我们那代人的教育,现在觉得很八股地讲中国的命运,那时候我们自己觉得我们是中国的,你只要是念过书的人,对这些或多或少都有责任。胡兰成老师教我们的这些,你不大可能只甘心做一个小说写的很好的人,现在知道这个多么困难。其实那个关注和关怀一直在这,你旁边正好碰到的某些朋友,你更近一步知道处境的急迫,你会觉得写文章太慢了,你写小说久了你会知道它有它的酝酿期,就像胎儿一样,怀胎两个月就把他给揪出来会害了他,那时候我会去做一些社会参与,当然你做这些,你会碰到越多在做这些少数边缘的人物,你看到他们缺乏资源,缺乏发声的管道,这么辛苦的时候,我自己会有非常大的道德压力。
问:您讲到这里,刚好我们就可以切入具体的文本来讨论了。您在写到2012年6月的这一段的时候,有讲到江一豪和“三莺部落”的部分,这恰恰就是您前面提到的“边缘人物”跟“社会参与”的描述,而里面在写到一豪的妻子(现在讲应该是“前妻”)黄惠侦的时候,就很妙的一笔带过:“那拍纪录片的妻子黄惠侦又是另一个精彩的故事了”。当然当年连载的时候还并不清楚,我们现在就很知道的,是她将自己和母亲、家人的故事用纪录片呈现,拿到了刚刚结束的台北电影节的“最佳纪录片”奖,而这部片子(《日常对话》)也是由侯导来监制的,可不可以请您来谈谈,这个在书中没有提及的“故人故事”,有怎么样的精彩?
朱天心:惠侦这个人,有一种力量,一直以来她拍的都是公益或者弱势的纪录片。我以前很怕她,很多次不管是开会或者街头抗争,她都是冷着脸不说话非常严肃,我觉得这个人城府好深,你会清楚知道她不是一个拍摄工具而已,她把自己的情绪管理的好好的。到后来第一次看到她的纪录片的时候,我会非常的讶异,因为我看过很多人做弱势的发言,他会让观众觉得整个社会都欠他的,所以他有任何什么不堪东西都是应该的。可是惠侦非常柔软,她自己在做这些事的时候,先拍出短短的,然后参加一个纪录片奖得10万块,再扩充成半个小时,再去四处投,大家看到就承诺她多个100万,你把它剪成90分钟,电视可以播。她就拿这100万继续弄,其实她资料都在。后来我就把她拉去跟侯导见面,NHK日本的找她,就是中间有一些比较复杂的事情。后来侯导看过素材答应帮她监制,NHK省掉很多,因为是侯导,必须要符合他们的文书流程都不用了,她就一步一步做,做到今天这样的规模,是我很喜欢的方式。你做这些,并没有人逼着你做这些,你做那一刻你会知道后果,从此没有什么什么了,你必须做什么什么,都是求仁得仁。我很怕人家做一点点就哀哀叫,怎么都欠他,她完全不是这样的。如果以后有机会的话,会讲到这一块。
问:当然从另一个角度,我们可不可以说,您对待其他创作者的态度,或扶持或推拒,这些也都体现了您在面对自己的创作历程的时候,一些特别的选择和在自己的“脉络”里发展出来的某种独特的看法? 您在1994年10月的部分,也恰好比较多地写到了“社会参与”的这一个层次。
朱天心:其实应该是说大概在我自己最盛名的时候,三十几岁的时候,正好是台湾解严前后,变动最大的时候,我觉得作为一个作家或者创作的人,其实不可能不被波动,我说的不一定是参与,而是你会充满了,我觉得是困惑多过其他。你熟悉的世界,因为台湾确实是不同的族群,你对历史的记忆都是经过外塑过的,就好像从不知道作为本省人在童年时代被压抑到这种地步,不光是语言,可能是戏曲都被看成比较没水准。不同族群之间最先学到的话都是脏话,你听到的东西就是这个样子,所以你会对那个族群也会有一个比较没有教养,比较没有文明的印象,不同族群接触上的碰撞,这些都势必会有。解严前后的百花齐放,所有不能说的全部可以说了,不该看的也全部看到。对你过往熟悉的世界几乎被捣毁的状态,作为一个创作者,只要是够认真的,就得去面对这些不熟悉,而不是说我只好视而不见,我觉得太难理解,那我还是会过我的“小日子”。在我看来是不可能这么做的,其实只是很认真把我自己的困惑,废墟或者是瓦砾,怎么样一块砖一片瓦地重新(垒起来),我觉得我其实一直在做的不过是这样的事情。
问:这是不是也就呼应到您前面讲的,对于“散文”这个问题,您的要求,或者说准则?
朱天心:对。一样作为散文书写者,作为在场的人,你要怎么锻炼自己的勇气和目光,不把目光回避开或涣散掉,没看到,或者你看到了,你却有没有这个勇气把它讲出来,我觉得对我来讲都是很高难度的事。但原本我不觉得是高难度的,觉得是有趣的事,可是看到当下之人,这么多人把目光调开的时候,才知道原来这是一个难的事情。
问:那如果从更宏观一点的角度来看的话,是不是您这样的态度与视角,也同您所处的世代,以及台湾的这个世代本身所经历的事情息息相关,这些外在的事件也从某种程度上塑造了您这一代写作者的心性质地?
朱天心:“打不死的四年级”,台湾会用这样的说法,就是1950年代生人。我们确实是打不死的四年级,台湾经济不好已经很久了,人们对文学的萎缩的态度,不是去正视这个问题,而是东怪西怪,觉得“四年级”把资源用光了,把位置占光了。在其他行业的话,我完全同意,因为其他行业一个公司CEO就一个,你不退下来,下面升迁很难,可是在文学里面大家各写各的,各出各的,各登各的,没有谁挡谁的问题。我自己会觉得像四年级写作者,你读一天书,你就要对社会或者这个地方有所回馈,我觉得是这一代人,不管个性怎么样,有些很虚无,有些其实也是顽童散漫的,但基本上跟你都有隐约的责任关系在。我也觉得四年级的这一代是心智最健全的一代。四年级他看过台湾发展的成就,他也看过国民党的暴行逆施,他看过热血青年,那种抛头颅洒热血,牺牲自己的青春甚至生命,他也看过各种社会上的腐坏堕落,所以谁都别想骗我们。你是最不会被洗脑的那一代,你的人生是顺向走的,人生是正向的,我觉得跟下面一代不同的是,后面的世代他们很难去辨别,他没有经过战争的尾巴、贫穷的尾巴,他很难分辨这个是一个宣传,或者这是一个假造的历史,不管对哪一边,国民党也好民进党也好,所以这上头的认识是不扎实的。所以我会觉得整个四年级是心智健全,再加上他是有这个责任感在,但是很难轻言退休。
问:对,这个族群裂解的状态可能又会被政治所利用,就好像现在在台湾,“年轻人”这个概念几乎是一个政治概念,很特别,它不以理念来划分,却包含着巨大的意识形态意味。
朱天心:每一代人本来他的学习就是纵向和横向的,纵向的跟历史、跟长辈的学习,我说的历史也不是学院里的历史,你知道过往,知道你出生之前的事。横向的,我觉得现在网络的出现,会把同辈间的影响力放大无数倍,像所谓“同温层”,会使得你对你出现之前的人、事、物毫无兴趣。
问:这一点在阅读上特别明显,您也是经常讲到您的担忧。
朱天心:没错,我甚至会觉得他们有时候会倒过来,我不知道大陆现在的阅读状况是不是有类似的,是网络上不存在这个名字、没有人热议的话,那就不应该“关注”。就好像有一次我跟两个学生,我记得我在其他访问里面说过,她们叫我来推荐书,我先介绍张爱玲,她们说:“张爱玲?她不是死了好久吗?”那我心里想说,看来托尔斯泰这一票人都不用读了。讲个活人吧,我说白先勇,她们说“那不是一个老头嘛?”没办法。最后我说陈映真,她们说好,那陈女士的名字怎么写?她们会觉得网络上有这个人吗,要马上Google“她”。我觉得互联网时代,把他们自己变成是一整块的,文学没有优劣好坏,重要的就只是他们自己的看法,好像在这里有一点不同的想法或者不同的声音,都真的是在找死。这样的局面,你很快就会把自己做改变的想法给压抑掉、否定掉。作为一般人的话,我OK,这样的生活比较好过,比较安全。可是要是作为文学艺术的养成,我觉得是一个很伤的事情。
问:而说到文学的养成,也就涉及到文学的建制面,特别是文学媒体、期刊这样的载体,也包括文学奖。以前的时候编《三三集刊》,就是您参与文学建制的一个阶段,所以想必您也会越来越注意到,现在台湾以文学为名的刊物,很多都是在用一些小的题目的吸引目光,有的甚至成了设计精美的产品图录。那如果让您来做选择,一种文学刊物是有精准的市场定位,族群分析,以及清脆可口的短文章,很多小杂志都是这样,可以一个下午快快翻完,轻松加愉快的,配一杯还不错的咖啡加上甜品,而另一种是严重的、深沉的、作者导向的,有时甚至是晦涩费解的,但也只有这样才能够体现出作家真正想要做的事情,真正想要写的内容的刊物,您会怎么选择?或者您会建议读者怎么选择?
朱天心:我当然是倾向后者。毕竟我们谈的是“文学的养成”,那里面都是马虎不得,就好像我前面讲的那个反面例子,所谓“同温层”。这里面好像也有个自尊心的问题,你说的时候就代表他这个是很微弱、显得不重要,只会觉得基于自尊不好叫卖:当你开的是一个很好的餐馆,认真在做菜,门口卖盐酥鸡的倒门庭若市的时候,我很难讲那个心情。通常面对这个的时候,只能说那你就自己再怎么样,并非怕得罪卖盐酥鸡的摊子。你很难讲我自己存在比较有意义,或者我做的比较精心、比较营养、比较有健康,好像无法去讲这些话,你只好让你的店还活着。
问:就好像当年白先勇他们当年编《现代文学》,洛夫、张默、瘂弦编《创世纪》,怎么可能会有一个主题先行,或者行销路线。其实当年的《三三》也是在这样的线索里,作家、诗人是在自己的创作里,作家与作家之间可以有竞争、有较劲,但那与“订制生产”毫无关系。白先勇写《明星咖啡馆》,就是这么个“作者本位”的氛围。
朱天心:是这样,是应该这样,可是我觉得很难了。台湾现在不想大事情,第一个消失的是文字或者文学,因为他们不需要这些了,可能需要的是图像或者刚刚讲的图录、物件、购物指南。即便它还是有文字的形式,负载的再不是这些“文以载道”的价值。文学的流失、消失,跟不再想大问题有关,这些好不舒服,好没有必要,因为你从研究文学,它通常就是挑战你各种既成的观念、刻板印象,就觉得好不舒服,我待会再来,或者我干嘛要看,干嘛啦,我宁可看看我脸书上撒哈拉的朋友今天讲他的一顿餐或者讲了什么,宁可看这些。
问:其实文学也就变成脸书了,只是一个纸质的,可能是名牌设计师设计的,看起来很精美的。
朱天心:大事是这样走,可能很难,我是觉得《印刻》的存在就是很值得珍惜的,可能也很难再会多一个,我觉得它是一个结果,不是一个可以操作而改变的。
问:这样也就要说回到您自己的文学养成上来,您前面说您给年轻的朋友介绍白先勇老师,那您年轻的时候,是不是也读白先勇老师的作品呢?
朱天心:在我小时候,我的阅读量是很大的,总是同时阅读很多作家,但是有时候就只看单一品类,一直钻进去的。他是介于我看琼瑶和张爱玲之间的时候,那时候看白老师,觉得看了他的再不会看琼瑶的东西了。再后来,我到了一个年纪还是会记得他曾经伴随我某个年纪的那个很温暖,或者觉得文学原来可以是这个样子,我已经过了割脐带的感觉,会想过他曾经给你的温暖。
问:他的几个作品里面对您产生影响更大的是哪个?
朱天心:我还是喜欢他早期那两部短篇集,主要还是《台北人》。
问:这确实是有趣的:如果从现在台湾最普遍采用的族群分析的范式,您对《台北人》的喜欢,会不会是因为您以及您的家庭也同样是这样的外省背景,所以反映到文学的欣赏和吸收上,就有了一个认同、或类似认同的感觉?
朱天心:不是这样。读白先勇,我那时候是国小五六年级的小孩,他吸引我的是文本中的一个沧桑感,我非常喜欢人物在时间里面的那种沧桑,倒不是很意识到族群的感觉,好比说我们同样都是1949年到台湾,由父辈带来过的,其实我的家庭一直是军中的中下阶层,所接触到的跟他小说里面的世界是完全不同的。倒不是族群的认同,反而是一个沧桑感,从文学的本有而来。
问:说到文学和人格的养成,在访谈的最后,也就要说到胡兰成先生,1979年5月与他同游京都,也是您书写《三十三年梦》的开始,不知道从今天来回看,他对您有着怎样的意义?
朱天心:我们那一代的小孩读西方东西远远多过读中国的,这其实是延续五四的那种气氛,觉得全部中国东西都是必须被舍弃、抛弃的,全部读西方的;胡兰成老师他的出现,是带我们补修中国学分,一点一滴从中国的东西学起。在我自己的整个人的构成中,当时觉得很辛苦,可是事后我会觉得走过那段,非常的幸运。他的出现在我们人生中也就是两三年,而且也不是朝夕相处的,只有一个夏天,听他讲《易经》课,或者讲禅宗的,每听必打瞌睡,因为他的浙江口音非常重。可是我觉得他就是那种打开你的视野,告诉你这个世界多大的人。我还是很感念他。
问:所以也就是早年的这样一种“士”的养成,才让这样的“记忆之书”(骆以军语)有了如此的坚韧、与现实逼视的力度。这也就是杨照老师在序里面强调的,您的“价值、是非判断”,其实是阅读《三十三年梦》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角度。
朱天心:对我来说,包括阅人阅事很难是抛开价值问题不谈,很难单独说这个人跟我很好,对我很好,我就放弃掉去用一个比较大的脉络甚至是历史这样的眼光去看他。直到后来我才会发现身边大部分人看人,就是凭借是彼此的“关系”,他对我好,我就不检验他了,可以把你的价值信念在个人感情上去放假。
这一点我好像始终很难做到。(本文节选稿发表于腾讯文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