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皱褶的文字,藏着什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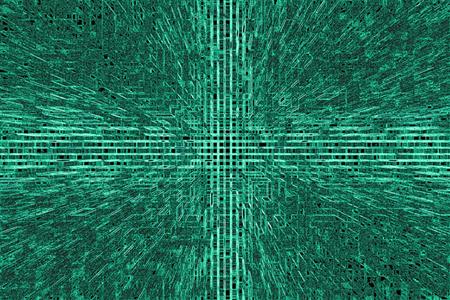
视觉中国
阿根廷作家科塔萨尔短篇小说集《南方高速》中文版,近日由新经典文化推出。
科塔萨尔是拉丁美洲“文学爆炸”代表之一,世界上有许多作家对他非常推崇,如马尔克斯、聂鲁达、莫言等。
在一场主题为“异次元漫游的文学大师科塔萨尔”读书会上,作家格非为读者解读了科塔萨尔独一无二的文学创作和迷人力量。他认为,对读者来说,科塔萨尔还是一个有待去猜的谜。
如同一张折纸
主持人:今天我们谈论的主题是“异次元漫游的文学大师科塔萨尔”。所谓“异次元漫游”,是指科塔萨尔的小说似乎能把读者带入一个奇特的、多维度的空间。他笔下的一切,如同一张折纸,折纸里一重重的世界会让读者目眩神迷,欲罢不能。它们好像在告诉读者,你所熟悉的那个世界、那个人可能隐藏着很多奥秘,你觉得无趣的日常生活可能是日复一日的奇迹。
科塔萨尔身上有许多标签,比如,他是拉丁美洲“文学爆炸”代表之一,他是博尔赫斯的精神之子。世界上有许多作家对他非常推崇,如马尔克斯、聂鲁达、莫言等。
科塔萨尔的确是一位迷人的作家,他的作品也逐步被翻译成中文。请问格非老师,您最早读到科塔萨尔是什么时候、有什么样的感受?
格非:我最早接触到科塔萨尔的作品是在上世纪八十年代我上大学的时候。那时候,袁可嘉主编的《外国现代派文学作品选》,外国文学刊物《外国文艺》和《世界文学》上发表了一些他的作品。这些作品中我印象最深的是《被占的宅子》,我读了很多遍。从此,我就特别关注这位作家。
主持人:读者读科塔萨尔作品的第一个感觉是,他的作品当中充满着奇思妙想,但读着读着,又会发现内容与现实有着强烈的关联。您怎样看科塔萨尔式的幻想和现实?
格非:我觉得,世界上有两种类型的作家,以拉丁美洲作家为例,有一类作家如博尔赫斯、马尔克斯,他们不同时期的作品之间有着内在的统一性。如果读者顺藤摸瓜一部部作品去追溯,可以找到一个清晰的线索。
还有一类作家,他们的写作会在各个方面展开自己的探索,包括幻想性与现实性之间的关系。我原先读科塔萨尔的时候,觉得他是幻想类的作家。但是,当我读他的短篇小说集《南方高速》的时候,我读了前一篇小说,不知道下一篇小说他会写什么样的故事,关注什么样的社会生活。这太让我吃惊了。
我觉得,喜欢写作的人一定要读科塔萨尔。科塔萨尔是一个宝库。尽管,他的每一个作品未必都那么完善,能带来文学史上的某种典范意义,但他的变化不定,特别迷人。让我震撼的是,他的探索,不管是内容、社会风貌上的,还是故事形式、叙事技巧上的,都是不知疲倦,没有停下来的时候。
世界上很多作家在悄悄地模仿他,在悄悄地利用他的资源。因为,他不像得诺贝尔文学奖的作家那么红,他的资源还没有被完全挖掘出来。世界范围内有许多作家或多或少和科塔萨尔的写作建立了联系,比如刚刚斩获诺贝尔文学奖的英国作家石黑一雄,其成名作《长日留痕》与科塔萨尔的小说《为您效劳》十分相似,可以说前者是后者的拓展版。而对读者来说,科塔萨尔还是一个有待去猜的谜。
对世界的洞见
主持人:马尔克斯在纪念科塔萨尔的一次演讲《人见人爱的阿根廷人》里说到,偶像让人妒忌、让人依恋,当然也让人深深崇拜。“翻开《动物寓言集》(编辑注:科塔萨尔出版的第一部短篇小说集)的第一页,我就意识到他是我未来想要成为的那种作家。”
格非:我不能说,科塔萨尔的作品比博尔赫斯的好,或者比马尔克斯的好,因为,关于这个“好”,每个人有不同的看法。
但是,我读科塔萨尔作品的时候有一个明显的感觉,即他可能是马尔克斯、博尔赫斯、略萨这些人的结合体,这些人的作品所涉及的东西,他都涉及了。比如,关于拉丁美洲的孤独、对现实政治的批判、对历史和日常生活的关注,以及幻想性,科塔萨尔都进行了自己的探索。
我推荐大家读一读《南方高速》里的那篇《追寻者》,这篇小说恐怕是我最近五六年来读到的最好的小说,小说人物是以萨克斯演奏家查理·帕克为原型创作的。这篇小说采用的是现实主义写法,没有玩弄一点点的花招,就是用传统的老套路,把一个故事、一个人物,以及一个奇特人物和他所处时代的关系,写得极其清楚。我看了之后,非常感动。
主持人:科塔萨尔有一次接受采访,有人问他,你写这个小说想表达什么,意义是什么?科塔萨尔回答说,你想多了,我其实没有什么目的。您觉得,关于创作的目的,他是不是真的如他自己所说的那样?
格非:这是一个有意思的问题。比如,我们问歌德为什么创作《浮士德》?歌德当年说过一段话,他说,存在是我们每个人的使命,我们来到这个世界只有一个使命,就是我们存在过。我觉得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小说家为什么会描述光怪陆离的世界,是为了穿透现实抵达这种存在感。我存在吗?有意义吗?是一个又一个的追问。所以,我推荐大家从《追寻者》开始读科塔萨尔的作品,读了《追寻者》大概就能对他的世界观有所了解:他怎么看世界,他的价值观、他的哲学观、他的好恶。作品比较完整地反映了作家对世界的洞见。
如果非要比较科塔萨尔、博尔赫斯和马尔克斯三位作家,我认为科塔萨尔更接近博尔赫斯。因为从本质上来说,科塔萨尔和博尔赫斯一样是个哲学家,有自己完整的哲学观和世界观。但科塔萨尔又十分不同于博尔赫斯。博尔赫斯的哲学观念主要通过书籍表达,善于在幻想中建立一种知识,并在知识材料中呈现荒谬感和虚无感,最终在抒情性中找到人的慰藉。科塔萨尔的哲学观念不是从书籍里来的,而是直接从现实的感受性中来的,从中他看到了荒谬和虚无。
看到虚无怎么办?博尔赫斯是从来不让步的。曾经有记者采访博尔赫斯时问,一个人活一辈子有意义吗?博尔赫斯眼睛眨都不眨地就说,没有意义。当记者起身准备离开时,咖啡馆里放起了音乐。这时,博尔赫斯说,等等,我要把刚才的答案再修改一下。这个答案是什么?他说,只要音乐还在继续,生活还是有意义的。我想,这大概是博尔赫斯对“虚无”做的最温情的一次让步。
而科塔萨尔则会在对现实的思考里,直接呈现出温暖的一面,并且,这种温暖时不时地出现在他的作品里。
看到别人没看到的东西
主持人:《南方高速》收录了科塔萨尔的三部短篇集,分别是1959年的《秘密武器》,1962年的《克罗诺皮奥和法玛的故事》和1966年的《万火归一》。其中,《秘密武器》中文版是首度面世。您觉得这三部小说集各自的特点是什么?这些特点是不是能说明他写作风格的变化?
格非:作家不可能永远到一个井里打水,如果那样做的话,这个作家很快就会被大家厌烦。作家要有写作的激情,是激情支撑着他完成他的工作。
一般认为,《秘密武器》代表了科塔萨尔在短篇小说创作上风格的成熟。《克罗诺皮奥和法玛的故事》是一部文体上难以归类的作品,也是科塔萨尔最受喜爱的一部短篇集。《万火归一》则被视为科塔萨尔最具代表性的短篇集。
我认为,《克罗诺皮奥和法玛的故事》相对比较抽象,但十分精彩。它展示了一个作家对现实的高度的概括能力,好像是穿透现实看到了别人没看到的东西。就像作家托马斯曼说的,一个伟大的作家必须具备两样东西:第一,你必须看透这个现实;第二,你必须具有魔法般的能力,会变戏法,把这个秘密告诉大家。科塔萨尔的作品呈现出了这两样东西。
《秘密武器》里前面两篇都是超现实主义作品,读者看的时候,会觉得像看安东尼奥尼(编者注:意大利导演)的电影。后面的作品又有了新的写法,作品和作品之间的间隙非常大。可见,那个时期的科塔萨尔的思维是多方面的,兴趣也是多方面的。
写第二部《克罗诺皮奥和法玛的故事》的时候,他可能有意识地想写一些童话般的、神话般的、更简单概括性的作品,所以,小说集里的这些作品内部具有统一性。
第三部短篇集《万火归一》里几个作品之间的主题都具有某种关联,也更加整饬,是一位成熟作家的一种非常好的状态。你可以感觉到他的笔触、技法,既不“过头”,也没有“不够”,可以说是恰如其分。
主持人:《南方高速》中的第一篇《魔鬼涎》启发了安东尼奥尼拍摄电影《放大》,《南方高速》也被改编成电影《周末》。您如何看待科塔萨尔小说和电影的这种关联?
格非:电影可以跟电影比,但是千万不能跟小说比,这是不对的。如今的读者总是容易犯一个常识性的错误:这个小说我没看过,可是我看过电影。看电影跟看小说是两回事。比如,石黑一雄的《长日留痕》和《别让我走》很好看,这两部小说的好看,完全在于写作笔法。笔法里有着一种淡淡的反讽,以及对于情感的极其微妙的把控。如果改编成电影,这些元素必定会损耗。
电影是通过画面,小说是通过文字。而文字是有皱褶的,就像衣服的皱褶一样,里面藏着很多东西,跟电影完全不同。比如,《万火归一》小说中有一个场景:一个角斗士被剑扎在地上,他的肩膀在微微颤抖; 一位总督和他的夫人在旁边目睹了这一切; 总督夫人和角斗士是情人关系,可是她不能让总督发现这种关系。因此,在那个当下,她一方面因为心爱的人将死非常痛苦,另一方面又需要在总督面前装出一副高兴的样子。这就是文字拥有的奇怪力量,而电影难以处理。
所以,尽管我认为科塔萨尔的有些作品很适合拍成电影,但小说和电影是两回事。我们读小说读的是文字,作者用这个词没用那个词,这里面的味道是不一样的。读者要去领悟文字带给你的魔力,这种东西是文学的力量,是永远不能被改变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