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为母亲的选择” ——我译露西·考德威尔作品
翻译露西·考德威尔的作品,对我而言是一个很容易做出的决定。露西是“80后”作家,也是两个孩子的母亲,仅凭这两点,她便成了我从事翻译工作以来距离最近的一位作家。露西从不避讳母亲这个身份,她笔下事无巨细的育儿细节,敏感而深邃的为人母的心绪,常常道出我所不能言。我曾开玩笑地对编辑说,感觉不是在翻译,而是自己在写。这句话实属僭越,但的确是我某些时刻的真实感受。
和中文世界的大多数读者一样,我读的第一篇露西的作品,也是《所有人都刻薄又邪恶》,这篇小说获得了2021年英国BBC国家短篇小说奖。在露西的作品中,它的确很有代表性:第二人称,细腻的心理描写,一种不断往复叠加缠绕的文字质感……最重要的是,它完美地呈现了露西反复书写的主题,即母亲是一种生存状况。小说写了一位带婴儿的母亲与一个陌生男人在飞机上的邂逅,但这并不是一个单纯的浪漫故事,男女之间的张力具有更微妙的色彩。在飞机上手忙脚乱的母亲渴望平静、渴望秩序,她渴望获得帮助,但又害怕引起别人的注意。更重要的是,在公共场合,女性的社会化程度往往是遭到贬抑的,一位全职带娃的母亲就更是如此,她该如何讲述自己的故事,维护自己的存在呢?或者,从本质上而言,如何讲述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她身处的状况激发了她讲述的欲望。所以我们看到,女主人公对男人讲到了表姐的去世;讲到自己是一名建筑师,尽管职业生涯已名存实亡,但建筑师的训练依然塑造着她的日常生活;她甚至谈到要不要再生一个孩子,同时回忆起了那些早早步入婚姻的密友。后来,话题逐渐变得富有形而上色彩:人的善恶问题,生命演进中的“距离”问题,以及人究竟能不能真正改变,跨入另一重境界。很显然,女主人公渴望的并不是简单的闲聊。为了养育孩子,她的大部分精力都游走在生活表面,但她渴望潜入意识深处,与他人建立更有效的连接。这些看似漫无边际的谈话维系着她的自我和自尊,让同为母亲的我产生了一种深深的切肤之感。
但露西并没有直接越过生活表面的纹理,“他留下看着婴儿车、旅行袋和正在充电的手机,你把哭啼啼的蒂丽托在髋部,去洗手间的水池边刷奶瓶,然后去Costa讨要了一点热牛奶。你本可以自己喝杯咖啡,也该请他喝一杯,但你腾不出手”。她的笔从不回避这些小事,不惧重复,也不惧琐碎。在我看来,这远不是一种写作技巧,这是一种诚实,因为正是这些琐事、这些几可拆分到具体动作的母职日常,催生了观察和认识,甚至催生了写作本身。露西在一次访谈中说,“我一直很想要孩子,但也担心这会终结我的创作生涯。没想到的是,反而是母亲身份让我成为作家——任何让你在个人层面上更脆弱的事,都可能让你在艺术上更有分量”。这让我想起了自己带着小孩在游乐场度过的时间,在那些不容分神的时刻,阅读和思考犹如探出水面的吸管,让人倍加珍惜,甚至对阅读和思考的渴望都带着一种甜美的色彩。那些看似虚耗的时间,同样蕴藏着丰厚的养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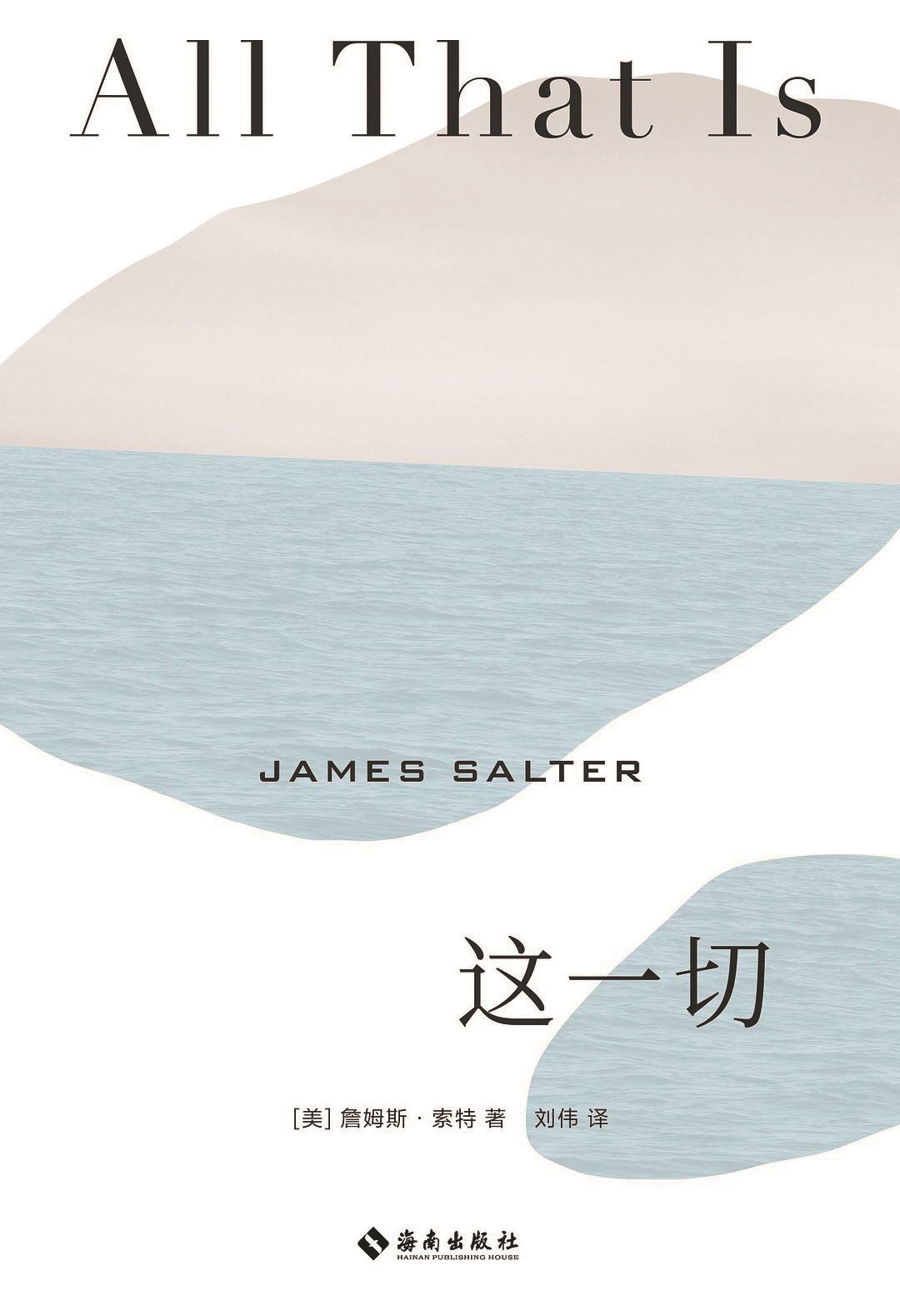
露西的另一篇小说《如此这般》,也呈现了普通母亲的日常。她细细描述一个母亲如何观察环境。她或主动或被动地透过孩子的目光看待周围的一切:观赏池、金鱼、商务区的餐厅,还有餐厅里排队的人群。她要不停地做出判断和选择,这种对环境的嗅觉近乎动物本能,放大了感官,甚至放大了肢体动作。露西像写行动指南一样,详细拆解如何在餐厅里安放婴儿车和儿童座椅,如何点餐,如何带一名男童如厕。这些琐碎的事在一位母亲眼中无一不显得重大,这是她作为母亲的训练,更是她作为一个人对生存状况的感知。最后,在类似现实和幻想的交叠之处,她弄丢了一个孩子,她精心选择的环境背叛了她,她作为母亲的嗅觉背叛了她。这是一个失败的时刻,充满悲剧意味,人在和环境的对峙中败下阵来——围绕这个主题,文学发展出了数不尽的形式,露西把这个主题浓缩到一位母亲的日常行程之中,同样具有惊心动魄的效果。
巧的是,这两篇小说使用的都是第二人称。露西是我见过的最喜欢使用第二人称的作家。第二人称使用起来很难,有时也并不讨喜。它不像第三人称那样拥有全知视角,坦然地做上帝,也不像第一人称那样坦然地化身为人物,为自己的一举一动负责。第二人称是一种游离而分裂的视角,时而是叙述者,时而变成人物,常常显得脆弱而自大。但在翻译露西的作品时,我发现,第二人称天然地具有一种女性主义的色彩。它有一种内观的意味,直面脆弱,直接书写人的自我关注。它不假装真理在握,也不是一个笃定的行动者,它保持着开放性,保持着永不间断地自我探索和对话。
露西很喜欢用第二人称描写那些正处在自我建设或重建中的人物,比如青少年,比如新手期的妈妈,尤其是后者,她们正处于一段破碎而震荡的时期,孤独感是前所未有的。比如在《奉献》中,“你”刚刚结束圣诞假期,和丈夫孩子一起驾车返回伦敦的小家。无论从哪个意义上看,这个妈妈都不孤独,她被家人环绕,她的丈夫看上去很可靠,能够熟练地照顾小孩。但是,她一路上的种种遐想却深邃而飞扬,脱离了小家庭的藩篱,宛如独处。正是这第二人称的“你”,帮她从家庭和母职中抽身出来,她一方面回到了自身,一方面又触及到了更广泛的母性:“你想起了所有那些在你体内、在你脑中一闪而过的孩子们:你跟他们从未谋过面,从未亲吻过,从未拥抱过;但你在爱那不可测量的深度和范围内承载着它们。”一个新手期的妈妈可能很少有机会独处,但她需要练就一种内心的功夫,为自己创造出宛如独处的时刻。露西帮她笔下的人物做到了。
露西关注的另一类人是儿童和青少年,其中缠绕着她的私人记忆,也事关生命初始期的迷茫和顿悟。对作家而言,成年之前的记忆永远是一座富矿,它牵系着作家的直觉,那灵性未泯的眼睛常常能发现重大的主题。在露西笔下,那些尖锐、反常、不和谐的瞬间从来都不简单,即便成年之后,人也会一次次重返那些时刻。

比如《留在这个世界的理由》的首篇《阿里阿里哦》,紧凑而克制,是我特别喜欢的一篇。小说仿佛一个记忆切片,我们要靠种种细节才能体察到主人公的状况:生在一个多子女家庭,要不停和姐妹争夺母亲的注意力;对灾难有异于常人的好奇,而露西用一处隐笔暗示,他们后来的确经历了一场灾难,失去了小妹妹;他们的母亲是异乡人,喜欢开车带他们探索这个城市,这也是她逃脱繁重家务的方式。在一个儿童的视角中,这一切都是模糊而破碎的,但又处处充满暗示,让人无法挪开目光。未来如同大海灰绿色的雾墙,“巨大、脏脏的锯齿状冰山若隐若现”。这是一种原始记忆,并不确凿地指向某个固定的主题,却蕴含了一个人对生命的直觉。而任何一种原始记忆都是值得记录的,通过它们,我们才能看到生命丰富的底色。
露西的青少年主人公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即她们实现社会化的方式是非常规、非主流的,比如通过结交人群中的异类来探索友谊的本质,借助“陷害”的方式揭穿师生间的权力关系,甚至借助“死”来探索“生”,从这个意义上说,露西简直洞穿了青少年叛逆的本质。我个人非常喜欢的一篇是《追逐》,在这个故事中,主人公探索艺术的方式是堕落。“我”是一个学习艺术的女孩,在伦敦读艺术学校期间不小心沾染了毒品。于是“我”选择从学校退学,回到贝尔法斯特的家中暂作调整。在“我”的描述中,滥用药品是一次非常偶然的行为:“我们之所以要做这件事,只是因为我们年轻,在读艺术学校,而且时值期末聚会。对我来说,原因也没有任何不同。我无法解释原因是什么,或者为什么会这样,我并没有什么创伤要消除,也没有过奇怪或惊人的想法……”“我”的举动是一种盲从,是融入集体、融入都市文明的投降之举,幻想吸毒能让自己更符合关于艺术的刻板印象和陈词滥调。“在过去的一周里,他们一直在谈论柯勒律治,雪莱,还有托马斯·德·昆西,谈论地下丝绒乐队。”一个懵懂的年轻人接近艺术的方式,是拥抱那些泥沙俱下、带着巨大破坏力的因素。幸运的是,她逃脱了,不惜让自己的生命中出现了一段空白。回到家后,她认真观察并参与到妹妹的艺术项目中,发现了艺术简单直白、没有野心、不计得失的一面。只有在非常偶然的情况下,主人公才对妹妹的项目表现出赞赏,大部分时间她只是机械地做着和艺术相关的种种,不时闪回那段痛苦的回忆,前方依然迷雾重重,类似的探索还将继续,还会重复,甚至会贯穿人的一生。
虽然同为“千禧一代”,但露西的成长环境和我是截然不同的,她故事中的未成年人有更开明的父母、更丰富的物质文化环境,面临的选择也更加多元,但关于成长,有一种痛苦是相通的,那就是视角受限的懵懂之苦。人在看到更广大的世界、练就更成熟的心智之前,不得不承受家庭、学校和同伴带来的幽闭而矛盾的氛围,那是一种没有选择的痛苦,人只能在一方小小的天地里做一些不得章法的探索。或许是为了回应这种痛苦,露西把《留在这个世界的理由》放在了全书的最后,视角变成了母亲,写了她和生病的新生儿在病房里的消磨,以及人在那种情境下对于生命意义的渴求。到了最后,哪怕全部理由都失效,生命依然有可能因为纯粹的祈祷而停留。在这一篇里,那个未来要承受无数育儿之苦的母亲对孩子说:无论如何,请留在这个世界。

刘伟,英语文学译者,译有詹姆斯·索特《这一切》,杜布拉夫卡·乌格雷西奇《狐狸》,露西·考德威尔《留在这个世界的理由》,雷沙德·卡普希钦斯基《十一个时区之旅》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