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鱼亥豕,应能避免
近期,某知名出版社一本新书因编校疏漏被读者指出数百处文字差错,且类似问题并非个例。相关话题引发广泛关注,也再度将出版物的编校质量问题推至公众视野。
本报为此邀请业内专家、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编审卫建民,从出版业的旧事谈起,细数一些前辈学人于字斟句酌间较真文字正误的往事,回望传统出版流程中精益求精的匠心。希望这些旧闻轶事,能唤醒出版界对编校质量的敬畏之心,重拾严谨细致的工作态度,以更多制作精良的书籍,回馈每一位读者的信赖。

1949年上海观察社发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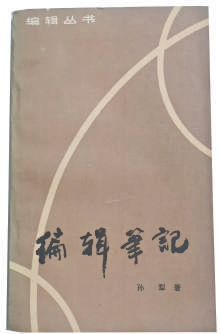
山西人民出版社1985年出版
王力(笔名王了一)先生的散文集《龙虫并雕斋琐语》,于1949年由上海观察社出版后,多年没有再版。上世纪80年代,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发现这本学者散文的价值,雇人从旧版抄录,印行新的版本。新版出版后,王先生寄给作家刘绍棠一本——刘绍棠在上世纪50年代曾短期就读北京大学中文系,与先生有师生之谊。师生互赠著作,本来是学界文坛的平常事,不料今此从燕园寄出的书不平常。
老一辈名家于细微处较真文字正误
原来,刘绍棠收到书后,发现王先生亲笔做了一张勘误表,把书中印刷的错误一一改正;一本169页的书,错讹误植竟有68处!惊叹之余,刘绍棠给《北京晚报》写了一篇文章,对出版社的粗制滥造提出批评,标题是《大学者的一件小事》。文章发表后,读者纷纷给晚报来稿,继续批评其他出版物出现的错误。王先生也给晚报写信,说后来再检查,发现这本小册子的印刷错误有110余处,要求出版社再版时更正。169页的书出现110余处错误,几乎一页一个错误,这样的出版物真是不堪卒读!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知错便改,立即毁版重排重印,并严肃处理有关人员。多年后,这家出版社再出新版,质量大大提高了。
对学者、作家来说,自己研究的成果、创作的书籍出版后出现许多错误,绝不是件小事。王力先生是语言学家,他的著作如出现语言文字错误,他肯定看得更严重,因为语言学家、教授的双重身份有放大效应,会产生误导。实际上,绝大多数学者作家、编辑记者以及所有以文字为业的人,对自己发表的文章、出版的书籍质量都是关心的。30多年前,我在原来工作的出版社请钟叔河先生编了一本《知堂谈吃》,把周作人(号知堂)谈饮食的散文辑为一册出版。用郁达夫的话说知堂散文,“一篇之中,少一句就不对;一句之中,易一字也不可”。这种文章风格,也是对编辑的考验。饮食、烹饪虽小道,但涉及历史典故、地方风俗,偏僻字、异体字不少;我作为责任编辑,不懂的就查工具书,小心翼翼,生怕出错。书印出后,适逢钟先生来京,就顺便送他几本样书;他在回长沙的火车上就已经读了一遍,抵达后来信告诉我校对认真,只错了一个字。书的编者还有耐心再读一遍刚印出的书,这本身就是对我们这些年轻编辑的教育。1994年,孙犁老人让我把有关读书的信抄几封寄给《文汇读书周报》的陆灏兄,作为谈读书的随笔发表。文章刊发后,老人来信说:“《文汇读书周报》已见到,版式很好,您又耗费不少精神,该报校对也好,只错了一个‘蔓’字。”一整版文章只出现了一个错字,可见老一辈读书人对文字多么重视。喜欢、熟悉孙犁作品的读者都知道,老人写过许多有关读书、校对、编辑方面的文章,还出版了一本《编辑笔记》。他对创作的严肃性,对中文语言的规范、准确、纯洁不断发声。读者、作者实时监督新出版物的编校质量,主管部门定期抽查,是新闻出版业健康发展的保证。我记得,过去有的报纸专门在版面开辟“更正”专栏,及时反馈读者的意见;有的出版社奖励评论该社图书的作者,把挑剔的读者当作畏友;还有的新闻出版机构让新招聘的编辑人员先在校对部门工作一段时间,有意培育新人当编辑的感觉。
只要编校得法能消灭错误
我国是历史悠久的文化大国,在书籍的编辑、出版上有优良的传统,前辈曾留下许多宝贵的经验。近年,我发现,技术进步只能装备新闻出版业的下游,机器人尚不具备审读古籍的功能。一部书稿有没有出版价值?如何编辑、修改一部书稿?目前还是由有资质的人工按传统的方法作业。千余年前,司马光在洛阳编辑《资治通鉴》,草稿都是正楷,没有一笔草书,誊抄草稿时预留空行,增删文字,随时能剪裁、粘贴。北宋时的书多数是卷轴式,四丈成一卷,司马光说他是三天删定一卷,这是他自定的工作量。到了现代,我们这一代出版人是读作者的手稿,稿子大多写在“天地宽大”的大稿纸上,也能剪裁、粘贴,编辑作业的形式还保留着传统的方式。进入信息化时代,编辑读书稿的电子版,修改的符号无非是电脑自带的工具,并不能代替编辑对书稿的判断。举例说,我在孔夫子旧书网发现杨伯峻先生的一页手稿在拍卖,内容是他在中华书局工作时对书稿《老子词汇》的初审意见。我本来想买下来学习,不料被捷足先登者抢走了;好在卖家没打水印,我及时下载,随后抄录在《杨伯峻学术论文集》的空白页。在这一页的审读意见上,杨先生从三个方面对书稿提出意见,认为稿子的水平不高,建议退稿。杨先生的意见,显示了他的学问和眼光。在出版社的生产环节中,首先是评估一部书稿的质量,审读其是否有出版价值,是否已达到了出版标准;其次才是编校质量。一些东抄西拼,甚至胡编乱造的书稿,出版后即使没有差错,也已然是最大的差错。杨先生以他的学识,在源头保住了百年老店的声誉。
书稿的评估、审读;书籍的编排、印制,既然还离不开人工,那就难免出错。成语“鲁鱼亥豕”专指书籍传写、刊印中的文字谬误。在篆文中,“鲁”与“鱼”,“亥”与“豕”,二字笔画字形相似,容易写错,就把这种现象称为文字书写、出版中难免的错误。蒲松龄曾在《聊斋志异》里说:“鲁鱼亥豕,应不能免。”就是对这种现象的同情和理解。其实,只要工作认真,编校得法,出版物中的错误是能完全消灭干净的,我们已经有许多经典著作多次再版,是没有一个错字的。早在两千多年前,吕不韦就组织人员编辑《吕氏春秋》,工程竣工后,他把书稿悬于咸阳城门,把金子也摆在城垛上,并公开告示:能增损一字者予千金。这就是“一字千金”的故事。我的理解是,吕不韦对他领导的文化大工程如此自信,倒不完全是炫耀《吕氏春秋》的编校质量,更重要的是要广开言路,博采众长,继续吸收其他学术流派的思想观点,争取达到他那个时代的最高学术水平。
数字时代守护出版行业初心
看新闻,近年有一些名社大社、百年老店出版的个别书籍受到读者批评,读者所指,主要是书籍的学术质量和编校质量有问题。有的出版社闻过则改,立即通知经销部门下架;有的则装聋作哑,对读者的批评不予理睬。读者对公开出版的图书提出各种意见,是读者应有的权利,也是读者对出版物的反馈,出版社应视为福音,而不应当作乌鸦的聒噪。一本书出现编校错误,涉及多个环节,像40多年前出版的《龙虫并雕斋琐语》,因有从繁体字到简化字的转换,又是雇人从旧版本抄录,在第一个环节就埋下连环爆炸的地雷。责任编辑缺乏负责的能力,校对按错误的原稿机械校对,一本错误百出的名著就出版了。质量不合格的图书,既损害读者利益,也伤害出版社的声誉,还有连锁反应的经济损失。我是出版业的保守派。在信息化、互联网时代,在瞬息万变的光速时代,如果我们能坚守一些传统的、不变的出版法则,脚踏在“从前慢”的辙迹,科学、全程监控产品生产线,我们出版的书籍质量才有保证和更具生命力。
去年,有一家出版社要办培训班,主持人让我给青年编辑推荐一些书,我随手开了一份书单,都是旧书:《商务印书馆九十年》《回忆中华书局》《我与三联》《一编审足矣:周振甫编辑出版文选》,还有赵家璧《编辑忆旧》、叶至善《我是编辑》。我对出版社主持人说,这一类的书,我还可以开出一长串,你们先让青年同行了解名社的历史和社内作者、同业回忆,看看老前辈是如何当编辑的。我还说,出版机构要有读书风气。青年人如果爱读书,一切都好商量。我又告诉要去培训班的朋友,1924年,冯友兰先生邀请顾颉刚先生去中州大学任教,顾没能去,在回信中谈到他的计划:“自明年起,每日必有半日之读书,余下半日,虽不读书,亦必浸润于学问之空气中。”读到这封信后,我连着几天都在回味其中滋味,甘之如饴。一家出版机构的编辑、校对人员,如果人人爱读书,天天都“浸润于学问之空气中”,大家都来练内功,其编辑出版的图书质量总会不断提高吧。
还是看新闻,我最近看到人民教育出版社在办公大楼安放叶圣陶先生塑像。我心里说,这就对了!叶老晚年还在说,如果有人问他的职业,他就说他的职业是编辑。叶老作为该社的首任社长,著名的教育家、出版家、作家,学为人师,行为世范,应是所有出版从业者崇敬的前贤。
(作者为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编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