果戈理和鲁迅:共通的伟大与悲哀
说到俄罗斯文学,总会想到托尔斯泰和陀思妥耶夫斯基。昼与夜,爱与恨,高贵与深渊,咏叹与复调。这个“和”字,就如同晨昏线一样清晰、确定、无法质疑。文学史喜欢这样均衡的组合,比如李白和杜甫、拜伦和雪莱、歌德和席勒……当然,也有无法组合的人物。有些人是因为过于丰沛,比如莎士比亚;有些人则是因为过于奇特,以至于和谁放在一起都显得有点格格不入,比如——果戈理。
果戈理的格格不入,源于他的思考方式,他的每一个毛孔都大张着迎接这个世界的所有刺激。他是一个自我斗争着的矛盾体。在《果戈理学》这篇绝妙文章里,奥特罗申科以“果戈理和……”的句式,绘制果戈理充满错误与矛盾的灵魂画像。相比于“果戈理是……”,“果戈理和……”或许是描述果戈理最合适的句式。作为中国读者,我能想到的第一个短语是:果戈理和鲁迅。

果戈理肖像
无处不在的尘土气息
如果,果戈理和鲁迅在现实生活中相遇,可能很难做成朋友。从性格上来说,他们几乎是对方的反面。鲁迅倾向于理性判断,果戈理总是情感喷薄;鲁迅做事有计划有条理,果戈理几乎可以说是一团混乱,想一出是一出——一个典型的果戈理笑话是:《钦差大臣》在莫斯科演出时,各界名流汇集,演出中场时主持人邀请剧作家上台讲话,而果戈理竟然站起身来,径直走出了剧院,坐上马车,再也没有回来。他们相似的点在于喜欢独处,并对世界有着笃定的、高度直觉化和象征化的认知。他们关注的不是事物的表面现象,而是其背后隐藏的模式、本质和未来的可能性。虽然存在如此多的不同,但鲁迅很可能比果戈理自己都更理解《死魂灵》的意义。
《死魂灵》是一部怎样的书呢?1842年,《死魂灵》第一部在莫斯科出版问世后,形成了一种奇怪的现象:所有人都毫无保留地接受这部作品,包括这部书所讽刺的对象,以及他们的反对者——那些对俄罗斯现实不满的知识精英。别林斯基盛赞果戈理揭露俄国现实、批判农奴制的勇气。而地主、军官还有农奴们,都被这个故事逗得哈哈大笑。《死魂灵》第一部完美发挥了果戈理的天赋:一段似乎没有终点的漫游旅途;一个看似滑稽实则充满计算的目标——购买死去的农奴;一个为了目标奋力前行,有时看到梦想的炫目光辉,有时又被现实绊倒的投机专家——乞乞科夫;一些以各种奇怪方式在庸俗生活里浮沉的俄国人——地主、军官、警察局长和马夫、农奴们……投机取巧又惹人喜爱的乞乞科夫,和他那些或蠢或笨或自以为聪明的朋友们,受到了读者热情的欢迎,以至于果戈理认为自己不仅是普希金的接班人,更应是但丁的接班人,自己肩负的不仅是文学的使命,更是国家的使命、宗教的使命。他希望按照道德训诫的方向来写第二部,像但丁创造贝雅特丽齐一样,塑造出一些光芒四射的、良善的乃至伟大的文学形象,指引祖国人民朝着正确的道路前进。
沉浸在热烈掌声里的果戈理完全没有意识到,崇高与伟大并不是自己擅长的主题,“庸俗”才是属于他的主题。庸俗的气息,尘土的气息,本是无处不在的,但只有当马车轰隆隆开过时,我们才能看到那壮观的尘土风暴,才能感到这气息是呛人的、有害的。果戈理最精彩的作品,他赖以生存的讽刺与幽默,就建立在他对这种精神气质的准确把握上。他只要在圣彼得堡的涅瓦大街上走几圈,在每一次的擦肩而过中,在耳边听到的只言片语中,就能迅速捕捉到那种漂亮制服和皮草大衣都挡不住的日常的庸俗,这是他在作品中不断书写的浸润于世俗之中的可怜、猥琐与肤浅。
作品中,果戈理最擅长的是对话和抒情,以及对细节的放大与定格,如直面观众的舞台般的呈现:
“什么?请您原谅……我的耳朵不大好,我觉得,我听到了一句非常奇特的话……”
“我要买死掉的农奴,但在最末的户口册上,却还是活着的。”乞乞科夫说明道。
马尼洛夫把烟斗掉在地板上面了,嘴张得很大,就这样地张着嘴坐了几分钟。刚刚谈着友谊之愉快的这两个朋友,这时是一动不动地彼此凝视着,好像淳厚的古时候,常爱挂在镜子两边的两张像。(《死魂灵》,鲁迅译)
这种放大与定格,也是鲁迅喜欢的人物呈现形式——祥林嫂“间或一轮”的眼睛,阿Q大喊“我要与你困觉”后的寂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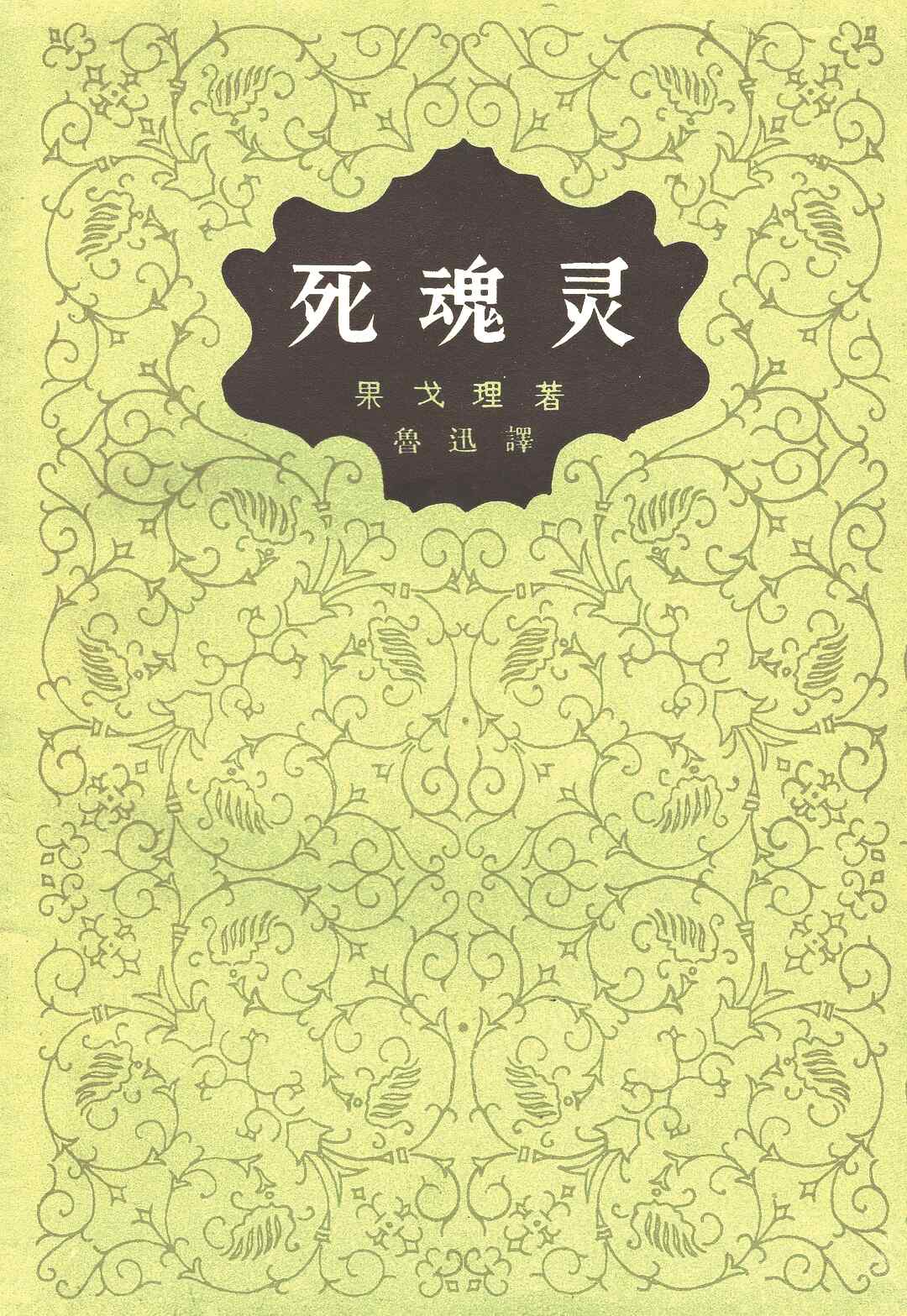
《死魂灵》,【俄】尼古拉·果戈理著,鲁迅译,人民文学出版社,1977年版
大欢喜与大苦痛
果戈理和鲁迅之间最重要的一个共同点是:他们都“死于”《死魂灵》。果戈理在生命尽头烧掉了那份永远写不完的手稿,而译者鲁迅在溘然长逝时,也没能等到最新一篇《死魂灵》译文的问世。
1836年,果戈理从巴黎给茹科夫斯基寄出了一封信,信中写道:“我的创作宏伟辽阔,也不会很快收尾。似乎有一个隐秘之人用威力巨大的指挥棒在我面前写着。”《死魂灵》的创作在巴黎进展迅速,生机勃勃。随后四年在罗马,更是喷薄而出。彼时的果戈理不会想到,这部作品竟然在之后的十年里翻脸变成了折磨他的魔鬼。
《死魂灵》有一种可怖的魔力,一种属于史诗的魔力,那便是它可以被一个人创造出来,却无法被一个人完成。作者会在它的永恒面前消耗有限的生命,在不断追逐那种近乎神性的过程中,越来越无法忍受自己的软弱与缺憾。对于像果戈理这样的凭借直觉与情感来创作的写作者来说,这便是足以剥夺生命的“酷刑”。果戈理将自己写不出《死魂灵》第二部的原因,归咎于自己天赋的丧失、某种神力的消散,这一觉悟让他痛不欲生。
果戈理不知道为什么文字再也不像湍流一样从他的笔尖流淌出来,鲁迅也不知道自己为什么强撑病体也想把《死魂灵》第二部的残稿译完。比果戈理幸运的是,鲁迅与欢喜、苦痛已经周旋许久,并不将自己的生命与创作依托于“天赋”。“做《死魂灵》的工作,在作者是一个大欢喜,也是一个大苦痛。”鲁迅借着译笔,带着他那惯常的冷峻为果戈理写下了判词。在寻找翻译这句话的确切用词的时刻,他或许早已意识到,这位与自己素未谋面、语言不通、性格迥异的俄国作家,竟然与自己有着相似的灵魂,同在大欢喜与大苦痛中挣扎浮沉。
他们都书写人性的庸俗与卑劣。他们都向往真正的、近乎宗教性的崇高精神。他们怀抱着救世的愿望,把自己的笔化作悲悯而痛切的目光。他们梦想着一个充满“大写的人”的社会,却一次次发现,眼前所见的只有到处游荡着的乞乞科夫。令他们痛苦的事实,不仅是乞乞科夫自私自利、招摇撞骗,而是乞乞科夫的灵魂中还有充分的自尊和自信,让他在谎言被揭穿的时候气急败坏,认为自己受到了莫大的侮辱。令他们痛苦的事实,不仅是孔乙己好吃懒做、卖弄学问,而是孔乙己永不承认自己的小偷小摸,打折了腿也要用手撑着来店里。令他们痛苦的事实是,乞乞科夫们并不是游荡在大街上,而是游荡在每个人的心里。
“过去的生命已经死亡。我对于这死亡有大欢喜,因为我借此知道它曾经存活。死亡的生命已经朽腐。我对于这朽腐有大欢喜,因为我借此知道它还非空虚。”(鲁迅《野草·题辞》)
不就是如此吗?在大欢喜与大苦痛之间,在生与死、明与暗、爱与憎恶之间,如熔岩一般不可自抑地奔涌,爱着腐朽的野草,又将其烧尽,直至烧掉自己最后一丝热度。或许,就是这种无法言说的相似,将鲁迅宿命般地引向了果戈理,引向了《死魂灵》。
“含泪的微笑”
果戈理的俄语散文,是出了名的难以翻译。鲁迅不懂俄语,只能借助德语和日语译本迂回前进。作为翻译家的鲁迅,主张翻译要以“硬译”(直译)为主要方法,忠实原文,“宁信而不顺”。他为了补足无法阅读俄文原本的缺陷,也下了极大的功夫,为找到一个正确的词而殚精竭虑。而作为作家的鲁迅,却有着先于逻辑判断的直觉——在不知不觉间,鲁迅已经在《死魂灵》的译文中注入了自己的气息。他的直觉与果戈理是相通的。
米尔斯基在《俄国文学史》里是这样描述果戈理的语言风格的:“注重感官效果而非声学效果,密实饱满,结合了崇高的诗意雄辩和荒唐的闹剧元素,充满真实口语的震颤和活力,从不空旷松散。”按照这个描述去看鲁迅翻译的《死魂灵》,会觉得似乎语体上太过清瘦而克制了些:
“出色的都市,体面的都市!”乞乞科夫说,“真过得适意极了;交际场中的人物都非常之恳切,非常之优秀!”
“那么,我们的市长,您以为怎样呢?”玛尼罗夫夫人还要问下去。
“可不是吗?是一位非常可敬,非常可爱的绅士呵!”玛尼罗夫夹着说。
……
主妇常常向乞乞科夫说着这样的话:“您总是什么都没有吃,您可真少呀!”这时,乞乞科夫就照例回答道:“多谢的很,我很饱了。愉快的谈心,比好菜蔬还要有味呢!”于是大家离开了食桌。(《死魂灵》,鲁迅译)
玛尼罗夫家的餐桌,本是家人围坐、孩子打闹、充满轻浮客套话语的俄国乡村式餐桌。但在鲁迅笔下,字里行间竟有了些《在酒楼上》的索然味道。这种味道,于翻译而言,是多余的,却是珍贵的多余。这是鲁迅在复述果戈理时的语气。果戈理的讽刺脱胎于滑稽,是庸俗的也是热闹的,会有蓬勃喷发的斯拉夫式热情。若说果戈理的故事在俄国的舞台上热热闹闹地演着,那中国观众席里的鲁迅则是冷冷淡淡看着的。冷淡不是因为不喜欢或不在意,而是因为他能立刻穿透那些庸俗的热闹,聚焦在包藏在果戈理纷繁情绪感受里的那一个核心。
普希金评价果戈理的作品是“含泪的微笑”,带着改变祖国的热望,将俄国社会中的黑暗一面揭露出来。别林斯基也是这样去理解果戈理的,但果戈理对这样的评价,一直感到惴惴不安,以至于后来与别林斯基有了那场轰动的“分手事件”。但果戈理始终也说不出,如果不是“含泪的微笑”的话,那他究竟是为了什么写出这样的作品,为什么能写出这么些迷人的反面角色。鲁迅是早就知道的。他在评介果戈理的文章结束处写道:
况且健康的笑,在被笑的一方面是悲哀的,所以果戈理的“含泪的微笑”,倘传到了和作者地位不同的读者的脸上,也就成为健康:这是《死魂灵》的伟大处,也正是作者的悲哀处。(鲁迅《且介亭杂文·几乎无事的悲剧》)
果戈理的悲哀之处,在于他的感受和天赋远远超过了他的思考能力。他其实并不是一个二元对立的人,并不想站在制高点嘲笑别人,哪怕他最擅长的就是看到一个人最真实的卑劣之处。他相信这世间有完美的人,直觉上却写不出一个真正的好人。他让笔下人物大喊着“你们笑什么?笑你们自己”,台下的观众也还是在不停地笑,笑到流泪,笑到咳嗽,笑到前仰后合……而后,他们就在满足的微笑中起身离去,开始新的一天的生活。
鲁迅知道《死魂灵》的伟大,也知道果戈理的悲哀。因为这也是他的伟大与悲哀。
(作者系青年作家、《北京晚报》编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