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之:乡间的鲁迅
三汇中学一年的生活,给了我“大城市”所无法给予的许多东西,广阔的田野,金灿灿的油菜花,足以令人怀旧的“小山城”的颓败的景物,坑坑洼洼、弯弯曲曲的古镇街道,这都不是今天真假混杂的“现代古董”所能拥有的魅力,当然,还有那批天真烂漫、求知欲旺盛的乡村孩子。不过,乡村生活也有它难挨的部分,这就是信息匮乏的寂寞。每当夜深人静,我们还是渴望在丰富的社会信息与切实的人间关怀中变得充实。人性,永远在梦想的洒脱和现实的饱满间徘徊,没有终结。
读书无疑是打破寂寞的最好的方法。然而,这并不容易,因为,直到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初,三汇中学还是一处被排挤在现代信息网边缘的孤岛,能够找到的可读之物甚少。
一
我随身携带的行李箱只够塞下最基本的被褥衣物,除了一本教书必备的字典,其他书籍都难以装入。学校办公室里有个报架,上面有《人民日报》《参考消息》《四川日报》等几种,但是一律都是三天以前的。因为当天的国家大报都得在成都印刷,成都印好发往达州得整整一天,达州分装好再运送到渠县又得一天,第三天能够从渠县县城到达三汇镇,再从三汇镇过渡到学校最快也是下午光景了。办公室里还有一部电话机,但是没有拨号键盘,打到任何一处的电话都必须先使劲摇动手柄,这样才能接通电话局,然后说出你要拨打的地方,由电话局接线员统一转接,完全是民国时代的风范。当然,常常也是无法接通的。我们男教师宿舍里有一台九寸的黑白电视机,不知道是学校的配置还是原来房主李主任所有,但只有反复拍打才可能突然出现一片雪花,偶有人影晃动,总之我们从未成功收到任何一段连续的节目,后来也就闲置在那里了。
不过,学校里却有一处小小的图书室,宽大粗糙的阅览桌上堆着一些过期的报纸,还有数排藏书架,上面主要是各科的教材、教参和其他教学资料,少许陈旧的“十七年”小说。一位慈眉善目的老太太守在那里,因为几乎没有人进来,她就不紧不慢地织毛衣,做手工。百无聊赖之中,我也去图书室翻看过期报纸,一来二去也就和老太太熟络起来,她说:“靠里边还有些旧书,你可以自己进去找找。”于是我掠过那些花花绿绿的教学读物来到了最里层的书架,在这里,发现了一长排的鲁迅著作的单行本,半新不旧的,全都是一九七三年“文革”期间的版本。
 三汇中学的教学楼,作者摄于2024年
三汇中学的教学楼,作者摄于2024年
这当然不是大学学术的推荐书目,但是,遥远的三汇中学,没有可能跟随八十年代的学术发展,为这些孩子的语文学习备好新版的《鲁迅全集》。这些二十年前的印刷品,已经能够满足我彼时彼刻的阅读需求了。
二
就从鲁迅读起吧!
在大学的现代文学课堂上,我也是从鲁迅读起的。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王富仁老师的《〈呐喊〉〈彷徨〉综论》打开了我们这一代人的视野,一时间,阅读鲁迅、评论鲁迅成为理所当然的事情,借着评论鲁迅来“自我发现”却是更大的企图。学生年代胆子大,竟然首先就从老师的论著中寻找破绽,于是我写出了《〈伤逝〉与现代世界的悲哀》,也因为王老师的宽容,推荐到当时大名鼎鼎的《名作欣赏》发表,从此走上了阅读鲁迅的学术之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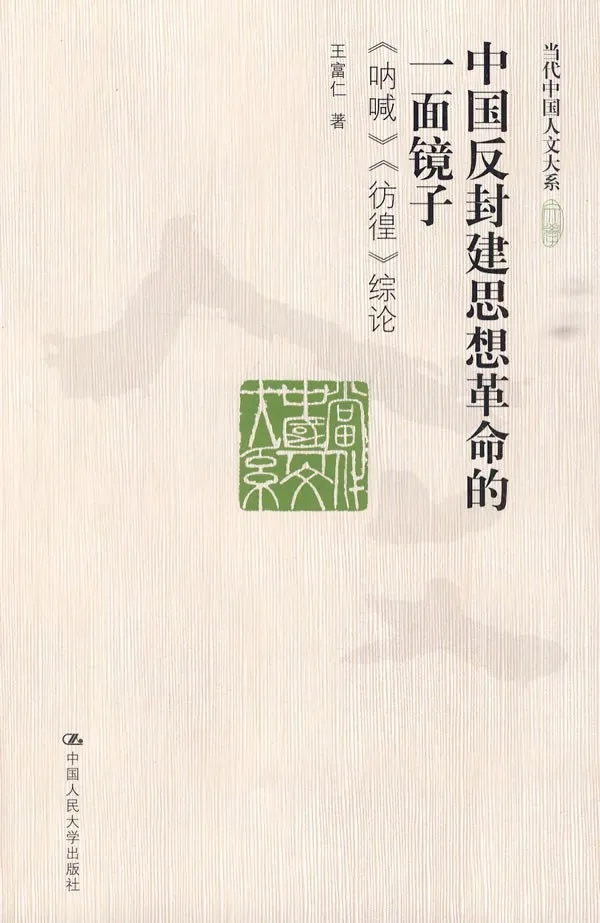
王富仁《〈呐喊〉〈彷徨〉综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年
虽然历经中国历史的变幻,鲁迅却始终屹立不倒,这曾经引起了某些愤世嫉俗者的疑惑,质疑鲁迅精神与某些基因的内在关系。其实并不是鲁迅一定要拽住我们,以“导师”自居,而是每当中国社会发展进入某些晦暗的时刻,当那些眼花缭乱的学说和思想都隐身不见的时候,能够在暗影重重中支撑我们的精神,激励我们生存的恰恰就只剩下鲁迅了。王富仁老师的“思想革命”学说固然彰显了一个新时期的鲁迅形象,但是真正打动他的“鲁迅记忆”却延续在最朴素的生存之中,当我读到这样的文字,在心中激荡的回响久久不息:
《鲁迅全集》没有给我带来什么好处,反而把我可以有的“锦绣前程”给毁了。但我没有后悔过,因为我觉着有些人活得怪没有意思。活得巴巴结结的,唯唯诺诺的。鲁迅虽然一生不那么顺,但活得却像个人样子。人就这么一生,窝窝囊囊的,想说的话不敢说,想做的事不敢做,明明对人对己都有好处,却还是不说,专捡那些对人、对己都没有好处但能讨人喜欢的假话大话说。我喜欢鲁迅,就喜欢他说的不是假话大话,说的不是专门讨人欢心的话,虽然当时年龄还小,懂得的事理不多,但这点感觉还是有的。直至现在,一些学者仍然认为鲁迅对人是很恶毒的,但我读鲁迅作品却从来没有产生过这种感觉。我从我的经历知道,鲁迅实际是对人、对自己的民族、对人类没有任何恶意的,只是他不想讨好人,别人听了他的话感到不舒服,而在中国,有权势的人总是能收到很多很多恭维的话、甜蜜的话的,而他们在鲁迅那里却收不到这样的话,鲁迅就不招在社会上有势力的人的喜欢,而一当有势力的人不再关爱他,就有很多人前来找他的岔子。(王富仁:《我和鲁迅研究》,《鲁迅研究月刊》2000年第7期)
鲁迅不仅打动了少年王富仁(虽然他那个时候可能还没有想到过什么“思想革命”,什么“研究体系”),在八十年代结束的时候,其实也继续打动着我,虽然我已经知道了“思想革命”,也自觉地认同了新的“研究体系”。但是任何理性的学习都不能代替真切的人生感受,当我不得不栖身在城市的远方,在校园思潮的边缘重新生活的时候,也必须重新面对周边的荒寂和自我精神的孤独,某些历史的情景似乎因此被“重建”,而我则别无选择地只能与鲁迅相遇,在那个缺少知识和当下信息的角落,鲁迅是唯一可以拂去尘埃,自由捧读的内容。我觉得,人生的境遇不仅让我进一步走进了鲁迅的世界,其实也走进了少年王富仁的世界,在这个现代中国人都有可能经历的“典型”环境中,我们都有机会阅读和体验那一种“典型”的情感。
《呐喊》《彷徨》我都读过了好多遍,那就再读《故事新编》吧。图书馆里的老太太让我随意借阅任何书籍,我抱了一大堆的鲁迅读物回宿舍,既有作品,也有各种各样的注释和阐发。虽然这些“政策图解”式的阐发几乎没有什么说服力,但是它们都与鲁迅的原作排列在一起,却也构成了一种奇异的“学术氛围”,告诉我这是一件有无数人积极参与的事业,而此时此刻,与他们为伍的我是值得的。多多少少,它们的存在也给了我信心,给了我动力,或者在我后来捉笔表达心得的时候,成了我可以面对的讨论的对象。现在,我明白了,生活的寂寞也可以通过这种学术氛围的形成和解构获得超越。
“文革”时代的“鲁迅论”没有什么理性的含量,这留给了我充分的自由阅读的空间,面对《故事新编》的文字本身,我投入、沉浸、咀嚼,努力辨认那些奇谲诡异的神话叙述的真切的人生意味,然后记录下我各种新鲜的感受。《呐喊》《彷徨》之后的精神世界好像正在为我徐徐展开,那里有夷羿“英雄末路”的尴尬,有眉间尺义无反顾的复仇,也有不肖子孙对创始之主女娲的无赖似的纠缠,这仿佛是一个五四退潮、“启蒙”终结的故事,而鲁迅似乎从现实的沙漠被抛入了历史的荒原,在当代生活的远方回望人生。不知怎的,这样的情景也令脱离城市喧嚣、置身田野乡村的我更能“共情”。
三
我用文字叙述自己的这些阅读的发现,就是出于对鲁迅文字世界的再现,并不需要太多的理论的周旋,这样的读书体会反倒更加真实和朴素。当然我渴望回应和印证,于是在一番表达的挣扎、文字的搏斗之后,我试探着在身边支教的同事中寻找知音。历史李老师和语文康老师都主动或被动地成了我文章的听众,尤其是康老师,原本就是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新入职的文学编辑,对文字的敏感和文章规范的看重已经成了她的一种职业本能,她有时候近于苛刻的挑剔让我很是沮丧,但一种征服编辑的顽强也因此生成。历经反复的磨砺,终于康老师流露出了满意的表情,这不禁让我暗自庆幸。翻阅那些已经在复写纸上成形多时的稿子,康老师说:“你可以找个杂志投出去啊!”
对啊,投稿吧!我马上想到了北京的《鲁迅研究月刊》。一九八七年,因为王富仁老师研究的争议,我连续关注和阅读了这份杂志上的许多文章,那些质疑、批评王老师的论文令人莫名紧张,有时甚至产生隐隐的窒息之感。但是也是这一份杂志,连载了王老师数万字的长篇回应,一时间传诵广泛,让很多关心王老师的师大师生深感宽慰。我记不得杂志的准确地址了,只好在信封上写下一个笼统的“北京阜成门北京鲁迅博物馆”,当然,装入的稿件是整整齐齐的。三汇中学附近没有邮件寄送处,第二天一早,我就出发,走了半小时的机耕道,再乘轮渡过河,找到三汇镇上的邮政所,用挂号信将稿件寄往北京。

作者通过轮渡到三汇镇上的邮局,将稿子投寄《鲁迅研究月刊》
三汇与北京,在我的心中隔着千山万水,我并不期待很快就有什么消息。不过,等待却也没有那么长久,数月之后,一封鲁迅博物馆的邮件寄到,告诉我论文将在近期刊出,落款署名“高远东”。再过了一段时间,杂志也寄到了。我激动地拆开装有两册样刊的大信封,轻轻抚摸着信封上的蓝色名字:鲁迅研究月刊。想象着它如何来自我曾经熟悉的北京,又如何穿越崇山峻岭来到这偏远的川东乡村,由此打通我感受过的热烈的一九八〇和冷寂落寞的一九九〇,似乎也打开了我人生的一条新路,或许对《故事新编》的阅读就是这一新路上的正确的选择。
我不记得文章发表的喜讯让我有怎样的庆祝,是不是拉上朋友在校外的田野上乘兴而行?是不是渡河上街,到三汇镇里游走餐饮了一番?又或者是在夜色降临之后,在台灯下兴冲冲地高声朗读,向我的同事康老师炫耀杂志精美的印刷和新鲜的墨色?这一段记忆的模糊很可能还是被《故事新编》带给我的通向未来的光亮所掩盖了。总之,我记得最清楚的还是愈加勤奋地阅读和写作,是一篇又一篇的阅读心得传到了康老师(编辑)的眼前,又是遭遇了一次次的批评和质疑,而到最后,我竟然完成了对这部小说集的完整的阐释。
对我来说,《故事新编》是完整走进鲁迅的一次尝试,对于我曾经寂寞的支教生活来说,鲁迅是我重新发现人生意义的一个契机。它也让我的语文教学焕发出了新的光彩。那时的高中语文没有《故事新编》的篇目,但这并不妨碍我在自己的课堂上为同学们讲述这部小说的热情,而且我很快发现,其中那些神异的想象可能更能引起同学们莫大的兴趣。几次鲁迅的补充阅读之后,同学们都让我继续为他们推荐鲁迅的作品,似乎课文中反复出现的鲁迅也不能满足他们的渴求。新一年的五一劳动节,就在学校放假的前夕,我正在收拾东西,准备回重庆看望父母,一个学生找到我,问我能不能在重庆替他买到《鲁迅全集》。这是一个家庭条件并不宽裕的孩子,我看到过他背着大米来学校“搭伙”,用自家的粮食换取日常生活的饭票。他的要求让我吃惊不小。当然,那个时候,重庆的书店里也买不到鲁迅的全集,我也一时不能帮他完成这个心愿。

作者和他的学生们
新时代的今天,我们常常听到这样的感叹:鲁迅对今天的中学生来说还是有点难,或者说离他们有点远。有时候我百思不得其解,难道当下的孩子在理解能力上大幅退化了?或者,就是社会本身发生了什么翻天覆地的变化?在我的记忆中,鲁迅不就在遥远的乡村找到了知音,而且深深地影响了一代质朴的孩子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