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访徐浩峰:文学不负责答案,只提供窘境
该怎么来定义徐浩峰这个人呢?说他是作家?是导演?是武人?是传统文化研究者?是影评人……似乎都对,又都不全然。早在“斜杠青年”这个词出现前,他就已然“斜杠”了很多年。
相较最火的那段时间,这几年他的名字在公众场域里似乎已少被提及,但他却又好似片刻未得空闲,待上映的电影,后边就排了三部。他还一直笔耕不辍,在小说以外捡起了搁笔有年的影评功夫:《光幻中的论语》用夫子论道与圣贤文章扫除蒙在“十七年电影”上的蛛网积尘,让我们得以重新审视这笔久被忽略的中国电影宝藏;新作《通灵宝玉与玫瑰花蕾》更是围绕《红楼梦》这本可能是中国人最熟的小说做起文章,《石头记》变作了攻电影创作观这块“玉”的“他山之石”,勾连刘别谦和曹雪芹握了手,介绍莱昂内成了林黛玉的知音。
一、《红楼梦》本身就是一部完美的电影剧作
Q:聊聊新书《通灵宝玉与玫瑰花蕾》吧,为什么会生出用《红楼梦》来阐述电影导演方法论的念头?
A:那还要追溯到86,87年的时候,因为我是个美术生。站在那时候北京的街头搭眼一望,总能看见大大小小的孩子,都背着制式相同的绿色画板。为什么有此风气?因为那时候美校生算中专生,出路很多,你学得好,可以考美院,成绩不济,也可以去各个出版社,或者报社,当个美编,寻个出路。学生一多,考前班自然也多起来。寒暑假的时候,几乎各个中学的教室都会被任教的美术老师租下来。
我记得我们那时候上课之前,还要先把教室里的桌椅板凳都搬出去垒在楼道,空出地方,再围成一圈画石膏像。而除了上面说那几种,还有一种出路就是去剧团或者电影厂,做美工。我们这些学画的孩子那时候就有一个集体活动,常一块骑自行车,跑北影厂,去找这些美工老大哥聊天。
Q:初中生和美工一块侃大山?怎么认识的,不会有代沟吗?
A:代沟当然有,但也有搭桥让你渡过代沟的介绍人。就是那些开班授课的美术老师。其实有时候,学画跟学武也差不多,老师最重要的不是教了你什么,而是能不能给你提供一个师承,一个出身,一个舞台。当时北影厂的美工,主要是第六代那一拨的人,就是王小帅、娄烨他们那一代,电影学院毕业的,不少美术系的都分到了北影厂,人家都是正经学西画的出身,懂得自然比我们多得多。所以我们就总爱去找他们,而且他们也都是刚毕业的大学生,也愿意当这个孩子头,我们问什么都愿意指点两句。
所以那时候,我们往北影厂跑得很勤。而那时候北影厂最大的项目,就是这个六部八集的红楼梦(编按:指1989年上映的,北京电影制片厂出品的系列电影《红楼梦》,谢铁骊,赵元导演,夏菁,陶慧敏,傅艺伟,刘晓庆等主演),所有人都为这个大项目跑前跑后,忙得不可开交。聊天的话题自然也都围绕着这几部电影和《红楼梦》。
那个时候,就有这种说法,说《红楼梦》本身就是一部完美的电影剧作,符合电影剧作的几乎全部规律,完全可以直接照着拍。其实国外也有相近的说法,你看黑泽明也说:看了15遍《战争与和平》以后,他就学会了写剧本,咱中国要是也有一部能担此大任的名著,那肯定就只能是《红楼梦》责无旁贷了。后来在电影学院系统学习了苏联式的剧作理论,再反过来,看《红楼梦》,觉得跟老师讲的剧作理念,每每多有应和,到后来,又广览一些影史名作,又常会发现这部片子用的手法,那个导演的剧作技巧……往往也都能在“红楼”里找到端倪。这种惊喜发生多次,自然就有了想总结下来,写成东西的念头。
Q:《光幻中的论语》讲论语,《通灵宝玉与玫瑰花蕾》讲红楼,未来这个主题会不会发展成一个新系列?如果有下一部,那又会是以哪部传统典籍为主题展开?
A:你说的这两本书其实都是我在《上海文学》上的专栏文章的结集。在那个专栏最早的几期里边,我讲到中国传统理想主义的时候,举的例子就是《资治通鉴》里边司马光对历史事件的评述,这种评述往往不是从成败的角度评述的,而是说某件事办得好,或者没办好。也就是说你会发现司马光很多时候谈的不是利弊,而是是非。这是《资治通鉴》,那么除了这种道德文章之外,你看《聊斋志异》,蒲松龄虽然讲的都是鬼狐,但往往他寥寥几笔一点评,就直接能拉回现实里。可以说就是一流社论记者的水平。
所以我在给学生介绍学习方法的时候,就让他们学习去摘《资治通鉴》里的“臣光曰”和《聊斋志异》里的蒲松龄点评,把这些学通,你就掌握了中国的理想主义和现实主义。结果三年过去,我认识的小孩里,没有人干这个事,反而他们还调过头劝我,说徐老师您把这些都整理一下摘出来吧,我们肯定愿意看!如果未来真的有所谓第三部的话,那有可能就是这个了。所以你看,学生犯懒其实还是有好处的,让老师可以有钱赚(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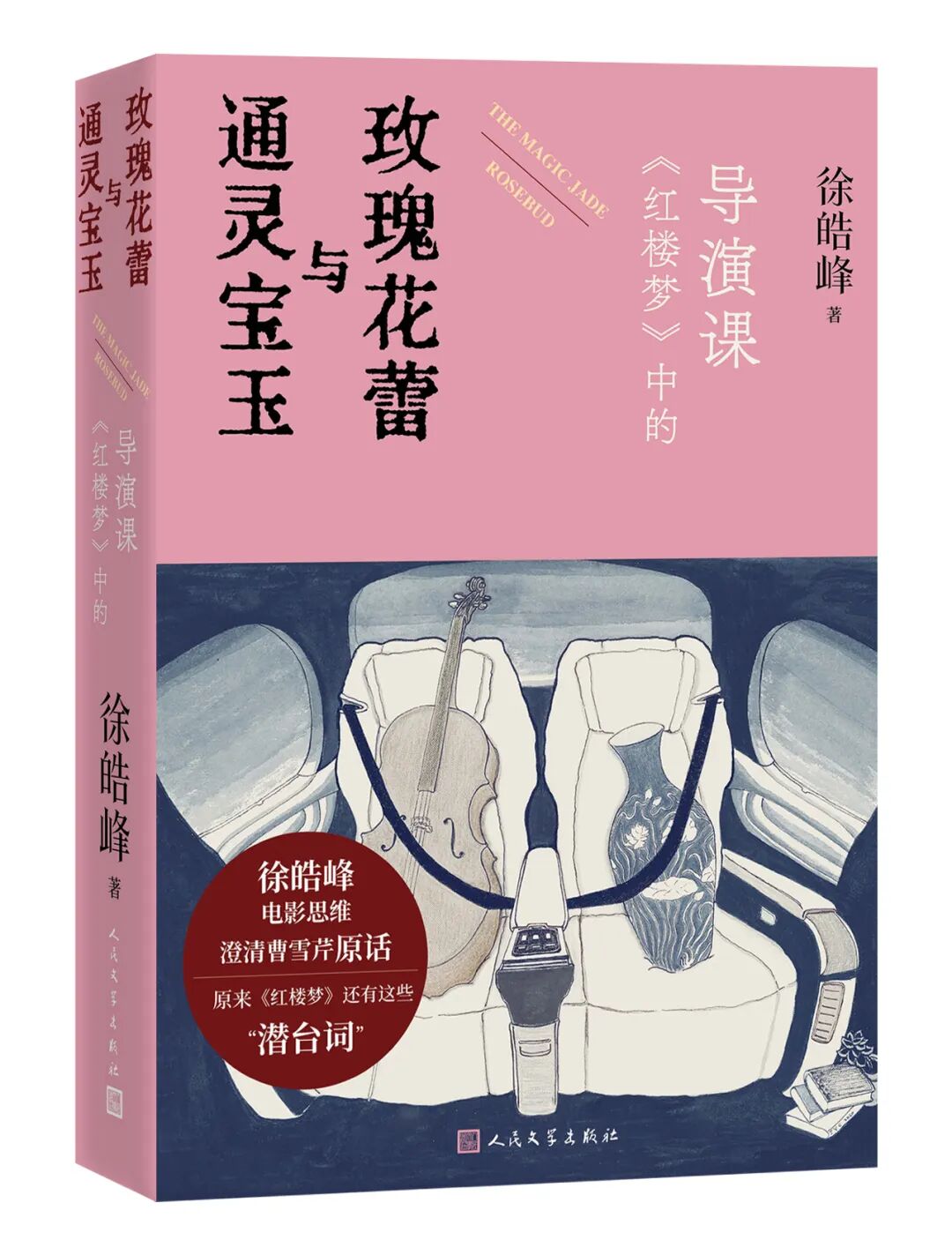
《通灵宝玉与玫瑰花蕾》封面,徐皓峰为其笔名
Q:我看了你的这些影评文集,像《刀与星辰》和《光幻中的论语》,自然也包括这本其实很有些影评性质的《通灵宝玉与玫瑰花蕾》。我有个问题很好奇,你既是导演,同时又是一个影评人,拿曲艺界的话说这个好像叫“两门抱”,那你是如何平衡这两种身份的?它们中的一种会不会给另一种带来某些困扰?
A:(笑)我明白你的意思。我过世的老师周传基先生就跟我们聊过这个问题。在他教第五代的时候,由于他的很多观点在那时看来都很新颖,学生就问,周老师,您对电影理解这么深,镜头感这么好,您说您要是自己导电影,那作品该有多棒啊!您怎么就没想实操一下呢?但周老师在课上就跟我们讲,说我虽然研究电影理论研究了二三十年,但这修为主要还是在理论和鉴赏层面的,如果我要改行当导演,导演的修为没有10年,必不能成。
因为一部好的电影,一定不能只是满足于完成叙事,而是必然要根植于生活的。不是说审美好,品位好,会分析别人的电影,就一定能成好导演,这中间必然还有至少十年的,逃不了课的修行,而在这十年的成熟期里,你的电影一定有拍得不好的,甚至会拍出一些坏的电影,学生看到,会觉得水平不过如此,自然就会质疑你的学问。
我这辈子最骄傲的是我的学问,为了保住这个骄傲,我不犯这个错误。另外一点,一个会做导演的影评人去褒贬同行,同行必然争不过他,嘴仗没法打。这么搞显然不仗义。所以他也叮嘱我们,当上导演,就不要再做影评人。
其实我一直遵循他的教导,早年虽然给不少报刊,电影杂志断断续续写了很多年影评,但自从2011年做了导演,其实就有小十年没再碰过影评。也有很多杂志还在向我约稿,问我怎么不写了,我也只说是遵循一个传统,至于你说后来的这两本《光幻中的论语》和《通灵宝玉与玫瑰花蕾》其实对我来讲是另一个范围,它是理论研究。你看罗杰·伊伯特和宝琳·凯尔,他们写的影评文章,大多数都是写当时出现的电影,但你看我这两本书,其实都有意祛除了这些当代的作品,绝对没有褒贬同行,所以说不能算影评,只能算是个理论性质的研究(笑)。
二、“我折腾你,最后我反而尴尬”
Q:正如你所说的,我们上一代很多老影人,比如很多第四代或者第三代中国导演们,他们一直秉持的理念是不止满足于完成叙事,更要根植于生活的。但中国电影在“十七年”时期之后,或者说,在进入了那个非常历史时期之后,似乎就变成了一种一切都要让位于一种澎湃的情绪,一切为了那个情绪服务的状态。那个历史时期之后,我们的电影可能又有那么一个时期重新拾起了对历史的反思,对人们情感的精准描述,对个体命运与历史背景之间关系的思考。但你看我们现在的电影院里,好像又回到了一切都要服从于群体情绪的那种状态,某种程度上,你会不会觉得我们的中国电影是不是有一种历史周期循环反复的感觉?
A:你要是说循环感,那我体会到的可能是另一种循环感。我一直觉得中国电影的根基特别好。咱们常说四大名著,但是原来也有一种提法是“五大名著”,多出来那部就是《儒林外史》,极其经典的社会问题小说。其实不光《儒林外史》,你看《老残游记》《孽海花》《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没一部不是精彩至极!在我看来,恰恰是这部被拉下来的“第五大”名著和这些小说,才是中国电影的根。
中国电影打从诞生开始,最受关注和追捧的都是社会问题片,我们自己的影帝影后,什么阮玲玉、胡蝶,她们也都是被这些社会问题片所成就的。你看阮玲玉有《小玩意儿》《神女》,胡蝶有《姊妹花》《狂流》……所以中国的影后一开始就不是模仿好莱坞女明星的路线,我们的影帝影后是要承担社会责任的。
而到我成长的那个年代,你看我的老师,第四代的代表人物郑洞天,80年代的时候他就拍了《邻居》,直面高等院校腐化的问题;《鸳鸯楼》讲新时代带来新冲击,也催生人们的情感关系和观念产生新改变。包括头几年票房特别好的《我不是药神》这些……你要是说循环,我觉得这才是中国电影的循环。电影确实有它的政治属性,但归根结底还是要服从于它的经济属性——大家都卖票去看的,才是硬道理。你要讲的不能是一个人两个人的问题,你得讲大多数人的问题,观众才会买票。
当然,时代还是会有它自己的循环往复,人类历史有意思的一点就在于认知其实是没有办法那么轻易在代际间传递的,一代人总会有一代人喜欢的东西,但这东西到最后往往殊途同归。你看我们年轻时候看郑老师的《邻居》《鸳鸯楼》,觉得这才叫电影,就得看这个才过瘾。但我们下一代小孩就不爱看这些,就要看香港枪战片,但是看枪战片这帮孩子过了几年之后,他们也不看电影了。又有一帮新的小孩出来,这帮孩子看着之前这一两代人喜欢看的东西,他们也懵,也需要重新形成认识……
但不管怎么说,到了一定年纪之后,不管是哪一代人,都会对自己的人生有困惑,开始喜欢那些能让他们对生活,对世界产生思考的电影,这就是我理解的循环。我觉得中国电影的这个根,始终是没变过的。
Q:在《通灵宝玉与玫瑰花蕾》里你写到:《红楼梦》结尾,宝玉离家出走,看似他一走了之人不在了,但是红尘里其实处处都是他。他变成了红尘。我发现这种观点似乎也变成了你近年来创作小说等虚构作品的一个重要主题,比较典型的像《诗眼倦天涯》,甚至有大部分情节都在想象内发生。《入型入格》最后也有“我之外无一人,无一人不是我”的表述,《脱锁连环脚》等作品里也出现了类似的情节。为什么会一再出现这个近似于神秘主义的主题?
A:其实在我看来,文学不是哲学,文学很多时候,就是作为写作者的我,提供一个和你的生活常识完全背反的东西,对你形成一种刺激就够了。至于我这个和你常识完全背反的东西成立不成立,对不对,那不是文学艺术负责的。
雨果曾说过,他觉得《旧约》里边最好的就是《约伯传》,《约伯传》讲的其实就是信仰问题,一个被上帝反复折腾的老实人,最后决定不信上帝了,他这一不信,上帝反而尴尬,只能掉头劝他,你还是信我吧。雨果那个时代就有我们现在常能看到的那个话题:如果只能带一本书去荒岛,你带哪本?雨果的答案就是《约伯传》。从上帝的视角看,《约伯传》其实就是一个“我折腾你,最后我反而尴尬”的故事,这个就是文学,文学不提供答案,只提供窘境。我在创作这些作品的时候,也希望能收到同样的效果。
Q:但读《诗眼倦天涯》和《脱锁连环脚》这些作品的时候,我常常会产生“这要如何拍成一部电影”的疑问?你的这些作品在阅读时甚至会给人一种《盗梦空间》式的感觉。
A:哈哈!也可以这样说。
Q:但就一部武侠片而言。这种故事或者说讲述故事的方式会不会也形成一种对观众的巨大挑战?
A:其实观众喜欢挑战。我一直认为每一次电影的大倒退,都是由保守的资方造成,在他们看来,电影是一个配方型产品。“我美国的香肠,德国的啤酒都是这个配方,配方百年不变,一变就没市场,只有严格遵循这个配方才能赚到钱。”但就是这种配方思维,让好莱坞把自己给玩没了,好莱坞的一流人才,十年前就都开始转战拍剧,好莱坞电影变得空前地没意思,这都是因为片方不懂得,电影不是配方产品,而是文化产品。人都是喜新厌旧的,交响乐再美,听得多了也烦。你做文化只知道重复旧套路,注定要失败。
好莱坞历史上有好多超级大片,各方面制作都很精良,但就是因为成本太高,不敢冒险,为了保险起见,只得复制五六年前的成功套路,但这五六年间,当年的这个成功套路已经被各种低成本的B级片重复了无数次。你再用大制作重复这个已经让人熟知的套路,观众则必然不买账。可惜大多数的投资人并不明白这个道理,他们其实还是义乌小商品批发市场的思维,什么东西好,我就仿什么,似乎别人成功了,我才敢成功,但我们都知道,真正一流的公司都是做研发的,对吧?
三、《门前宝地》是想要满足一些夙愿
Q:那我们再聊得尖锐一点,你现在已经有连续三部电影(编注:《刀背藏身》《入型入格》《诗眼倦天涯》)都处于一种已经拍竣,但无法与观众见面的情况,这种状况本身是不是也就意味着你追求的这种求新求变的电影思维,在我们当下这个市场里注定是会举步维艰的?
A:我个人不会做这种大局上的联想,在我个人看来,这三部都是特例和个案,它们其实各自无法公映的原因都是不一样的。所以我也不愿意把这三件事用一个大而化之的理由一起包裹起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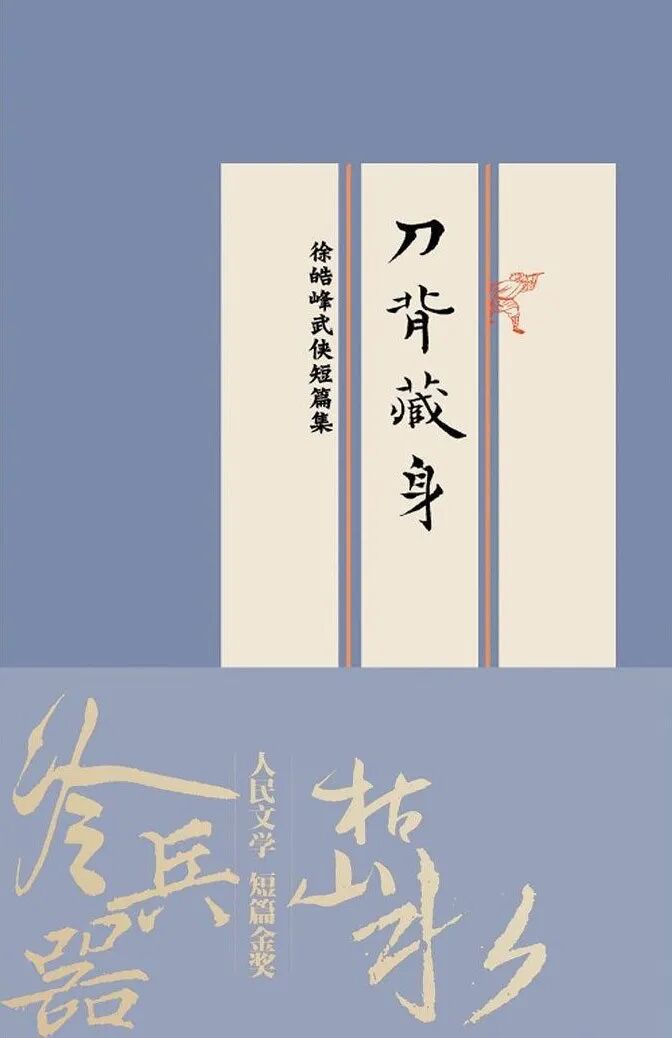
短篇集《刀背藏身》封面
Q:好,那我们先抛开暂且看不到的,聊聊我们已经看过的,比如之前的《门前宝地》,这部电影在内地的票房和口碑相对你之前的作品来讲,应该都算相当的不理想,这次挫折会不会对你之后的创作观产生一些影响?
A:不会,因为《门前宝地》在我作为一个导演的角度看,其实并不是一次失败。因为这部电影打开了我在国际上的销售渠道,它在国际市场上的总营收超越了《师父》,我们做了全美发行,把这部电影卖到了欧洲,甚至卖到了俄罗斯和印度。而且这个片子也进入了美国著名的年度五十佳片评选(编按:指美国著名娱乐网站Polygon一年一度举行的世界电影年度五十佳评选,该评选以注重流行文化与娱乐性著称,《门前宝地》在该网站举办的2024年度五十佳电影评选中位列第三十位),人家那个评选很注重市场性,如果你的电影只是在电影节上拿奖,但最后没有销路,他们是不会评你的。
Q:其实我看过后觉得,《门前宝地》还是一部很有你个人风格的作品,但我个人觉得稍微美中不足的就是删掉了郭龙饰演的老馆长和李媛饰演的会长之间的前史。看小说时候会感觉,这两个人之间的前史,包括他们对武林,对新旧交替,对守成还是思变之间的态度和后面这两个年轻人之间是有很多照应,存在一种强烈的比照关系,某种程度上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象征,这条线删掉之后,剧力感觉一下就有点弱了下来,对整部电影的深度也造成了一定影响。
A:其实这个还是取决于一开始对电影的定位。因为我从来没有拍过一部从头打到尾的电影,所以,这片子一开始的定位就是更注重动作戏,而且就像我刚才说的,你想让这个片种往世界范围冲一冲,对这种特殊行业的人情世故的刻画,就必须收敛。这个问题其实很微妙,因为我们毕竟不是一个大片,如果我们真把这个片子的规模做成大片了,片长150分钟上下,投资好几亿那种,那反而可以放手去描绘这个国家,这个江湖的人情世故,国外的观众反而会接受。
你看七个小时的《战争与和平》,我们中国人一样会看得津津有味。因为作为一部史诗巨著,你如果拍不出我们想象中的那个俄罗斯,拍不出那些让我们一开始理解起来有些困难,但却是特别地道的人情世故,风土乡音的话,观众反而会抵触。
也就是说不同的标准,不同的题材,观众自然就会有不同的期待,这些东西其实都是一开始导演就要跟投资方说清楚的,这部电影要争取谁?在我看来,就是争取国外的那些工薪阶层,中国的武打片曾经在他们的流行文化里是有位置的,但现在,优势没了,好莱坞已经学会了咱们当年飞天遁地,快速剪切的那一套,我这次做的,其实就是实验一种新的武打形态,然后再次带给西方的普通观众一种新鲜感,让他们再次对我们的动作片产生兴趣。
Q:确实,就算是不喜欢《门前宝地》的观众也不得不承认,这部片子在打戏方面是真真切切做到了保质保量的。安志杰和向佐可以说从头打到尾。说起来除了像《师傅》里的陈观泰这种客串明星以外,这好像是你第一次真正系统性的和香港的这种所谓“武行”演员合作,之前除了于承惠这种真正的武术大师,就是张傲月,宋洋,廖凡这种没受过训练,或只有一定的舞蹈功底的演员,通过你的调教,让他们至少“看上去”显得能打,会打,和这两个所谓真正的“武行”演员合作,对你而言是更简单还是更困难?
A:其实在我这里都一样,不管是像张傲月这样只有舞蹈功底的,还是另外几位非武术运动员出身的,在拍我的戏时候,我都会先把他们送到真正的武术家那里接受训练。向佐和安志杰也要走这个流程,向佐开拍前就直接到珠海的梁师傅(编按:指梁绍鸿,咏春拳宗师叶问门徒,“实践咏春”创始人,徐皓峰《门前宝地》一片的动作指导,王家卫《一代宗师》的武术顾问)武馆去学习。因为赶上疫情,安志杰在美国回不来,没来得及去珠海训练,但在拍戏的时候,只要没有他的戏,他就跟着梁师傅在剧组里训练。
所以调教的方法其实是同样的,当然武行也有先天的优势,职业武打演员的优势就在于他们体能都非常好。像安志杰是橄榄球运动员出身,在美国甚至有一种说法,说只有被橄榄球队淘汰下来的人,才会去打篮球,由此可以想象他们的身体素质得有多变态,哈哈。而向佐这次跟我合作更是十分的坦诚,我之前的作品他都看过,知道我比较喜欢在电影里做这种对传统功夫的展现,所以在我们前期沟通的时候,他就主动提出来,可以在电影里把他习练的蔡莫拳全拿出来。
Q:蔡莫拳?这种拳法好像没听说过……
A:北方人大多没听过这个拳法,但蔡莫拳本身在香港很有名,七十年代的时候在那边还有个别称“诡手”。
Q:我们当年在港片里倒是经常听说有蔡李佛拳……
A:对,这其实是他们南派武人在将各家拳法融会贯通时常用的一种命名方式。蔡李佛拳,就是把蔡家拳、李家拳和佛家拳三种拳融合而后产生的拳种。所以蔡莫拳……
Q:就是蔡家拳和莫家拳融合?
A:对的。这种命名的方式在广东非常多。你看像陈观泰学的是大圣劈挂,大圣就是孙猴子,这门拳种就是把猴拳和劈挂拳结合在一起,蔡莫拳也是一种组合拳,就是把蔡家拳和莫家拳相结合,当年的九龙城寨里,其实就有人习练这种拳。但你看那个电影《九龙城寨》为什么看不到有人打蔡莫拳?就因为蔡莫拳其实是不外传的,他不像咏春拳这种,交了钱到拳馆就可以学,洪金宝当年为什么能拍那么多关于咏春的电影?像什么《败家仔》《赞先生与找钱华》。就因为咏春是谁去都能学,这个拳法到底是怎么回事,谁都能看到,但蔡莫拳明显就神秘了许多,所以向佐这次有这个态度,我个人是非常感谢的,然后因为梁叔(梁绍鸿)岁数大了,我们这部电影其实还是更想满足老人家的一些夙愿。
所以为了不弄乱整部片子的动作形态,最后还是没有让向佐用蔡莫拳,只在拍兵器打斗的时候让他用了一些蔡莫棍的棍法,因为棍是南北方通用,然后又是群殴戏,所以只要我不说,没多少人能看出来那个其实是蔡莫棍。而向佐本人虽然主要是受李连杰的这种武术队式的训练,同时也兼习他家传的蔡莫拳,但这两种都不是我们这部电影要拍的,所以我还是让他在开拍前去系统地接受了咏春的训练,而他自己也要迅速地适应这种新的形态,他完成得很好,给了我很多惊喜。
四、咏春、古龙和自己的青春片
Q:自从《师父》之后,我感觉你对咏春拳这种南派拳种好像产生了一种很强烈的兴趣,不光是一部电影,你好像连续三四部电影都涉及咏春拳的东西,包括现在还没上映的《入型入格》里也出现了六点半棍和八斩刀。这是你的个人兴趣吗?
A:其实是我的一种习惯。你看于承惠于老在世的时候,我和他合作就是他有什么东西,我就拍什么。他的枪,包括他打划拉巴子,他擅长的东西,他能呈现的东西我都会拍。这应该也是我的一种珍惜。后来认识了梁绍鸿老先生,我也是照方抓药,您有什么,我就拍什么。其实也是想做一个记载和流传。所以拍《门前宝地》时候,我们拍了六个纪录片,其实也是想借助这部电影,做一个历史资料的留存。

《师父》剧照
Q:当年有个新闻,说你想把古龙的《天涯明月刀》搬上荧幕,但最后好像也没能成行。如果有机会,在不考虑任何具体条件限制的情况下,让你把一部别人的武侠小说拍成电影,你的选择会是哪一部?
A:其实不光《天涯明月刀》,其他的一些古龙作品,像《欢乐英雄》这种也找过我,最后没拍成,其实也都是一个原因——资金问题无法落实。我记得当年片方曾经问过我,如果让你去拍古龙,你会选哪部?我告诉他们,我最有感觉的是《七种武器》里的《孔雀翎》,对我来说,这部作品是古龙精品中的精品。
第二个是《白玉老虎》,有人认为这本小说是“半部杰作”,但如果我拍,就很可能要再少一半,就结束在赵无忌从地藏府脱身后,发现这一切都不过是另一个局,答应要教他绝世武功的地藏把他困住,其实就是为了带着他的老婆跑路,他本应该死在地藏那个洞府里,但却在不可能的情况下,阴差阳错竟然把武功练到了大成。最后的结尾,就是路边一个大洞里,爬出一个胡子很长,但头发已经有些稀疏的人,爬出来之后什么也不干,就是坐在那里看星星,好像从来没见过星星一样 。
Q:连原作那个不是结局的结局都不要了?
A:对,统统不要。这么改是想把赵无忌从主角变成配角,真正的主角换成他妻子,把整部电影变成一个女人的故事。大家都说《白玉老虎》是一个没有写完的故事,但在我看来,古龙写得非常完整,赵无忌就是一个标准的武侠小说主人公。结婚当天,爹死了,老婆走了,自己的武功也不高,人也还不成熟,就是这么一个很常见的主人公成长的故事。但他的妻子,一个没有武功,同时也身不由己的女人,她的命运会如何发展?我觉得这个才是我感兴趣的故事。另外还有一部就是《大地飞鹰》,对这个感兴趣倒不是因为故事,而是恰好有我喜欢的异族风情。
Q:看来古龙是你最喜欢的武侠作家。
A:与其说喜欢,倒不如说是惋惜。古龙一是过世太早,再一个是这个人太浪子,而浪子生活往往很费钱。所以他早年写东西很多时候都有凑字数之嫌,即便他后来已经是富人了,但是这个受穷时候的习惯却一直保持,你看他的一些构思和对人物情感的描写都是非常棒的,但文学上的完成度却似乎总差一口气。所以古龙的东西在我看来更像是爵士乐,很多都是即兴的,就是这几个小时你上台,能把客人弄高兴了你就挣这个钱。这个爵士乐手本身没准都不识谱,但有天才的手感,可能前80分钟都是泛泛,但没准最后20分钟,突然感觉来临,有超水平的天才发挥。
写作需要文笔。但我们这种美术生,我的中学同学普遍都有过的那个遍读名著的时期,我在画画。所以文笔对刚开始决定写东西的我,是个难关。恰巧那时候家里有好几套中学同学送的古龙小说,我就把它变成我提高文笔的一个训练,基本上把那几本小说都逐字逐句改了一遍。改着改着,感觉就出现了。所以对他的东西,我可以说有一种深厚的感情。
Q:如果有一天,你要拍一部完全没有武术,没有武行,也没有武人,摒弃掉一切暴力因素的片子,那可能会是一部什么样的电影?
A:导演这门行当吧,大多数都是少年成名。你看像我的师兄娄烨、王小帅,还有那些世界级的导演,特吕弗、戈达尔基本都是二十多岁就做了导演。所以大多数导演也都会有他们的青春片。但我这种非常罕见。我37岁才拍自己的第一部(编按:此处应指2011年徐浩峰的第一部院线长片《倭寇的踪迹》),人到中年才上路,算是那种比较罕见的,没拍过自己的青春片的导演。
你问我将来有一天会不会拍一部完全与武术和武林无关的电影,我现在就可以回答你,我肯定会拍,而且已经确定要拍什么,就是我自己的小说《花园中的养蛇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