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老北大”的生命之真——读《问西家书》谈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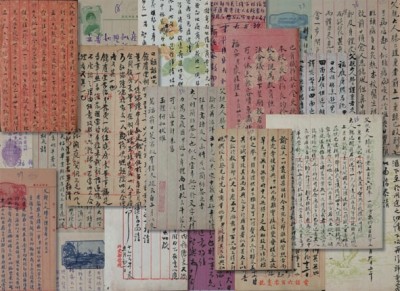
“问西家书”部分函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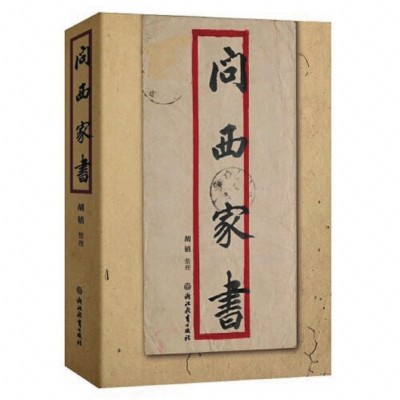
《问西家书》,胡镇整理,浙江教育出版社,2025年4月第一版
举凡年代久远的大图书馆,都会有一些独特收藏,声名较著者世人皆知,更多的则长期无人解识、默处一隅。譬如浙江图书馆,文澜阁本《四库全书》自属镇馆之宝,其入藏、历劫、搜辑补录、转移与复归,在在有人梳理追述;而小小七册“问西家书”,是北京大学1915级学生孙家桂(毕业时改名智舆,字问西,以字行)的近300封书信,提供了丰饶真切的历史信息,极为难得。感谢该馆古籍部胡镇的发掘整理,今年初夏由浙江教育出版社甫一推出,即引发学术界的关注。
一
在众多文体中,书信应是较少虚构的一类。如果说清代奏折存在大量造假成分,官员日记亦不免曲笔和有意编捏,书信的真实度要高许多。尤其是家书,述说日常细碎,以及书写人的观察和感受,常可弥补叙事的缺环。前些年笔者为清中期枢阁大臣王杰、王鼎作传,痛感史料过简,经搜罗细读其家书,始得以拼绘出一个稍觉圆整的形象。《问西家书》皆是孙问西在离乡后所写,记录了一个游子的天涯漂泊,追求与梦想,成功与挫败,喜悦与沮丧,是他个人的生命之真,亦为那个纷乱时代留下一份别录。这宗信函起于1914年,止于乃父辞世的1934年,主要写给父亲孙蓉第,也有他回乡省亲时妻子恽蔼写来的两封,读来令人感慨系之——问西在此期间也会给其他人写信,此后当然还要写很多的信,却因没了老父的珍护弆藏,绝多已化为乌有。
孙问西(1894-1959),富阳龙门镇人,1914年1月离乡求学,以专业第三名考入北洋大学预科。时在民国之初,青年学子多有政治抱负,“蔑弃文学,等视弁髦”,问西却以保存国粹为己任,决定改考北京大学,1915年夏被录取。读书的一应开销自是取之于父母,问西深知省俭,也将花费详细禀报,曾制作了一个费用表,逐项开列三个学期的预算,如“九月至十二月份费用”,就有:学费12元,讲义费2元,寄宿费4元;膳费21.6元,仆役洋灯及零用费24元,火炉费6元。胡镇认为“孙问西一年的上学费用,几乎相当于一个农村家庭两年的开销”,是可信的。由是亦知,那时从乡村普通人家走出一个求学者,背后是父母的东拼西凑、抵押告贷,是妻儿和兄弟姐妹的长时段苦撑,绝非一个人在奋斗。
二
在校四年,发生了袁世凯称帝和二次革命、撤销帝制和张勋复辟,还有声势浩大的五四运动,问西在书信中都有记述。兹略作节引:
目下帝制问题及洪宪年号均已发明令取消。其原因,盖由广西之毅然继云贵而宣布独立,广东之电告,军心动摇难以维持。江苏、浙江诸将军之电陈平和解决,以安大局,以舒民生。康有为、汤化龙之联合致书总统,逼请退位,免军财之耗,伤生灵之涂炭,藉以收拾残局。加以日本之跃跃欲动,外交界之警告频来,于是帝制之取消会议始行决定,而有帝制及年号取消之申令。但将来大局如何,尚未可逆睹也。北京甚安宁,一切秩序如常,浙江想亦无甚惊惶。(《问西家书》,浙江教育出版社2025年版,第59页。下引该书,仅注页码)
叙述简要,评说直接,也证明那场“众星捧月”般的闹剧,并未在京城引起大的动荡。而张勋的辫子军不同,孙问西记述共和军攻打张勋的南湾子宅邸较详,曰:
自本月一日复辟以来,警报频传,以故终日惶惑,心绪纷繁,即欲读书而亦不能。自十日起消息渐紧,十一则共和派、复辟派之谈判,遂决裂。张勋负固不屈,筑土壕、积沙袋于其南湾子宅邸之要冲,预备作城巷之交战。南湾子者皇城之东南隅也,离本校不过一里余路。男以为事变未即起,拟于十二日往西山暂避,殊知即于是日黎明四时许开始击斗。男为枪炮声惊醒,方醒时以为共和军之攻击大门南边之紫禁城也,惶恐异常;及出寝室一听,方知声来自东南,则共和军攻击张邸也必矣。斯时亦已无可逃避,故伏地而卧,以免为流弹所中焉。自四时起至七时,炮声、步枪声、机关枪声复连重叠而出,无一息之间隔。自七时后声稍杀焉,午后则惟时闻枪声……避寝于洋房讲室内,殊知因受凉,隔一日而痢疾作矣。(第76页)
乃因亲历,写来尤觉生动。短短十几天,又一场闹剧收场,复辟之不得人心,于此可见。
三
入校的第二年,蔡元培出任北大校长,问西很敬佩也很受鼓舞,学习更加努力。校园中从来都有各色人等,其室友就酷爱饮酒、赌钱、嫖娼,呼朋引类,问西为之苦恼,却也淬炼出读书的定力。蔡元培对师生之关怀,也在《问西家书》中得以呈现,他曾因家事请求帮助,蔡校长不以为唐突,为之细心分析情由,寻找更合理的化解方式。
临近毕业前,问西写信向父亲吐露真情:“胡先生钧愿为男留心帮忙。胡先生现为参议院议员,在京极有势力。”“高等文官,男若在京拟姑一试,但不可对人言,以男在京常对同乡宣言男不屑应试、彼考试官何配试男等人。”“若新国会解散,男拟设法举款二三千元办众议员。”(第108页)理由是一旦在众议院得势,就不难弄个部长、次长的位置。孙问西抱负远大,却非好高骛远的性格,设定目标皆经反复斟量,也留心编织自己的关系网。这些话自不便为外人道,却是一个望子成龙的父亲最爱听的,积极为之求门子,托人情。
1919年的毕业考试,孙问西排名经济门甲等第一,得到了留校做助教的机会,因报酬不高,教务长还答应给他加一些课时,另有酬劳。而问西的首选是出国,参加了“高等文官考试”,获经济专科第一名,入职外交部,次年即派往中国驻意大利使馆,堪称顺遂。他的英文甚好,到罗马后又发愤苦学意文、法文,仅数月便可“会谈普通之话及写普通书札”。问西函告远在家乡的父亲,表示“一年以内尽男之心力,当可精通(意文)。明年拟入罗马大学院研究外交、政治、经济各学科,以冀取得博士之学位”(第190页)。正因为这份执着和努力,问西很快就脱颖而出,奉派往瑞士参加万国禁烟会,并独立编译完成数万字的《国际联合会报告》。驻意公使唐在复对他很倚信,屡次保举,晋升“主事加随员衔”,并于1923年荣获三等一级外交部奖章。而经济上的拮据几乎无时不在,国内政局不稳,长期拖欠驻外人员的薪水,老家则多有期待,问西曾挤出一些钱寄回,也于信中反复解释:
需要款项一层,倘男积有余款,自当随时寄上。惟外交部自二月后未发一文……男在此每月由公使借垫一百五六十元应付。往常之费物价太贵,欲添做衣服一袭而未能。现在瑞士物价更昂,日前在旅馆偶以饭菜太坏,每次添要两个煎鸡子,到结账时(每星期一结账)每二个煎鸡子索瑞士洋二元半,合中国洋一元三四角,男不禁为之惊骇。兹在联合会办事,虽博得秘书之虚荣,而关于日用之费尚须赔垫若干。微闻会事终结后有百数元之津贴,倘果有之,男得不做衣服即将此款奉寄,但款到恐亦须在阳历十二月中矣。(第202页)
毕业后成为外交官,却仍是没钱养家,问西只好在信中不断地“画饼”。而越画越不圆,家中兄弟啧有烦言,甚至提出要分家,乃父好生为难。
鉴于这种情况长期不见好转,升迁亦迟迟不得落定,孙问西心灰意冷,虽有唐公使挽留,仍于1924年6月踏上返程。经过一番运作,他得以重回外交部任职,期待则的是外交高级职位。按说他的条件是足够的,北京大学优等生,又有北大教员、外交官经历,参与过国联项目,被誉为“当今留学界不可多得之才”,可又怎么样呢,那是一个军阀混战的时期,其实文阀的明争暗斗亦无时不在,前朝勋旧,民国猛人,数不清的豪门势要,结成一个看不见的大网,年轻后辈要出头谈何容易! 问西曾被选任驻古巴使馆三等参赞兼副领事,已经总长、次长谈话允诺,仍被他人抢去,只能付之一叹。
四
浙江人文醇茂,历来在京居高位者甚多,孙问西颇知走动公卿,为何还是备经坎坷? 答案是缺钱。《问西家书》的叙事跨越二十年,阅读一过,最深刻的印象是他的经济窘迫,很少有不缺钱的时候。读书时向家中要钱,工作后仍会向家中要钱,每次都会认真写清需求的理由,说明将来会还,也确实还了一些,但总体上亏欠家中很多。要说他的家族还算殷实,但支裔既繁,乃父又有九个儿子和至少两个女儿,只能勉励维持。他在离乡前已结婚,发妻在老家独自抚养两个儿子,少不得含辛茹苦,竟于1920年病逝。小妹代为照料其子,问西充满感激,承诺妹妹出嫁时将予数百元办嫁妆,而待伊真的要嫁人时,咬牙跺脚才拿出一百元,在信中连说羞愧。
孤寒,应是多数读书人的宿命,而乱世尤甚。
“兹值军事方殷……京中各机关干枯万分,薪水均欠至一年以上”(第263页),此问西信中所写,绝非虚言。为经济所迫,他想到做茶叶外贸的生意,想去东北买块地做财主,想要开矿,而前提为先有一笔启动资金,偏是最缺这个。他甚至将脱贫寄望于再婚,在家信中一再言及:“男自己命中无财,故非得一有财之女子为内助不可”,“私意须觅得一女家有钱之女子方可允诺”。为做媒者甚多,问西先选中“家中富有资财”的“上海张家花园之小姐”,亦有姿色,但张家探知其家境后婉拒;又竭力谋划去南洋做个领事、副领事,“南洋有资产之华侨甚多,华侨女子面貌可观者亦颇不乏人。顾少川夫人面貌清秀,陪嫁数百万财产”,述说时满带艳羡;而几经挑拣和被挑拣,有人为介绍前内务次长、总统府秘书长恽宝惠之女恽蔼,家世显赫,品貌绝佳,对方经调查对孙问西也很满意,遂迅速敲定。恽家略知问西的境况,包揽了婚礼等一应使费,而订婚戒指毕竟要男方置办,又难煞这位准新郎。问西写信托父兄向钱庄借贷,从外国洋行买了一枚白金钻戒,因能以外文对话,得到打折优惠,“定价四百八十五元,男与该洋行经理磋商许久,减去四十五元,合四百四十元,与大人来函所示之价相若也”(第306页),可见出几许小得意呢。
世事难料。问西如愿抱得美人归,可新妇恽蔼很快就发现肺病,咳血不已,已批准的加拿大副领事也因此无法赴任。他在不久后迁入恽府,日子大为改观,至于此前朋友告知的“十万陪嫁”,则纯属想象。二人婚后琴瑟和谐,次年春诞一女,两年后又得一子,孰料恽蔼产子后即告不治。岳母代为照顾两个孩子,未久亦病亡,幸有恽家姑妈接手养育,庶免于饥寒漂泊。之后,岳父仍尽力提供帮助。孙问西曾任职于盐务署、北平特别市市政府、青岛特别市政府、江苏高等法院,也曾做过福建罗源县县长,“脚跟无线,如蓬转”。后来到大学执教,才算稳定下来,著有《美国现代史》《民生主义经济政策》等书。
应予说明的是,孙问西节操凛然,抗日战争期间不光没有担任伪职,还把两个年长的儿子送到前线和军校,长子承熙英勇牺牲。
“问西家书”第一册,于末页黏贴着一张价格单,可知这批私人信件曾流入市场,标价14元,为浙江图书馆所购藏,真是侥幸。其是一位“老北大”的读书历宦的行履印迹,也是一幅政坛、学界和民生的时代长卷,亲情络绎,苦情络绎,蕴涵博富。钱穆先生暮年作《师友杂记》,曰:“能追忆者,此始是吾生命之真。其在记忆之外者,足证其非吾生命之真。”而往事必然如烟,追忆每多拣选,《问西家书》则携带着岁月的风尘,于实境讲实事,抒发实感,喜怒哀乐皆在其中,诚可谓二十世纪前期一位北大学生的生存之艰,生命之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