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燕:再论文学史的权力——重读刘大杰《中国文学发展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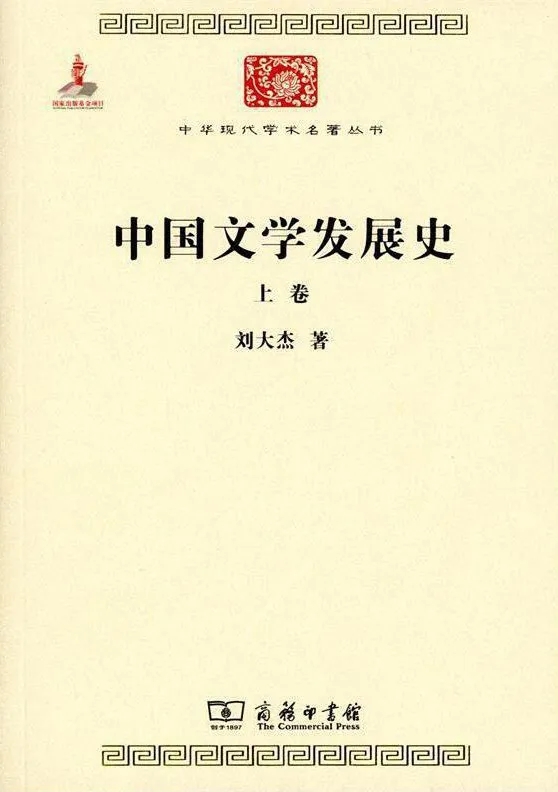
《中国文学发展史》,刘大杰 著,商务印书馆2015年版
最早知道有刘大杰的《中国文学发展史》,是一九七九年在北京大学上中国文学史课的时候,这是中文系本科生的必修课。当时,还没有合适的教材,有老师在讲台上,手里拿的是一册小学生练习簿,上面密密麻麻写满他自己的教案。也有老师参加过游国恩、萧涤非等领衔的高校版《中国文学史》编写,并且熟悉余冠英、钱锺书等领衔编写的中国科学院文学所版《中国文学史》。这两套俗称“蓝皮本”的文学史大名鼎鼎,可是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初出版后,许久都没有重印,很难找齐。于是,就有老师建议我们去看刘大杰的《中国文学发展史》,这部书在一九七三、一九七六年重版过。这样,我便去了东安市场的中国书店,在那里找到刘大杰的书,却没想到一大摞新书堆在那里,据店员说根本卖不出去。我回来报告老师,老师说:“那你不知道,刘大杰的《中国文学发展史》是各种文学史里最有个性的,你要去找它最早的版本来看。”
等我毕业多年,读了先后出版于一九四一年、一九四九年的刘大杰《中国文学发展史》上下卷之后,才渐渐明白当年我的老师(他们是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初进大学的那一批人),为什么说它是最有个性的。
那时,我已经看过自林传甲、黄人以来的不少中国“文学史”,或称“文学流变史”“文学沿革”,两套重印的蓝皮本《中国文学史》,更是因为频繁阅读,书脊都破裂了。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前,书籍出版,包括古代文集的整理、线装书的影印,都不像现在这样发达,读一部好的文学史,仍然不仅能窥见像过去胡适所讲的一个系统的文学史观念,还能认识好些难得一见的作家作品,以广见闻,是一件事半功倍的事情。因此,在那个年代,学界都还重视“文学史”这样一种著述形式,有人在写更详尽的“大文学史”,也有人提倡“重写文学史”。而在我的印象当中,自林传甲、黄人、谢无量那一代到两套蓝皮本,这一个甲子的文学史写作,又是从文学观念和讲述形式各异,到逐步形成共识以及固定的叙述脉络的过程,即由百花齐放收拢定于一。像两套蓝皮本文学史,最后都是用了集体编写的方式。虽然主其事者在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就已成名,可是,当他们编写这两套文学史时,据说也都收敛了各自的锋芒,更讲究共识、通识,在行文上也力求风格一致,注重叙述的平实与文字的简洁。如果是放在这样一个文学史写作的时间序列当中,那么,应该说刘大杰的《中国文学发展史》就恰好是在百花齐放的文学史写作阶段将要结束时,所出版的最后一部具有个人性的文学史,它理所当然地保留了那个时代的特点,也就是在我老师那一辈人眼里闪亮的个性。
比如,在短短的《自序》中,刘大杰会说“我在写这本书时”如何,说这“正是我这工作成绩的苦痛的说明”,“我”字不离口。对于“我”之个体的这种张扬,在后来的文学史里,几乎看不到。我至今记得,在我年轻时受到的学术训练里面,是很忌讳写文章反复提到“我”字的,字面上看不到“我”却又让人知道处处是“我”的见解,才被视为文章高手。但是,刘大杰不管这些,他的自我很大,丝毫不受压抑。
又比如,刘大杰在文学史中引了很多古今中外的名人名著,他讲卜辞,是从甲骨卜辞的发现讲起,讲卜辞怎样引起林泰辅等日本、欧美学者的注意,中国学者罗振玉、王国维、郭沫若等又在这方面取得过怎样优良的成绩。他讲《诗经》,也是既引述从陈启源、魏源、胡承珙到王国维《殷周制度论》以及傅斯年等人的研究,又引用美国考古学家莫尔干的古代社会分期理论、佛理采的《欧洲文学发展史》《艺术社会学》、罗威的《我们是文明吗》;讲先秦散文,引瓦夫生的《辩证的唯物论》;讲屈原,则引梁启超的《楚辞解题》,还有汤姆生的《科学概论》、托尔斯泰“人生的殉教者、艺术的圣徒”之语。在后来的文学史里,我们也不大看到这样丰富的征引,因为文学史与研究性的论著不同,它只提供结论、定论,而不必展示研究论证的过程,这已经成了学界默认的规矩。但是,在刘大杰这里,我们不仅能看到结论,还能看见结论之所由,看见他那个时代活泼泼的学术潮流与阅读风气。
这些都是刘大杰《中国文学发展史》与众不同的地方。尤其对我们这样的晚辈来讲,因为我们已经先接受了后来文学史的规训,然后才翻开刘大杰的书,当然,立刻就能感受到他扑面而来的那种个性。
刘大杰最为学界称道的地方,还在于他旗帜鲜明地提出要尊奉法国朗松的文学史观,将“文学发展史”首先视为文化史的一部分,其次是讲文学的进化而非退化。刘大杰当然不是将朗松引入中国的第一人。朗松发表于一九一〇年的《文学史方法》一文,一九二四年就有了黄仲苏的中译本,而朗松的《法国文学史》,在一九二〇年代也有了中文节译本,但刘大杰算得上是将朗松的文学史理论及方法运用于中国文学史写作实践的第一人。这大概不会有什么疑问。
我们知道朗松的主张,是要将文学研究与历史学、社会学相结合。在他影响下,刘大杰也指出,写中国文学史,必须要将文学与社会、宗教联系起来,所以,既不能像五四前的文学史研究那样,“死守经学范围”,也不能像五四后的文学史研究,“死守纯文学范围”,在讲述一个时代富有特点的文学时,还是要说明这一文学是在什么样的政治状态、社会生活、学术思想下所产生的。
比如,在分析杂剧何以兴盛于元代的时候,刘大杰就特别重视戏剧与个人性的诗词写作不同,它必须依靠商业资本、依靠“繁荣的社会经济与富饶的大都市”这一点。在他看来,正是由于游牧民族的蒙古人“把欧亚打成一片,国际交通四通八达,造成中国商业资本主义空前的发展”,使“当日的北平”仿佛“今日之上海”,成为“全世界最富最繁荣的国际都市”,在“人口多经济发达”的这样一个都市里,“经营戏场的人可以得利,对于演员与剧本的报酬也可以增加”,随后还有“舞台设备的改进与剧本的精求”,这才吸引文人学士参与其中,带来一场空前的“戏剧运动”。
《中国文学发展史》从殷商到清末,都是这么写下来的。这也就是为什么我要说,从文学史写作的时间序列来看,刘大杰仍然可以说是接续了以胡适《白话文学史》为代表的文学观念与文学史叙述风格,但是,他的《中国文学发展史》到底走出了一条不一样的道路,别开生面。
经过晚清民初的提倡,五四前后文学史教学及出版风起云涌,到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文学史已经成了体制化文学教育中最重要的部分。一九三八年,当时的教育部便规定中国文学史为大学必修课程,也就是说当刘大杰写《中国文学发展史》的时候,实际上“前人栽树”已经绿树成荫,他当然能在大树底下好乘凉,其实要走出这片绿荫,倒并不容易。可是,他贯彻朗松的理论,并总结文学史编写二十多年的经验教训,同时吸取文学史及历史、宗教等相关学科的研究进展,还是将中国文学史带到了一个新的境界,使其成为胡适以来文学史写作最完美的收官作品。到今天我们来读他的书,依然不得不为他思想的敏锐、眼界的开阔和文笔的生动,再三感叹。
但尽管我们说《中国文学发展史》是五四以来那种文学史叙述模式的收官之作,不过,看刘大杰本人,他那时才四十多岁,似乎并没有收官的意识。
《中国文学发展史》上下两卷出齐不久,转眼就迎来了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新的课程改革,文学史教学的改革也在其中,各大学都忙着编写新的文学史教材,直到一九五七年教育部颁布《中国文学史教学大纲》,一锤定音。刘大杰是这份部颁《大纲》的起草人之一,而就在《大纲》发布的这一年,他又急急忙忙抛出了《中国文学发展史》的修订本。
显然,这回是踩着了锣鼓点儿。因此,在一九五九年的《文学评论》杂志上,就有中国科学院文学研究所胡念贻、乔象钟、刘世德、徐子余几位当时算是年轻学者联名写下的文章《评〈中国文学发展史〉》。在评论中,胡念贻他们也承认《中国文学发展史》“曾经是一部影响较大的书”,却又毫不客气地指出,新的修订本依旧保存着“旧的资产阶级的唯心主义观点”、“五四以来许多资产阶级学者中间流行的论调”以及“庸俗社会学的观点”,据此,他们要求刘大杰应该“来一个彻底的改变”。我之所以留心这篇评论,是因为我自己在文学所读过研究生,又工作过十来年,还见过其中两位作者乔象钟、刘世德先生。我也注意到,刘大杰在回应中虽然说自己的书是有缺点,可更多表达的是他内心并不服气。所以,到了一九六二年,当两部蓝皮本文学史出版,刘大杰的《中国文学发展史》也再出一版,遥相呼应。到了一九七〇年代,学术出版几乎成了沙漠,唯独刘大杰的《中国文学发展史》还能再出新版,也就是几年后我在书店里面看到过无人问津的那一版。
我自己也没有想到,在刘大杰去世后三十年,我来到他教过文学史的复旦大学,也教一点文学史。距离刘大杰《中国文学发展史》的最初出版,已超过八十年,而中国文学史,如今仍然是中文系本科生的一门必修课程。我在四十年前开始写《文学史的权力》的时候,曾计划过,要将刘大杰《中国文学发展史》的不同时期版本放到一起做比较,看他是如何在三十年里一再修正自己的思想及文学史叙述,那既是一个人的学案,也是文学史写作在这三十年间寻寻觅觅、曲折转圜的一个剖面。可惜在没有互联网的时代,现代学术资料的收集是个大问题,而资料不足,问题便很难讲透。近年来,碰到一些年轻人,对我讲“文学史”作为一种古典文学的教育、传播形式在现代中国的起源及发展而使用“权力”这个词颇不理解。他们已经不像我这一代人,对于在大学里要不要讲文学史、怎么讲文学史,事实上是由权力所支配,还有所敏感。我想他们大概也不知道这里有过刘大杰。刘大杰曾经是那么执着于《中国文学发展史》的一版再版,按照后来一段时间人们的说法,是不惜迎合时势却又最后失势,也未见得不是为了在大学的讲台上,始终占据一席之地,拥有话语权。
甲辰年大寒写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