师陀与杨刚的交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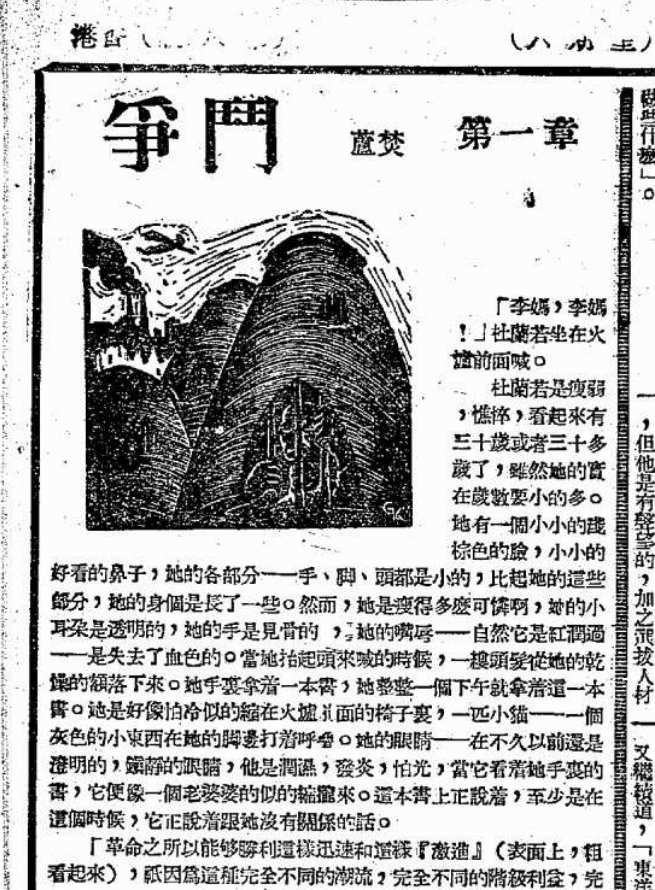
1940年11月至12月,《争斗》前七章在香港《大公报》连载
85年前,香港《大公报》的一个人事变动,为作家师陀创作反映一二·九学生运动的长篇小说《争斗》创造了机会。事情的起因是:1939年8月,《大公报》副刊主编萧乾接受伦敦大学东方学院的邀请,在《大公报》的资助下,决定离开香港赴英讲学,同时还担任《大公报》的驻英特派记者。职位空缺后,《大公报》属意一名因循守旧的北方作家,但萧乾却坚持推荐他的作家朋友杨刚,但《大公报》负责人胡政之对杨刚的共产党员身份很有顾忌,认为这与《大公报》“不党不私”有悖。
萧乾则以“商业报纸赢利需求”力劝胡政之:杨刚爱国,她笔头快,判断力远比我强,1936年你不是说过“兼容并蓄”吗?如果把你那位请来,刊物会马上回到1923年以前的学院派老样子,而今天已经抗战了!我保证所有多年来同刊物保持联系的作家们,都会同报纸分道扬镳。
第二天,胡政之经过认真思考后要萧乾发电报惠请当时还在塔斯社上海分社担任英文翻译的杨刚前来香港。收到萧乾的电报后,杨刚立即向党组织汇报了此事。中共上海地下党负责同志听后,考虑到上海成为孤岛后,非常需要骨干力量继续坚持斗争,主张杨刚不要去。杨刚内心很想去香港工作,但作为一名党员,她首先要听从党组织的安排。杨刚只得电告萧乾,告知自己目前无法前往香港就职。但电报刚发出不久,从香港到上海的南方局负责同志获悉这一情况后,力主杨刚前去《大公报》,这样更利于革命工作的开展。经过认真考虑,党组织同意杨刚去香港接手《大公报》副刊的工作。得到通知后。杨刚立刻给萧乾发出第二封电报,告知自己接受邀请马上动身前往香港。8月底,杨刚抵达香港。
1939年9月1日,杨刚正式接替萧乾开始在香港《大公报》工作,担任《文艺》和《学生界》两个副刊的主编。上任后第四天,杨刚发表了《重申〈文艺〉意旨》,她决心将《大公报·文艺》打造为文化战士,她要为《大公报》副刊“环上甲胄,披上战袍”。
杨刚为此特意提出:“《文艺》副刊在这风雷剧变的局势下,……永远是帅字旗下的‘一名小兵’。”
为让《大公报·文艺》香港版摆脱以往“尽量不登杂文”“不参加文艺界任何斗争”的传统,杨刚决定扩大副刊的刊登范围,尽可能多地刊登符合共产党革命思想的各种作品以影响社会,并提倡:凡可以称为文章的东西,在《文艺》的哨位上应该是一位击不倒的勇士。他可以明攻,暗袭,奇动,各中要害。《文艺》在抗战上没有躲避宣传,今天也无所谓标榜。
正是在杨刚的主持下,《文艺》《学生界》两个副刊增加了来自敌后游击区作家的战地生活报告等内容。据统计,《大公报》香港版《文艺》副刊共发表来自延安的作品118篇,其中萧乾主持期间发表44篇,其余74篇都是由杨刚编辑发表的。
1939年10月,为纪念鲁迅先生逝世三周年,《文艺》副刊特地在香港文艺界发起了一场关于“民族文艺”问题的讨论。许地山、刘火子、黄文俞、郁风、刘思慕等十多人参加了座谈会。这次座谈会的纪要在《文艺》副刊上发表后,引起强烈的社会反响,“民族文艺”一度成为香港文艺界的热门议题。1940年,杨刚又发起了一场“反新式风花雪月”的大讨论。为此,她发表文章《反新式风花雪月——对香港文艺青年的一个挑战》,旗帜鲜明地反对弥漫在香港的“世外桃源”气息,并批判香港文学界迷茫的个人主义倾向和对祖国空虚的呼喊。这场讨论再次在香港文学界引起了更为热烈和广泛的反响。乔冠华、冯亦代、袁水拍、郁风等人积极赞成杨刚的观点,主张战时文艺应该为抗战服务,创作者要努力写出有血有肉、反映时代风貌的文艺作品。此外,杨刚在主编《学生界》时,非常关注香港学生的学习和思想状况。她常通过互动方式将《学生界》与学生之间的距离拉近再拉近。
除正面宣传中国共产党的政策方针,歌颂敌后军民的感人事迹之外,杨刚在主编《文艺》和《学生界》副刊期间,还积极邀请解放区、沦陷区作家创作敢于大胆揭露反动派的黑暗统治和腐败黑幕以及反映中国人民积极抗日救亡的作品。正是在这一时期,师陀受杨刚邀请,开始根据自己经历的一二·九学生运动创作长篇小说《争斗》。该小说讲述了1935年一二·九学生运动在北平爆发前后,革命青年杜兰若、革命教师马已吾,以及进步学生杜渊若、胡天雄、李文多、瑞莲等人在筹划以及进行和平游行示威时遭遇血腥镇压的故事。小说还描写了年轻女学生瑞莲因遭受国民党反动军警残酷殴打而不幸去世,她的母亲董太太进城得知消息后悲痛欲绝。
《争斗》不是师陀为香港《大公报》创作的唯一作品。根据《师陀著作年表》《师陀著作年表(增订稿)》和《〈师陀全集〉中〈师陀著作年表(增订稿)〉勘误》可知,1939至1941年,师陀为香港《大公报·文艺》还创作出短篇小说《颜料盒》《桃红》《恶梦》《贺文龙的文稿》《塔》以及散文《方其乐》《归途》《上海的难民》《战时一景》《风波》《招顶》《住了》《淑女》等作品。
由此可见,那一时期师陀对于杨刚的邀约回应得十分积极。杨刚对于师陀的文章也是全力支持。谈及师陀与杨刚的交往,最早还要追溯到1935年。晚年的师陀在1988年第3期《新文学史料》曾发表回忆文章《两次去北平(续篇)》。在文中,他两次提到杨刚:
约在一九三五年冬天,萧乾同志已经从燕京大学毕业,在《大公报》主编《文艺》普通版,前来北平宴请写稿人。被宴请的人全住在北平,却分为两批:头一批是周作人、俞平伯、杨振声等人,第二批是冯至、吴祖缃、屈曲夫、刘白羽、杨刚等人,其中也有我……在我们那批人中,杨刚是活跃分子,到处跟人碰杯,到处找人谈话,并教我以后多跟她联系……杨刚大约是地下党员,跟顾颉刚合编过一份综合性刊物,我曾写过稿。
我第二次去北平,就现在还记得的,还有下列几件事。首先是开高尔基逝世纪念会,地点是海甸燕京大学,通知我前去参加的是杨刚。
由此可知,杨刚与师陀1935年冬便已相识,1936年当杨刚与丈夫郑侃帮助顾颉刚编辑中国早期社会综合刊物《大众知识》时,就已向师陀约稿。
1937年6月20日,杨刚还在上海《大公报·文艺》副刊第351期发表了《里门拾记》一文。在文中,她对好友师陀1937年1月在文化生活出版社新近出版的短篇集《里门拾记》进行了十分中肯的点评。《里门拾记》是巴金主编文学丛刊第4集之一,该书共收录师陀《毒咒》《过客》《秋原》《受难者》《巨人》《村中喜剧》《路上》《雾的晨》《酒徒》《倦谈集》《巫》《百顺街》等12篇短篇小说。在文中,杨刚认为:“这是位出过一册《谷》和一本《里门拾记》的人,还有一些他自己所谓的‘鸡零狗碎’……里门拾记是辛酸的,哭哭笑笑的,但也掩不了它字里面的和善,那使他在恶骂的时候并不见出刀笔,以及他自来自去无所依赖的笔锋,那初读来,令人想到鲁迅,细究究,却以为鲁迅近于宫笔,芦焚则滃云点染,取其神似而已。”在文章的最后,杨刚对师陀有过这样的评价:“倘若中国的农村小说有它的前途,芦焚正在试着一条中国的有些迷惑性的路径,这条路可以像晦涩诡僻回去,也可以把这个懵懂的尚不曾十分明白自己的民族性揭发出来。”可见,杨刚对于师陀的写作是十分认可的。这也为师陀在香港《大公报》连载《争斗》打下了坚实基础。
自1940年11月至12月,《争斗》前7章在香港《大公报·文艺》和《大公报·学生界》连续刊载。
但在《大公报》连载7章后,《争斗》却因故停载。至于原因,师陀在自述中说是“因香港沦陷于日寇之手,《大公报》停刊”。可据相关文献研究资料显示:《争斗》第7章最后一部分发表时间是“1940年12月31日”,而香港《大公报》停刊时间是日军即将攻陷香港前夕的“1941年12月13日”。《争斗》的停载与《大公报》的停刊相差有近一年的时间。可见,师陀的这个说法并不准确。对于停载《争斗》,1941年1月4日香港《大公报》在《大公报·文艺》第1002期给出了自己的解释:
启 事
《争斗》作者现在病中,续稿未到,此文暂停发表,敬希读者见谅
编 者
笔者认为这种说法并不足信。因为,师陀当时生活较为贫困,他常常为生计发愁,而稿费是其重要的生活来源。为了生存,师陀需要不间断地写小说、散文、诗歌、戏剧,而且小说《争斗》已写到第7章,师陀不大可能“因病”轻言放弃该小说的创作。这背后的原因应是小说《争斗》直接体现了中国人民反抗日本侵略者入侵的民族精神,这让港英政府十分紧张,害怕得罪日本而强令《大公报》不许再发表该小说。作为我党长期从事新闻工作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杨刚在面对港英政府和《大公报》上层压力时,为了守住《大公报》副刊——这个来之不易的宣传我党抗日救亡的舆论阵地,不得已最后选择暂时停止连载《争斗》是很有可能的,而真实原因又不能对读者言明,故只能编造一个理由。
但师陀并未放弃,时隔6个月,1941年7月他将与《争斗》前7章一脉相承的后两章,以《无题》为名,在上海租界的《新文丛之二·破晓》上继续发表。只是可惜,其后再也没有继续发表。
1941年12月25日,香港被日军占领。1942年1月9日晚,奉党组织命令,杨刚随同邹韬奋、茅盾、金仲华、羊枣、胡绳、廖沫沙、于伶、叶以群等文化名人撤出香港。
其后,师陀与杨刚似乎很少再有交集。
(作者系中国现代文学馆征集编目部主任、研究馆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