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明春:用文学之笔书写“医者仁心”

四川作家李明春的文学创作的题材多集中于乡土文学。这位长期在农村基层工作的作家履历繁杂,曾当过夜校教员、生产队队长。农村基层的许多事情,李明春不仅是亲历者,还是决策者,所以他的创作几乎是“本色书写”,乡土气息和生活气息浓厚。而新作《天下国医》则聚焦了中医,以川东中医世家传人龚天缘游学为主线,讲述其遍访中医世交、破解疑难病症的传奇,将专业医理融入文学叙事。
6月6日,四川作家李明春长篇小说《天下国医》研讨会在京举行,沈阳师范大学特聘教授贺绍俊赞赏小说“游学+调研”的结构,称其“像一份为中医发展提交的文学提案”。而李明春坦率地表达,这部扎根基层、融入巴渠文化的作品,既是对传统文化的回望,也是对“中医如何走向未来”的叩问。
中华读书报:您在后记中提及《天下国医》的初衷缘自和子女的闲谈——是否还有更深层次的原因?
李明春:酝酿多年,一次家庭闲谈引发,有了写的念头。真正创作冲动来自于阅读,有所发现,有所触动,迫不及待想写出来告诉人们。动笔想到文学表达,下笔则一发不可收拾。
历史上,中医药曾是世界上最好的医学,中国人均寿命曾比欧洲最好的法国高出十年。在古时候,医家在诸子百家中与道家,儒家齐名。是不依附于任何宗教或学术门派的独立存在。这不是“阿Q”自慰,总觉得应该理直气壮给中医药正名,中医药不是神学,不是玄学,实实在在是治病救人的医学。
2013年世界发生了一件大事,各国协作完成了人类基因组序列图。全世界一片欢腾,一个叫做“精准医学”理念应运而生,认定医学会来一场天翻地覆的革命,人的平均寿命定会突破百岁大关。十余年过去了,才发觉精准医学任重道远。物极必反。 三十年河西四十年河东,机遇默默向东偏移,西医开始向中医致敬,市面竟有了《西医学习中医简明手册——应读、应背、应知、应会》问世。 诟病眼下医患关系紧张,国民对医疗福利不满,成了世界性话题。这里面有医学本身的问题,绝不是无病呻吟,是病家不满情绪发酵后的气息散发,是砂子硌得眼痛不得已的叫喊。一时间,全世界医学界克服弊端的新招迭出,有规定最低诊断时间不低于 15 分钟的,有要求声情并茂书写平行医案的,有严禁抗生素滥用和输液泛滥的……不能说这些措施不好,而是说这些原本是中医先生的平常要求,何以成了稀缺物质?非要大声疾呼,在西医领域大力推行?
现实生活中,文学与医学同为人学,两者的交集往往是文学从医学中获取素材和灵感, 少有文学在医学实践中运用。这一境况在二十年前有了改变,叙事医学兴起,作家和医生有了具备叙事能力的共同要求,受众虽有读者或病家之分,但达到情感共鸣的追求一样。注重病家的心理调节正是中医的优良传统,尤其是当下技术至上,重机器不重人文的风气中,医家和病家思想沟通越发重要,为了呈现和思考这样的生活景象,北京大学医学院做出惊人举措,邀请全国著名作家去给研究生讲怎样写小说,要求学生向作家学习,作家下笔心中有人物,医生下笔心中要有病人,同样需要共情共鸣。
现实社会中,世界上但凡实施社会医疗福利的国家,不分民族,不论社会发展水平,不分社会制度,国民与政府之间的医患矛盾日渐激化,甚至医疗福利越好的国家矛盾越突出。抛开政治原因不说,西医(现代医学)是实验医学的本质决定医患双方只能是对等而不可能做到平等。私人投资研究的成果,无论是新药还是新器械,私人要收回成本后盈利,甚至是暴利。与此相反,中医药无论是药材,药方,诊断手段,价格都亲民,避开了对等交易的要挟,会很大程度上缓解医患矛盾。
中华读书报:作为非医学专业作家,您如何确保小说中专业中医诊疗场景的准确性?
李明春:书写专业性强的中医药,本人时刻牢记文学的本分,谨守“真实”底线,书中所涉及人和事,要么来自生活原型,要么来自正规出版物,虽经裁剪,终是有根有据,既不敢天马行空。同时也不敢原样照搬,生怕误导读者,模仿出麻烦来。
中华读书报:在创作过程中,您在大量的中医文化研究和实地采访有什么印象深刻的经历或发现?
李明春:印象最深刻的是中医医生两极分化的境况。往往在同一栋楼坐诊,好的医生要预约,有提前几天、提前几周的。不出名的,一天看不了几位患者。由此产生恶性循环,找名医看病的病家越多,医生积累的经验越丰富,名气越大,找他看病的人越多。相反,名气越小,找他看病的人越少,积累经验的机会越少,医术提高越慢,找的人更少。这才是导致中医药整体水平下降,日渐衰败的致命原因。
中华读书报:主人公龚天缘有原形吗?您遍访中医,小说中提到的很多中医世家绝技,都是真实的吗?创作时如何平衡专业性与故事性?
李明春:有。全国最著名的当属上海中医名家何承志,有家谱可查,何家行医创立于公元1141年,至今延续已逾千年。作者老家古镇世代行医的不少,他们后代的不同变化为我提供了丰富的素材。书里提到的绝技,都是亲眼所见(包括阅读正规药书),亲耳所闻。如治骨折用热水止痛,是我当知青时,去县城看望受伤的生产队长时亲眼所见的事实。用手指甲伴烟吸治呃逆见《李可老中医急危重症疑难病经验专辑》(山西科学技术出版社2021年版)。
中华读书报:龚天缘游学的过程,是否在隐喻当代中医需要打破门户之见?这种"现代游学"模式对中医传承有何启示?
李明春:老家有个不成文的规矩,中医先生不教自己的孩子学医,必须拜别人为师,既有交流的考量,也有怕管教不严的担忧。出门游学,实际是出门拜师,避免医术“近亲繁殖”退化,也起到了打破门户之见的作用。
这种传承方式与学院培养相比,学生实践机会多,经验积累快,符合中医经验医学的传承特点。缺点是与西医跨界交流少,视野狭窄,更需要以游学的方式加以弥补。
中华读书报:如何处理中西医碰撞的敏感话题?小说中何姝与她的男友杨靖等西医角色的设置有何特殊考量?
李明春:中西医论辩百年未见分晓,我自然不敢妄加评说。现在取得共识的是要用现代科学解读中医药学原理。中医的确神奇。呈现神奇,我拒绝用梦幻,神授、秘籍去顶撞科学常识。立足中医药学的经验医学本质,用勤奋、积累、传承来铺垫人物成长之路。遇上科学常识一时无法解释的,我选用古人援物类比的方法,如以笛子演奏类比把脉,同样是管道,同样凭指头感受,笛子能获得丰富多彩的旋律,把脉也能感知复杂多变的病情。以此俗说之法化深奥为浅显,化抽象为形象,企望获得读者认可。
书中何姝、杨靖等西医医生的设置,是想从西医的视角来观察、审视中医,表达中西医一种相辅相成的辩证关系。
中华读书报:在《天下国医》中,您是否尝试了一些创新的写作手法或叙事结构?这些尝试对作品产生了哪些影响?
李明春:同我以前的小说不同,《天下国医》用人事、人情、人脉三条线索作为叙事结构。人事,包括天缘堂诊馆的创办、管理、发展和游学的因果由来、过往曲折、成败得失;人情,包括主人公与乔柳梦凄美的爱情,与何姝、白薇等人的友情; 人脉,包括龚、白、朱、吴、史五家世代情谊,以及广泛的社会关系。三条线索交替推动情节发展。叙事方式在描写概述对话的传统手法基础上,大胆夹杂大量的议论、解释。作为尝试,自己当初下笔忐忑不安。所幸反应还好,从市、省、中国作协分别组织的改稿会,研讨会上的发言,还是作品面世后普通读者的反应看,至今尚未有人诟病,得到社会认可,表示尝试成功。
中华读书报:乔柳梦的遗传病线索贯穿全书,这种"医不自医"的困境设计有何深意?
李明春:“医不自医”是句成语,指医生给自己或家人治病时,联想很多,顾忌很多,往往疗效不佳。作品关于柳梦患病和治病的人设和情节设计,基于对当下治病重机器轻人文的反思。柳梦的病是心病,机器难以诊治,为龚天缘用中医“病由心生”的医论指导诊断治疗打下伏笔。龚天缘在这里,他既是中医先生,也是中药引子。
中华读书报:在写作中,您觉得最难把握的是什么?如何把握"传奇性"与"科学性"的边界?通过写作,您对于医学本质有怎样的思考?
李明春:最难的是对中西医评判的分寸把握,既要中肯,又不能过分。写到中医神奇的地方,我一定要写它的局限性。如写了中医把喜脉的绝招后,借书中人物的口说,几十年练成的绝活,不如三元钱买的验孕棒。
困难之处在于中西医理论基础不同,不能用简单的对错来判断。西医基于科学,注重分析,认为真理存在最简单处,一切经过实验。代表性的观点是“精准治疗”,主张在基因的层面上,通过基因比较诊断疾病,用基因修复、编辑的方法来治疗疾病。中医从来讲究天人合一,基于思辨和经验,一切来自实践积累。西医的检测治疗手段日新月异,而中医几千年前的《黄帝内经》至今管用。从哲学的角度讲,没有绝对正确的西医,也没有绝对错误的中医,相辅相成才是正道。
中医的传奇来自科学尚有无法企及的地方,或无法破解的难题。医学不是神学,无论西医还是中医,讲的是治病救人,不是讲长生不老。中医常讲,治得了病,治不了命,命里注定有生必有死,这也是中医同神学的区别。中医有个可贵的地方,注重病人自愈的功能。世界对医学的作用有个共识,即:少数治愈,多数是帮助,总是在安慰。这与中医注重病人自愈是吻合的。
中华读书报:小说结局开放式处理,是否暗示中医传承仍需探索新路径?
李明春:有一种美学观点主张,文学作品是作者与读者共同完成的。小说开放式处理,就是给读者留下想象空间,想象越多,证明作品越有魅力。就作者本人来讲,让龚家三代老人为后人选择媳妇,状写争论而不下结论,留下空格给读者,作者的意图有迹可寻。选择白薇,无论婚姻观念还是中医理念,无疑是选择了传统,坚守将是方向。选择何姝,将是中西医联姻,中西融合形成一种新的医学。若是选择了乔柳梦,最有可能是叛逆,婚姻也好,事业也好充满变数。作为作者,最不愿看到的结果,是读者和自己想的完全一样。
中华读书报:小说中多次提到中医与现代医学的碰撞与融合,您如何看待这两种医学体系的关系?未来它们将如何共存发展?
李明春:这是一个严肃而棘手的话题,不是我这个写小说的人能回答。西医和中医的理论体系平行,很难找到交集点。但也不是一点不沾边,需要时间,等到科学新观念,新手段的出现。这不是空想,关于经络,关于气,已有新的科学假设试作解释,真到了一切真相大白那一天,一种新的医学将会诞生。
就现实来讲,有一种主张中西医结合,取长补短,各得其所。写作时我思考过,有自己的想法。算憧憬也好,算蠢想也罢,我对中医的“医者仁心”,“患者平等”的 主张情有独钟。这可能是平民草根的幻想,不切合市场经济,商品交换的实际,但符合平民百姓的需求,是天下草根的向往。中医药可以在平民医学这方面大有作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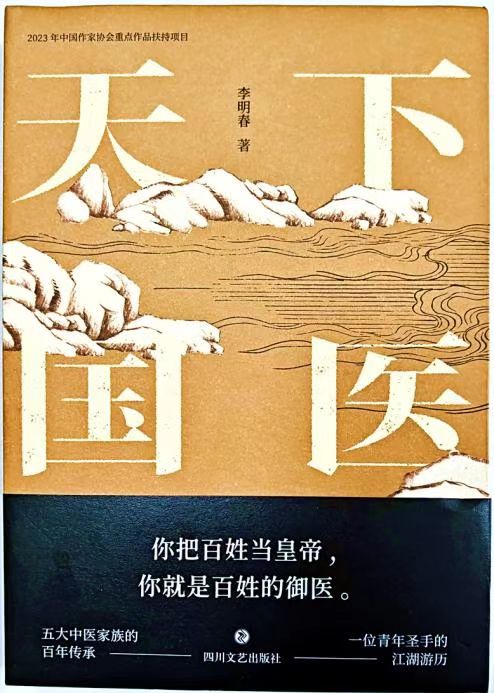
《天下国医》,李明春著,四川文艺出版社2024年10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