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一次研讨孙犁作品座谈会

1994年4月18日拍摄于天津学湖里孙犁先生寓所。前排从左至右为韩映山、孙犁、徐光耀,后排为本文作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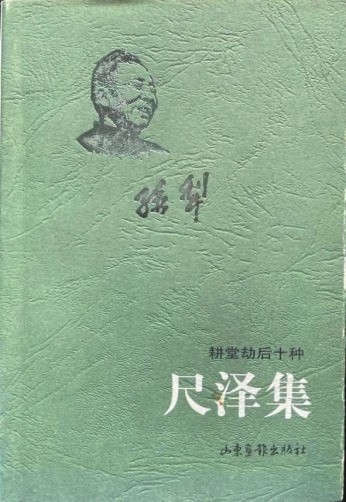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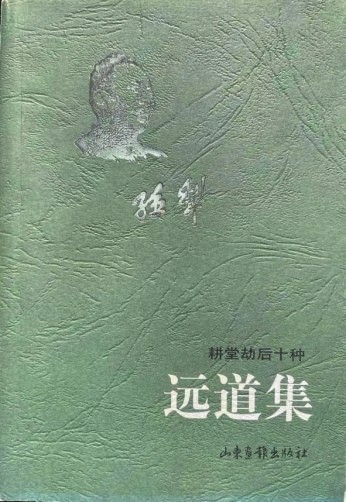
1998年4月到1999年9月,山东画报出版社先后出版孙犁的《书衣文录》《芸斋书简》和“耕堂劫后十种”。1999年11月13日,出版座谈会在北京的三联韬奋书店召开,主题为“回眸:孙犁二十年”。事前,已经给参会的作家、评论家每人送了一套“耕堂劫后十种”,所以,他们发言时都准备得充分,谈起来也有不少独到的见解。座谈会开得很有成效。
我当时把每个人的发言都录了音。会议结束后,请杨锋磊对录音进行整理。小杨很尽心,用了一个多星期才初步整理好录音。我把其中的一万来字寄给刘宗武,老刘修改后,又给我寄回来。我也在文稿上改动了一些整理时没写准确的字,就存放了起来。最近,在一捆资料中发现了这个26年前的整理稿。
我又读了一遍这整理稿,回忆起那时候的场景。现在,我把这个未全部整理出来的录音稿先拿出来发表(括号内文字都是我加的),余下的今后再整理出来。发表“回眸:孙犁二十年”部分录音稿,是对孙犁先生的纪念,也是为研究孙犁作品及其出版提供一点史料,特别是对那些发言的逝者,我觉得也是很好的纪念。
以下是“回眸:孙犁二十年”座谈会发言记录。
刘宗武(天津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时为孙犁研究会秘书长):
孙老这十本书,汪总(汪家明)是总策划、编辑人。孙犁以前的作品就不用说了,从1976年以后孙老又恢复了写作,最早写的是《远的怀念》,可能是1976年写的吧,一直到1995年4月写完了《理书四记》,《天津日报》发表的,除了1995年下半年以后还有点信外,文章是绝对没有了。这十本书可以说是从粉碎“四人帮”以后一直到1995年二十年之间孙老的全部心血,共一百二十几万字。这几本书出的最早的是《晚华集》,大概是1979、1980年前后出版的(《晚华集》,1979年8月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最后一本《曲终集》是1995年出的(《曲终集》,1995年11月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前后将近二十年。这十本书,印数最多有一万多册,最少是二千多册,出的参差不齐,而且很多书脱销了,很多读者都存不全,恐怕在座的能保证这十本书都有的也不是很多。山东画报出版社的汪总编和我出了孙老的《书衣文录》之后,觉得很有必要把这十本书都出一下。后来征得孙老家属的同意,我们就把书重新编了一下。今天我们就这十本书的出版和孙老粉碎“四人帮”以后写的这么多东西来座谈座谈。
下面请孙犁研究会的会长、《天津日报》的副总编滕云同志来主持这个会。
滕云(时为孙犁研究会会长):
今天我们聚在一起来讲讲我们对孙犁的感情,我觉得这是一个很难得的机会。孙犁同志近十三年(实际是十六年)出了十本书,大家都看了,原来陆续都出过,但是这次山东画报出版社投入很大的力量,出得很漂亮,我认为这是一个文化上的功业,是一件有功德的事情。
孙犁同志的《曲终集》出了以后,很多同志对他这个书名很有想法,我也跟孙犁同志说“你为什么取这么个名字呢”? 当时我也可以理解。现在重新看《曲终集》,特别是它的后记,实际上孙犁同志并不是没有考虑“曲未终,人还在”的情况,他的意思是说,假如不与老天爷说再见,还要继续写的,没有说是绝笔了。但是,1995年以后他确实是辍笔了。孙犁同志在文学上驰骋了一生。昨天晚上我还翻了翻这十本书的后记(除了有两本书没有写后记,其余的都有),我深深感到孙犁同志这十本书,他的后记,构成了他晚年或者说是这二十年探求生命的曲线。《晚华集》出来以后,我看是带着粉碎“四人帮”以后的欢悦,对自己文学生命复苏的期待和一连串的希望,后来的好几本都是这种心态。《老荒集》《远道集》以后逐渐地有抑有扬,自己的心态也抑抑扬扬,所以我说这十本书是孙犁同志晚年生命乐曲的一首旋律,高高扬扬,扬扬抑抑,抑抑扬扬,最后的《曲终集》也没有完全抑,还是有扬。
虽然孙犁同志在医院里听不到我们的声音,但是我们的心贴近孙犁,这个机会确实是不多了。实实在在地说,趁孙犁同志还健在的时刻,专门为孙犁同志召开的文学集会不是很多了,所以我希望大家畅所欲言。
从维熙(著名作家):
我在一篇文章中谈到,就一个概念、一个涵义上来说,孙犁同志是独一无二的。这并不是说他在文学造诣上在中国的大师级文学作家中没有第二人,而是说他的人文行为、人文标准、人文气质,他从解放区来而又给我们留下的不同于其他从解放区来的一大批作家的文字,所以我觉得孙犁是一个很特殊的作家。
从我们这一代人来讲,受影响的主要有两个方面。一个是类似自己的童年生活,这是在梦魂牵绕,不可割断的;第二个就是当初用文学产生巨大的心灵震颤的人。我觉得就我们这一代人来说,上世纪50年代初期,受影响最大的像房树民,像故去的刘绍棠、韩映山等等,还有天津的阿凤,还有几个工人作家等等,那影响力之大,既是春雨润无声,又是雷霆万钧。所以说我们在年轻的时候就把孙犁视为心里的一颗明星,那时我们年龄在十八九岁,当然我们现在不同了,就是说我们自己也有不少作品了,我写的作品累积起来恐怕比孙犁的还要多,但是跟孙犁同志是没办法来比的。他的文字很沉淀而又不失于飘逸,他的整个人文行为我觉得在今天来回眸有很特殊的意义。现在某些文学趣味、文学意象与孙犁那一代人,包括我们这一代人,包括以严肃文学为己任的这一代人好像都游离得很远,当然他们都有他们不可取代的时代背景。我说孙犁只有一个的意思,就是说他可能是中国历史上一个文学时代的终结,我自己是这么想的。
这套书看了以后,我比较喜欢它很适合于像孙犁这样的人的性格,我觉得孙犁同志如果能看看这书的话,他心里一定高兴。他不希望搞什么精装啊,追求什么辉煌,他是淡泊名利的。我觉得他看了这样一套书,会心里满意的。
曾镇南(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
这套书具有一种朴素的风格,我觉得像孙犁那一代人比较信奉的“朴素是最高的美”。这套书整个的装帧设计都是朴素的,但是比起原版来说它又增加了一些手迹、图片等等,封面也有孙犁的头像,我非常满意。一个是非常尊重孙老原来自己编订的顺序,我就怕出版社随便把每一本书的篇目进行修改、变动。这套书完全是按孙老原来编订的原貌出版的,这对研究者来说提供了不少方便,因为孙犁这套书的每一本都是可以集中进行研究的。我比较集中地认真研究过其中的两本,就是最早的两本——《晚华集》和《秀露集》,写了一批文章。当时想一本一本地接着进行研究,接着写下去,后来由于生活和写作遇到了一些曲折,没有能够做。最近我想重新做这件事,就觉得这套书为我研究提供了很大的方便。
另外,我想谈谈对孙犁的认识。我觉得孙犁是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上一个优秀的、风格独特的小说家,如果从当代文学这个历史范畴里来看,有了“劫后”的这十本书,我觉得孙犁可以称为当代文学史上杰出的思想家、革命家、文学家,我觉得可以用毛泽东评价鲁迅的这“三个家”来评价孙犁。
为什么说他是思想家呢? 这十本书有一个共同的主题,就是对中国社会的解剖,对中国知识分子、中国文化现象的解剖,通过对文化现象的解剖来解剖我们这个民族的灵魂。从这套书的一个总的主题可以看出一个非常博大的、非常精微的思想家的风貌。这个思想家不见得有非常严密的思想体系,他的思想跟鲁迅的一样是具体的思想,是针对具体的社会现象、文学现象、作家作品的具体的思想,这种思想对于我们来说是非常可贵的,所以我感到他是一个思想家,一个很杰出的思想家。尽管他1995年已经封笔了,但这些集子里的每一篇文章拿出来,我认为在今天都有现实意义,都能给我们的思想以启示,给我们一种思想的丰富和单纯的感觉。
从这十本书里,我觉得孙犁可以称之为革命家。由于时代和环境的变化,这个革命家跟鲁迅当年的那个革命家在社会上的反响是不一样的。当年鲁迅是一呼百应,是文化革命的主将,是呼啸着前进的猛士,后面跟着的是大群的战士。孙犁现在是在一种新时期的文化环境里,他的革命精神,我认为是锋芒内敛的。但是,作为一个思想战线上的战士,孙犁战斗得那么辉煌,他的笔锋触及那些丑恶的、违背艺术规律的、违背人性的现象的时候,对方是完全抵挡不住的。像他这样的人真不多。我觉得对孙犁在新时期经历的一些思想的论争,将来历史、后人会作出公正的评价。对孙犁革命家的这一面可能有不同的看法,但我认为,针对中国的旧文化和各种各样的带着洋奴气息的假洋鬼子文化,我们仍需要这样的革命家来观照和解剖。
为什么说孙犁是杰出的文学家呢? 我觉得,他以他风格独特的创作,使各种不同思想倾向的作家和但凡懂得点文学的人都不能不敬服。他的《铁木前传》和《阿Q正传》一样是我国现代文学史上的双璧。哪个倾向的作家看了以后都不能不表示佩服,哪个研究中国文学的人写到中国当代中短篇小说史的时候,都绕不过《铁木前传》。
孙犁在创作上的贡献是很显著的,但我认为,作为一个称职的文学家,他的贡献更重要的是在文学理论方面。我是一个文学理论批评工作者,我认为,孙犁不但是一般意义上的前辈和老师,而且是我从事文艺批评的一个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思想源、思想库。他在文艺理论上的贡献,我认为在当代文学史上是没有任何一个文学家和批评家能够超越的,他提供了非常丰富的关于文学艺术的大量的、独到的、精辟的、永不磨灭的见解。如果能把孙犁对文学艺术的很多看法在大学课堂上广为传播,让我们年轻一代的文学批评工作者、理论工作者、博士生、硕士生们能够从心里带着感情地去掌握它,那么我们的文学批评的面貌将是如何地不同啊!
舒乙(中国现代文学馆):
我拿着这十本小书以后,感到非常惊讶。我觉得它出得特别好。比如说这个封面设计,有孙犁的头像,有他自己的签名,里面的用纸也是非常考究的,它用的是一种黄颜色的纸,跟整个书的风格近似,表示有一点岁月的沧桑感在里面。另外,它的开本非常小,拿起来很方便。它有非常多的插图,这些插图不是放在前面,而是插在里面,甚至于不是单独的一页,而是半页或者四分之一页,这样一来印刷是很麻烦的,但绝对是为读者提供方便的。
再说说孙犁本人。在这一百年里我们诞生了很多杰出的作家,我觉得孙犁应该是这批杰出作家当中的大作家,应该这样给他定位。我国在20世纪里称得上是职业作家和非职业作家的、有作家资格的、冠以作家头衔的有三万多人,但这三万多人能真正在历史上留下来的不太多,也就是说其作品能经得起时间考验的,应该说是不多的。留在历史上可以传下去,连后代都要去念的,我说一句非常苛刻的话,大概也就是百人左右,这是一般的规律。可惜的是当代的读者对孙犁注意得太少,这有自身的原因,是由他的文品和人品决定的。大家看这两句话,头一句是“大道低迴”,是他的人品,第二句“大味必淡”,是他的文品,恰好这两句话人品、文品都能概括。由于他自身是这样的,现代的读者注意他比较少,相对来看,孙犁是比较寂寞的。但是作为他的读者、欣赏者、崇拜者、研究者、出版者,我们应该大声为他叫好。
中国这百年的辉煌大体上是两个高潮。一个高潮是由1919前后开始,一直到1949年,诞生了很多伟大的作家和作品;从1949年到今天又是一个高潮,这个高潮的高峰是在近二十年。但是孙犁跨越这两个阶段,而且在这两个阶段他都有高峰,这样的作家是很幸福的。孙犁,他恰好是这两个高潮的一个载体的具体体现,是百年辉煌的代表者的最后几个之一。他们代表着整个百年的辉煌,代表着整个中国文学的一个时期,对巴金先生、孙犁先生我们都应该这么看。我觉得能称得上大作家的,其标准就在这个地方,就是说他的作品会延续很长的时间,会跨越很多地域。比如说他写的是河北北方的一个县,但是它会跨越到山西去,会跨越到湖南去,会跨越到广东去,还会跨越国界,到日本、美国、欧洲去,让世界的人都知道中国有这么一个作家,这就是大作家。他思想的犀利,文笔的特别,给人一种震撼的感觉。我们应该把这些感受传递给广大读者,让他们更加注意有这么一个人。他是中国现代文学的代表者之一。
我很欣赏孙犁的一个地方就是他那个“淡”。文章要做到“淡”,这是“五四”的光荣传统,往后的散文就完全偏离了这个传统,所以“五四”散文的传统有一个时期是没有被继承下来的。这个“淡”有点像清酒,醇味很浓,但喝下去不像二锅头那么辣嗓子,有点像香片茶,有点像太极拳,不像咖啡,也不像拳击,这是我们中国的一些特点,孙犁先生非常好地继承了这个传统。我们应该把孙犁推崇为中国20世纪文学的大散文家。散文绝不能作成文字的堆砌,绝不能作成词藻的集合。要恢复像孙犁他们的这种作风,即有事讲事,非常简短,非常淡雅,这是中国散文的优秀传统,也是现当代文学的优秀传统。孙犁是这种传统的非常棒的一个坚持者。
另外我想到,从他这里边我们可以学到很多思想,我很同意刚才曾镇南先生说的,孙犁有很多了不起的思想,而这些思想好像是不太经意地甩出来的,但你看起来就非常感动,觉得这几句话正是你想要说而说不出来的,他说出来了,也就是说他这里面有很多思想的闪光点。
我想到几件事,比如说他坐在家里大量地读书(他晚年有好几本都是题、跋),他家里藏了很多书,他把这些书拿出来念,然后在这些书上写很多题跋。在书上写很多题跋的人是很少的,就是《书衣文录》,这种东西是很可贵的。孙犁绝对是个学者,大量地念书,从前人那里汲取营养,然后写出来介绍给读者,他这些东西都发表了,这是我们看到的一个认真做学问的、以尊重知识为己任的典型。他往往也并不是完全表扬他读的那些书,很多是持批判的态度,比如说他在《新文学史料》发现里面有一篇刘半农研究,刘半农晚些时候曾采访过赛珍珠,好像当时有那种录音的设备,去了好几次,录下了赛珍珠的那些话,想出一本《赛珍珠传》或者是口述史啊这样的东西,他没做完,后来就让他的很有名的一个学生做了。这篇刘半农研究的文章里披露了这些事情,孙犁就对这件事情发表了很多评论,说刘半农先生那么大一个作家,居然天真地去做这种事,他觉得不太好,当然像胡适先生等人认为还是比较好(舒乙先生此处所谈文章为孙犁《曲终集》中的《读〈刘半农研究〉》)。
孙犁最后总要来几句总结性的东西,那几句总结性的东西非常了不起,那是一种人生经历的提炼,我就觉得特别好。比如说他读几个人回忆鲁迅的文章(舒乙先生此处所谈文章为孙犁先生《曲终集》中的《读〈文人笔下的文人〉》),这几个人都是大人物,里面有夏丏尊、林语堂,好像还有郁达夫等,他就说这几个人怎么来写鲁迅。最后的结论是,这几个人当中文章写得最漂亮的、他最喜欢的是夏丏尊。夏丏尊既是教育家,又是作家,他写的文章既有知识,又有人物,这才是文人学习的楷模。这种点睛的东西是非常珍贵的,他能够通过自己的提炼,把他阅读的感受总结出来一点东西,然后告诉你。虽然只是几句很短的话,但是像这种文章,我认为价值无穷。
郭志刚(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
我一直在学校里教书,本来我也没有多少机会去出席什么会议,去认识很多的朋友,通过研究孙犁倒是自然而然地、有意无意地结交了不少新朋友,而且这些朋友说出话来,我感到那就是朋友对朋友的话,就好像和知己之间说出来的话是一样的。我自己心里想的,也许我说不出来,但是他们说出来的好像就是我心里想的。对于孙犁,刚才曾镇南同志提到了“三个家”这种高度,我虽没这么说过,但是我觉得他说得非常有道理。
孙犁的作品从世界范围来说,他的读者应当说是不少,但是还不能够说是跟他的作品的成就已经很相称了。我好多年以前写过一篇文章,就是关于走向世界,我在那篇文章里说了有关这方面的一些问题。一个民族的好东西,当然是走向世界的条件,但是好不一定就能走向世界。我觉得孙犁就是个例子,我作为一个中国人,特别是作为一个河北人,跟他有同乡之谊,我接触孙犁的东西比较晚,比较系统地接受是上世纪70年代末了,我知道他好,但是我也知道他目前大概很难像别的作家那样走向世界。主要是个文化问题,中国的文化确实是非常独特的,要让世界充分地了解不容易。一个原因是过去的历史造成的,因为过去我们不强大,我们经济上很落后,在世界上的地位不高,因此我们虽然有一大批优秀的作家,也不容易被介绍到世界上去,包括鲁迅在内,他的地位和他实际的成就是不相称的。比如说,中国的古典诗词好不好? 好,这在世界上也是独一无二的,但是目前还不容易向世界推广,因为它在语言上、艺术上、技术上还存在很多障碍,你要让外国人真正进入中国古典诗词的境界,那确实是太难了,不知道需要做多少外围性的工作。
孙犁在某种意义上也可以说是这样的,因为他写的基本上就是河北、山西这些华北地区的事情,而且他很注意风俗人情的描写,像这种描写离开河北,比如说到了广东,就不见得对孙犁的理解像我们这么贴近了,更何况向外国介绍,让外国读者了解呢? 不容易,主要就是存在这么一个文化上的障碍。
有一次给学生讲的时候我举了钱钟书说的一些话。钱钟书说我们现在都搞比较文学,实际上你作为一个中国人,了解外国文学是非常难的,有些地方你觉得自己懂了,但实际上并没有懂。他举了这么一个例子,说一家人围在一起谈话,谈的话题一家人很容易就沟通了,有时侯说一个词,一个眼神,一个手势,不用把话说下去大家就懂了,但是如果这时有个外客坐在旁边,他就不见得懂。这跟我们的作家走向世界或者是研究比较文学的状态也有点相似,就是说不熟悉一个地区的风俗、文化、人情、历史等等,想了解一个作家很难。孙犁就有一些障碍,因为他有一些反映文化上的特殊的、深层次的东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