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人刘天昭:文学是一个深刻的奇迹
凭借诗集《变得厉害》,诗人、作家刘天昭被评为2024年度刀锋图书奖“年度诗人”。
刘天昭35岁时才开始写诗。
在那之前,她在清华大学学习建筑,在《南方都市报》写社论,出版过散文、自传体小说,还写了很多年博客。直到人生走到一个阶段——“不知道为什么心里有一口气在起伏”,写作中也自然带了跳跃和节奏,就分了行。
诗从刘天昭的指尖漏出,被写在手机里,发在朋友圈、微博上,它们不追求章法形式,都是真情实感,“诗都是自然发生的,我只能等待,甚至无法等待,只能该干吗干吗”。
生活成了一张被不断揉皱又展平的纸张,又像阳光穿过树叶缝隙投射在地面上的斑驳光影,刘天昭的诗歌便藏在那些褶皱与光影里。
2021年,刘天昭的第一本诗集《竟然是真的》出版,其中收录了她2014—2021年创作的91首诗。三年后,第二本诗集《变得厉害》面世,收录了她2021—2024年创作的106首诗。
两本诗集共同构筑起两扇相对的窗,一扇指向世界的辽阔,一扇镌刻私人的生活印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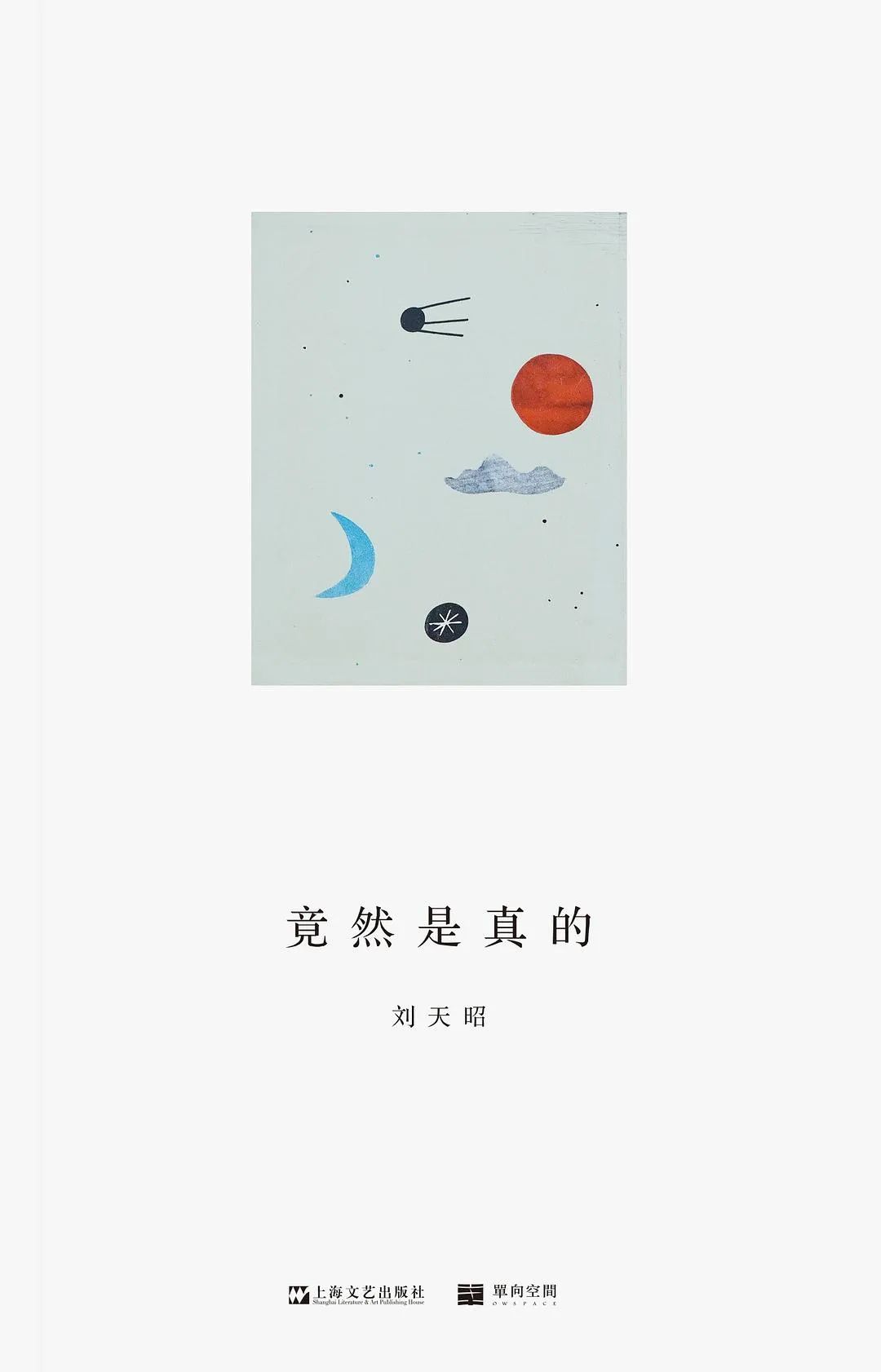
《竟然是真的》
刘天昭 著
上海文艺出版社,2021-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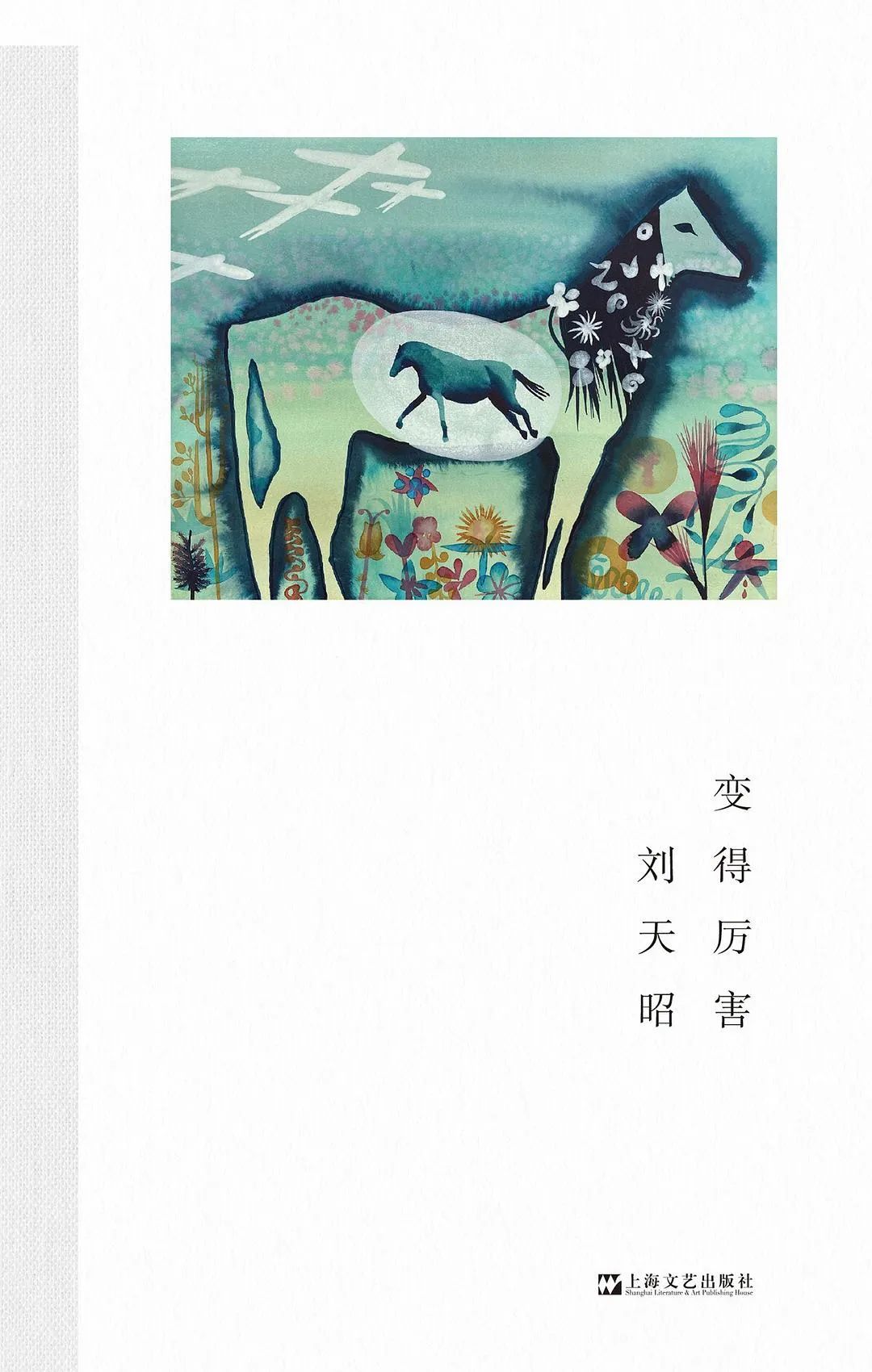
《变得厉害》
刘天昭 著
上海文艺出版社·艺文志eons,2024-8
生活与诗歌
刘天昭对自然、季节和气候变化有着近乎本能的敏感。
在《这不是比喻》中,她写道,“一到春天我就困倦/醒也醒不过来/醒来也不想动……春风一吹我就生病/骨也硬,肉也肿/又麻又疼,又烫又冷”。与春天相比,她似乎更喜欢秋季,在《不可能厌倦秋风》中,她说,“在语言的诡计中/我以为我已经关闭了四季/我以为我厌倦而轻松/但是就迎来了秋风/来自树木和天空/月亮和海洋/时间和宇宙”。她将地球称为“偶然的星球”,而“独特的四季”则是其中的神域。
季节和天气在诗歌中如基调般的存在,这并不是刻意为之,而是生活在诗歌中的显影,刘天昭本人也并没有意识到这一点:“如果是这样,那可能就是因为它们在生活中也是如此。我也说不清为什么,年轻时候完全不在意的,后来渐渐就变成了这样一个人,春风秋雨来到生命深处,像失忆的人偶尔仿佛想起了什么似的。”
春风秋风之间,刘天昭的诗安静而蓬勃地生长着,这一创作轨迹与法国新浪潮导演埃里克·侯麦的电影风格有着某种程度的联系。

侯麦作品《秋天的故事》聚焦中年人的情感故事。(图/《秋天的故事》)
“我很喜欢侯麦,看过他的五部电影,虽然那是很久以前的事了。我一直想要重新看却一直没能够,但他带给我的印象依然是强烈、明晰的。自己想象中应该那样拍或者那样写的东西,原来早就存在了,就是那种感觉。”在生活的许多缝隙、散漫又啰唆的话题中,刘天昭都能联想到侯麦的电影。
在刘天昭的两本诗集中,都各有一首关于侯麦的诗。在整理出版的时候,她一度有点担心自己对侯麦的理解不同于文化共识——她觉得自己不懂电影也不了解那些共识——但她仍然觉得自己的诗基于某种诚实,于是就把那些诗放在那里了。
刘天昭的诗歌无远弗届。在诗集《竟然是真的》里,她会描写自己在天猫超市购买叙利亚香皂的经历(《叙利亚香皂》);在公园散步时,她会“想象自己去伦敦/走在卡姆登街上”(《又热又霾的礼拜天下午》);也会在汽车路过公园时,“看见初夏树林中的野草地/飘飘地想到俄国风景画”(《拒绝成形的日子》)。
生育让刘天昭的生活处境天翻地覆,整个人也发生很大变化。诗集《变得厉害》中,镜头常常扫过厨房的灶火和育儿的琐碎细节。“这种变化不仅说不清楚,我对它的体会也都是片面、模糊的。不过(生活)肯定不只是收缩,它也打开了另外一个很大的空间。”刘天昭还在慢慢体会这种变化。
在稠密中年,与AI对峙
在《变得厉害》中,刘天昭更多地描写了关于衰老的感受,“竟然是磅礴的”“转眼便是不用质疑不可回避的衰老,没有界限……心灵不知何时割断了绳索,也许是获得了解放——不怎么记得过去的自己了”。
她形容中年女人的时间,“就像一碟儿酱,谁都来蘸一下子”(《酱》);也偶尔用年轻的目光回看自己,“享受那惊奇/而并不真的回忆”(《不年轻的女人》)。更多的时候,她“将此刻作为稠密中年的缩影储存起来”(《天气》)。
“作为中年人,我最深的变化可能在于,真的相信了人生有限。就(会)很珍惜,有时候难免着急,怕来不及。随着自己越变越小,世界也越变越大、越深,变得更有真实感也更神秘了。”刘天昭这样形容“稠密中年”给自己带来的变化。
然而,AI“忽然巨人般踏入现实”,攻城略地,击穿私人生活。在刘天昭的诗中,也有不少对于大数据、算法、AI攻克人类意识的担忧。
她敏感地意识到当下的某种新常态,“意识/可能是人给自己训练的AI”(《涌现》),“更多的人正在/变成AI,AI已经不必变成真正的人”(《太快了》),而在这个技术狂欢的时代,她用诗歌与自我意识固执地维持着一片自留地。
“我一直对‘意识’感兴趣。我自己意识过剩,意识活动和对意识活动的意识都比较放纵。有种说法是,意识是物理主义要攻克的最后的堡垒。我当然希望攻不下来,但是很不放心。在ChatGPT出现之前,我已经带着强烈的热情和愚笨的头脑读了一些这方面的书,本来觉得也许还可以在这个堡垒中再喘息一段时间,但是忽然听说算法可能即将呈现出意识,如果真的是这样,那么意识显然在原则上是可还原的——这个事情对我来说太重大、太本质了。”
“原来生活来自文学。或者说文学/基底于生活如同数学基底于物理世界/原因不明,并且包含奇异的跳跃”——在《出租车带我经过我从未去过的街区》这首诗中,刘天昭道破生活与文学的玄机。

上海街头的出租车。正如刘天昭的诗所写,“出租车带我经过我从未去过的街区”。(图/Unsplash)
在刘天昭看来,一直以来,她的写作都是因为在生活中感受到了某种必要性:“是首先看见了有一团可以写,甚至是必须写的东西在那儿了,然后才写。我现在相信自己是一个作家,但是并不能为了写作而写作,也不能为了写作而生活。写作是很幸福的,盼望还是盼望的,但是差不多也只能依靠命运的馈赠。”
“另一方面,在一个更抽象的意义上谈论文学,我觉得它是一个深刻的奇迹。文学,或者说叙事,它是对不可读取之物的读取,是把存在变成‘存在的镜像’的魔法,然后让这一切都变得可以使用,并且变化、繁衍。在那首诗(《出租车带我经过我从未去过的街区》)里,文学的意思可能接近于对人生的自觉,那种意识塑造了生活。‘人生’这个概念,就是文学的创造物。”刘天昭说。
“我接受了命运”
《新周刊》:你为什么会在35岁开始写诗?诗歌带给你最大的意义和快乐是什么?
刘天昭:我在写诗之前写了很多年博客,后来在写作中自然带了跳跃和节奏,就分了行。至于为什么写博客,虽然写得不好,但是还是可以说,那原因可能跟“为什么世界上会有文学”一样。
后来有一次,我感觉到心里有点什么可以写,但是好像不写也没关系。有一个自由意志的缝隙。现在说起来,我想是因为我接受了命运,或者说找到了命运,因此自由了。这说起来太复杂了,可能跟看见季节什么的都是一回事儿。
《新周刊》:在《我奶奶》这首诗中,你提到自己的奶奶,“一个不识字的知识分子/一个命运教出来的自由主义者’,你说“她不写作/她不需要写作”。你觉得什么样的人需要写作和诗歌?
刘天昭:我想象我奶奶晚年是与命运合体的人,充盈混沌,无所外求。我想写,主要是因为写作的体验本身特别高能、特别快乐。另外,它也有点像生活的果实,对流逝的回馈,有一年年终的时候我从头看了一遍这一年的诗,像一种盘点,也很高兴。

4月18日,在2024年度刀锋图书奖荣誉典礼现场,刘天昭发表感言。(图/新周刊)
《新周刊》:你在《不妨化个大浓妆》中说:“作女人是件滑稽的事/作男人也是”。身为女人的方方面面(作为家庭主妇、作为母亲、作为刘天昭),你所感受到的禁锢和负面因素多一些,还是乐趣和自由多一些?
刘天昭:女人是和男人相对的词,我只有在面对一个想要与之建立男女关系的男人的时候,才有强烈的自己是女人的意识,但是那是很多年前的事了。绝大多数时候,我不怎么想得起自己是个女的,也不怎么从性别的角度思考自己的生活。那首诗也不是在讲性别,而是在讲角色,角色与生命的关系。
《新周刊》:在《变得厉害》中,你多次提到年龄与衰老,但几乎从没谈论过死亡。在你这个人生阶段,死亡应该已经成为无法回避的话题,为什么死亡没有进入你的诗歌之中?
刘天昭:我不知道为什么我没写过死亡,我经常觉得那些诗并不是我写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