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摸索现代汉语诗歌的可能性

西川,1963年生,诗人、散文和随笔作家、翻译家,北京师范大学特聘教授。出版有诗集、随笔集、论著、诗剧等多部作品及多种诗歌诗论译作。曾获鲁迅文学奖(2001)、中国书业年度评选·年度作者奖(2018)、闻一多诗歌奖(2024)、德国魏玛全球论文竞赛十佳(1999)、瑞典马丁松玄蝉诗歌奖(2018)等。作品入选多种选本并被广泛译介于三十多个国家和地区。其英译作品《蚊子志:西川诗选》(译者Lucas Klein)入围2013年度美国最佳翻译图书奖,并获美国文学翻译家协会2013年度卢西恩·斯泰克亚洲翻译奖。
一、
每个人多多少少都是由时代造就的
施展:在最近由广西师大出版社·纯粹Pura出版的您的长诗集《巨兽》中,我发现“巨兽”同名于您1992年创作的长诗《致敬》第四部分。如今三十多年过去,您为何依然选择“巨兽”作为书名?时至今日,它有什么特殊意义?
西川:《巨兽》这本书出版以后,有朋友以为我是以“巨兽”自比,这其实是一个误会。我还没这么“自牛”。这个误会可能来自斯洛文尼亚诗人托马什·萨拉蒙的一句诗:“每个诗人都是一头巨兽”,但我的“巨兽”本是我1992年长诗《致敬》第四节的题目,我拿它做了这本长诗集的书名。我曾在《诗歌和诗人的“沸点”》(2010)这篇访谈中说过:“《致敬》里我最满意的一篇是《巨兽》。我现在依然觉得它对我来说是一首比较重要的诗,它是对于那种无名状态的、那种黑暗的、你没法命名的、压迫过来的东西进行的一种书写。”所以我的“巨兽”不是用以自况的。我为《巨兽》这首诗发明了一种写作形式:说话——被打断——说话——被打断,我觉得我们的生活就是这样:往前走——被打断——继续往前——再被打断。《致敬》之后,我经常从生活本身获得语言方式和文学形式,而我此前的语言方式和文学形式大都是从别人那里学来的。《致敬》是我写作的转折点。
记得2009年秋天,我曾在加拿大某地朗读过《巨兽》的英译文。朗诵会后一位听众跟我聊天,他认为我描述的是一种后现代状况——他这么理解也可以,对这首诗可作多种解读。1997年我在荷兰参加鹿特丹国际诗歌节时,曾在一个儿童专场上朗读过《巨兽》,孩子们居然听得咯咯笑。我敢肯定,在国内不会有任何人愿意请我去为孩子们朗读《巨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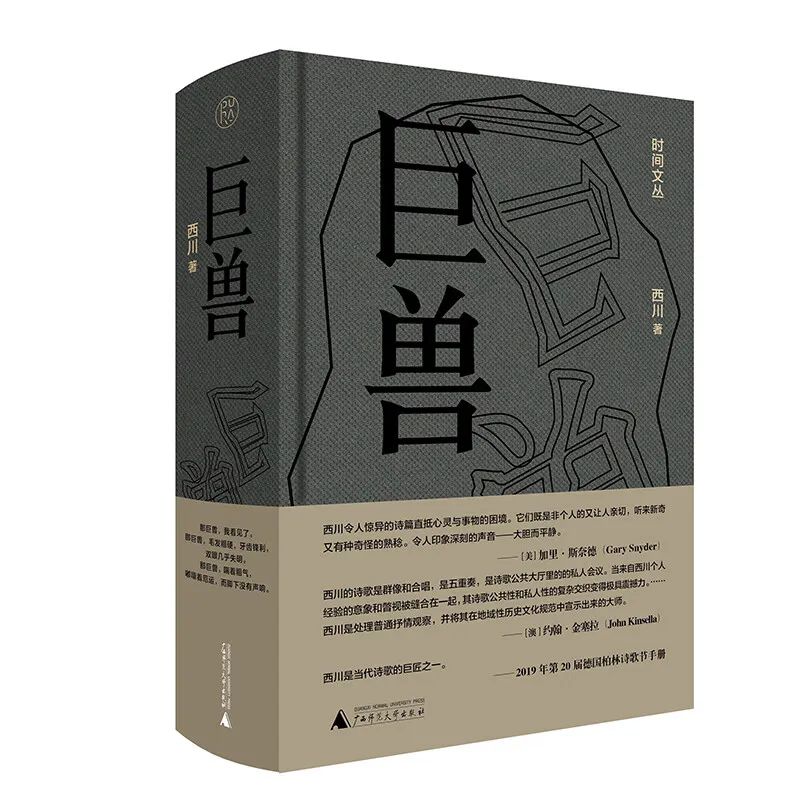
《巨兽》
作者:西川
出版社: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纯粹Pura
出版时间:2023-12
施展:您说过,短诗写作只占用您五分之一的精力,其余时间都一直在从事翻译、批评、长诗与随笔写作等工作,包括对中国古代诗歌和绘画的研究,以及许多跨界艺术工作。同时您还提到,在知识分子、诗人、译者、艺术家这四个身份中,您最喜欢的身份是艺术家。我很好奇,这些诗歌之外的活动,是否影响了您的写作?徘徊于译者、研究者、创作者等多重身份之间,您最大的感想是什么?
西川:从来没有人问过达·芬奇他做科学笔记是否影响了他的绘画创作,也没有人问过米开朗琪罗他的诗歌创作是否影响到他的雕塑工作,仿佛他们天然就该在不同的领域工作。我提到这两个人不是在托大,而是因为他们的例子广为人知。唯一的问题是:咱自己为什么不能这么干?网上有我一个演讲视频叫《有多少才华才可以横溢?》。这个演讲主要是说给美术圈的人听的,但文学圈、诗歌圈的人听听也无妨。
对,我干很多事,经常换频道工作,主动地和被动地。必须说明的一点是,换频道的前提是拥有换频道的可能性。我想我的诸多“可能性”是我多年在不同领域学习、思考、尝试养成的。诗歌圈的人大多只看到了我在诗歌领域的翻滚,不了解我在其他领域的游走。我懒得跟一些人废话,也没有强烈的愿望要别人看到一个全面的我。近五六年大家通过网络获得了一些我在诗歌领域以外的信息,其实我一直不完全属于所谓的诗歌界。我曾长期执教于一所美术院校,所以我对视觉文化方面的事当然有所了解,我对这个领域存在的问题也多少知道些。因此,我才会写《北宋:山水画乌托邦》这本书。
我已经写作多年,有时会对自己感到厌倦,所以换换领域换换频道透透气,有助于我不时调整自己。
施展:假设在诗集《巨兽》和访谈演讲集《我的身体就像一座旅馆》中分别选择一首诗或一篇文章,来表现您目前对诗歌艺术的看法,您会选择哪个作品?为什么?
西川:在诗歌方面,我的《开花》具有更大的社会知名度,但我个人更偏爱《鹰的话语》。《鹰的话语》在1998年写完后,有半年时间我跟任何人都不曾提到我已写出这么一篇作品,仿佛那是我的秘密,不想与人分享。那是一种非常特殊的体验。文章我也写了很多。我刚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再版的《唐诗的读法》(原由北京出版社出版)其实本是照着一篇长文写的。——如果这篇太长,那短篇文章,我选《汉语作为有邻语言》吧。这里面包含了很多我对现代汉语的思考。我讨厌那种创作谈式的东西(尽管我经常被要求提供这样的稿件),要谈就谈点硬东西,谈点客观的东西。主观的东西往往是经验之谈,虽然有些主观的表达也值得一读,但它们缺少用以衡量的标准。
施展:我关注到《巨兽》附录了《西川创作活动年表》。您提到从1976年起学习国画和写作古体诗,1981年入学北大之后才将兴趣从中国古典文学转向西方文学。后来,1985年您发表成名作《在哈尔盖仰望星空》,1992年出版代表长诗《致敬》。回顾您从13岁到30岁的成长经历和学习情况,您在青年时代的成长路径好像每隔五年左右都发生了很大变化。这些改变基于怎样的契机展开?您又如何看待自身经验的独特性?
西川:我曾不止一次地告诉身边的年轻人,我之所以成为现在的我,不完全是出于我个人的选择。每个人多多少少都是由时代造就的。在你问我这个问题时,你可以同时回顾一下近几十年中国的变化。我写作上的变化与社会生活环境的变化多有纠缠。我一直让自己向社会生活、历史生活敞开,我从生活中获取材料、观念、语言、文学形式和精神能量。我有幸成长于1980年代,我在那十年间实现了自我现代化。今天的年轻人没能赶上八十年代,但这也没什么可遗憾的,他们只须记住他们有自己的新世纪。他们如果浪费了新世纪,那只能怪他们自己。这21世纪的生活,我也要。
现在回想起来,如果我入读的不是1980年代初的北大英文系,我可能后来就变成了一个穿长袍马褂的人。如果我没赶上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的政治、经济大转型,没有经历朋友们的离去,我也许不会那么认真地逼视自己和生存环境、思考历史环境的转变逻辑。如果我没有发展出一套既与当代世界文学沟通又与别人不完全相同的文学观念,我就不会一次次获得机会受到邀请游走世界各地。如果我没有世界文学、文化视野,我也不会觉得我有必要重新讨论中国古典文学和艺术。
到今天,即使我的写作想变得暮气沉沉,时代生活也不允许。我始终在做各种尝试和实验,以衔接时代能量。当然,这么做的代价也是有的,那就是别人的不理解,尤其是与我年龄相仿的人的不理解甚至敌意。无所谓啦!
施展:除此之外,您在《西川创作活动年表》中特意注明了很多人生中具有特殊意义的时刻,比如“1970年4月24日晚在徐州街头望见中国第一颗人造卫星穿过星空”。我相信,这些记录对您有非凡意义,也体现出一种个人和历史进行迂回对话的意味。您有兴趣的话,我想听听您整理年表的想法。
西川:我自己做创作年表首先是为了让自己记住一些事。进入九十年代以后我就不再写日记了。1997年我出版诗集《大意如此》时曾应编辑要求在书后附录了一个创作年表,后来我就在此基础上继续记录自己的主要文学活动,一些事情的时间点我必须记下来备查。另外,在《巨兽》后面附上自己的创作年表,也是为了呈现一个客观的自己,堵一些人的嘴。网上总有酷评家和出于各自的原因敌视我的写作的好人和高人们,对我做过的和没做过的事胡猜乱想、说三道四。我没有精力,也不知道通过什么途径一一回复他们,就在自己的书后面附了个创作年表。
你注意到我创作年表中提到“第一颗人造卫星穿过星空”,那是我童年的记忆。我之所以提到它,是由于它是历史的一部分,它出现在星空的意义远大于我成长史的意义。我有一组诗叫《九次写到童年》,未能收入《巨兽》,但网络上有其中的部分章节。我不只是在写我的童年,我没有那么自恋,我写的是我童年的那个时代。在今天,我觉得非常有必要回溯那个时代,我写童年不仅是因为我老了。
年表,某种意义上,是提纲挈领的自传,但其中每一个时间点、每一个小事件都可以放大。我的生命与世界、与时代、与他人、与我说不清道不明的许多东西,明亮的、幽暗的、灰色的,交织在一起。
…………
(本文为节选,更多内容请见《钟山》2025年第2期 )
(施展,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博士研究生,北京文艺评论家协会会员。有文艺评论发表于《光明日报》《文艺报》《中国艺术报》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