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技术时代思考诞生的意义 ——《犹如流光:诞生,死亡》述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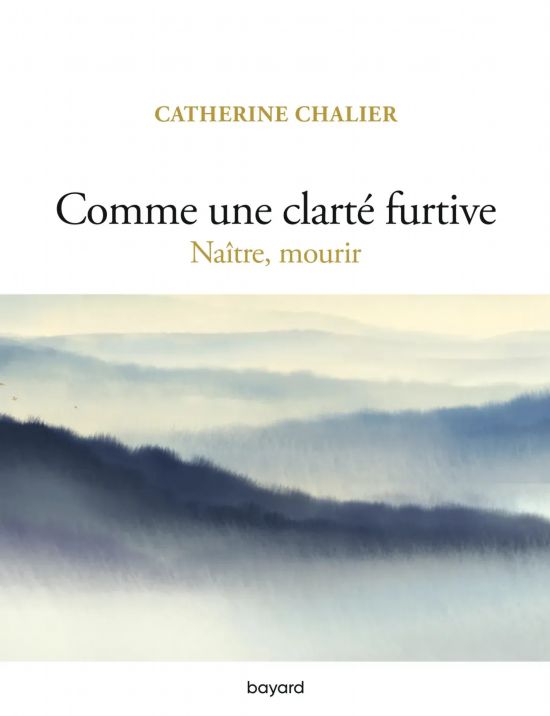
在回忆录《说吧,记忆》(Speak, Memory)中,纳博科夫(Vladimir Nabokov)一开头便写道:“摇篮在深渊上方摇着,常识告诉我们,我们的生存不过是两个永恒的黑暗之间瞬息即逝的一线光明”(19)。这句话精辟而生动地概括了现代人对生死和生命的想象:生命从黑暗的深渊中浮出,在走完成功或失败、艰辛或顺遂、光辉或黯淡的岁月后,复归于死亡寂寥的深渊。如果说那置于生命两端的“永恒黑暗”是一种对虚无的描绘,那夹在两者之间转瞬即逝的一线光明,则似乎只是为了照亮那永恒的黑暗,只是使黑暗显得更黑,同时也使生存显得更为短暂和孤独。这瞬间光华能否安慰人们对永恒黑暗的惧怕?
夏利耶(Catherine Chalier)在其著作《犹如流光:诞生,死亡》(Comme une clarté furtive. Naître, mourir)的开端引用纳博科夫这句话,不是为了肯定这个被视为毋庸置疑的“常识”,而是提示它代表了一种相当具有普遍性的生死观,即透过死亡理解生命(7)。这种观念源远流长,在物质主义盛行的今日更为常见。当今世界,人们通过克隆、赛博格、数字永生等各种“人类增强”技术来对抗与生俱来的脆弱,甚至试图超克死亡。这些发展在带来对人类有限性之解放的同时,也伴随着诸多隐忧,例如新技术运用造成的对伦理和制度的冲击,以及驾驭其灾难性后果的困难,等等。以物质主义和后人类主义来克服有限性,并不等于克服了人类在生命理解上的局限;相反,对生命问题的思考在后人类和超人类主义的挑战之下正变得越来越迫切。我们应当自问:人类对正义世界和美好生活的追求,除了仰赖科技手段和物质条件的改变之外,是否也需要人们先能珍视和善待已经拥有的生命禀赋和伦理?在此意义上,夏利耶这本旨在探讨人类诞生的哲学意义的书便颇具现实感:唯有当我们对人类生命品质的理解更全面深入时,我们对技术时代的应对才能更得当。
诞生也有哲学意义?在这方面,人们过于关注死亡而忽略诞生。该书开篇便指出,古往今来,哲人们都试图用各种方式来“解救”死亡的有限性。他们或者像柏拉图的传人那样,将生命视为明暗交织的过渡,人在此中寻找丢失的光明,希望能在生命的尽头拥有它;或者像一些现代哲学家那样,承认我们的有限性是全然与虚无相伴的,源出虚无又回归虚无(7)。然而,夏利耶追问:死亡是否是对生命的终极规定?抑或我们此生的意义是否只是对天上光明的追寻?我们的生命是否还存在另外的可能?是否还有一些被“常识”以及古典或现代哲学所忽视的亮光的踪迹?这些亮光虽常被遗忘却仍令人向往。(7-8)
作为列维纳斯(Emmanuel Levinas)哲学的当代传人,夏利耶继承和拓展了他关于生死问题的诸多思考。同列维纳斯一样,夏利耶对这些问题的关注源于她与时代处境的对话。现时代的问题处境,固然是由技术和生命政治所强化的对生命的物质主义理解,以及科层化和程序化运作造成的柔性规训与理性剥夺;但更深层的困境则在于,当代思想和哲学自身,无论是将生命的实质视为劳动、身体、力比多,还是将其视为某种存在或力量,最终不仅无力抗拒对生命的物质主义理解,而且从根本上与之同步,这尤其体现在对死亡的想象上。在这本书中,夏利耶不仅丰富和充实了列维纳斯在死亡和有限性问题上对海德格尔(Martin Heidegger)和希腊传统的有力质疑,而且进一步从诞生性角度深化了对这些问题的思考,首次从哲学视角对诞生的意义进行了整全而深刻的考察。
哲学与死亡:向死而生
在古希腊,人被称为“有死者”,人与神的区别是有死者和不死者的差别。正是作为有死的个体,人才会追求在城邦生活中让有限而脆弱的生命获得某种不朽,无论是以荷马英雄建功立业、流芳千古的方式,还是以哲人苏格拉底殉道赴死、证明灵魂不朽的方式。正是这种对伟大的追求将人与动物区别开来,如同海德格尔所说,动物会“完结”,只有人能带着对“向死而在”的领悟死去(334-35)。
虽然“向死而在”的论述在20世纪才广为流传,但自古以来绝大多数哲学家都是透过死亡这端来理解人的生命,鲜少关心诞生这端。在古希腊哲学的华彩乐章《斐多》(Phaedo)中,苏格拉底坚信,通过对智慧的爱,哲人的灵魂能超越肉体和死亡,回归永恒之地。他认为肉体属于物质,追求欲望、激情和享乐,因而趋向堕落、死亡与腐朽;只有灵魂,因为分有对天上理念的记忆,而有可能在尘世生活中拒绝肉体的诱惑,获得永生。他以坦然无惧的临终告白向众弟子表明:哲学就是学习死亡。深受柏拉图主义影响的奥古斯丁(St. Augustine)为自己年轻时对有死者的贪恋而忏悔,因为这种爱同有死性相连,只会带来死的悲伤和生的绝望,为此他劝说人们只应当爱那超越死亡的无限者(63-66)。
现代哲学看重人的此在而否认上帝存在和灵魂不朽,也否定了古典哲学对死亡恐惧的解决之道,从此将对死之“畏”担在了个体此在的生存本体论中,甚至以之作为哲学的起点。“人都是要死的”,正如波伏娃的一部小说(Tous les hommes sont mortels)标题所示,过去这个编织在和谐思想整体中的局部事实,在上帝死后变得如此尖锐,以致成为现代哲学的肉中之刺。以海德格尔和萨特(Jean-Paul Sartre)为代表,他们格外关注死亡,并将生命视为以死亡为终点的旅行。
在海德格尔那里,由于此在对死亡的预见与谋划,经由“畏死”(264)这一此在基本的现身情态,也经由“操心”这一结构环节,死亡成了此在最本己的可能性,促成了此在向死而在(347)。诚然他并非最早经由死来思考生的哲学家,他在自己的著作中明确指出了基督教神学家从圣保罗到加尔文,以及现代哲学家如狄尔泰、西美尔和雅斯贝尔斯等前辈和同辈有关向死而生的思考对他的影响(345)。此外,他的向死而在其实更早源出希腊人对人作为“有死者”之命运的理解(Chalier 27)。只是过去的哲学家还从未如此将死亡提升到存在论的核心地位。
作为存在主义哲学家的代表,萨特同样将死亡视为生命的舵手。不过较之海德格尔对死亡的回收利用,萨特对死亡的看法比较消极。他几次引用马尔罗的话——“死亡将生命变为命运”(152,156,655),并反复强调:死亡全然剥夺了我自为的自由,既无法等待,也不可能预见,是荒谬和偶然性的;因此向死而在是种自欺,死并非我的可能性,而是作为界限的处境,从外部到来(646-48)。他不仅完全不同意海德格尔将死亡视为此在最本己的可能性,还认为死是对一切我的可能性的虚无化。
在萨特看来,无论关于过去还是未来,生命的意义都是由当下决定的(653)。这既意味着意义的相对化和自我中心化(652),也意味着意义在终极上的虚无化,因为死亡终将夺走所有意义(653-54),并将对此意义的解读交与他人。他悲观地说:“如果我们应当死去,我们的生命便没有意义,因为它的问题不接受任何解决方法,因为问题的意义本身仍然是不确定的”(654)。死亡令我只能处于全然被动的“为他”状态,将自由同死亡之间的对立,转化为我的存在同他人的存在之间的对立:“在死亡时刻,我们存在,就意味着在他人的判决面前,我们束手无策”(156)。死亡成为一种被他人“异化”的状态,“是他人的观点对我关于我本身所是观点的胜利”(655)。
在海德格尔和萨特那里,无论是将死亡视为最本己的可能,还是被他人异化的状态,对死亡的认识都不可避免地要同他人发生关系。海德格尔深谙,此在无法在自身的经验中领会死亡,只能经验他人之死。他在《存在与时间》中写道:“此在能够获得某种死亡经验,尤其是因为它本质上就共他人存在”;“他人的死亡却愈发触人心弦”(331)。萨特同样看到,正是由于遭遇他人之死,我才不得不被动地遭遇死亡,死亡和他人一样是我的自为的外部处境。它们虽非我自由的基础,却是我的自由出发的地方。如果没有死亡和他人,便体会不到自由及其价值。
当然他们的焦点始终只是自我的死亡,他人的死是次要的。海德格尔问道:“从此在之为共处的存在的存在方式中可以汲取一种答复,那就是选取临终到头的他人此在作为此在整体性分析的替代课题。但这样一个近便的答复会引向预设的目标吗?”(331)答案显然是否定的。表面上是因为,“任谁也不能从他人那里取走他的死”(333);实质性的原因在于,任谁也不应让我忘记自己的死。萨特则将死亡、他人以及他人之死都视为我的处境性,它们虽与我发生关系,但只是作为对我的自由的外部限定,需要被我自为的目的所照亮。尽管如此,萨特仍不得不承认,客观地看,死亡将把我生命的意义带向他人。
诞生作为开端启新的奇迹:为爱而生
虽然人们时常使用诸如“生命之光”这类表达,却少有哲学家关注或从积极的角度思考个体生命的诞生。这或许是由于婴孩与生俱来的有限性:他们如此脆弱,得全然依赖他人;他们的存在先于自我意识,先于其选择和自由意志,这对哲学而言是彻底“非哲学”的,完全不具备哲学所追求的独立人格与自由精神。在哲学家那里,诞生通常是沉默甚至消极的:柏拉图哲学很多时候将诞生视为堕落;海德格尔将诞生视为被抛;萨特则认为诞生和死亡一样,都是一种“事实性”或者说“给定物”,是荒诞和外在的。然而这并非人们对诞生的全部理解,在一些文学、宗教和少数哲学家如阿伦特(Hannah Arendt)和列维纳斯那里,诞生带来的喜悦、医治甚至救赎的能力受到了关注和欢呼。
夏利耶让我们注意到雨果(Victor Hugo)诗歌对此主题的杰出贡献(9)。雨果不仅在自己的著名小说《悲惨世界》和《九三年》中刻画过令人难忘的儿童形象,更在其诗作如晚年诗集《做祖父的艺术》(L'Art d'être Grand-Père)和史诗性诗集《历代传说》(La légende des siècles)中,大量表达过对儿童身上脆弱而明亮的诞生性的着迷。他笔下的孩童既是现实,也是天使般的存在,例如他写道:
婴儿带来一丝孕育了他们的天空的光明,
他一无所知,他来到,你得接待,
他有青草和树叶的颤抖。
……
他望着这个奇怪而令人害怕的地方,
不明白,惊讶,且没看到上帝,
他咿咿呀呀,声音谦卑,带着信任,令人感动。
他以歌唱结束哭泣,
胆怯地说出第一批词语,如同第一次走路,
然后满怀期待。(《历代传说》598)
这些诗句既描写了婴儿从身体到心智的稚嫩柔弱,也表达了对新生命的惊喜、怜爱与敬畏之情,仿佛正是这稚嫩柔弱赋予了新生儿一种独特的神圣性。这些诗句传递了诗人的感悟:每个生命都珍贵无比,其价值不依赖于这个世界和我们的尺度。在一首题为《缺失》(“Manque”)的诗中,雨果写到自己的第一个外孙乔治,他未出母腹便不幸夭折。在这个乔治流产后另一个乔治出生时,他感到那仿佛是第一个乔治的再生,但很快便意识到这种想法不对:“他们是两个人,也可能是三个”(Art 51)。他明白任何人都无法被他人取代,即便那只是一个早夭的胎儿。
《历代传说》收集了一组描写儿童的诗,其中有革命暴力场景中儿童的出现拯救了将被处死的父亲的感人一幕(《内战》),有一个年幼孤儿令人同情落泪的短暂一生(《小保罗》),也有针砭社会弊病的流浪儿童形象(《社会问题》)。所有这些对儿童及其周围人事的描写都贯穿了雨果特有的浪漫现实主义风格,即以现实主义手法来传递一种十足的“浪漫”激情。在这些诗里,雨果不仅表达了对悲惨世界中儿童不幸命运的哀叹,更深挚赞美了儿童带给世界的慰藉和希望。在名为《儿童的作用》的一首诗中,他写道:
他的翅膀抖动着掠过,只要一碰上我们,
就让我们改变,他无声无息地把光明
注入我们充满风暴与黑暗的心灵。
我们高傲的嗓门只是完美的铜号,
唯有鲜红柔嫩的嘴才能发出柔和音调;
唯有它能征服,安慰,发出警告,
从口吃的儿童可以听到上帝的声音。(610)
在雨果激情澎湃的诗笔下,儿童仿佛具有隐匿的神性。这种神性以卑微柔弱的方式存在,迥异于成人世界的强横和贪婪。儿童与生俱来的对爱与被爱的需要,虽是弱者的表现和处境,却赋予他们一种独特的光彩、智慧和气息,使他们仿佛比成人更接近上帝。儿童对他人纯真的信赖、依靠和期冀,无言地呼唤人们出离各自的仇恨与愤怒,学习以友爱和宽恕的方式共同生活。雨果凭借诗人的敏感和仁者心肠领悟到了这份柔弱却神圣的力量,正是这作为有限性的新生提示我们:人来到世上,本应向爱而生。
对诞生的领会当然不止于诗人的直觉和柔情,也出自少数哲学家的敏锐和深邃。夏利耶指出这方面的代表人物是阿伦特和列维纳斯(9),他们分别从政治行动和道德伦理方面阐释了诞生隐含的开端启新的潜能。
诞生性(natality)既是阿伦特哲学思想的核心观念,也是她据以批判西方哲学和政治哲学传统的独特视角,她在最终出版于1996年的博士论文的英文修订本《爱与圣奥古斯丁》(Love and St. Augustine)以及《人的境况》(The Human Condition)中都对这一概念进行了阐述。她虽身为海德格尔著名的学生并深受其哲学思想影响,却同海德格尔相反,不是以“有死者”那阴郁的畏,而是以积极乐观的新生性和行动观念作为理解生命现象和人类生活的钥匙。她在《人的境况》中指出:“人虽然会死,但他们的出生不是为了死亡,而是为了开端”(246)。这是对变化无常的现世生活的肯定,表明每一个体卑微脆弱的诞生,都拥有“爱世界”(amor mundi)与开端启新的可能;这也是对每一个体独一性的肯定,肯定在缺乏确定性而瞬息万变的现实中,人们有限而充满冒险的行动有可能具有无限的意义;这更是对“爱邻人”以及人们经由言行和记忆而建立起来的政治共同体的肯定,因为无人能在向死而在的孤独中开端启新。
在阿伦特看来,人的出生不仅仅是一个生物性事实,也意味着人有一个终极性起源,这个起源使人在走向自己的死亡之时也能在对起源的回忆中行动和生活。显然,她对出生的理解受到了《圣经》和奥古斯丁的启发,这使她的诞生性观念几乎是一个“圣诞”的世俗化版本。她在《人的境况》中说,福音书中宣告的“福音”——“一个婴孩诞生在我们中间”——是对世界的信心和希望最简洁而荣耀的表达,这种信心和希望是人存在的根本特征,却被作为有死者的希腊人完全忽视了(247)。在谈到包括宽恕在内的行动作为开端启新的“奇迹”时,她也常以“拿撒勒人耶稣”为典范。当然,阿伦特并不关注耶稣的神性,而是将关于他的福音书视为由人的诞生和行动带来奇迹的世界观哲学。她深谙爱世界的困难:世界充满了恶与苦难,因而不能没有超世界的爱。但这也带来了新的挑战:由于这爱是超世界的,便容易从世界中疏离,使爱世界流于空谈——她认为奥古斯丁就是这样。她对奥古斯丁爱的观念的解读既借助奥古斯丁对诞生和起源的强调来批评海德格尔对死亡现象学的沉迷,也批评奥古斯丁过于受到柏拉图哲学的影响,以“爱上帝”优先于“爱邻人”。她认为这同海德格尔以与本真自我的关系优先于同他人的关系一样,都是对爱世界的背离(Fry 24)。
爱世界的愿望使阿伦特徘徊在与两希传统的对话中,既无法割裂两者,也无法完全认同任何一边,亦使她将分属两希传统的诞生性和行动在开端启新的意义上结合在一起。正因为将诞生视为开端,她相信人能够去行动;而行动作为人类政治事务的启新也如同人的另一种诞生:“由于人就是一个开端,所以他能够去开始;做人和变得自由是一回事。上帝之所以创造人,是为了把开端能力即自由引入世界”(Between 167)。人是一个开端意味着人能超越生存的无意义和死亡的毁灭性逻辑,赋予在广袤无边的宇宙中生存的渺小个体一种扎根建造家园以及热爱这个家园的可能;人能采取行动则意味着人有可能改变自然或历史的非人性进程,无论这个进程在当下看来多么坚不可摧。在一个日益以后人类和超人类作为议题的时代,追溯开端有助于我们反思人类存在的意义,理解为何应当尊重个体与人的多样性,以及如何面对死亡等问题。
与此同时阿伦特也提示我们,诞生固然是开端启新,但每个人也都是在他人的等待之中来到世上。世界先于每一个体而存在,每个人都站在过去与未来之间。有的文化形态更强调个体价值,如希腊文明,有的文化形态更重视传承和延续,如中国传统,它们各有其道理和问题。过于强调个体,则生命难以克服死亡带来的荒谬感;过于强调延续,无论是家族血脉的传承还是数字化永生,也同样是屈服于物质的荒谬。关键在于如何理解个体与代际的关系,或者,如何化解个体与传承之间或此或彼的张力,实现它们的良性互动。对此,夏利耶经由犹太传统和列维纳斯的哲学,揭示了一种先于个体并呼唤个体对其进行回应与传承的生命禀赋:生命作为爱的表达,同话语、声音和气息相关,在个体的诞生和彼此应答中绵延。
生生不息:从光到光的修复与更新
夏利耶指出,视人为有死者的希腊人,无论荷马笔下的英雄还是柏拉图的师生,都深深渴望灵魂不朽;但希伯来人,尤其是先知,却称人类为“亚当的儿子”(bnéi Adam; 27)。这个称呼在当代希伯来文中仍在使用,它提示了人类存在的两个维度:人在代际传承中的独特出生,以及人是“上帝”的造物——“亚当”(adam)来自“泥土”(adama; 69),这“泥土”有了“上帝”的气息才能成人。
“亚当的儿子”首先意味着人总是作为他人的儿女,无人能赋予自己生命。这也是有限性的体现。《圣经》中出现了大量族谱与人名,相当多名字仅代表某个过往的逝者,此外我们对其一无所知。先知的名字出现时,常会连同其父亲的名字一道,如“亚摩斯的儿子以赛亚”(《以赛亚书》1:1),“希勒家的儿子耶利米”(《耶利米书》1:1)。这些不被省略的名字并非对死亡的提醒,而是对诞生的记忆,记录那些在代际传承中虽会逝去却不可被替代的个体。逝者的名字具有生命之链的含义:虽乍看之下“太阳底下无新事”,一切似乎只在循环往复,但每个生命都有其绝对的独特性,每个名字都应当被保留。尽管在渴望于个体生命中实现无限的希腊传统看来,这种格局仍显“逼仄”,却为人的有限性开启了一种积极意象。
在西方,由于深受希腊哲学影响,基督教较多强调个体性而相对忽视“亚当的儿子”这一希伯来传统。在希伯来传统中,有限性主要同出生相关,并非仅指死亡。比起关心死亡的希腊哲人,希伯来传统更关注此世,仿佛在他们看来,死亡是平淡无奇的。在《圣经》中,人同上帝相似并不意味着人可以避免死亡,死亡始终是人的宿命,但不再具有尖锐的负面特征。以色列族长亚伯拉罕和雅各死时,都是安然离世,“归到他列祖那里”(《创世记》25:8;49:33)。也就是说,他们坦然接受了自己作为“亚当的儿子”这一有限性,明白生命本是被给予的,亦将给予后人。这条生命之链启示人们,无论个人曾如何重要,都只是其中一环。个人既非开端,亦非终结,也无法全然担当自己的死,哪怕他能接受甚至选择死亡——萨特便指出过这一点。《圣经·诗篇》中说:“死亡的绳索缠绕我;阴间的痛苦抓住我;我遭遇患难愁苦。……我的心哪!你要仍归安乐,因为耶和华用厚恩待你”(116:3-7)。唯有那给予生命者,能安慰人们对死亡或多或少的恐惧不安。
在这条生命之链上,每个人都是有限和无限的交织,被召唤去将他获得的生命传给他人。唯其有限,他才能领会这个召唤,明白希望不在于个人对生命的占有,而在于养育和给予新生。在此意义上,“无后”犹如死亡。然而这跟“不孝有三,无后为大”仅有表面的相似;在《圣经》中,“生养”超出了肉体血缘的自然延续,应在灵性意义上得到理解。自然生养作为人类生存的本能,无须格外鼓励或要求,但《创世记》却特意嘱咐他们:“要生养众多,遍满地面,治理这地”(1:28)。这嘱咐让人们关怀自己“身后”的世界,关爱那些承载了希望的未来建设者。
与此同时生命之链并非线性史观,并不朝向任何历史终极,而仅以每一当下瞬间作为回应弥赛亚来临的时刻。当下并非过渡,而有其自身的终极性;个体不会消融在群体中,而有其不可替代的名字。人是生灵,不是工具,正如雨果曾如此描写的流浪儿童:“没有什么比这个小幽灵更加黑暗。/一个原子容纳的地狱数量/令思想家吃惊”(《历代传说》618)。这不仅是因为对儿童的遗弃和伤害也是对未来世界的不义和破坏,更因为儿童自身便是生命之源和希望之光,在他们被遗弃和伤害的世界,生命和希望也被漠视和践踏。没有人是微不足道的:“一个原子”便能容纳无数“地狱”。
列维纳斯对生死的思考深受上述犹太传统启发但又保持其独立的哲学思维,更适应现代人的理解方式。他不仅肯定了诞生性对有死性的超越,也创造性地诠释了诞生性的道德内涵,即个体经由对责任之回应而实现主体性的“诞生”。列维纳斯认为,鉴于心灵能够回应某种先于意识与记忆的美善事物,同“无限”有种先于主体意图和意愿的关联,因此出生即是对“无限”的承载,让“无限”进入每个人并成为他们的独一性(Chalier 13)。但这种心灵的禀赋还应当经受人世的考验,直到在“孕育”他人——为他人负责——的同时完成自我的“重生”,成为责任的主体性。对此,列维纳斯以“母性”来进行描述(Levinas 145):它使责任和爱的关系在我与他人(以及未来的人)之间繁衍与传承,既是对未来的呵护,也是对我的有限性的修复,和对个体生命的更新。
这种从诞生(和再生)的角度理解生命的方式迥异于哲学家惯常的死亡角度。自古及今,通过预见(我的)死亡来理解生命是种较为普遍的心理,人们据此获得对生命时间之珍贵的意识,从而达致更高的人生境界。然而,在列维纳斯看来,为避免窄化,我们的生命想象至少也可以尝试向另一端——诞生——所带来的启示敞开。单就死亡而言,人在此世的一切操心忧虑终将归于虚无;若从诞生性那一端看,就连死亡也可以呈现出别样的风景。不同于哲学家通常对情感的轻视,列维纳斯提醒人们珍视情感的发现:我们的认识虽无法还原死亡,但他人之死带来的极度情感创伤却能向我们展现死亡另外的面向——死是对爱生命之紧迫性的召唤,召唤一种责任主体性的醒悟或者说“诞生”。
这里同样,诞生和生命不只是生物性的,无法仅仅通过物质来衡量,亦非柏格森据以反对物质主义的生命冲动和创造性自由,而是一个能发出爱生命之召唤的地方,是向他人开放的表达。与海德格尔那个让人们向死而在的“良知召唤”相比,列维纳斯强调一个赋予人们生命的“无限”的召唤。它让人们通过对它的回应而彼此回应,由此,生生不息也是声声不息。而死亡则意味着不再拥有倾听和回应的能力。这种对生死的理解虽然显得诗化,在技术时代却发人深省:当人类的数字化生存日益成为一种可能代替生命的选项时,生命是否可以缺少诞生性的话语和气息,还是仅仅意味着信息和物质性交互?当那象征人类生存之有限性的死亡可以被无限悬搁,那将被悬搁的,也许不仅是有限性,也是新生的感受。那时,人们虽不在生物或信息学意义上死去,但也并不在拥有心灵的意义上活着。倘若生命不再意味着拥有心灵和自我超越的可能,无需向他人开放,那么它将会是什么?
过去时代,造人曾是神的权能。今天,当数字永生进入人们的视野和争论时,生命技术允许人们选择自己想要的孩子,避开自己不喜欢的,这对于人类意味着什么?人们果真能通过技术克服自己的有限性,从而获致完满?这种获得会否以丧失诞生的神圣性为代价?问题或许不在于技术造人是否应当,而在于诞生的奇迹会否被造人技术遮蔽。
事实上,早在玛丽·雪莱(Mary Shelley)出版于1818年的小说《弗兰肯斯坦——现代普罗米修斯》(Frankenstein; or, The Modern Prometheus)中,“造人”的伦理困境便已受到质疑。人造人被造而不被爱,他因丑陋而成了众人眼中的怪物。他向往人类爱的言语,渴望关怀却遭毒打和唾弃。他的生命不被祝福而充满痛苦和暴力,于是选择报复。《弗兰肯斯坦》不仅可被读作对技术狂的警示,更可被视为关于生命品质的寓言:如果生命仅有物质和能量,却缺少对其神圣起源的尊重,缺少爱与被爱的关系,以及自我超越的维度,未必不会沦为灾难。弗兰肯斯坦的失败在于,他错误地以为自己可以成为造物主,从物质中找到生命起源的秘密,却不过制造了一场生命的灾难。这个关于技术和生命的灾难性预言在某种意义上已被玛丽·雪莱不幸言中:一百年后,当人类试图像造物主一样规划和制造地球未来的种族和“新人”时,他们只是制造了毁灭和恐怖。正是怀着这种忧虑,夏利耶在这本书的结尾指出:每个诞生的婴孩,都是一个对生命之神圣起源的肯定;这提醒我们,尊重他人的诞生和死亡,领会“你不可杀人”的诫命,比沉思自己的死亡更加要紧(33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