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怪物住在我们与古人之间久远的时光里”
编 者
“妖怪”源于人类对神秘世界的想象。中国的妖怪文化历史悠久,最早集中记载各种妖怪的开山之作就是《山海经》。作为学术研究的“妖怪学”,从科学、民俗、文化等多种角度揭开了“妖怪”何以成为“妖怪”的秘密。本期特邀北京大学医学人文学院教师王鑫、作家张云、北京语言大学博士研究生曹家瑶撰文,辨析“妖怪学”的丰富内涵。
“怪物住在我们与古人之间久远的时光里”
□曹家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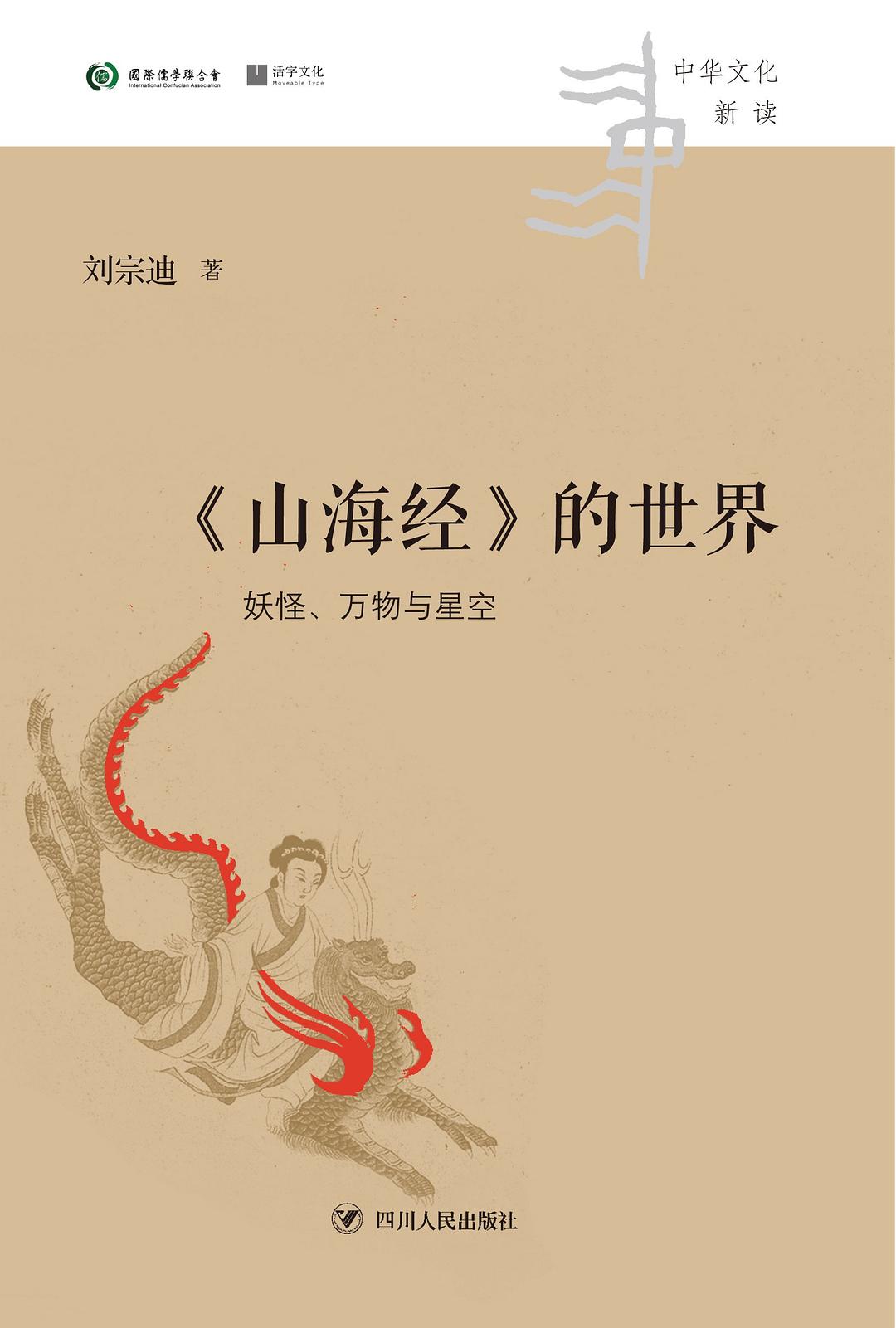
《〈山海经〉的世界:妖怪、万物与星空》,刘宗迪著,四川人民出版社,2021年11月
近年来,随着中国传统文化的复兴,学术研究与大众文化都把更多的目光聚焦于《山海经》一书,且论者观点繁多、学科分布广泛,涉及文学、教育学、历史学、地理学、艺术学、旅游文化产业和戏剧影视等多个方面。最广为乐道的无疑是《山海经》中吸引眼球的、异于生活的奇珍异兽,它们成了当代奇幻小说创作、游戏怪兽形象设计和美术视觉传达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灵感来源。
作为丰厚的神话资源,《山海经》乘着文化自信、神话热的东风也活跃在网络视频平台中,长视频领域“山海经”的搜索单元下有优质内容1000余条,短视频领域更是全面开花,“山海经”的词条参与数量高达121.1亿次。在大众文化领域,《山海经》依托“神兽全集”的表象,成为“解禁上古封印”“开启华夏神器”的钥匙。《山海经》的知识性质属于“整体性知识”,是中国早期文明未经分化的“百科全书”,因此这种对世界整体的认识也是《山海经》争论已久、无法分类的重要原因。
作者以“日常生活”的角度,在《〈山海经〉的世界:妖怪、万物与星空》(下称《〈山海经〉的世界》)一书中专就《山经》部分论述,运用博物学、语言学、生物学、民俗学、天文学、文化史等多学科知识,详细列举《周礼》《管子》《梁丘藏》《日书》和睡虎地秦简等传世与出土文献资料,对《山经》中记载的怪鸟异兽、灵异妖怪、山川群神进行详细考察,吹散厚厚的历史冗论,讲述它们的真相和由来,澄清古今读者对《山海经》的误读与偏见。
解释万物的最大张力:生活
本书的核心要旨在于实际的生活体验。要读懂古书,就要站在古人写书的角度。我们发现生活中的“司空见惯”是那么的“难以言说”,如何描述一张桌子?如何介绍一只猫?识其名目简单,总结出它们的外貌和功用实难。在西方博物学系统未传入中国之前,我们描述物品的最大极限难以突破一个范围,就是生活文化,鲁迅说:“天才们无论怎样说大话,归根结底,还是不能凭空创造。描神画鬼,毫无对证,本可以专靠了神思,所谓‘天马行空’似的挥写了,然而他们写出来的,也不过是三只眼,长颈子,就是在常见的人体上,增加了眼睛一只,增长了颈子二三尺而已。”故而《山经》在介绍某一陌生动物的形象时,往往会采取比拟的方法,借用人们熟悉的动物来描述其身体的各个部位,如“有鱼焉,其状如牛,陵居,蛇尾有翼,其羽在魼下”就是用自然界中常见的鱼、牛、蛇、鸟等动物来描绘穿山甲。可见,不论是怪物还是妖怪,《山海经》中的描述习惯坚持“能近取譬”的原则,以至于当无法沉浸在古史的语境时,后人阅读会有“猜不中谜语”的苦恼,紧接着就“躺平式想象”,自由创造了。所以作者在书中彻底摒弃了这样层层叠叠的“想象”,基于其对古代典籍的广泛阅读和精湛理解,用一种设身处地、体察入微的眼光,重新审视《山经》文本,对其性质、内容和成书过程进行细致周密的考察,最终将世人眼中那个光怪陆离、荒唐无稽的异域世界还原为了上古先民真实、普通的生活空间。
作者将遍布于山脉的妖样怪兽分为两类,一种是怪物,一种是妖怪。《山海经》中的怪物有两种不同的描述方式,这与世人在缺乏博物学知识的背景下,对怪物的理解路径有关。首先是因为读者不了解《山经》记述动物的方式而导致的“缝合怪”:由于早期博物学尚未建立像今天这样标准的形态学术语体系与描述方式,所以对于不了解这种记述方式的人来说,《山经》里没有谜底的谜语,可以被猜为世间任意一种罕见的怪物,一如“样子像老鼠,脑袋像兔子,身体像麋鹿,用尾巴飞行”,这样的缝合怪其实是蜜袋鼯;其次是《山经》记载了大量的“畸形怪”:它们被描述为多目、多足、多尾、多首等,其中有些固然夹杂着想象和夸张的成分,也有不少内容确实源于古人真切的博物学观察,如“其状如肺而有目,六足,有珠,其味酸甘”的珠蟞鱼,大抵为中华鲎,“其状如鲋,一首而十身”的茈鱼,确为章鱼,“其状如鸡而赤毛,三尾、六足、四首”的儵鱼,即鱿鱼。它们显然正是这三种海洋生物的真实写照,但缺乏海滨生活经验的读者无法猜对,这些不合乎常识的长相奇异的动物就只能是古人捏造出来的畸形怪兽。
妖怪与怪物是有区别的,《左传》有云:“天反时为灾,地反物为妖”。如果说怪兽仅是山林偶遇的视觉冲击,那妖怪则还要加一条“见则灾祥”的心灵暴击。由于缺乏对自然规律的认识,人们经常会把预兆当作原因,来为自己的无能为力开脱。《山经》中记载的那些“见则”有天灾人祸发生的动物——如“见则郡县大水”的长右之兽、 “见则天下大旱”的颙鸟——为何会被视作具有灵异力量的妖怪,作者也在“妖怪的秘密”一章中列出一张“妖怪清单”,动物与自然灾害的相关性鲜明自见,水生动物在旱灾时自然会浮现出地面,而陆地动物在洪涝时自然会徙居觅食,“这些记载仅仅意味着动物的行为跟自然灾害之间存在着相关性,并不意味着某种动物的出现与自然灾害之间的因果性”。所以《山经》中大量朕兆知识的记载,再一次反映出《山海经》文本作为知识手册的务实性,也凝结着先民认识自然现象、总结自然规律的智慧。
我们对《山海经》的误解也正如作者的总结:“这些原本平凡的生灵,之所以变成怪物,只是因为在我们和古人之间横亘着漫长的岁月,让我们已经无法理解古人原本朴素的博物学话语,无法再用像他们一样的眼光看待世间万物……怪物既不住在深山里,也不住在大海里,更不住在古人的幻想里,而是住在我们与古人之间久远的时光里。”
还原现象的本质和意义:化生为熟
《〈山海经〉的世界》中最后一部分让我们坐在了先民的身边,徜徉在同一片星空下,在《失落的天书》已有的知识基础上,诠释天地如何合一,山海如何同祀。
其实对于自然信仰的崇拜,该书在前期解释怪物时就有铺垫,星散于“五藏山经”的除了各色怪兽,还有在每座山后规律性出现的“X身人面”“X面人身”的山神,所以《山经》中的自然崇拜与神话叙事是研究《山海经》绕不开的话题,也是我们与古人共觞、被神话深深吸引的情之所系。
作者熟稔《山经》各脉特点,而神仙云集、奇幻瑰丽的唯有《西山经》,所以他利用中国古代天文学知识,探讨了《西次三经》中所记载的山川群神的由来:即《西次三经》的绚烂源于秋天夜空的诸多亮星,这些神灵及其所栖居的山川,实际上是西方白虎七宿和其周边数组星宿在地上的投影,如人面虎身的陆吾神和开明兽即是天上的参、觜、伐等星宿的化身。山神众列、秋尝狂欢对应狩猎七宿,揭示出上古神灵崇拜的天文学内涵,而“天人合一”也有了实际可感的理解。先民穷尽智慧和时间,抬头望天,远眺连山,低头观影,终见自己生存于自然的法则,时间的行走即为神明的遨游,星辰的坐标画出农桑的宇宙。这样翔实而独特的角度呈现出作者本人在研究《山海经》时始终坚持的现象学的立场,他回到文本本身,回到文本产生时的语境,设身处地地用《山海经》时代人们的眼光来阅读文本、理解文本,实现了“化生为熟”。
在作者层层剖析之下,不论是《山海经》本身,还是书中那些怪物、妖怪、神灵、神话等,无不回归到其原生空间中的本真状态,呈现出一个令世人陌生又熟悉的真实面目:在本书的结尾,他也阐释了神话学的真实面目,神话是一种解释圣地、赋予圣地意义的文本。圣地是分散的,所以神话的本态也应是零散于山河天地,“中国之所以没有形成那样体系完备的神话,正是因为中国没有像荷马史诗、印度史诗、北欧埃达那样的神话编纂活动;而中国之所以没有神话编纂活动,则是因为中国自古就有发达的历史编纂学传统。文化是有惯性的,这种惯性导致《山海经》的神话记忆散佚融合在《尚书》《逸周书》《春秋》《世本》《国语》等历史文献中,所以我们“也根本没必要为缺少希腊、印度、北欧那样的神话史诗而感到缺憾甚至自卑”。
《山海经》的热议是一件好事,但是我们需要知道最初的《山海经》是什么样子的,如此才更能理解它的深沉魅力,更能找到两千余年我们对其心驰神往的原因。神话是每个民族最悠久、最坚韧的文化生命之根,滋养着文学的潜流和文化的筑基,一如汉赋的汪洋恣肆,及陶渊明《读山海经》的意蕴广深,一如长妈妈哄迅哥儿的哼眠,和伴随中国孩子的童年。
“发觉礼俗之本意,使荒诞古怪皆能明晰”
□王 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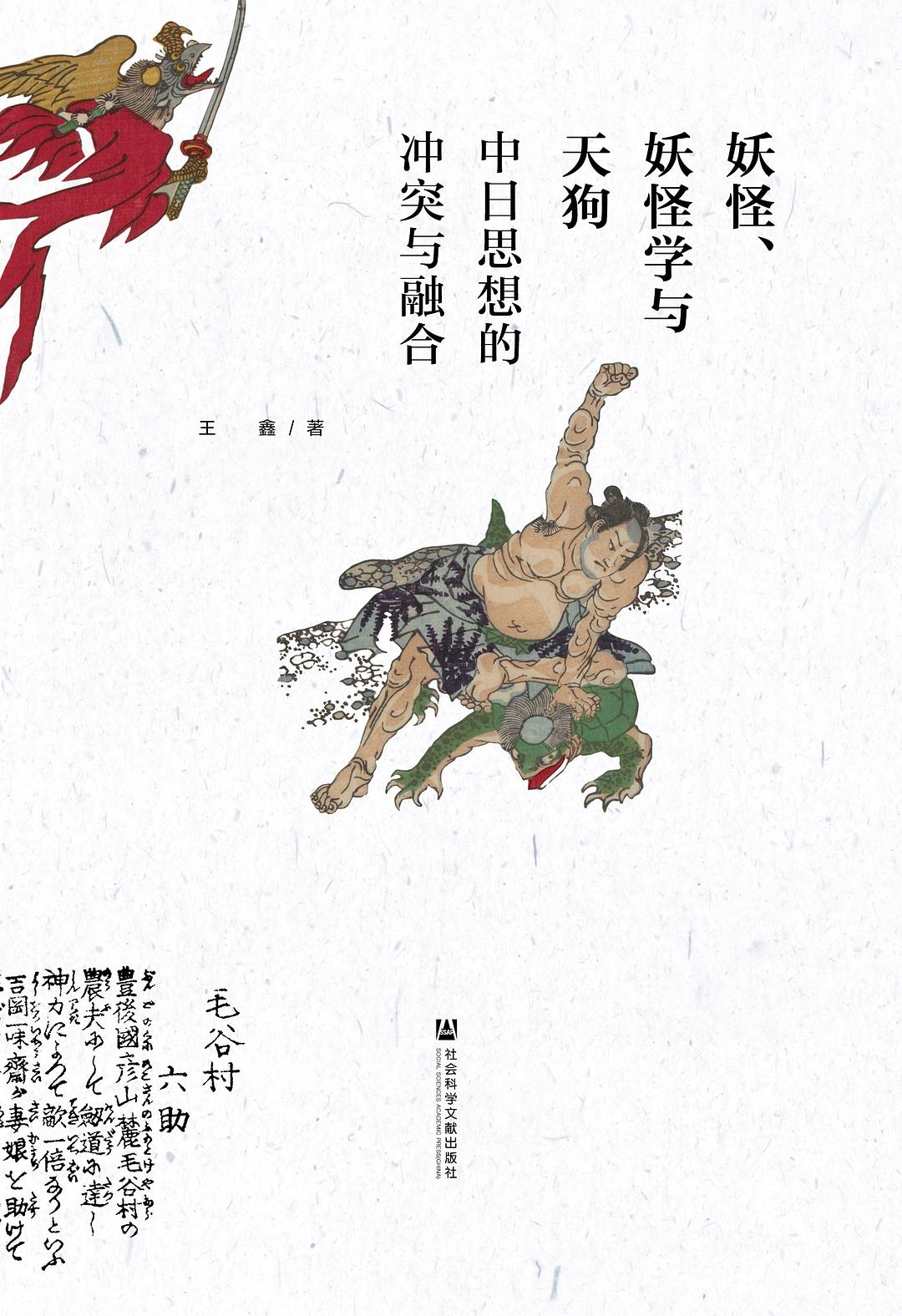
《妖怪、妖怪学与天狗:中日思想的冲突与融合》,王鑫著,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9年3月
我对“妖怪”的兴趣,始于大学时期在系资料室的一次邂逅。彼时,我不经意间翻阅到一本老师刚从日本带回的插画版日本“鬼”文化书籍。当时,网络尚不发达,书籍获取也不似如今这般便利,此书是资料室中唯一一本介绍日本“鬼”文化的书籍。书中那个长着犄角、獠牙,身着虎皮裙、手持棒子的“鬼”的形象,彻底颠覆了我对“鬼”的传统认知。源自中国的日本“鬼”,为何与中国存在如此显著的差异?这个疑问在我心中长久萦绕,难以释怀。因此,硕士阶段我以此为课题进行了探索,但仍有诸多未解之谜。博士期间,“妖怪学”深深吸引了我,原来妖怪亦为一门学问,在日本拥有百年传承。尽管我在日本的动漫中频繁看到妖怪的形象,却未曾知晓这些形象与文化背后有着百年民俗学研究的支撑。直至我加入以时任京都国际日本文化研究中心所长“妖怪学博士”小松和彦教授领衔的日本妖怪学研究团队,聆听了来自日本、韩国、法国、美国等各国学者从民俗学、文学、历史学、图像学以及地理学等诸多视角的妖怪研究之后,方觉“妖怪学”竟是如此博大精深的一门学问,是能够由各国学者展开跨文化跨学科研究的领域。
日本“妖怪学”鼻祖井上圆了为了消灭妖怪、破除迷信开创了这一领域,其犹如一盏明灯,照亮了我国清末民国初年民众启蒙、开启民智的道路。蔡元培将其妖怪学著作翻译引入中国,江绍原更是以此为基石开创了“迷信学”。就在日本的妖怪即将被“剿灭一空”之际,柳田国男重新发掘了它的价值,开始整理记录妖怪故事与传说,探寻妖怪的新价值,柳田认为它是唯一未被频繁舶来的更未被精妙之物所取代的东西,其中可以窥探平常人的人生观与信仰变迁。受柳田民俗学影响的周作人对“鬼”亦心怀偏爱,认为研究中国人的国民性应当将重点置于以“鬼”为核心的礼俗研究之上,因此处“可见中国民族的真心实意”,“贯古通今,明其变迁,比较内外,考其异同,于其中发觉礼俗之本意,使以往觉得荒诞古怪不可探究的仪式传说皆能明晰,人类文化之发展与其遗留之迹亦可知晓”。
日本的“妖怪”一词源自中国,而日本的“妖怪学”又反哺中国,这其间究竟历经了怎样的变迁?中日妖怪之间有着怎样的纠葛?怀揣这些疑问,我尝试从思想史的视角予以了解答。透过妖怪能够看到古代日本对中国思想的吸纳与改造,那个发源于儒家天命思想的妖怪在传入日本后被日本统治阶级进行了有益于统治势力延续的改造,剔除了威胁天皇统治的易姓革命部分。随着阴阳道的兴起,阴阳师与修验僧竞相角逐法术,越来越多的“妖怪”被缔造出来。中世之时,绘卷的出现令妖怪从幕后走到台前,其形象被越来越多的百姓大众所熟知。进入江户时期,原本那些令人胆寒的妖怪现身于浮世绘等大众文化中,成为大众娱乐的对象。
作为日本妖怪著名代表的天狗也时常出现在绘卷与浮世绘中,那个至今仍屹立在日本鞍马山下的巨大红脸长鼻子天狗像令人震撼。它为何与中国的天狗存在如此巨大的差异?两国间的天狗是否存在关联,在历史的长河中,它们经历了何种演变?在从造型上难以将两者关联起来的情况下,我尝试从思想史视角探究了日本对中国天狗的接纳与改造。日本的天狗,其形象丰富多元、性质纷繁复杂,众说纷纭、难以定论。“天狗”一词由中国传入,最初见于《日本书纪》,和中国的天狗一样,是流星等星辰的称谓。然而,由于其易姓革命的危险性质,被日本断然抛弃,在接下来的200多年间杳无踪迹。平安时期再次登场的天狗其形象性格已截然不同,演变为妨碍佛法的“鸱鸟”形象,这一形象的塑造源于日本密教的发展和秘密修法的流行。台密为对抗东密的《六字经法》,将密教修法中常使用的结缚“天狐”“地狐”改为“天狗”“地狗”,并命名为“三类形”。鸱鸟形象则取自中国依据道教三尸信仰编撰的《青色大金刚药叉辟鬼魔法》一经。三尸信仰传入日本后与佛教相融合,青色大金刚药叉演化为青面金刚,如今在日本街头仍随处可见青面金刚像。日本鸱鸟形象的天狗正是在如此纷繁复杂的时代背景与思想背景下应运而生的。虽然本书解开了部分谜团,但在妖怪这广袤无垠的世界中,仍有众多未解之谜有待我们去探索。
小松和彦教授常说:“‘妖怪’恰似一面镜子,能够映射出古人精神世界的某一侧面。妖怪学能够弥补传统文化研究中缺失的部分,是构建日本文化论与日本人论的重要素材,是‘人之学’。现代的妖怪学既要以史学视角追根溯源,更要以人类学视角追问‘现在’‘为什么’。”即思考妖怪研究在当今社会的作用,以史为鉴、古为今用。在广袤无边的古代文化遗产中,“妖怪”宛如一颗独特且神秘的明珠,折射出古人心灵世界的深沉与繁复,见证了中日思想文化的冲突与融合。妖怪,作为古人想象中的超自然存在,其形象繁多,异彩纷呈,从面容狰狞恐怖的山魈鬼魅,到美丽迷人的狐仙花妖,每一个妖怪的背后都蕴含着特定的文化内涵和社会心理。通过妖怪学研究,我们能够更为深切地理解古人的内心世界,体悟他们的恐惧与渴望、信仰与智慧;通过各国妖怪的比较研究,我们能够更好地了解中外思想文化的互动,重现中外思想文化交流碰撞的历史。在当今社会,“妖怪”所蕴含的文化价值和精神内涵仍然值得我们去挖掘与珍视。妖怪学研究可以推动跨学科交叉研究的发展,发掘传统文化与固有信仰,能够丰富现代文艺创作,为文学、电影、动漫、游戏等提供充裕的素材和创意,助推文化产业的发展;能够满足人们的精神需求,满足人们对未知和神秘世界的好奇心与探索欲望,给人们带来娱乐和精神上的享受。
什么是“妖怪”
□张 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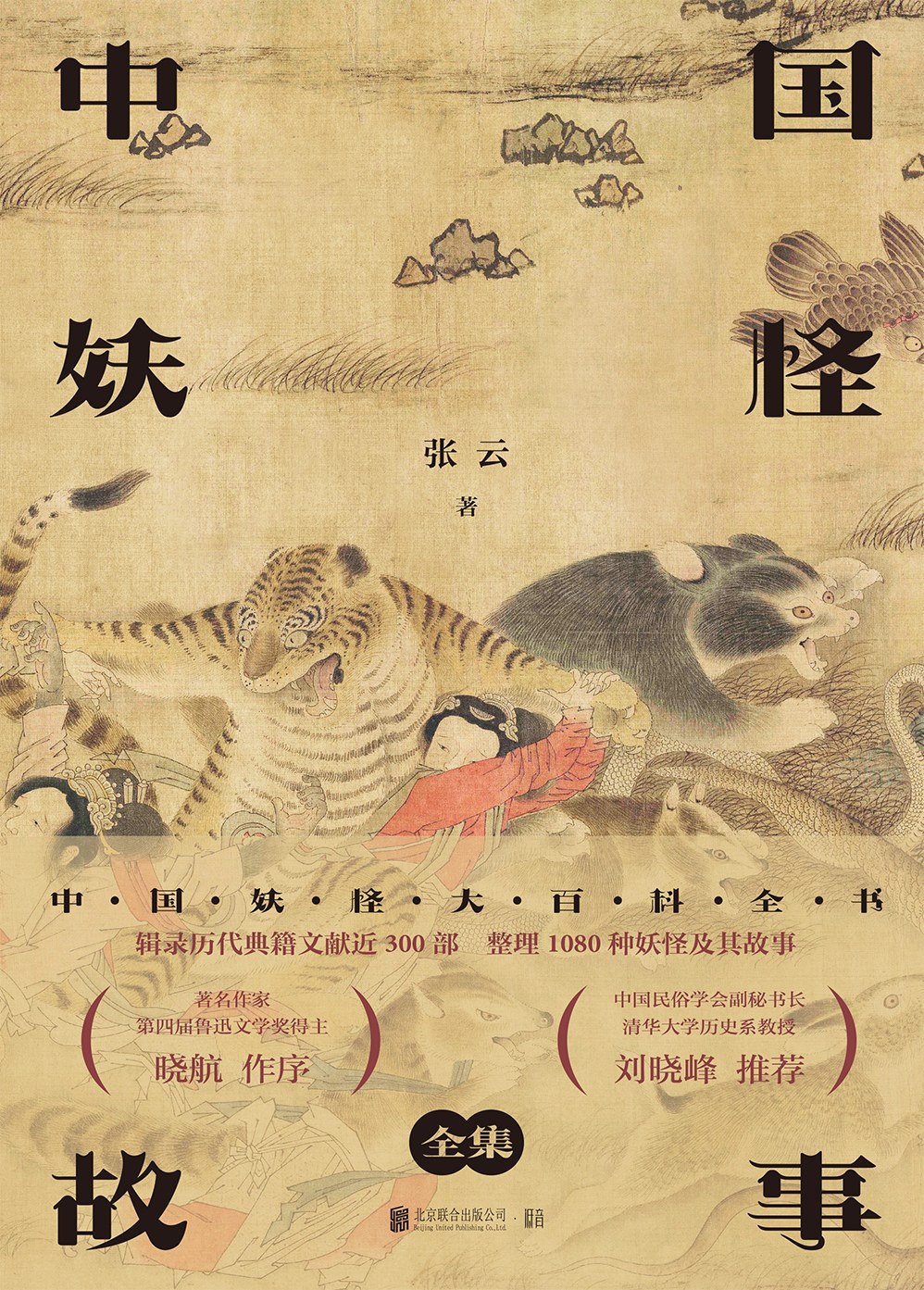
《中国妖怪故事(全集)》,张云著,北京联合出版公司,2020年6月
妖怪和妖怪文化在中国源远流长,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全世界很难找到一个国家像中国这样,将关于妖怪的记载、想象形成一种深厚的文化现象,其延续时间之长、延伸范围之广、文学作品之多,举世罕见。
妖怪和妖怪文化是中华文明的璀璨奇葩,值得我们一代代传承下去。
那么,什么是妖怪呢?
我们的老祖先将妖怪定义为“反物为妖”“非常则怪”。简单地说,生活中一些怪异、反常的事物和现象由于超越了当时人类的理解,无法解释清楚,就被人们称为妖怪。所以,所谓的妖怪指的是:根植于现实生活中,超出人们正常认知的奇异、怪诞的事物。妖怪,包含妖、精、鬼、怪四大类。
妖:人之假造为妖,此类的共同特点是人所化成或者是动物以人形呈现的,比如狐妖、落头民等。精:物之性灵为精,山石、植物、动物(不以人的形象出现的)、器物等所化,如山蜘蛛、罔象等。鬼:魂魄不散为鬼,以幽灵、魂魄、亡象出现,比如画皮、银伥等。怪:物之异常为怪,对人来说不熟悉、不了解的事物,平常生活中几乎没见过的事物,或者见过同类的事物,但跟同类的事物有很大差别的,如天狗、巴蛇等。
中国的妖怪、妖怪文化历史悠久。有足够的考古证据表明,早在石器时代,我们的老祖宗就开始对妖怪有了认知并进行了创造。可以说,中国的妖怪历史和中国人的历史是彼此相伴的,“万年妖怪”之说一点儿都不为过。
从先秦时代,中国人就开始将妖怪和妖怪故事记录在各种典籍里,此后又产生了《山海经》《白泽图》《搜神记》《夷坚志》《聊斋志异》《子不语》等无数的经典作品,使得很多妖怪家喻户晓。中国的妖怪和妖怪文化不仅深深影响了中国人,还传播到周边国家,深受异国友人的喜爱。比如,日本著名的妖怪研究学者水木茂称:“如果要考证日本妖怪的起源,我相信至少有70%的原型来自中国。除此之外的20%来自印度,剩下10%才是本土的妖怪。”由此可见中国的妖怪和妖怪文化对日本的巨大影响。由于种种原因,中国妖怪及妖怪文化还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很多人甚至将我们老祖宗创造的中国妖怪误认为是日本妖怪,这是令人十分惋惜的。
笔者用10年时间,写成《中国妖怪故事(全集)》一书,在深入研究中国历代古籍尤其是志怪分类和定义的基础上,厘清妖怪的内涵,从浩渺的历代典籍中搜集、整理各种妖怪故事,重新加工,翻译成白话文。其间参考各种民间传说、地方志等,确保故事来源的可靠性与描写的生动性。该书记录1080种(再版后增加到1919种)中国妖怪,是目前为止国内收录妖怪最多、最全,篇幅最长、条例最清楚的妖怪研究专著。
《中国妖怪故事(全集)》出版以来,反响强烈,深受读者喜爱,这让笔者感到既欣喜又惶恐。中国的妖怪故事中,不仅妖怪的形象充满想象力、故事情节生动,而且其中蕴含着许多为人处世的道理,值得珍惜和深入挖掘。长久以来,中国妖怪的故事虽然丰富,但妖怪的图像留存较少,甚为可惜。有鉴于此,我们又推出了《讲了很久很久的中国妖怪故事》系列,目前出到第三册,每册都是精心选取了100个妖怪故事,加以润色加工,并严格按照典籍记载,为妖怪画像,以期能为大众以及中国妖怪的爱好者们打开一扇中国妖怪故事的缤纷之窗,为中国妖怪和中国妖怪文化的普及和发展贡献绵薄之力。今年年初,又推出了《妖怪说》,尝试在万物有灵中洞悉古代历史的神秘和驳杂。
中国妖怪文化博大精深,源远流长。我们的老祖宗创造了它们,它们的故乡在中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