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浪潮”访谈 | 朱婧:写作,让我们看见那些无视之见

《人民文学》“新浪潮”栏目自开设以来已有二十多年的历史,现已成为杂志的品牌之一。此栏目的作者均系首次在《人民文学》发表作品。今年,将召开全国青年作家创作会议,中国作家网与《人民文学》杂志共同推出“新浪潮”作家观察专题。鉴于栏目优秀作者众多,经过认真考虑,兼顾地域、民族、体裁等因素,我们选出第一期12位青年作家:朱婧、江汀、李晁、羌人六、栗鹿、沙冒智化、杨知寒、康岩、三三、蒋在、杜梨、焦典。作家访谈和相关视频将陆续在中国作家网网站和各新媒体平台、《人民文学》杂志各媒体平台推出,敬请关注。

朱婧,江苏扬州人,文学博士,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副教授,硕士生导师,中国现代文学馆客座研究员。著有小说集《譬若檐滴》《猫选中的人》等。曾获人民文学奖新人奖、江苏省紫金山文学奖等。
梁豪:朱婧你好,今年4月在四川古蔺举行的人民文学年度奖颁奖典礼上,我们第一次碰面,我的粗浅印象,你是一个安静、敏感、柔和的人,这样的人,往往是一个更多地向内生长的人。这种感受跟我对小说《吃东西的女人》的体会高度一致。记得当时与你交流,我说在这篇小说里,感觉你把自己狠狠地掏出来了。
《吃东西的女人》就像不同阶段的你、日常呈现和躲藏于内心的你之间进行的一场对话。你借此重新整理和修复自己,当然,还有想象性的再造。我不确定以上所说是否恰当,如果有几分在理,我想这是需要相当的勇气的。正是这份刀刃向内、冷静直观的勇气,让这篇小说得以挣脱各式套路的女性写作,给人一种情思上的绵延的震荡。
朱婧:《吃东西的女人》确实是发生在“今日之我”和“昔日之我”之间的对话,所以,在小说里,我征用了涩泽龙彦《镜与真》中朱橘与“五年前的朱橘”之间的故事与之呼应。女性主人公遭遇生命巨变,需要重建生活的逻辑。再认识或确认自我,也意味着如何去处理过去的记忆。通过重新描述记忆,赋予曾经的生命经验新的位置、形式和秩序,由此重建自我,也是这个小说的方法。哲学家理查德·罗蒂曾谈及普鲁斯特的小说,按罗蒂的阐释,记忆的过程可被视作是一个由微小的、相互激荡的偶然性构成的网络。其中的无数细节充满偶然性,偶然性只有在回顾时才会有意义——每次重新描述,它们就会有不同的意义。这是小说里女性主人公不同阶段的大量生活细节被打捞的理由,那些生命中曾经的美妙、遗憾、憧憬、彷徨塑造“昔日之我”,但也可以在新的时间位置被重新理解。“昔日之我”之中可以生出“今日之我”。很难说记忆是人的本能行为,或许遗忘才是,需要不断回想,不断召唤,才能让消失的内容重现,亦或加深。
在小说《光进来的地方》中我也写过这样的状态,对于一个失去妻子的男性来说,“记忆不费吹灰之力可以轻易在我面前重现妻子的形象,一切栩栩如生,每一次都是她,每一次又全不相同。我拥有的素材有限,可我不惧怕重复利用,一次次像幻术一般召唤她到眼前,由此她从未远离,始终存在”。应该说,在更久之前,我就在小说里尝试去理解记忆的作用,到了《吃东西的女人》,它成为小说的方法。关于对丈夫过往记忆的重述,让她意识到平凡日常中的珍贵内容不可复现,也足以成为眷恋和热爱的明证,人类之爱的纽带并不因为死亡而轻易终结。构成文本自身的并非是情节,而恰恰是回忆这一过程本身。在小说,重述记忆帮“她”理解旧我,也铸造新我。女性主人公通过重新描述自己的世界而变成“真正的”自我,而这一种描述的成功与否,关系回忆的形式和生命真相的距离。它确实需要你所说的冷静直观的方式,它需要综合有意味的记忆、认识和顿悟为一种有价值的文学形式。
写作一定意义上也在寻找自己的精神同行者。由书写自己的经验开始,连接起更辽阔的世界和更深远的人心,同时也是理解这暗夜行路并非独自。我近几年的作品,从《在那天来临以前》《光进来的地方》到《鹳》,我反复重写、重现“丧失”的故事。到了《吃东西的女人》,告别丧痛与自新的故事汇流,对“丧失”展开的提问也似乎作出了阶段性的回答。去记得吃过的一次次饭,去认真地吃一次次饭,体会“味外之味”。去充分地生活,去亲身体验生命中的细节和滋味,承认它,接受它。不再担心丧失,在丧失中也可以完成创造:于沉睡的记忆中一次次打捞,去寻找“某种缝隙,不是已经完成的、等待我们记述的某种经验对象,而是悬而未决、有待完成的诸多可能性”,由此去完成创造,由此永不枯竭。
梁豪:现代意义上的中国女性主义小说由来已久,以至于形成了一定的传统。今天女性写女性,跟前辈作家们相较,共通的地方是什么,又有何差别?如今风行一时的林林总总的女性本位发言中,你认为哪些是可取的,是否有值得商榷的地方?
朱婧:《吃东西的女人》追踪的是记忆的能量和真相,尤其关于女性如何获得自己的语言,陈说自己的经验,形成自我意识,书写自身的历史。在小说里,一个野心勃勃的男性在年轻时曾深刻影响过当时更年轻的女性主人公,当女性主人公身陷“万物有托,余独无依”的处境,他试图利用旧日影响对她施以救济。然而当她足够成熟后,她能够理解她当时所渴望的并非这个男性本身,甚至她渴望的是成为那个男性,由此能够拥有他部分的野心与自由,这也是小说末尾所指:“她有了他的体态,他行路的姿态,高大阔步,孤星一人,但自由自在。” 当需要重塑生活时,昔日偶像并未对她发挥情感上的作用,却参与了她自我想象的构建。有多少女性能够理解自己年轻时对处于高位的男性的迷恋,或许来自对这些男性身上自己渴望得到、又恐怕不能得到之物的迷恋,比如好高骛远但心境自由,比如与扎根固守相反的灵活流动,比如更容易获得的前途机遇和更容易占据的权势资源。女性更容易由于各种原因,放弃对自由的追求和实现。这种选择常常是一种处境的产物,传统的社会结构使得女性在追求自由时所要付出的代价远远高出男性。
我的博士论文做的是现代都市及其催生的文化与文学。城市生活是我的日常,女性是我的身份,新兴的社会经济力量不断改写当下社会的经济格局和社会分层,我也试图通过阅读和写作理解消费社会的逻辑对不同阶层女性的生活和精神的影响。我从女性作家的作品中获得的影响和借鉴是必然的。早至张爱玲、萧红、丁玲等,到八十年代谌容、张洁、铁凝、王安忆等作家和九十年代陈染等人的“私人小说”,无不在以女性自身的写作回应着时代内容,诸多女性作家既在写具体的女性经验,也在更辽阔的时代书写女性的命运和现实,由此连续性的女性写作有可能形成女性文学的谱系和传统。我想这是女性写作的意义所在:帮助我们书写女性的经验,理解女性的处境;向俗规和特权寻求理解和平等,在写作的疆域彰显女性的天赋和能力,容许更多对女性敞开的变化和可能。女性写作,关乎一个女性如何观看、倾听和关注她身处的世界。二十年的写作中,我一直在写与自己生命等长的女性故事,或多或少,也是希望女性写作不要与作为女性的独特的经验分离,不要与爱、理想与信念分离。关于当下诸多女性议题,我所关心的也是我一再在小说中表达的,即如何处理观念与现实之间的冲突,和这种冲突下的现实。文学不是为观念所征用的工具,它存在正因为它有可能面对更具体的现实,联系更深远的历史,对未来作出预判和警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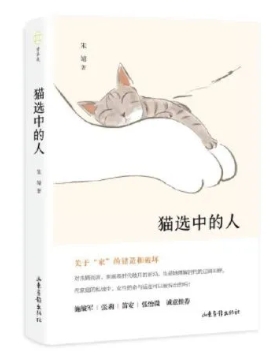
作者:朱婧
出版社:山东画报出版社
出版时间:2023年04月
梁豪:文学多少需要一点先知先觉的敏锐,一种混沌的试探,否则,只能气喘吁吁地追着某类观念、概念或议题跑,到头来还要遭受那些直击要害的社会学、政治学、经济学、民俗学、人类学甚至新闻报道的冷眼和嫌弃。所以,文学恐怕离不开或浓或淡的批判精神,它包括对批判之反思、之批判,所谓文学对社会的引领作用,回首历史、展望未来,是在这里而非别处迎来契机的。这是文学获得主体性的关键所在。其实,鸡生蛋也好,蛋生鸡也罢,关键在,鸡得是真鸡,蛋得是真蛋,而且我们有必要追问一句,“生”的意义究竟是什么?
下面这个更具体一点的问题,我想你会是一个理想的答复者:怎么看待自我的现实经验和想象性经验在创作中的关系,有大致的配比吗?
朱婧:我在大学承担写作课程的教学,我们每年开设“纪实与经验”工作坊,试图寻求有效的文学方法处理现实经验,这也是初写作者常需要面对的问题,工作坊的工作记录和作品也在中国作家网登载过。其中,被列为范本的是法国作家、批评家菲利普·福雷斯特的作品《永恒的孩子》和《然而》。这两部作品的缘起,皆因菲利普·福雷斯特真实的失女经历。福雷斯特把自己的写作归为自撰体小说,可以说是“我”的写作的回归。《永恒的孩子》主题是感人至深的哀悼,同时也从伦理学、美学和哲学维度进行思考。福雷斯特以文学的方式处理真实的经验材料,因为“小说还必须对自身进行反思,从而证明现实与虚构是紧密相连的,甚至是密不可分的”(《福雷斯特《薛定谔之猫》中文版序言》)。
取材记忆、联系现实和想象的写作者中,最无法忽略的自然是普鲁斯特。格非说普鲁斯特:“当他在回忆往事的时候,有如一个侦探,每一个细微的感觉,每一个晦暗不明的空间、片段和枝节,都会在黑暗中被无限地放大,感觉的触须异常地敏锐和纤细,探向每一个幽深的角度。”格非所强调的是普鲁斯特对于“非意愿记忆”发现的能力,也就是本雅明所说的“无意识的回忆”,它更接近于“遗忘”而不是“回忆”的内容。记忆是一种选择性行为,那些被忽略、遮蔽、省略的内容,并非不存在,而是尚在沉睡,而我们的观看、我们的写作能够帮助打捞那些沉睡之物。前面我谈到的《吃东西的女人》利用重述记忆再造自我,也是在沉睡的回忆中寻找自己新的命名物。在小说《鹳》中,我写过一次美术馆的观览:“在那个安静宽阔的展厅,她还在油画里看到老式缝纫机。缝纫机的踏板和轮轴都安静地停歇,不甚清晰的边缘有些黏腻感,好像能闻到机油的气味。”我们的观看对于我们意味着什么?按约翰·伯格在《观看之道》中的阐释,我们从不单单注视一件东西,我们总是在审读物我之间的关系。这段文字来自我在东京新国立美术馆观展的现实经验,画作中的缝纫机关系我儿时对于母亲的记忆。平常午后,居室一角,母亲踩踏着缝纫机,挪移着布料,我往往陪在一旁,有时昏昏欲睡,鼻息里有缝纫机机油和新鲜布料的气味。三十年后,我在美术馆的画作上看到那个下午和那时的母亲。
梁豪:对于创作,这其实是一个很“实操”的问题。我们常说一个写作者需要足够敏感或足够细腻,抛开语言技巧层面,其实是指他对于过往经历的一种捡拾能力。要看我们是否是一个有心人,能够唤醒甚至创造一段记忆,让我们看见那些无视之见。你对于缝纫机和母亲的那段讲述,提供了一个非常生动的例子。
朱婧:这样的母亲出现在我的散文《读中文系的人》、小说《一日与永恒》《那般良夜》里,“母亲”也是我关注“家庭中的女性”的写作起点。本雅明谈普鲁斯特时说,回忆是否“只不过是某个人自己生命当中那陈旧不堪、转瞬即逝、多愁善感而又孱弱的时光完整的展开”?但是他也同时肯定,“普鲁斯特在某个精彩段落里描述那几乎纯粹属于自己的时光,然而他所使用的手法却竟也能够使人人都可在自己的生命中发现这样的时光”。我确实也想由此去照亮母亲未被看见的时刻,去照亮我自身中断写作、隐入家庭、养育孩童的十年生活,也照亮更多“家庭中的女性”的“沉身的无光”。我写了《那般良夜》《光进来的地方》《我的太太变成了鼠妇》,以期冀“消失的”在复现的过程中愈加明晰,“无光的”打开人生的缝隙让光进来。文学的想象和现实经验的联结,需要作者发现合适的通道。
梁豪:你的本职是南师大文学院的一名老师,平时需要完成并不轻松的教学和科研任务。你认为在高校教写作、“拆解”文本,对自己虚构写作、整合文本,有什么样的影响?是促进作用更大,还是会对写作造成一定的祛魅,让动笔变得艰难?
朱婧:在大学写作,是我的职业和身份的现实,也关系我的来处。2019年1月,我写过一篇散文《读中文系的人》,文题取自林文月先生同名散文,回顾自少年起受父亲和老师的影响,到后来成为中文系教师的经历。文章中回忆:“少年时期的文学生活,那些读中文系的人领我走过的路,像行进的火车的车窗外的风景,闪过少年的我的眼前,我可能睡着,可能遗忘,可能彼时无法完全理解,但事实上,那些风景永远不曾熄灭,它们像接连点燃的火柴,微光连续起幽暗中亦明的路,指向我走到这里。”2008年,我回到母校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做了一名大学老师。2019年2月,我赴东京访学,感林文月先生京都访学在她学术生涯的转折性意味,4月写成论文《越境者的文学景观——观察台湾作家林文月的一个角度》,梳理林文月先生个人写作史的衍变,这之后,起意以林文月先生的经历写作小说。2020年1月,短篇小说《先生,先生》发表于《花城》杂志,以“宁先生”致敬林先生。小说写中文系的薪火相传,以“维护传统古典于不坠不灭”。2023年4月,小说家张怡微为我的小说集《猫选中的人》所写的评论,曾经探觅这两篇不同文体的写作之间的隐秘。诚如张怡微所说:“‘读中文系的人’,甚至不是一项心知肚明的职业精神,也不是投入诸多热情的业余爱好,而是一种高度理想化的信念。”我也相信,如果没有一定的认同,很难给出如此的理解。
现代以来,大学是一个相对自由的、适合写作的地方。在学院写作,特别是教文学课程的作家,日常往往需要研习各个时代不同地方写作同行的作品,对个人的写作可能会构成一个参照的维度。同样,在遴选作家作品的过程中,也可能返身观照不同时代作家的写作。如此前一再谈及,我这几年的小说集中注意“家庭中的女性”,大学的教学与研究会让我去思考和发现通向这个母题的道路。我从19世纪英国诗人考文垂·帕特莫尔的长篇抒情诗《房间里的天使》和伍尔夫《给女性的职业》,梳理“家中天使”的形象,勘查这一类维多利亚时期理想女性,如何在后续的文学作品包括A·S·拜厄特的《占有》《婚姻天使》等和其他理论著作中一再出现,为自己的创作寻找文学谱系上的呼应,也由此对一种写作的价值意义建立确信。

作者:朱婧
出版社:译林出版社
出版时间:2019年10月
梁豪:稍稍有心的读者不难发现,你的作品中遍布着你刚才提及的那些痕迹或脉络。它们构成了你写作的“前文本”。广义地说,我们写下的所有文字,无一例外都有一个巨大的“前文本”。有的是走过的路,有的是看过的书,而书山亦有路,最终彼此交会,踏作心灵的旅程。它们在你身上奏效了,这是彼此认同和贴近的结果。
朱婧:对我来说,做学术研究和文学创作时需要切换相应的频道,在规定的时间内集中、有效、节制地调整思维状态和语言状态。研究工作和创作工作的结合,成为一种必要的工作方法。这几年,我关注女性写作,既进行相关文学创作,也做一定的研究工作,这些工作之间也能互相呼应。往往是因为所关注和思考的内容不能完全以一种工作的形式囊括,继而在另一种文体的写作中,寻找“可能和意外”。我前面讲到的,从林文月的学术研究到以此为起点的小说创作是为一例。同样,因为关注明清时期特定阶层的女性结社和创作活动,我写作了关于明末清初女词人徐灿的研究性随笔,又以此为基础创作小说,此为另一例。
梁豪:有时候,命运的陨石会主动撞向我们既定的人生轨道,让我们这些进行文学创作的人在疲于应对中,同时找到全新的思维和言说的突破口。对此,我们只能静观其变。而如果这一切没有发生,谢天谢地,我们大可把自己的日子和思绪捋得更顺畅、整饬一点。
而在太阳每天都照常升起的今天,很多人谈及从事文学创作时,纷纷抱怨地快被圈完了,题材不好找,从故事内容到叙述手段都容易雷同,另辟蹊径谈何容易。也因此,我欣赏你从日常生活中提取题材的方式和方法。你如何看待小说的题材问题,会有这方面或别的创作焦虑吗?
朱婧:小说的题材问题,具体关系到如何理解题材的价值和如何理解写作者和所选题材之间的关系。就比如说我们前面说到福雷斯特试图通过文学寻找关于“哀悼”的回应,对自己遭遇的现实问题予以解答。写作由私人事件起,却抵至深远。也比如说,在女性写作的历史上,无论采用日记体的日本王朝女性文学或是简·奥汀斯的“起居室文学”,将女性的日常变成艺术题材,也可以逐渐修正现存的价值秩序,改变关于写作内容“重要”与“不重要”的定义。包括我自己写作聚焦的“家庭中的女性”,如前所述,自然是因为这种“日常”和处于“日常”中的人,是我富于感情的对象,也是我文学上的选择。
格非在《志贺直哉及其“自我肯定”之路》中谈及“什么是文学的政治”,他认为志贺直哉在文学的社会性问题上遭人诟病,是因为他并不直接记述或复现社会政治和现实,而是首先将这种社会、政治内容转化为某种作用于个人意识的“情绪”或“心境”,从而通过呈现这种“情绪”和“心境”,来表达自己的政治意见、立场以及对社会的看法。他也提出由于互联网时代的信息爆炸,作家们获取写作材料的途径已经变得十分便捷。这为写作者完全无视自己内心的声音和深邃的情感,排除内心深处的挣扎、不安和痛苦,致力于描写对象的“客观化”提供了可能。由此,大量采用“取用”的现实,而失去“内心的实景”的危险被提出。如此,比起积极获取更“巨大”或者更“丰富”的题材,我的理解是,对于写作者来说,题材也是一种面对内心实景的选择。
刚刚也讲到过,高校教师的身份,教学科研和写作并行,也意味着存在这样一种丰富的文学资源,我可能从我的研究对象中寻找能激发创作动力的题材和启发创作方法的路径。
梁豪:女人的相对面是男人,文人或说知识分子的相对面是所谓普罗大众。你认为当我们在进行写作抑或思考时,是要进一步廓清前后者的差异和分水岭,还是试图在彼此间架起沟通、理解乃至融合的桥梁?
朱婧:一个写作者不一定预先有了明确的站队,比如男人/女人、知识分子/普罗大众,才开始写作,而且文学本身更关心的是“相对面”的晦暗不明的地方。也许可以直接说,我写作更关心的是从我自身出发的体感和处境,它可能包括你说的差异和分水岭,也可能包括你说的沟通,但所有都是在写作完成之后文本的显形。这种显形涉及到写作者的表达,也关系到读者的阅读体验。

记者简介:梁豪《人民文学》杂志编辑,青年作家。北师大文学硕士。著有小说集《鸭子飞了》《人间》。
点击“阅读原文”,阅读朱婧《吃东西的女人》(发表于《人民文学》2023年第9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