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字,比我们走的路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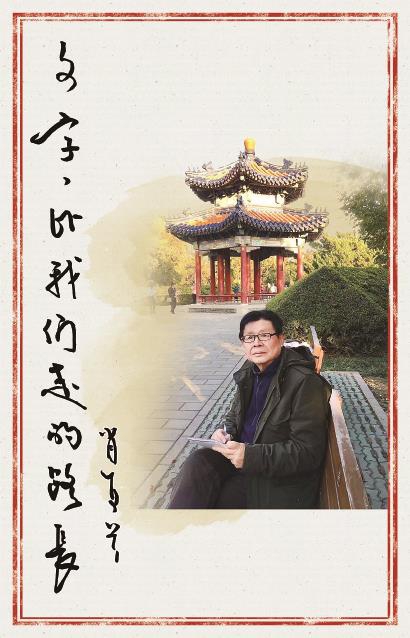
肖复兴,著名作家,1982年毕业于中央戏剧学院,先后任《小说选刊》副主编、《人民文学》杂志副主编、北京市写作学会会长、中国散文学会副会长等,著作百余部,曾获“中国好书”奖、冰心散文奖、老舍散文奖等多种奖项。
身为“京味作家”的一员,肖复兴的文学创作自是扎根于北京与北京文化之中的。
而他笔下洋洋洒洒的文字,则带领着他不断抵达远方。那个远方,是在琐碎日常中构建的文学的诗意、生命的诗意、时间的诗意。
写有情感、有故事的北京
周末周刊:“从某种程度而言,地理或说地域性,是书写城市的坐标,是一部作品中另一位不说话却同样风情万种的主角。”北京这座古老城市是如何成为“京味作家”肖复兴笔下的主角的?
肖复兴:大概20年前,我开始了对北京的书写。我从小在北京长大,21岁去北大荒,27岁回北京。北京,尤其是北京城南、前门一带、前门西侧老街,以及老街上我曾经住过的老院粤东会馆,我对它们非常熟悉。
2003年的一个冬日,我到人民大会堂开会。散会很早,我心想,过了马路就是以前住的老街老院,就回去了一趟。走进老街,看见墙上的拆迁布告,心里一惊。那天,我从老街走到以前住过的老院,很多看着我长大的街坊都还在,那里的一切都还那么熟悉。
周末周刊:那里的一切都还那么熟悉,那里的一切都将改变。
肖复兴:我心想,幸亏自己来了,要是再晚一点儿,恐怕就看不到老街老院了。我为什么不写写这里呢?这里有我成长的记忆,这些记忆是活生生的,是和北京这座古老城市的历史联系在一起的。从那时起,我开始写北京,也真正意识到老北京和我的生活、写作之间的关系。
因此,我有意识地去了解老街老院,并由此蔓延到北京城南的很多地方。没事我就到那里去。“这小子又来了。”不管认识我还是不认识我,那里的街坊给了我非常大的帮助,让我知道了许多以前不了解的事情,对那里曾经自以为非常熟悉的一切有了新的体认。
周末周刊:旧景往事扑面而来,又在您时隔多年后的寻访中形成了新的样貌?
肖复兴:开始时也没想得那么周全,随着跟他们聊天的次数增多,我对这地方的感情越来越深,越来越觉得自己在这里生活了20多年,其实有很多事情是不知道的。我应当从头开始认识这个地方,向那些知道的人虚心请教,这样才能把东西写深。大家的经历丰富了我,大家的智慧帮助了我,我才能把书写得更丰富。
有一次去杨公祠,大门封了,我走旁门进去,碰到了一个老爷子。我问他,前面应该是大殿,我能不能去看看?他说那里现在是私人住宅,就是他家。我一路走一路问他,能不能找到老街坊问问这里的历史变迁。他看我对这里有兴趣,就邀请我到他家去。他家的门敞着呢,一个老太太正做着肉皮冻,我就进去了。他很详细地给我介绍了这里整个的变迁历史。他说后边原来是花园,现在花园没了,但原来的树还在,八角亭、石碑还都在……寻访路上我碰到很多人,我和他们素不相识,但他们愿意跟我聊,我才有信心写出来。
周末周刊:于是,有了《蓝调城南》《我们的老院》《咫尺天涯:最后的老北京》这一系列关于老北京的书写。
肖复兴:这是我最早写的有关老北京的三部书。写北京的作家很多,各种门类的写作都有。而我写北京的侧重点是城南,就这一亩三分地,绝不蔓延。我一定要写我熟悉的;我一定要写有情感、有故事的北京,一定要写人物,而不是单纯地写地理。有了人物,就有了命运的跌宕,笔下的城市就是有情感、有故事、有温度的。同时也要有我自己的经历,不能抛开“我”来写。这些人物要跟我有交织,我才能写出互动,让读者读来觉得亲切可信。

肖复兴写生作品
过去的水和今天的水融合在一起
周末周刊:那些老街坊读过您写北京城南的作品吗?
肖复兴:他们一看都知道里面写的是谁,尽管我已经进行虚化处理。对我来说,写作的内容有真实的存在才有底气。
周末周刊:那些您曾经或者正在经历的“真实”,变成文字后与您再度相逢的时候,让您产生哪些新的感悟?
肖复兴:写作的过程,实际上是对这种生活赋予了一种文学的生命或者别的什么东西。在这个文学的重新塑造过程中,你在不停地回忆,不停地认知自己、认知别人、认知时代。而这个认知的过程,也是不断反思的过程。
过去的东西还要有作用于今天,才能体现出它独特的价值。让读者感觉“虽然你叙述的是过去的故事,但对我的今天依然有新鲜的意义”,我希望能够写出这样的东西。
周末周刊:确实,您的文学主题常常与记忆相关,但您的书写并不停留于过去,而是走进当下的时光,面对今天的读者。
肖复兴:写作,从本质上来讲就是写记忆。记忆不全是陈旧的,是经作家在当下咀嚼与构造之后用文字重新塑造的。这样的文字是经过作家生命和时间双重提炼的,所以才能成为文学作品。否则的话,它就是另一种形式的老照片。
我觉得,写过去,是要写过去对于今天的意义,写过去和今天的感情融合在一起,如同过去的水和今天的水能融合在一起。
周末周刊:您写下北京的城市记忆,想要留下的是对今天的城市更新、城市发展有意义的东西。
肖复兴:发展是必须的。今天的北京跟过去的不一样,就是因为发展。我的写作中,希望看到城市的发展。我写过一篇文章《洋桥记事》,写城市的建设带来巨大的变化。20世纪七八十年代,我在洋桥住了好几年,房子四周都是农田。当年铁道兵修建北京地铁之后,复员留在北京安家立业,就在洋桥那里的农田里建了一片红砖平房。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洋桥那片地铁宿舍陆续拆掉了,那里建起了高楼大厦,变成了应有尽有的新型社区。
但另一个方面,一座古老的城市在发展的过程中,还不可避免地面临着如何保护的问题。建设中不可能不拆掉一些东西,不可能所有东西都保留下来,如何保护、如何发展,这是城市建设的伦理。
周末周刊:《咫尺天涯:最后的老北京》中收录了36幅您手绘的插图,图中的不少景象如今已被湮没在了历史长河中。
肖复兴:新生事物可以持续地蓬勃生长,而旧物不可再生。那些历史遗留下来的老建筑、街道、物件,是宝贵的活化石,把它们保护起来,城市的文化才能更好地积淀下来,对后人有所启示。
时代在发展,北京在前进,老北京的胡同和四合院变得越来越老旧。但它们不因苍老沧桑而变得没有意义。相反,它们更有意义了,因为它们是北京这座古城历史文化的载体,承载着人们的记忆。因此,城市的发展不能唯“新”是举,保护和建设具有同等的价值和意义。特别是,像我所记录的那些老街老院,它们是和我们的生命、情感和记忆紧密联系在一起的。走进那些大街小巷,遥远的记忆一下子被激活,历史与当下迅速产生连接,让我们对这座城市产生最真实亲切的情感。
保持写作活力的有效方式
周末周刊:地域文化与文学创作之间的关系,说到底还是一个写作者身份认同、精神认同的问题。北京的城市文化为您的京味文学创作提供了怎样的文化滋养?
肖复兴:土耳其诗人希克梅特说过一句话,让我印象深刻:“人一生中有两样东西是永远不能忘却的,这就是母亲的面孔和城市的面貌。”认同这座城市和认同母亲同样重要而不可分割,这应该就是你们所说的写作者身份与精神的认同。你走在这座城市里,无论看到变化的,还是想到以往的,那情感就和在别处不一样。
有一次,我读到李健吾先生写老北京的文章,其中写道:“繁华平广的前门大街就从正阳门开始,笔直向南,好像通到中国的心脏。”让我很震撼。我曾经无数次走过前门大街,没有一次有过这样通向中国心脏的感觉。我问自己,为什么?这里就有你对北京历史与文化的了解、认知和感情到底有多少的问题。只有真正深入地去了解——当然不是只从典籍里,还要从具体的生活中去了解体认,才会发现北京这座古都的博大精深。它能够给予我们的文化滋养是极其丰富的,而我写的只是浅浅的一洼水而已。
周末周刊:文学中的地域性,以其鲜明的历史和地理特色而独具风格与价值。在全球化的时代,这样的文学创作会走向何方?
肖复兴:我始终认为,在全球化背景下文学的地域性应该加强,如此才会让本土的文学创作更具自己的特色。文学创作不能一味怀旧,也不能一味趋新。就像写芝加哥的索尔·贝娄,写伊斯坦布尔的帕慕克,他们的写作都不曾淡化自己的地域性特点。
假如缺失了地域文化,城市会千人一面,与之相关的文学书写空间会越来越拘谨。例如,没有了地域性,京味文学便没有了书写的背景和空间,其文化历史的血液便无法在作品中流淌,人物便容易成为空心人。我相信地域性文学创作的发展前景应该是广阔的。
周末周刊:因此,您对北京的书写总是落脚在人的生活上。比如,您写《天坛六十记》,记录的是“如水如云一般来来往往于天坛的寻常百姓庸常的生活点滴,普通人生平凡的际遇投影”。
肖复兴:是的,《天坛六十记》并不是一本介绍天坛历史或天坛风景之书,而是记录我在天坛所见所闻所画所遇所思的点滴,是一个个生动的人物。
周末周刊:这里的天坛成为一个载体,承载着您与他者、与城市的相遇和交流。
肖复兴:我家原来离天坛很近,坐几站公交车就到了。我那时候喜欢画画,每次我坐在那儿写生,旁边都会围着好几个人看,慢慢地,我就跟他们聊起来了,他们讲的好多事我不知道。我觉得如果把他们写出来应该挺有意思的,那是我不熟悉的生活,是老百姓最真实的生活。
周末周刊:就像您在《画为媒》一文中所写的:“到天坛写生,不仅为了画画,还可以接触好多人,随手记下各色人等的人生百态与百味。”这种“萍水相逢”,为您的文学创作带来了丰富性与活力。
肖复兴:我觉得画活物和人的速写最有意思,就像农民到地头收割农作物,颇有成就感,还可以捎带认识很多人,知道很多事,扩展自己的写作视野。这也是我让自己保持写作活力的一种有效方式吧。
萍水相逢,所以丰富多彩。有一次,我看见一个老太太坐在那儿打盹,我就画她,画完,给她看。她看了,说了句,我也会画。我赶快拿出笔,说您给我画一幅。她给我画了一朵牡丹花、几片叶子,我真没想到,她画得那么好。
前天,我也上了天坛,遇见一个老爷子,他跟我讲了个故事。他会中医按摩、针灸。他老岳母80岁的时候,得了病,身上疼,他就每天给老岳母按摩两个小时,整整坚持了9个月,把老岳母的病治好了。我心里挺佩服这样的故事,佩服他的坚持。
在天坛,我观察各式各样的人,他们跟我碰撞、跟我交流,给我很多信任和温暖,而他们的生活是我所不熟悉的。如果我没有到生活的现场,就不会遇见这样的人、这样的故事,就不会一再地感受到普通人生活中的不平凡。
得跟烙饼似的翻几翻
周末周刊:在生活的现场,捕捉萍水相逢者的故事。一个作家如何练就观察生活、将寻常生活写出诗意的能力?
肖复兴:孙犁先生说过:“最好多写人不经心的小事,避去人所共知的大事。”对此,我很赞同。我的散文,就是希望写一些小事,而且这些小事是我们每个人都能经历的。
我一直喜欢散文。读中学时,我喜欢冰心、萧红、韩少华和何为的散文。年老之后,我喜欢孙犁、沈从文和汪曾祺的。这些作家的散文有共同的特点,都是书写普通生活,并从日常中写出一点温暖的诗意,让我的心微微一动。
生活里总有这样那样的不如意,甚至坎坷与痛苦,但生活里也有诗意的闪烁。特别是苦难中的诗意,使得我们面对生活时多了一份勇气、信心和韧性。这是我们中国人朴素可贵的性格,也是散文最值得珍视的品格。
周末周刊:对小事的书写,亦可抵达文本“最值得珍视的品格”。
肖复兴:普通人不会经历许多的大波大澜,经历的多是小事、小涟漪,许多的点滴恰恰构成了我们人生的几乎全部。我们珍惜这些小事,就等于珍惜自己的人生。
所以,我重视的就是这些小事,如何把这些小事写好,让读者动情动意,这是作家的本事。日本导演是枝裕和特别擅长在琐碎的日常中构建电影,在寻常时光中流淌出真实的生活质感。生活中哪有许多惊心动魄的大事?都是婆婆妈妈的小事。他的电影《如父如子》《步履不停》等,哪个不是这样的事?他有一本书,书名就叫“还是得活在日常里啊”。
我写作,就是要“死磕”这些琐碎的小事、别人不经心的小事,把它挖掘出来。因为,失去了琐碎的小事、失去了日常,写作往往会大而无当,没有血肉,无法打动读者。所以我努力把有味道的日常小事挖掘出来,以求赢得更多的共鸣。
周末周刊:作家与读者都是生活在日常里的,作家用自己的“有心”捕捉的那些“失去”的日常,恰恰可以令读者“心有戚戚焉”。
肖复兴:但是,捕捉到了这些琐碎的日常,你千万不要轻易地去写它。你还要在心里头掂量掂量,得跟烙饼似的翻几翻,你才能把它烙熟。今天遇到一个事,得想一阵子,在脑子里弄清它的脉络,再去考虑怎么写。现在,有些散文写作太随意。
周末周刊:一旦对琐碎的日常留意起来,便会发现各种各样的小事太多了,就要面对取舍的问题,您取舍的标准是什么?
肖复兴:选择的主要标准就是,它哪一点打动我。我觉得和陌生人的这种交往最能打动我,萍水相逢的人最容易敞开心扉。在《童老师》这篇文章中,我写了我在天坛遇到的“北漂”童老师。他是退休后跟随子女来到北京的。他和我说,在老家当老师的时候,很多人认识他,而到北京后,不得不接受没什么朋友的心理落差。那天,他和我告别转身而去的时候,我唤了他一声“童老师”,这让他回头一愣。这一愣,就是打动我的点。
苏联作家巴乌斯托夫斯基说:“对我们周围一切的诗意理解,是童年时代给予我们的最伟大的馈赠。如果一个人在悠长而严肃的岁月中,没有失去这种馈赠,那他就有可能是位诗人或作家。”我始终谨记这话。
好的文字应该是一种梦
周末周刊:2024年,您的儿童文学作品《风啊吹向我们》出版,这部作品聚焦了少年友情对于成长的意义这一命题,书中人物的原型同样来自您自己的生活。
肖复兴:这本书是写我初一那年的生活。那时,我在学校里并不显眼,很容易被淹没。在茫然无措的时候,我遇到了第一个朋友,他对我的鼓励很重要。书中的小秋是两个人物的结合,其中一个就是他。他喜欢看书,借给我一本《千家诗》,线装的,我印象特别深。他让我开阔了眼界,原来世界上还有好多我不知道的书。
另一个人物原型是我初三时认识的我们学校高三的一名学生,我在学校“百花园地”上读到他的专栏,写的是童年的故事,特别吸引我。他还在《北京文学》发表过一篇散文,是我们学校唯一在刊物上发表文学作品的,那是了不起的。这两个人给予我的友情非常纯真、非常美好。我想到他们,就想写这本书。
周末周刊:这本书中的人物都与您密切相关,正如您说的,“重叠着我自己生活中的浓重影子”。
肖复兴:我把童年和少年时代最美好的回忆、最富有诗意的想象、最充满憧憬的寄托,都写进这本《风啊吹向我们》里了。时隔多年,书写这段恰同学少年的经历,需要的不仅是昔日人物情景的重现,更是细节的丰盈、想象的弥合、对远逝时光的唤醒、诗意的理解,以及可以与今天的现实生活产生关联的新鲜认知。更需要一提的是,如果我没有碰到这两位同学,那我的成长就是另外一条道路,就不可能走上文学道路。
周末周刊:走上文学道路,您一走几十年。
肖复兴:我从小喜欢文学,这跟半路喜欢文学这个感情还是不一样的吧?一辈子相伴,所以它就离不开你,你也离不开它,它成为你生命的一部分。
我有时会想,如果有一天写作一分钱稿费都没有,我还写不写作?我还是会写。我就想起我最初写作的时候,在北大荒,一个冬天写了10篇散文,给谁看?没有人。那为什么还愿意写?因为文学让我的精神有了一种寄托,感情有了一个存放或者抒发的地方,成为我生命的一部分,它所起到的作用是任何其他东西都取代不了的。亲情、爱情、友情很重要,但它们也取代不了文学,而这三种感情,我通过文学都可以表现它们,这是文学最独特的地方。
周末周刊:那是1971年北大荒的冬天吧?2023年,您的《燕都百记》获花地文学榜“年度散文”时,您的获奖感言是:那个温暖的冬天支持我走到现在。
肖复兴:是的,那年我在北大荒的生产队里喂猪,大雪封门,我就陆续写了10篇散文,身边没有人看,也不知要往何处寄。思前想后,我挑选出一篇寄给了叶圣陶先生的长子叶至善。他帮我修改了文章,并在信里说,如果还有别的文章也可以寄给他。于是,我又把另外的9篇文章都寄给了他,他又陆续修改后寄还给我。他都是逐字逐句地进行修改,其中有一篇,因为改动多,他还重新抄写了一遍。大约在1972年春天,我将其中的一篇《照相》寄了出去,发表在新复刊的《北方文学》上,我最初的文学创作就是这么开始的。对于当时的我来说,那是非常珍贵的帮助与鼓励,所以那个冬天特别温暖。
周末周刊:您如何理解文学对于生命的意义?
肖复兴:在我的生命历程中,我对万事万物的美感、善感和敏感,都是文学艺术给予的。我觉得,美感、善感和敏感就是文学对于人的作用。它让人的情感更丰富更细腻,对美好事物的感知更敏锐更深刻。人不可能一辈子都顺利,总会遇到挫折,而文学可以为我们提供另一种生命通道,就像逃生通道那样为我们排解些许情感或情绪上的问题。
周末周刊:在互联网时代,一方面写作可以无所不在,另一方面文学却日渐寂寞,身处其间,真正的作家该如何选择与坚守?
肖复兴:商业浪潮汹涌,文学确实受到了冲击。同时,网络又使得写作尤其是散文写作失去了门槛,十分泛滥。我曾经打比方说,这让散文这种本来温润的文体,粗糙如同搓脚石,随便可以搓出一脚泥来。写作过于轻松,就难免像口香糖一般被随意咀嚼和吐掉。而好的文字应该是一种梦。它是心灵的外化,是精神的一种追求,它比我们自己走的路长、抵达的地方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