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诗辩护:菲利普·锡德尼的人生和诗学》|行动者和沉思者的双重人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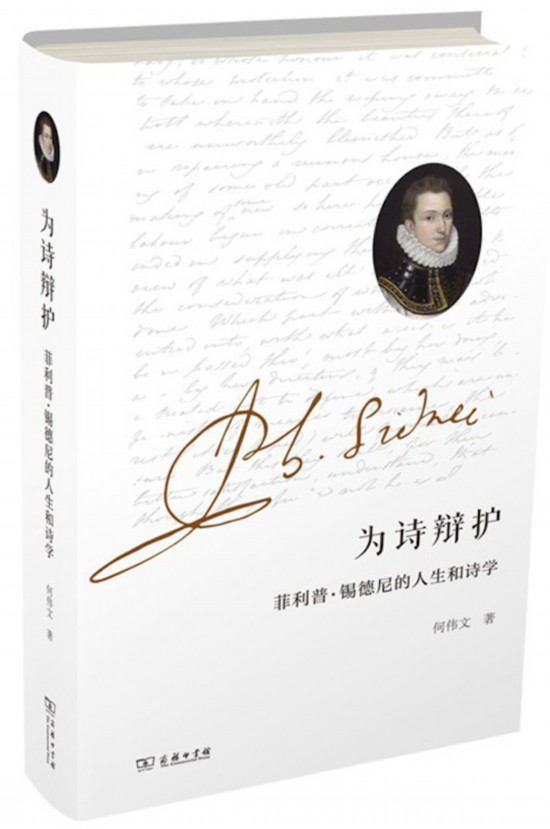
柏拉图在《理想国》中放逐诗人,把诗人驱赶出治理良好的城邦,因为“诗人的创作是和心灵的低贱部分打交道的”,诗人“像所有其他的摹仿者一样,和真实隔着两层”。在柏拉图看来,诗歌通过挑动情感,制造出一种在实际生活中通往这些情感的危险途径,进而毒害人的灵魂。面对柏拉图对诗歌的攻击,亚里士多德从真实、情感、道德等方面为诗歌辩护。在此之后,西方关于诗歌和艺术的思想史中形成了一个绵延千载的为诗辩护的传统。从中世纪的但丁、薄伽丘直至当代的艾丽丝·默多克、雅克·德里达等,为诗歌辩护者大有人在。
在十六世纪伊丽莎白时代的英国,菲利普·锡德尼的《为诗辩护》(A Defense of Poetry)就诞生于这样一个传统之中。面对清教徒从历史和道德角度对诗歌发起的攻击,锡德尼构建了一种集行动者和沉思者的使命于一体的新教诗学与之交锋,他本人也因为这部书在后世被视为“当之无愧的英国文学批评之父”。为何西方会有连绵不绝的为诗辩护的传统?如何理解锡德尼的诗学观念,它又如何与政治、社会互动?
为了更好地回答这个问题,或许我们需要稍稍离题。在思想史领域,长久以来存在关于“语境”(context)的争议,学者在讨论问题时多有偏重“内在理路”或“外部环境”的两种进路。前者拥抱哲学立场的内在整体性,注重思想本身的发展和逻辑演绎,后者阐明观念在特定历史脉络里在政治、社会和经济上如何被运用,以及这些观念如何显现于当事人所处的“语境”中。“观念史”(the history of ideas)取向的学者认为观念有脱离其历史脉络的自主性,抗拒社会史家化约论乃至于决定论的野心,甚或讥讽其对复杂问题的解释为“没有思想的思想史”。具体到对诗学的研究上,也存在类似的方法论框架问题。
何伟文在近作《为诗辩护:菲利普·锡德尼的人生和诗学》(以下简称《人生和诗学》)中,采用一种以关注研究对象整体性特质为核心内容的动态文化研究方法(Kulturgeschichte),避免纯粹的哲学阐释,独取观念的内在开展,也避免将诗学观念的变迁视为外在社会环境的产物。何伟文以锡德尼的文学批评文本和书信集为核心,分析锡德尼诗学与他那被赋予太多含义的人生之间的内在联系,并从中窥见诗学与政治、宗教的互动。《人生和诗学》中锡德尼诗学的“语境”是他那短暂而非凡的人生,只有了解了锡德尼的人生,方能在历史脉络中理解他的实用主义诗学。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何伟文为锡德尼撰写的是一部思想传记(intellectual biography)。何伟文认为,锡德尼不止是以文学批评家,更是以政治家、廷臣等多重身份来写作《为诗辩护》,他的目的既是为了解决诗学问题,也是为了解决社会和政治变革、宗教改革、人的塑造等多方面的问题。
《人生和诗学》始于锡德尼之生。锡德尼出生于显赫的贵族家庭,他的出生注定了他以成为廷臣为人生旨归。他自幼接受典型的贵族青年教育,在家中读书开蒙,年岁稍长后进入以人文主义教育和拉丁语见长的什鲁斯伯里文法学校。1566年夏天,十二岁的锡德尼亲历了人生中的第一次重大事件。那年他拜访位高权重的舅舅莱斯特伯爵,随他一起参加为迎接伊丽莎白女王到访牛津而举行的庆典活动。通过这一事件,涉世未深的少年已然对权力和地位有了刻骨铭心的记忆和全新的认知。一年之后,锡德尼进入牛津大学基督教堂学院,几年之后,像其他贵族子弟一样,未获学位即离开。
赴欧陆游学是锡德尼为成为伊丽莎白宫廷的廷臣所做的最后准备,他的父亲深信,“只有在为君主和国家的无私服务中,一个人才能找到值得他全身心投入的目标”。1572年,锡德尼在巴黎亲历了惨绝人寰的圣巴托罗缪之夜。在这年的圣巴托罗缪日,法国国王的妹妹玛格丽特公主和信奉新教的国王亨利即将举行婚礼,胡格诺派的重要人物因此云集巴黎。婚礼前夕,天主教贵族领袖吉斯的亨利派人刺杀了胡格诺派在巴黎的领袖——信奉加尔文教的科利尼,暴乱和屠杀随之而起。1572年8月23日到24日,数以千计的新教徒在巴黎街头或是屋内惨遭杀戮。在这场天主教徒对新教徒的攻击中,胡格诺派贵族被悉数屠杀殆尽。身为皇家贵宾的锡德尼在屠杀开始时住在卢浮宫或附近,8月24日作为高级别外国使团的成员被带往惨案始发现场视察,亲眼看见了科利尼被亵渎凌辱的尸体,随后被送到位于左岸的使团驻地。这一事件强烈刺激了锡德尼,使他强化了新教思想,并确信国际政治斗争就是反抗罗马教皇及其捍卫者西班牙国王的斗争,为后来的新教诗学埋下了伏笔。
回到英国后,锡德尼如愿进入伊丽莎白女王的宫廷,一开始还算顺利,第二年就被提升为女王的尝酒侍者。然而,锡德尼很快就发现他所属的莱斯特伯爵集团新教阵营及他个人的政治立场与女王截然不同。莱斯特伯爵和锡德尼热切参与反抗西班牙的积极外交,主张推进新教事业,而女王则采取一种迂回拖延的策略,以平衡欧洲大陆各方势力。如果说女王代表政治现实主义,那么莱斯特伯爵集团则代表理想主义。与女王迥异的政见,使得锡德尼在宫廷中前途渺茫,政治抱负化为泡影。在十六世纪中后期,无论是骑士还是绅士,抑或是廷臣,他们都有一个共同之处,那就是崇尚行动生活(vita activa),而不是沉思生活(vita contemplativa)。锡德尼壮志难酬,不得不“迈入诗人的行列”,被动选择行动者和沉思者的双重人生,以诗歌实现行动者未尽的事业。何伟文指出,锡德尼写作《为诗辩护》,很大程度上也是面对自身内部那个怀疑诗人的自我。
《人生和诗学》用一章的篇幅阐述锡德尼《为诗辩护》如何为诗歌谋得一席之地,而不再是神学的婢女。锡德尼《为诗辩护》采用文艺复兴时期讨论文学的常见格套,分为七个部分:绪言、叙述、命题、划分、论证、申诉、结语。在申诉之后有一个长篇离题的部分,采用“演说中的演说”形式讨论英国诗歌的现状。在《为诗辩护》中,锡德尼将诗学与哲学、历史学等学科进行比较,并让诗学在竞赛中胜出。锡德尼认为,诗人超越哲学家之处在于,他有能力通过教育和愉悦来激活和引导读者的意志。诗人超越历史学家之处在于,诗性虚构是一种比历史真实更可靠的求知途径。正如亚里士多德《诗学》中所论,“诗倾向于表现带普遍性的事,而历史却倾向于记载具体事件”,锡德尼承袭了亚氏呈现可然性知识(probable knowledge)的理论,指出诗人在诗歌中提供了一个关于真实的虚构世界,用来揭示人生活于其中的那个有限世界的真正秩序,并赋予诗人君主的地位。
《人生和诗学》其后的三章选取“诗人的神性”“有声画”和“无艺之艺”等核心概念阐释锡德尼的诗学。在“诗人的神性”概念中,锡德尼通过创造性地吸收亚里士多德传统和柏拉图传统的相关元素,并融入基督教精神和时代新思想等,来强调诗人的主体性。柏拉图认为诗歌是神赋迷狂作用的结果,诗人仅仅被当作“容器”。锡德尼以新教徒的身份从艺术创作过程和艺术理念两个方面,把诗人的创造与上帝的神性并列,强调其创造性价值,重塑其尊严和地位,从而达到为诗正名的目的。《为诗辩护》中“有声画”概念与十六世纪后半叶诗学理论的变革密切相关。诗歌原来被视作一种有韵律的语言,以其音律、韵律等回应并展现超验美的和谐比例,而在当时主要被看成一种描绘性艺术,摹仿行动中的人。在十六世纪,思想像画面一样可以被看见这一认识已被普遍接受。诗歌在脑海中产生的画面“打动和透入人们的灵魂”“占据其心目”,能够对人的心灵产生一种类似于宗教的作用,诗歌的美学功能因之与社会和政治功能联系在一起。
“无艺之艺”与伊丽莎白宫廷现实政治的关系更为密切,呈现出锡德尼诗学实用主义的面向。在《人生和诗学》中被译作“无艺之艺”的意大利词sprezzatura出自十六世纪风靡一时的《廷臣论》(The Book of the Courtier)。锡德尼在《为诗辩护》中所推崇的“无艺之艺”艺术风格源于当时廷臣的行事姿态。在十六世纪宫廷,廷臣竞相向君主献媚邀宠,而宫廷对礼貌文雅又有着很高的要求,这迫使廷臣潜藏蛰伏。由于这个缘故,宫廷文化看重寡言少语、不动声色、轻描淡写等品质。“无艺之艺”即把自己真正的渴求与计划隐藏在无动于衷的面具下进行欺骗的能力。反映在艺术风格上,彼时英国盛行的极端西塞罗主义使得作者竞相摹仿矫饰的文风,炫耀性地展示技艺,而锡德尼暗示技艺要行之有效,就应该被隐藏起来。他主张自然地表达其主体意识和情感,“自己还不知道”做得“合乎艺术技巧”才是“无艺之艺”的核心含义。锡德尼认识到英国文学呈现萧条景象的核心症结之所在及其医治良方,在西塞罗主义之争中表达诗人主体性的重要性。他从艺术风格切入,谋求本国文学的独立发展之道,最终开启了英国文学的黄金时代。
《人生和诗学》以锡德尼之死终结全书。在人生的最后两年,锡德尼得以获得机会,重新投身于服务国家的行动生活之中。当时英国援助低地国家,领导一个松散的新教联盟抗击西班牙,锡德尼被任命为荷兰海岸线上军事要塞弗拉辛的总督。1586年9月22日,在荷兰扎特芬,锡德尼在率兵与西班牙士兵交战的过程中身负致命重伤,两周后伤势恶化、不治身亡。锡德尼去世后,伊丽莎白女王出于政治目的主导了其形象的第一次转变。女王有选择性地利用锡德尼的意外早逝,延迟举行隆重盛大的葬礼。锡德尼的形象从一个时常被忽略的廷臣,转变为一个完美骑士的典范。女王用盛大隆重的葬礼,把公众的注意力从审判和处死苏格兰女王玛丽的血腥事件中移开。锡德尼之妹彭布罗克伯爵夫人主导了锡德尼形象的第二次转变,在纪念性诗文中锡德尼的形象从最初挽诗中多才多艺的恩主和战士转变为诗人,最后成为新教殉道者。锡德尼家族通过塑造锡德尼新教殉道者的形象重振家族雄风。至于十九世纪,锡德尼最终成为基督教骑士精神的关键符号,被塑造成耀眼的英国文化偶像,服务于大英帝国的扩张主义。在1806年由乔治三世御用历史题材画师本杰明·沃斯特所作,一幅名为《身负致命重伤的菲利普·锡德尼爵士》(The Fatal Wounding of Sir Philip Sidney)的画中,锡德尼临终前的姿势被刻画得如基督受难一般,目光宁静地投向远方,这进一步牺牲了历史真实,以达到渲染情感的效果。
何伟文的《人生和诗学》值得商榷之处在于,对锡德尼本人的文学作品,如《阿卡迪亚》(Arcadia)、《爱星者与星星》(Astrophel and Stella)等,这部专著鲜有讨论。文学作品的缺席与纯粹理论化的分析对于读者全面认识与理解锡德尼创制的文学世界略有遗憾。此外,由于锡德尼的人生过于短暂,三十二岁即殒命沙场,并且他所写作的绝大多数文学作品与文学批评皆诞生于仕途失意的数年间,通过现有资料追溯锡德尼诗学思想的历时性变迁也十分困难。
或许正如亚氏在《修辞学》中所云,“情感包括所有使人改变看法另作判断的情绪”,锡德尼之死所塑造的英国文化偶像“打动和透入人们的灵魂”“占据其心目”,起到震撼人心灵的作用。这似乎回到了锡德尼《为诗辩护》的本意,即通过诗人的虚构引领读者走向德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