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纳富瓦诗歌的在场与不在场
“在场”(Présence/Présent-e)是博纳富瓦诗学和思想的关键词。这个词最早出现在他的论著《诗歌的行为与场所》(L’Acte et le lieu de la poésie,1958)中,1981年,诗人又将在法兰西学院上的第一课命名为“在场与形象”,于是,他有了“在场诗人”的称号。博纳富瓦认为,诗歌、绘画、建筑、雕塑等一切艺术形式都要与现实建立本质的联系,最终形成语言,“还原世界存在的在场面目”。诗歌语言以文字的形式,在一个更加丰富的世界中反映一个非概念化的真实现实,这个现实即在场。博纳富瓦的诗歌以寻找在场为目的,但他同时十分重视“无”或“不在场”(Absence/Absent-e),并在作品中不断以不在场反衬和凸显在场。在场与不在场既是对立又是统一的,不在场是真实世界的必要组成部分,在场的呈现以它为基础,没有不在场就无法体验在场。本文拟探讨两者的辩证关系,理解博纳富瓦的在场诗学,以此纪念这位一生坚持以诗歌“改变生活”的伟大诗人100周年诞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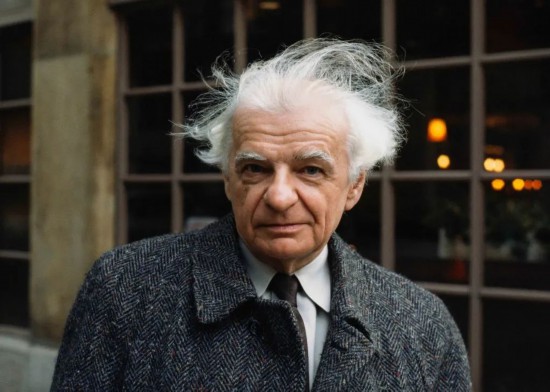
博纳富瓦,图片源自Yandex
一
语言的沉默
博纳富瓦诗歌的在场,首先指的是语言世界之外发生的事情。诗歌话语不同于日常语言,诗歌话语是事物的一种现时呈现,是一种在场的展示。在这个过程中,诗人除了用文字创作之外,别无选择。博纳富瓦认为创作诗歌的困难在于:“当语言本身的话语是在场的时候,它是一个系统。”系统化的语言话语承载着伦理和哲学的历史重任,引导读者领会那些深刻但尽人皆知的道理。伦理、哲学思想可以以具体、生动、感人的方式移植到诗歌中,但那不是博纳富瓦的目的,他写诗的目的是使“事物的在场出现在话语中”,在即时性中寻找“在场的花园”。
如何实现自己的这一诗歌理想?“为了从真实走向更真实,兰波和里尔克用新的方法使用语言”,博纳富瓦的新方法是尽量使语言沉默,在《杜弗的动与静》中他如是说:“离我很近的词/如果不是你的沉默,我该寻求什么。”经过长期而痛苦的思索,诗人发现更详尽、更清晰、更精练的话语,其意义却更模糊、更贫乏、更没有深度。在许多现代诗歌中,沉默是诗人的一种理想。为突破语言系统的藩篱,博纳富瓦在很大程度上也将话语让步给沉默,以少说、不说、留白替代言说,“让语言在我们被展示的这张生命的脸上/熄灭”。
但他不是像兰波或荷尔德林那样不再创作而沉默,而是实施“对语言内壁的沉闷打击”。因为这个内壁像是一扇紧闭的门,它表现了一些东西,但又将另一些更重要的东西关在门外,阻止人们进一步看到事物的本质,所以必须用重锤将它敲散,敲掉它厚重的部分。这个主张或许是从贾科梅蒂的雕塑创作中获得的启发。博纳富瓦花十年时间撰写了贾科梅蒂的传记,副标题即“一部作品的传记”。博纳富瓦为很多名人写过传记,例如兰波、波德莱尔、莎士比亚、叶芝等,在这些传记作品中,他都将注意力集中于作品,而不是人物生平。在讨论他人的作品时,博纳富瓦实质上是在与自己对话;1967年,他与其他诗人一起创办了诗刊《蜉蝣》(L’éphémère),其目的正是“一方面诠释贾科梅蒂作品,一方面模仿贾科梅蒂的创作思想来进行自己的诗歌创作”。在探讨贾科梅蒂的艺术观和世界观的过程中,博纳富瓦发现,虽然他们之间存在着分歧,甚至对立,但在场是他们对接的一个点。通过观察和研究,他确信贾科梅蒂的绘画或雕塑作品涉及的都是在场的问题:“值得注意的是……即使在贾科梅蒂面前有一个人,在他的画作中却可能没有任何人。这个无人的‘在场’,就是他面对在场的反应:惊讶、惊恐、本能的依恋、痛苦的纠结。”在画一张脸时,贾科梅蒂努力捕捉的是“他者在这张脸上的表现特征”。如果要做一个头颅建模,他突出“头骨的隆起部分”,以死亡的在场表现一个生命的存在。尤其是对于人体,贾科梅蒂只保留人体的骨架:他去掉肉体部分,以揭示它所暗示的存在理念,以及它所包含的生命之谜。用博纳富瓦的话来说,贾科梅蒂最终雕刻的是“在空间的一副骨架”。例如在《不可见之物》(Les Invisibles)这部作品中,他“卸下”表情、身体曲线等材料,而采用几何线条和变形的构图,以此达到让作品包含多重生命意义的目的。总之,贾科梅蒂经常以无表现有,以不在场表现在场。
博纳富瓦将贾科梅蒂表现在场的方式运用到自己的诗歌创作中,那就是让话语“瘦身”,删繁就简,让复杂的句子结构不在场。泰洛这样描述他的语言风格:“博纳富瓦很多诗歌的句子都很短,而且多为独立的短句,没有从句,即使在这些短句中,他也尽可能少地用动词,较少用修饰语,不推理,使诗句的意思保持中性。”在《离散,不可分割》(L’épars, l’indivisible)这首诗中他写道:
是的,通过声音
暴力地对抗沉默,
通过肩的撞击
暴力地对抗距离
——但你用冷漠的霹雳分享
Oui, par la voix
Violente contre le silence de,
Par le heurt de l’épaule
Violemment contre la distance de
Mais de ta foudre d’indifférence tu partages
在原作中,只有一个动词(诗人曾说:“愿动词熄灭”),句子很短,没有韵。但我们仍然能够深切地感受到“声音”与“沉默”、“摩肩接踵”与“距离”的“暴力对抗”,感受到这种对抗在另一种“冷漠”与“霹雳”的对抗中消费殆尽。另外作者在第二、四句最后的“de”(在此de=of)后面省略了补语,使“沉默”没有归属,使“距离”没有限定,一个不知从何而来的“声音”撬动了这一切,可这一切又独立于交流所需要的结构。正如布朗肖所说:“这一非动词的规则,并不专用于意义的约定。如同空虚并非一种缺乏,而更是一种饱和,一种被空无填满了的空无。”
独立短句和名词结构的广泛使用,修饰语的不在场,动词在句中的省略,博纳富瓦用这些手段使诗歌话语既超越了语言系统的规约,又远离了表达概念的陷阱。为了避免一种强加于人的确定性,他用中性的表达,不加评论或描述,拒绝事物过于精确的差异化再现和含义的明确指向。这样的语言拥有一种强大的表现力,即以语言最大限度的沉默最大限度地表现了在场。言约旨远,直指人心,这是博纳富瓦的诗歌呈现在场的主要手法之一。
二
音乐的在场
在场对于博纳富瓦而言,是不断更新的神秘现实。要认识它,“认识存在于我们生命中的神性”,博纳富瓦没有像兰波那样以“打乱一切感官感受”的方式激发灵感和想象力,而是“通过音乐”,通过由文字构成的“音景”(soundscape),使世界重新神圣化。在诗歌文本形成之后,诗歌的意义就相对固定了,与诗歌文字相比,诗歌的声音具有引向在场的更大能量,能够唤醒在概念下沉睡的在场,因为“新的文化素养蕴含在音乐而非语词中”。博纳富瓦以音乐的在场,使诗歌中以文字表达的“精确意义”即“概念”不在场。斯坦纳认为:“当诗歌力图脱离清晰的精确意义,以及句法的常规,它就会倾向于一种理想的音乐形式,这种倾向在现代文学中起着有趣的作用,赋予语词和诗文等同于音乐的价值。”博纳富瓦在诗歌的语义和音乐之间建起一种联系,通过诗歌语言的“简化”构造音景,使简化之后的想象物最终具有音乐的属性。在《雨蛙,夜晚》(Les rainettes, le soir)这首诗中,诗人融合语言和音乐,或者更确切地说,让两者有机共存,但语言在此失去了理性陈述的权威,失去了控制结构、指定意义的权威:
夜晚的雨蛙
鼓噪着喇叭,
无声无息流淌的池水,
在水草上闪闪发光。
Rauques étaient les voix
Des rainettes le soir,
Là où l’eau du bassin, coulant sans bruit,
Brillait dans l’herbe.
[rok] [etε] [le] [vwa]
[de] [rεnεt] [lə] [swar]
[la] [u] [o] [kulɑ̃] [sɑ̃] [brɥi]
[brijε] [dɑ̃] [εrb]
在这首诗中,文字不再是表达意境的主要载体,而是通过声音挪用的技巧成了语言的附属物。音乐进入这个文本的模糊区域,将文字包围在文字自己的句法中。从语音的角度看,第一、二句元音发音的口型都是从小逐渐转向大:[o] [e-ε] [e] [a] / [e] [ε-ε] [ə] [a],两句合在一起形成一条高低起伏的音乐曲线,尤其是两句以[wa]为韵,重音在[a]上,而且第二个[a]要读长音,第三句的首个元音又是[a],这样的安排形象地表达了雨蛙此起彼伏的“呱呱”鼓噪声,使得由文字表达的“声音聒噪”(Rauques étaient les voix)的意思得到了强化。夜晚蛙声阵阵与下文的“无声无息”形成强烈的对比,其程度的加强来自音乐与语义的结合。第三、四句连续用了四个鼻化元音描述“池水”,诗人利用鼻化元音在词末闭音节中读长音的特点,使人从声音中感受到池水的长流不断;另外,前三个鼻化元音连续不间断,在第四个元音前插入[ɥi] [ijε],形成了这样的音效:[a] [u] [o] [a-ɛ] [u-ɑ̃] [ɑ̃] [ɥi] / [ijε] [ɑ̃] [ε],似乎让人听到池水回旋的潺潺之声。然而,在字面上,却又是“无声地流”(coulant sans bruit),似乎池水不似江水或河水,不应有潺潺之声。这样,语义上的“无声”与语音上的“流水有声”形成反差,无与有互为前提和条件,有中生无,无中生有,体现了诗人一贯坚持的关于世界存在的观点。
这样的解读也许是非常主观的,但从诗中得出一个精确的结论并不是诗人的初衷。博纳富瓦在诗句中加入音乐,不是为了更清晰地表达自己的思想,他指出:“诗歌中,词语的音乐性改变了词语的效果。受音调、音韵、节奏的支撑,诗句中的词语与其说是被用来从观念角度阐释世界的面貌,或建立一个欲望的舞台,不如说是在摆脱枷锁之后发出的直接召唤,我甚至要说是沉默的召唤,这召唤令事物重新焕发伊甸园的光辉。”通过在诗歌中构建音景,诗人逐渐放弃或超越了原有的形式,诗歌逃离了线性的、指称的、逻辑上注定束缚它的语言句法,进入了诗人视之为即时、直接、自由的音乐形式。博纳富瓦说:“旋律和音乐是文字的一部分,它将文字从概念表述的固有的抽象和支离破碎中解脱出来,从而为那些满怀信心进入歌声的人重新打开了直接性和统一性的世界,进入了简单而深刻的生活世界。”通过对词语声音的处理,诗歌在有限中为我们打开了通向真理的大门。
斯坦纳认为:“诗歌走向了音乐,当诗歌抵达其存在的极致之时,诗歌也就成了音乐,这个观点明显有着强大的言外之意,音乐归根结底要优于语言,音乐表现的更多更直接。”但博纳富瓦并不主张音乐先行,因为他不是巴那斯派“为艺术而艺术”的继承者,而是为“改变生活”(changer la vie)而创作的诗人。他借助音乐,目的在于减少文字,消除概念,消除永恒,同时希望表现“一种创造者独具、带有他自己精神烙印的创造行为,如何在每个听众身上无穷更新”。诗歌文本的意义在于交流,而音乐能满足真正意义上的交流:从符号学的角度看,音乐为文字文本打上了诗人的烙印,体现了诗歌作品的个性,但诗歌同时又具有社会性,召唤大众理解。对于诗歌的社会功能,博纳富瓦怀有坚定的信念,坚信诗歌有表达“意思”的可能性,同时他又毫不动摇地怀疑诗歌的意义,质疑它所表达的“意思”。因此,音乐在一定程度上能避免诗歌文本沦为概念,同时保证它成为交流的场所。在音乐中,我们可能重新获得对个人存在的内在运动和节律的感受。因此,博纳富瓦的写作像一场远足,沿途遇到的一个个景象或意外的声音都让他惊讶,他拨开树枝,用眼光和耳朵捕捉一切,回应途中遇到的呼唤。这样的诗歌通过音乐的在场,让我们听到事物的在场,让我们“置身于万物的统一之中,置身于眼前的充实之中”。
三
形象的批判
艺术形象(image)在超现实主义者那里很受欢迎,博纳富瓦没有否定它,但他提出了自己的分析和批评。博纳富瓦认为形象是用“名称替代了事物的表征,这些表征永远是片面的,它们与我们保持着距离,就所呈现的事物而言,为了定义或使用的目的,体现了其他不存在的事物”,也就是说,形象世界是被语言重新加工的世界。语言塑造形象有三种方式:普通语言描写相对一般的经验;精确化的语言将抽象的认知具体化;诗歌语言描述感受最为深刻的经验、内心的碰撞、下意识等。无论哪种方式,小说家和诗人都致力于让语言、形象、现实三者相遇且吻合,而实现这一目标的前提条件是充分信任语言和它的透明性。以博纳富瓦的《杜弗的动与静》为例:
内在的海被盘旋的鹰照亮,
这是一个形象。
我在一种深度里拥有冷冰的你,那里
形象不再出现。
这里有海和鹰的图像,而没有实际的海和鹰。就像马格利特(René Magritte)的《这不是一支烟斗》所表明的,即使以最逼真的方式绘画,画中的烟斗也只是一支烟斗的形象,不能像实物烟斗那样被塞进嘴里。“形象是我们的现代魔法”,“海”和“鹰”是诗人对美的感悟在某个瞬间的幻化,是他将瞬间偶遇的深刻人生经验定格为永恒。博纳富瓦认为文字应该表现世界的偶然性,服从于偶然事件不可预测的一面,因为“日常的生活、时间和偶然是唯一物质的”。偶然也是无意识的另一个名称,它主宰一切相遇,是认识生命和世界的钥匙。但反过来,无意识对诗歌创作构成了障碍,因为它“用图像的封闭取代了在场的开放”。即使是诗歌话语塑造的形象,也是一种圈套,诗歌能做的,就是使人认识到这一点,让“海”和“鹰”的“形象不再出现”。
博纳富瓦告诫人们,形象仅仅是一种抽象,它从人们的头脑中抹去了经验的维度,而经验促使人们思考时间和死亡以及有限性中固有的一切细节和谜团;生活在日新月异地变化,而形象却将动态的生活固化为一种窠臼,将我们对美好生活的愿望圈定在一种期待或者等待的状态而不是运动的状态,在前进的道路上竖起了屏障,使“人越来越依靠符号的拐杖跛行”。
形象的世界是不在场的产物。一旦进入语言的体系,以语言塑造形象,不管是添加还是减少文字对事物的描述,都有损于它的“本真”(ce qui est)的完整呈现。就算形象充分表现了世界,语言在试图阐释这个形象世界时,也只能体现它各个部分在某一时刻边界分明的特性、连续性和相似性。因而,文字的形象并不是我们身体感受到的现实。博纳富瓦辛辣地批判了西方对形象的过度热爱,认为形象倾向于二元论的视野,通过提供一个替代的宇宙,一个形象世界,来取代尘世的世界,将一个梦想中的“那里”与一个被拒绝的“这里”分开。在《在场与形象》中,他说:
我们西方有史以来有多少有害的二元论,在一个被贬值的此和一个被誉为优的彼之间有多少不切实际的天方夜谭,有多少荒谬的文字被“形象”的忧郁天才地传播,由此西方重新创造了疯狂,如果不是爱的话!这些梦想对于始终是虚无的意识形态、对于权力的欲望来说,是一个多么重要的工具,它们成了旗帜!形象肯定是谎言,无论形象制造者多么真诚。
语言塑造了各类形象,织就了一张遮盖真实的帷幕。因此,博纳富瓦主张“要想重新找回‘真实的生活’,首先必须要撕毁遮盖它的帷幕”,“为了爱,/我们不再需要令人心碎的形象”,应该“在言语的有限使用中彻底否定它”。“当话语通过遮蔽而歪曲现实,并代之以形象和非实体的反映的时候,话语中就有一种死亡的力量,这时候应该让它重归沉寂。”因此,尽管描述形象世界的语言是纯洁的,正确无误的,但实际上是一些死亡的语言,应该允许它再一次死亡,实现一次否定之否定,理性地否定它的在场。只有否定这种封闭的形象,才能在语言的死亡之中诞生新的话语。
同样,博纳富瓦在指出形象的危险性之后,又确认了它的生命力。在对它进行了精确的批判之后,他承认形象是欲望的一种自然形态,诗歌不能完全没有形象。例如他诗歌中的形象永远是鲜活的,如同我们四肢中流动的血液,是“这棵树”“这股清泉”“这一石块”“这只船”,是我们脚下的大地。形象的悖论之处在于,在某个瞬间它使诗人的智慧直接抵达事物的内在核心,但它并不是永恒的美的同义词,由诗歌语言建立的世界不是一个理想化的永恒世界。不能将诗歌创造的形象绝对化或固化,而应该“相对化”。以此来看,语言具有奇妙的魔力,诗人以相对化的眼光来看待形象,然后重新赋予其意义,其中既包含对语言的爱,也有对语言的怀疑:
正如你们所见,形象就是拥有词语的人的欲望,他能让词语按其意愿言说。但是,在他所感受到的极大的自由面前,他也忧心忡忡,因为在内心深处,他知道要想真正理解大地,唯有像生命所需要的那样去体验之,即在时间的流淌中,在已接受的此在所强加给我们的限制中去体验。
里查尔认为:“矛盾始终处于博纳富瓦的诗学批评与创作的中心。矛盾是他始终不懈要在每一首诗中言说的问题,也由此超越了矛盾。”对于形象的矛盾,博纳富瓦认为出路在于诗歌语言,而诗歌语言的出路取决于生活在诗人心目中的位置,生活永远是一切事物的决定因素。为了进一步阐明他的意思,博纳富瓦又继续补充道:“我不得不沉思我生存中的一些事件,它们所要传授的东西自我启示,介乎于我的独特性和所有生活的恒常性之间。”由于“生存中的一些事件”是个体生命在某个时刻的偶遇,所以被烙上“我的独特性”的印记。“我”“在时间的流淌中”的生命体验不是一成不变的,大自然中的山山水水也不会因一次相遇或分离而拥有或失去魅力,它那体现内在美的传统形象构成了“生活的恒常性”之根基。表面上令人匪夷所思的形象,却能将山水从陈词滥调的泥沼中拯救出来,令人耳目一新,而如果形象偏执于一方,一味强调“我的独特性”,那将重蹈超现实主义滥用形象之覆辙。
四
时间和地点的解构
作为“在场诗人”,博纳富瓦要求诗歌必须有一种本体功能,使读者能够通过作品直接与真实世界交流。关于真实世界,他在《未必真实》(L’Improbable,1959)的首页这样写道:“我把此书献给未必真实的世界,也就是献给本真。”在诗人的眼里,真实世界是“未必真实”与“本真”的矛盾统一体,未必真实才是绝对的真实。对于真实世界,他既抱有一种怀疑,又相信它的绝对真实。只有以一种怀疑的态度对待“真实”,才能真正触摸“本真”,这是诗人以诗歌再现现实世界的一贯主张。
当博纳富瓦将诗歌的目的设定为触摸“未必真实”即“本真”的现实世界的时候,他面对两方面的挑战:一方面,他要继续发挥诗歌的本体功能,发扬浪漫主义的传统,把诗歌看作一种传递希望的形式。为此他不赞同结构主义和解构主义者关于诗歌没有确切意思的观点,例如不赞同德里达关于“诗歌的意思向众多的方向发散,以致意思在某种程度上消失了”的观点,而坚持认为诗歌的主旨始终与生活的希望相连,声称“我要把……几乎确定的诗和希望结合起来”。另一方面,由于语言的任意性,诗歌要道出现实世界的本真并不容易,他寻求这个“未必真实”的现实,而现实往往超越语言。因此,对博纳富瓦来说,诗歌的世界在本质上不是真实的。然而“这种不真实必须被写出来”,诗人必须对自身感知的、模糊的、“未必真实”的现实元素加以“命名”,必须告知他抓住的那个瞬间“是什么”(ce qui est),正如他自己所说:“在现代法国诗歌中,有一支圣杯的队伍经过,这个地球上最生动的物体:一棵树、一张脸、一块石头——它们必须被命名。”
诗歌应当界定存在的事物,诗人的职责要求他不但要定义那些转瞬即逝的东西,而且必须把“新生的语词从个体意识活跃的黑暗中提升到集体的光明中来”。但是,由于语言在诗歌表达中具有共性,即使是个性化的诗歌语言,通过命名和界定,真实世界的生动之物也都被定格在概念中。将现实世界概念化,这是博纳富瓦一贯反对的:“词语应该拒绝使概念具有说服力,词语不应该再为概念服务,要让那些凭直觉观察的人失望,以便最大限度地使他们处在不可言状之物的光明之中。”在他看来,要规避现实世界抽象化、概念化这一陷阱,诗人必须以在场为工具,通过在场进入“不可言状之物的光明”,因为在场“是我此时此刻生存于我所在的世界,是我生活在这个世界上的现时经历”。因此,在场和“此地与此时”(ici et maintenant)密切相关,它是现时亲身处在事情正在发生和进行的现场,是事物直接呈现在面前,是经验的直接性、无遮蔽性和敞开性。博纳富瓦追问世界存在的本质,实际上是在追问“此地此时”。“此地与此时”的表述多次出现在他的散文和诗歌作品中,并贯穿他的全部诗学主张。这个表述在法语中是两个副词,但它们有明确的指向性,与指示代词、指示形容词、人称代词和不定冠词一样,具有指别(Deixis)功能。事实上,具有指别功能的词类在诗人文本中的使用不是偶然个别的现象,他的许多诗都以“一块石头”和“一个声音”为题目,而相同题目的诗作在内容上并没有直接的关联或连续性。具有指别功能词类的广泛使用,既是博纳富瓦语言的一大特征,也是他诗学主张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他来说,指别是通往诗歌创作的大门,是一种工具。通过运用这一类词使话语,诗人能够消解对事物的界定。
博纳富瓦说:“唯一有价值的未来就是在场的完美,在这里我们的时间不起作用了。”诗人要坚持在诗歌中呈现在场,而在场又必须处在“未必真实”与“本真”的“两个世界之间”,所以他必须解构事物存在的时间和地点,使它们始终不能自我精确定位,而必须处于动态之中。指别作为语词的一个类别,其意义从根本上说是不稳定的,其指称对象随说话人、说话时间、说话地点等语境要素而变化,典型的例子是代词“我”,它的定义是一个“指代发出这个词的发音人的词”,它只能在发音的时候有一个稳定的所指。兰波说“我是另一个”,“我看见了湖底的沙龙”,“我看到巨大的沼泽在发酵,/在这鱼篓的灯心草中整个利维坦在腐烂!”,在“我”与读者达成的共识中,无论能指的漂移如何,语言重新建立了与“另一个”的关系。再如在《反柏拉图》中,博纳富瓦写道:“就是关于这个客体。”(Il s’agit bien de cet objet)用斜体标出并在后文中重复的“这个”(cet),在修辞上表明所指代之物是诗人与读者共知的客体,因此它指代现实中有血有肉的每一个生命。类似的手段也出现在博纳富瓦的诗歌中,文本通过指示代词“这”引起人们对其真实性的关注。里查尔说:“博纳富瓦不像圣琼佩斯,他不把(诗歌)当作一个苦行的或进攻的工具;也不同于兰波,不把它作为满足物质欲望的工具。石头,对他而言就是‘这个’,一件‘某物’,一切企图都在此消解。因此,它是……中性的。”
博纳富瓦以指别不断拷问现实,以此揭示某些关系的真实性。在场抓住了此地和此时,将“一个被确认的地点与美”连接起来,只有在“这个”空间和“这个”时刻,美才能被体现出来,或者说,在场完全取决于不在场,取决于它存在的语境:“每个场所的普遍意义存在于人们投向它的目光中,存在于可能使用它的行为中。”
结 语
意大利学者安东尼奥·普雷特说:
博纳富瓦的诗有这样一种特质:一边呈现在场,一边质疑思想的局限性。当诗歌留住了一棵树、一块石头、一片天空、一片剥落的颜料,并开始观察自己的身影时,它却让自己走向了不可见的边缘。当它聆听傍晚的脚步声、风或水的沙沙声,当它迎接梦中人物的时候,它却试图落脚于此时此地,扎根于神秘的大地。……博纳富瓦赋予“在场”一种强大的能量,然而它的呈现常常是沉默无声的、深邃不可见的、隐秘不张扬的。
在博纳富瓦的诗歌中,在场是一个具体化的存在,是所有鲜活生命关系的总和。以超常规的语言构筑图像、再现声音是为了呈现在场,批判形象、否定语言,解构时间与空间也是,一切手段都是为了让禁锢人思想的概念不在场,让所有生命关系的生动与活力永久在场。在场与不在场在诗人的诗学主张中是对立统一的:诗歌是“存在与话语之间的关节”,是通往希望的桥梁。博纳富瓦对诗歌本质的在场定义,创建了法国当代诗歌史上独树一帜的在场诗学。这种诗学立足当下生动而鲜活的生活,否定诗歌创作彰显意义和追求永恒的传统。由于“在场”始终处在不断变化之中,诗歌反映“在场”的任务永远“不可终结”,诗人的使命永无止境,没有终点,永远在场。
原文载《外国文学动态研究》2023年第6期“作品及作家研究”专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