草原覆盖着语言的光芒 鲍尔吉·原野、汪政对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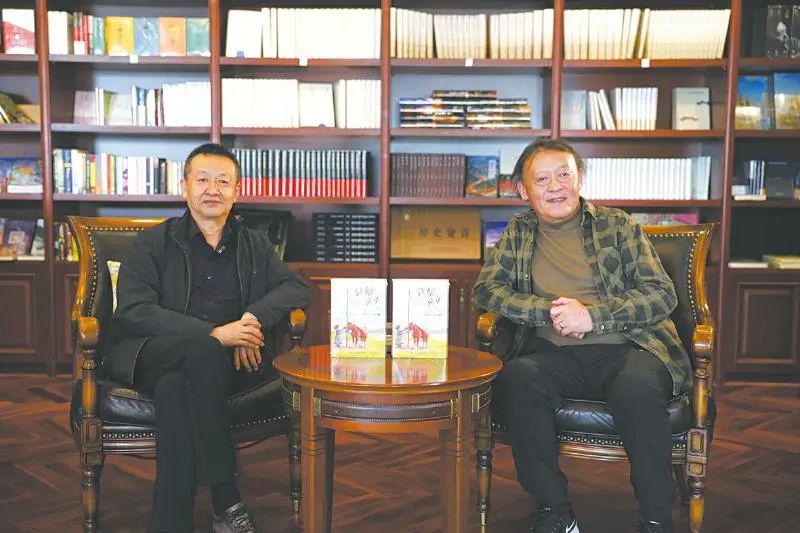
左:江苏省作家协会副主席 汪政 右:中国作协散文委员会副主任 鲍尔吉·原野
汪政:原野老师好!你在散文创作上深耕多年,一直想听听你关于散文创作的一些想法,包括创作初衷和你对理想读者的期待。作为作家,特别是像你这种身份比较特殊的作家,你希望作品写给谁看?你想在读者那儿达到怎样的一种阅读效果?像你这样的蒙古族作家,长期生活在东北地区,我首先想知道你的理想读者是谁?
鲍尔吉·原野:有机会和汪政老师对谈是荣幸。我最开始写作的时候,心目中没预设过读者。1987年,我29岁那年和家人一起从赤峰到沈阳工作生活,不适应,特别想家。但不能回去,因为把家人都带来了。有好几次我骑自行车在沈阳拼命骑,希望看到城边,但每次都骑不到城边,这个城市太大了,我感到惶恐。为了平复乡愁,我开始写作,写草原。一来草原是我家乡,二来它辽阔。写的时候播放蒙古歌,听长调、马头琴曲,喝酒,假装在草原。然而,我只有逼真地写出草原的一切——光线、气味、景色、蒙古语的词汇和牧民的脸庞,我的心才安稳下来,相信我就在草原。
汪政:这两天我在想,内地的写作和边地的写作实际上是两个类型的写作。现在大家都在提倡文化交流、文化交融。你有草原生活的经历,你写草原,你觉得很自然,甚至于没有明确的自觉的意识,自然而然地就这样写了。但是青岛的小读者或者青岛的读者,他们并不这么看。所以这个事儿你还得要想一想,因为他们拿到“草原童年美文系列”的时候,看到鲍尔吉·原野,对于内地的人来讲,作者的名字就跟我们张三李四不一样。
你一往情深地沉浸在你的这种写作的世界里,但是,我们不一定这样,我们会想,这跟我有怎样的关系?我为什么要读这样的书?我在书里得到什么?你可能不会想到这些,但实际上还是有这个东西在的。
就像你刚才说到了“辽阔”,我昨天也跟编辑讲到这个,你的这种写作,真的是给我们内地的读者打开一扇门,或者推开了一扇窗,让我们看到了辽阔的世界,它让我们对时间、对空间都有了一种不同的感受。
所以,细说起来,写作还是有分别的。面向自我的写作和跟他人的分享和交流,说得朴素和简单一点儿,你显然希望让我们都看到草原,看到你笔下的草原。
鲍尔吉·原野:好的,汪老师。我刚才说写草原的动因是想家,写来写去,有了文化自觉。后来我适应在沈阳这个大工业城市生活了,这是在上世纪80年代末到90年代上半叶,此时中国散文正处在上升期,好多人在写散文,也有好多发表的媒体。我准备把散文写好,把自己家乡的一切告诉读者。这种诉说不是猎奇,是想把美好的东西告诉别人,核心是草原文化,更多是蒙古族文化。
我觉得我的写作深入表达了蒙古族人的价值观,他们淳朴诚实,按着成吉思汗《大扎撒》所规定的准则生活。用流行语讲,他们是与环境友好的人。
我特别喜欢看内蒙古地图上的地名,从东到西,河流、山和泉水都有美好的命名,把美好的祝福膜拜送给了河水、山峰还有泉水。比如乌力吉木伦河、查干木伦河,都是吉祥的河。山也是,有的是神山,有的是圣山。泉水也有名字,比如往上生长的泉水、富裕的泉水,都有美好的寓意。牧区的骑手拿的马鞭子是装饰物,蒙古人不会打马,马是他的亲人。蒙古人认为火里住着火神,引火要用干净的纸,不能从火上迈过去。可以烧牛粪,但不能烧狼粪,狼粪是脏东西。牧区有碾粮食的碾子,牧民管它叫白老汉(吉利老头),不能坐到碾子上。这些都是可爱的习俗。写草原不仅写异样的地域,更要写异质的文化,否则不具备文学内涵。
王泉根教授跟我见面说:“您所写的《乌兰牧骑的孩子》,我读来是一幅草原风情画,有真实、深入和辽阔的美感。”他说,“我印象中有两本书写草原写得最好,一本是我初二读过的《草原烽火》,一本是您这部《乌兰牧骑的孩子》。”我喜欢刻画草原风情画,完成蒙古族牧民的群雕,显露他们的面庞与心灵质地。
汪政:这是你写草原的初心。你提到了孩子,提到了儿童文学,这套书也是写给孩子们的。不过在我看来,只有好的文学与不好的文学的区别,没有成人文学和儿童文学之分。
我们可能有一些共同的阅读感受。现在的一些儿童文学,只想给孩子们讲一些稀奇古怪的故事,很幼稚的故事。语言不讲究,这个问题我觉得要好好说说。孩子的成长是全方位的,有身体的成长,有心理的成长,有意志品质与情感的成长,其实还包括审美的,特别是语言的成长。他小时候接触到什么文字,可能会影响他的一生。
我们现在语言环境很复杂,也不是很理想。现在的资讯与传播又非常发达,孩子们无法把这样一个乱糟糟的语言环境给屏蔽掉。作为写作者,应该有一种使命感,用好的语言,多给世界做一点净化的、清洁的、美的工作。从某种意义上说,你的写作通俗地说,其实是带有一点唯美主义色彩的,你是努力把最干净的、最纯净的语言带给读者。
我跟你原来不认识,也没有向你打听过你的生活。所以这次一见面我就问你,你小时候说的什么话,你说是蒙古语。我又问你什么时候学的汉语?你说你上了半拉子学,是在社会上学的汉语。这样说起来,你实际上是有两种语言。你怎么看待蒙古语和汉语?你虽然没用蒙古语写作,但我觉得蒙古语对你的汉语写作是有影响的。我想知道,如果以蒙古语作为你的母语背景的话,你对汉语有怎样的认识?反过来也一样。
我总觉得一个会说蒙古话的人,从小讲蒙古话的人,现在改用汉语写作,他的语言的基因里面、血液里面,会流淌着他的母语。比如说调子,像你的作品,我们可以明显看出有一种音乐性在里面,诗意在里面。因为边地的东西,特别是少数民族的东西,它天然地就是跟艺术和诗联系在一起,比如像你刚才说内蒙古的河流、山川、大地,那里的人们对它们的命名都是沿着真善美的方向,向着神性和圣性的方向去的。
回到刚才的问题上去,你怎么看待自己童年的蒙古语生活?它对你现在的汉语写作有什么影响?我非常想以“在蒙古语的光芒之下,我们重新看待汉语”这样的题目分享你的创作。
鲍尔吉·原野:我们在探讨初心的话题。我学说话最初学的是蒙古语。在童年,父母老下乡工作,我和姐姐由曾祖母努恩吉雅带大。她用蒙古语给我们讲述民间故事,格萨尔王史诗。曾祖母是一个语言大师,她滔滔不绝地讲出整本的史诗,绘声绘色。有人物出场的环境描写,草地怎么样,空气怎么样,天空怎么样,这是非常好的文学启蒙,也在我脑海架构了蒙古语的全维度的世界图景。
最初的词语被蒙古语命名了之后,再学习汉语,特别是从事文学创作,我觉得心灵手巧,知道用哪个词,不用哪个词。蒙古语告诉我一切东西都可触可视。比如桌子、碗、手、鼻子。写作时潜意识地选择一个合适的汉语的词来表达,它有光线、色彩、气味和声音。但它最初是蒙古语命名的事物。我的写作里没有假话、大话、空话,因为我不知道蒙古语里的假话、大话、空话怎么来说。蒙古语言长于称颂万物,赞美父母与故乡,奔放婉转。这对我有深刻影响。
我赞成汪政老师所说,一个作家的责任是纯洁语言,包括美化和建设自己的语言。让语言变得优美而不是粗鄙。一个作家有责任让语言变得优美、细腻、准确、生动,而不是粗暴地对待语言。尤其是给孩子写作的时候,用纯洁的语言跟孩子交流,像送给他们最好的礼物。用优美的现代汉语给孩子们写作是功德。
汪政:因为不仅仅是对于儿童,对于我们成年读者来讲,读你的作品,也存在重新发现汉语,重新理解汉语文化的体验。你的作品让读者从当下的语言环境当中抽身出来,进入到一个优美的语言空间当中去,它可以纯净自己的语言生活。
这次青岛出版社推出了你的“草原童年美文系列”,借这3本书,我还是想听听你对散文的理解是什么?因为散文是你的看家文体,你在这个上面肯定是有心得的。用你一直挂在嘴边的那个词,你的散文是“讲究”的,也就是说,你的写作不是随意的,它是艺术创作的产物。
美是有规律,有标准的,我们的文学就要按照这些规律和标准去做。散文是艺术品,它需要构思、需要材料、需要去经营,怎么开头,中间怎么写,怎么结尾,都是有考究的,它是一个人工制品。因为你在散文方面有很高的成就,同时也有很长的创作经历,在散文界摸爬滚打这么多年,假如现在孩子们问你,请你给散文下个定义,你想如何说?你心中的好散文是什么?你的散文写作能够走到今天,支撑你写作的是什么?
鲍尔吉·原野:楼肇明老师是研究散文的前辈,上世纪90年代,我刚写散文的时候,楼老师给我好多指点。他告诉我有几种东西不要写,我都记在心上。他说语言就是一切,对语言的追求要持续到生命最后一刻。在人民面前,永远保持自己的卑微。要忠诚自己的民族。不去解读古人的经典,用白话文稀释它。要写活生生的有血肉的散文。不要在散文中写自己,更不要美化自己。写作保持真诚,什么时候不真诚了,流于大话套话,流于油滑,流于谄媚,流于人云亦云就不要写了。楼老师说,文学不应该粗暴,粗暴是对文学的破坏。楼老师的指导对我醍醐灌顶。
上世纪90年代,我和朋友邹静之常常在一起聊天,对我启发甚深。他说写诗歌、写散文的最高境界就是写出它的音乐性。我深信不疑,汉语分为四声,我十分愿意写出它的节奏感。比如说我散文篇目的名字《火的伙伴》《羊的样子》《刀的道理》,朗朗上口,为我所爱。我觉得语言好,是好散文起码的和终极的标准。
邹静之说好文章要有诗意。一 开始我不明白他说的诗意是什么,后来领悟。但诗意不可说,一说就没了,但是它存在。我努力在我写的作品里有一些音乐性,有一些诗意,有一些自己在语言上的发现。
汪政:我还是要追问一下,从文章这个角度来讲,你觉得你在写散文的时候,你总结自己也好,对读者的建议也好,散文它应该是一个什么东西?
鲍尔吉·原野:我觉得它首先是文学作品,是创造,有美感。杨绛先生写的散文,比如《林奶奶》《老王》,是中国散文里边最好的作品之一。杨绛的散文平白如水,但味道甘醇,这就是好散文。
我以为,散文的语言应该比小说的更考究、更生动、更准确。我愿意用“琳琅满目”形容散文的语言,像珍珠在玉盘滚动起来。有人问,有这样的散文吗?有。欧阳修的散文即如此,赵元任、沈从文、孙犁、杨绛的散文也是这样。陈之藩、周涛的散文很好。有的散文带点土气,但是干净,像苇岸的散文。我说的“土气”是泥土气。苇岸孤傲,不与庸俗合流,反射在他的文字里,就是语言的纯洁,像土里长出来的。现在的问题是我们一起在糟践语言。
汪政:我们又一次说到语言。说到语言的“好”,不仅仅是保持、继承,还包括建设。一个好的作家,就是一个语言的建设者,他应该贡献一些新的东西,像你提到的《史记》、欧阳修的散文,以及现代作家沈从文的散文,都对当时的语言有很大的建设。这样的例子在各民族语言史上都存在,比如但丁的写作使意大利语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如果没有普希金,俄语也不是现在这个样子。好的作家、伟大的作家能使本民族的语言发生深刻的改变。
你刚才说得很对。在中国古代,文学性主要体现在文言文当中,古人着力建设的是文言文。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一个重要标志,就是确立了白话文的文化地位。不过,白话文的文学建设时间不长,到现在其实也就100多年,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说,我们语言建设的空间还很大。
从这个角度说,我们太需要像你这样的作家,这样在文学语言的建设上的自觉者。你的散文作品,给我、给我们广大读者的一个最深刻的印象,就是它是一种别样的语言存在。同样的意思,我们一般不像你这样说、这样写。打开“草原童年美文系列”,这种带给读者陌生的语言现象比比皆是。比如,“我从草垛上看到一望无际的草原,草原上的草不躺着,它们站立在宽厚的泥土上”。我们一般不这么说,我们就说“草长在那儿”。这样简单的话就让我们打开了一个新的语言世界,体会到了语言的新的可能性。这是把汉字重新组合了,这一组合,就使语言发生了细微的变化。“草不躺着”这4个单字,在我们习惯的话语系统里面不会这样出现,但是你把它们放在一起了。
这不仅是语言的问题,首先,你要去看,去体验,认真去观察,不要笼统地说“草长在那儿”,我们要去看,去体会草和泥土的关系。我还可以列举出好多这类陌生化的例子,跟日常生活中模式化的语言有那么一点点错位。这样的错误形成你语言上的整体风格,与别的写作者有了区别。
鲍尔吉·原野:这个话题蛮有趣。我认为,在叙述或描写中,前一辈的写作者说“草生长着”,说完之后,他就把这句话给说死了。你得重新说,说“草不躺着,它们站立在宽厚的泥土上”,这就活过来了。
写文章是把每个字拍一拍,拍醒,让它们站起来,让它们活过来。我认为作家的创造性劳动首先是让语言活过来。一个作家如果喜欢用习惯的、他人的写法写作,实际是拉着一车僵尸,而不是生灵。
我还有一种私见,在我写得比较好的散文作品里,除了内容,还有一个价值的存在,即语言的存在。有一些作家的文章,如果除去它讲述的事情,它的语言和故事一起消失了。我的作品除了故事,还有语言的一条命在。
腾格尔对我说,“好歌有一条命”。他说得很好,语言也有一条命。故事只是故事。有些不怎么好的文学作品,除了故事之外什么也没有。我认为好的语言可以独自生存,是有生命的。
还有昨天举的例子,“河流肥胖”,这并不是拟人化的问题,而是想把它写活。“河流波浪滚滚”,这是过去的说法,已经把河流说死了。一个作家应该用活的语言来说话。
汪政:关于这活的语言,请你一定要跟读者们,尤其是小朋友们说一下,现在的小朋友们受到网络语言、流行语言的巨大影响,你一定要告诉他们一个语言的正道。
鲍尔吉·原野:小朋友们在课文里学到了好的语言。可是下了课,他们有可能使用芜杂的语言交流,互相影响,不辨美丑。
语言环境很重要,我想跟小朋友们说,学习优美的语言、优雅的语言,不使用粗暴的语言,永远不用生气的态度对待别人,把语言当成自己的财富。
汪政:原野老师,你以前有过写诗的经历吗?
鲍尔吉·原野:我最开始写作的时候写诗,很早以前我被别人称作诗人,我跟赵健雄、邹静之、林莽是写诗认识的。
汪政:出版过诗集吗?
鲍尔吉·原野:没出过诗集,后来有机会出,我没出,我觉得我的诗写得不好。
汪政:我为什么问这个问题?因为说到你的散文,说到你的语言,其中一个很重要的特征就是,你在自觉地,或者自然地营造一个富于诗意的世界。
鲍尔吉·原野:我一直喜欢读诗。中国的诗歌,我长期读杜甫,读了10多年,把好几本杜诗选本读烂了,又买新的。外国诗歌也读过一些。现在微信里读诗很方便。昨天早晨,我读了瑞典诗人索德格朗的诗:“当夜色降临,我站在台阶上倾听;星星蜂拥在花园里,而我站在黑暗中。听,一颗星星落地作响!你别赤脚在这草地上散步,我的花园到处是星星的碎片。”读过这首诗,我觉得一天都会愉快。我把诗歌当作营养,当成蛋白质和纤维素。
汪政:一般来说,作家对语言的贡献都可以掰开了、揉碎了来讲。一个作家对语言有所贡献,其实就是他建构了个性化的语言风格、语言世界。再进一步,就是这种语言能够成为一种风尚乃至一种标准,人们会去学习它、模仿它、使用它。对于一个作家来讲,这是一种非常成功的标准。一个伟大的作家在若干年后能够留下来的,就是我们依然能够使用他的语言和话语的风格。
你的创作为文学语言建设提供了非常好的范例。语言建设就是要创新,要对语言重新发现,用你刚才的话说,就是起死回生,从而丰富语言的功能。比如,在言说的惯性里,“躺”这个词说的肯定是人或者动物。现在你说“草不躺着”,这样的搭配让我们认识到“躺”还可以有新的用法。再比如,对内地读者来说,什么是“辽阔”?什么叫“辽”?什么叫“阔”?这在他们的脑海里可能是一个很抽象的东西,但你的草原写作让人们对这些词,这些字有了实在的理解。你的写作,整体上让我们重新发现了许多词,并经由这些词重新认识甚至重新发现了世界,这是非常了不起的。
草原写作具有“异质性”,它不仅在文化上,也在语言上让我们重新认识了许多习以为常的、已经固化的事物和经验。不妨再说“辽阔”,“辽阔”是什么?你写辽阔,并不是采用词典的讲法。你的辽阔是实景的、感官的,通过写作,你带我们认识了草原,又因草原让我们知道了什么是“辽阔”。
在你的作品中,读者会知道草原,还会知道“草”,并通过草体验到色彩的丰富。草不是单一的绿色,它五光十色,早上、中午的时候都不一样,春天、夏天、秋天也不一样。它就像在不同时节生长、成熟的庄稼一样,从中我们可以体会到季节的轮换。如果你没有写,或者我们没有看到这样的作品,我们对于草原、草、颜色等等词的认识就固化了。
另外,你的语法有些特别。我是语文老师,我看到你作品中有些词不在按照语法应该在的位置上,你悄悄地给它挪了窝,一下让我们对这些字词和句子有了奇妙的感觉。在我看来,这就是一个自觉地、有心地在语言上用功的作家。你在这几方面做了很大的努力,当然,有些东西是语言的天分,语言的感觉,并不是刻意这样写,它就淌出来了。蒙古语的语法可能跟汉语不一样,可能悄悄地改变了你对汉语词的排列,你觉得那样写很自然。但对我们来讲有一点陌生。
语言的建设就是这样。第一是造出一些新词,像普希金、但丁,还有中国的鲁迅曾经那样做的,包括从其他语种翻译过来的,都可以产生新词。第二是重新激活,腾挪踢打,赋予旧词新的含义。第三是通过写作重新认识一些词,使它回到原初。在你看来,我们说的草原不是草原,我们说的草不是草,你将这些词返回到了事物的本真。第四是语法的变化,语法稍微变化一点,语感、调子就不一样了。我特别想听听你在平常怎么琢磨这些事。
鲍尔吉·原野:您总结得好。您刚才说的关于语言的几个方面,我有的做过努力,有的并没有达到,但是我觉得能这样做的话,就是一个有出息的作家。作家需要警惕语言被固化,思维被固化。世界既然多了一个作家,这个作家应该和别人不一样,又要区别于其他作家,而不是彼此相仿。一个作家应该有这样的自觉。
有些词在我看来是死的,麻袋里边是干瘪的,上面写俩字,“草原”。实际上我们可能不知道什么是草原,只不过认识这俩字,说到草也是这样。我觉得我的任务是,半夜把这些麻袋打开,在里边装上东西,让它鼓起来。我作品中字词麻袋里边是有东西的,你解开它,能看到茂盛的草原,里边甚至有河流。
写散文是一件冒险的事情,写散文离不开日常生活,你一定会写到风,写春天,写月亮,写河流,写小孩子,写老人,这些事无数人都写过了,你还写什么?你没有立锥之地,过去说“脚无立锥之地”,说的就是散文家的处境。除非你在语言上有更新与复苏。草原的含义是你自己说的,跟屠格涅夫、契诃夫说的都不一样。你写的月亮也跟别人不一样。
汪政:你说月亮是退着走的。
鲍尔吉·原野:我觉得月亮确实在退着走。把世间所有事物重新说一遍,是一件很费力的事情,最重要的不是说得很独特,而是说得美,大家读了都知道你在说什么。我认为这不是一个风格化的问题,是你看世界的方式和别人不一样。我们谈论的话题有点接近语言哲学,像乔姆斯基或者维特根斯坦所研究的领域。席慕蓉老师对我说:“原野,我们对自己还是有所期许的。”她说的有意味,她不说雄心壮志,不说野心,不说以后要当大作家。她说我们要对自己有所期许。我也觉得要对自己有所期许,期许我的语言还能更好一点,像福克纳所说,“我希望我写得比我以前能好一点”。比以前好一点,这个目标永无止境。
我尤其愿意跟牧民们学习语言,他们用蒙古语谈论马,相互打趣,赞颂祖先和山川河流,一语多关,鲜活生动,妙不可言。
汪政:你把语言稍微动一下,减一点东西,加一点东西,就与惯性的语言有了区别。这3本书打开来,任何一页都有这样的语言现象。比如,“盎嘎骑着这匹枣红马,奔向草场”。这是我们说的话,你呢,前面也没交代,后面也没着落,你在草场前面加俩字“西边”,真的就不一样了。“西边”在你那里很重要,是吗?
鲍尔吉·原野:我固执地认为,盎嘎不能骑着枣红马奔向“草场”,世上不存在“草场”。它要么在西边,要么在东边,要么在北边。我认为这么写不是啰唆,是准确。
汪政:这里面还有一种草原生活的经验和蒙古语的经验,我猜测少数民族的语言是很感性的,对不对?
鲍尔吉·原野:我掌握蒙古语,并不像一个汉族人在大学英语系学成了英语。需要的时候用英语跟别人交流。但英语不在他心里。对我来说,蒙古语在心的底下,汉语在上边。
我掌握的蒙古语是感性的,可以摸到、看到、听到、闻到。有的作家写作使用的一些词汇,比如“必须”“问题”“一定要”,我觉得这都不是文学语言。蒙古族牧民不说这样的话。语言像路标一样在你心里躺着,告诉你不要用这个词,要用那个词。这样的区别就是作家与作家的区别。有人自称是蒙古族作家,却不懂蒙古语。他写得再好,也写不出草原的本色和蒙古民族的质地。
汪政:我们今天谈得最多的是语言,你的作品给我们读者启发,特别是小朋友。对小朋友来说,有助于他们建立起语言与生活的良好关系,对成人们来说,它让我们思考如何重建人与语言的关系,重建语言与世界的关系。因此,本质上说,关系到我们的文化态度和生活态度。你的生活方式、思维方式决定了你的语言态度。当语言动起来的时候,世界也动起来,人也动起来。我们的语言生活困难重重,不能用语言跟社会,跟自然,跟人,跟我们自己建立起丰富的联系,不能用语言发现世界、表达生活。但我们好像对此都麻木了。
鲍尔吉·原野:谢谢汪老师,我赞成您所说的,一个作家要在自己的作品里重新建立人和语言的关系,重新建立语言和世界的关系,我愿意为此努力。
我特别高兴的是,汪老师把这些话送给了正在读书的小朋友们,让他们珍惜语言。向好的文学作品学习。
汪政:一些少数民族作家,有其他语系背景的作家,他们能带给汉语很多新鲜的东西,比如阿来、张承志,他们的语言都有很独特的气质。
鲍尔吉·原野:也许他们自己没有察觉,但是确实很特别。
汪政:因此真的非常感谢你们这样带有异质性的作家,对汉语有外部的观察,再进入其中,跟我们一开始就在里面的感觉是不一样的。感谢你们为汉语作出的贡献。
鲍尔吉·原野:谢谢汪老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