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此”而非“此在”:吴宓晚年心境之考察
一个人与一个地方发生关系,古人多由出身和籍贯,在被动中形成,现代人则为生活或工作所选择,虽不无被动,却更有主动性,由此生成为一个人的地方性,或者说是人的在地性。无论是自然还是人为,它都是在自然环境和社会条件之中,由生命时间与区域空间的交换互动,而生成的日常生活、情感经验和身份认知。吴宓晚年一直生活在重庆,并且有诸多不如意,可谓岁月荒芜,生活惨淡。但他并没有选择离开,而是在抱怨中磨合,在习惯里忍受,而成为当代中国最为知名的重庆学人。
一

青年吴宓
吴宓来到重庆,纯是一个偶然事件。他到重庆,偏居一隅,本想寻个安静环境,教书吃饭, 读书养心,聊以度日,但世变之大完全出乎他的意料。他在1949至1950年间的生活、思想和心理感受,因该时段日记各一册,早被焚毁,无法查证。它们记载了中国社会大变革“惊心动魄、 天翻地覆之情景”,也记录了吴宓辞去武汉大学教席,到北碚勉仁和相辉学院任教的思想和心理变化及其痛苦抉择。从他后来的零星书信、文章和“交待”材料里,可以找到一些蛛丝马迹。吴宓离开武汉,先是打算到成都“研修佛学”,“出家为僧”,他说:“1948年秋,我即决意辞卸国立 武汉大学外文系主任职务,到成都任教,目的是要在王恩洋先生主办的东方文教学院研修佛学, 慢慢地出家为僧,并撰作一部描写旧时代生活的长篇小说《新旧因缘》,以偿我多年的宿愿。直 至1949年春夏之交,方能得来到重庆,暂止于北碚勉仁学院、相辉学院。”到重庆后,却因交通困难,不能前往,就暂住于梁漱溟在北碚主办的勉仁文学院,兼在相辉学院任教。1950年,两校合入西南师范学院。后来,他有过后悔,亲朋好友也曾动员和介绍他调往北京和西安高校任教。既然来了,也就不用再去追问他为何而来,而是关注他如何落地,如何与地方发生磨合与纠缠。
实际上,他在1949年4月29日离开武汉大学到重庆,6月份就后悔了。他在给吴协曼的信中 说:“甚悔不应轻离武大,此时欲归不得,前途又无善计。”后来,他一想起4月29日,就感叹不已,1952年作诗“岂竟余生老蜀川,忧危困辱已三年。全身污渎哀心死,恋旧明时恨物迁。渐习核词同伪语,独持深意对浮妍。慰情至计依红袖,梦里生涯便是仙”。1959年4月29日,再作 感怀之作,“堕地飞花已十年,人间何处着啼鹃。旧交纵在非同道,新曲难工只自怜。秘记楹书愁付托,离鸾寡鹄怅琴弦。溪山大好绿如许,急锻密耕少墓田”。他在“自编年谱”里,也感叹:“1949年四月,不回清华,又离弃武汉大学而来渝碚,遂走入相辉,编入西师”,“举动之极端错 误,而祸害久长者也”。1969 年12月,他给郭斌龢写信,谈到自己遭受批斗,真恨“不能早死”,“甚悔前多年,不去清华、北大、陕西师大而留在西南师院,受此种种”。他是真后悔自己的选择,但他终究也没有选择离开。
这里,就有了一个问题。那就是他为什么不离开重庆呢?他的学生季羡林曾在回忆文章里说:“雨僧先生留在四川,没有回来。其中原因,我不清楚,也没有认真去打听。”赵瑞蕻也曾有过疑问:“又听说他最后转到重庆西南师范学院教书了。那时我有点奇怪,心想抗战胜利后联大结束复员,吴先生为什么不回到清华园,重新住进‘藤影荷声之馆’呢?”他在西南师范学院的同事彭维金教授也认为:“就他在西南师院任教的28年来说,无论在外语系、历史系,还是中文系,都未能用其所长,尽其全才。”1961年9月,吴宓到陕西师范学院讲学,见到朱宝昌教授,他自己正被学校批判,在陕西师院却受到热烈欢迎,“未受轻侮”,于是,他感觉该校作风“大异西师”。1964年11月18日,开展社教运动,同事耿振华批评学校领导思想保守、放 纵,不重思想只重知识。吴宓的感受却正好相反:“宓昔恒以西南师院太重政治,用法过严酷。其处罚右派之重且多,冠于全国各校,与耿君所评则适反,可怪也!”学校小环境,紧跟大环境,有样学样,还生怕走样,甚至过之而无不及。任继愈就认为:“吴宓偏偏被安排在最轻视知识的环境中。赶上视人才如草芥的年月。”“轻视知识的环境”是社会大环境,也是吴宓生存 的小环境。
当时学校小环境让他意想不到。1964年12月24日,他以“君子恶居下流”,“危邦不入,乱邦 不居”为戒,心想“倘宓不在西师,祸累当不至如此之重也”。社会大环境会让吴宓不能不受批判,学校小环境却让他多次受批判。实际上,中国社会现代化,一直以城市为中心,从封闭到开放,由东向西,呈梯级延伸扩散。越是西部或乡下,其开放程度反而越低。在人们一般的思维习惯里,会自以为环境越偏僻,管理就越松散,也就会有更多的个人空间,但在一个资源相对贫乏的年代,其情形也许正好相反。处中心者,资源越多,活动越多自由,处边缘者却想尽办法争取 资源,积极主动,甚至以激进方式实现目的。吴宓偏居西南,身负盛名,名望天下,自然会树大招风,颇有典型性和代表性,加之他做事认真,有热情,不超脱,爱冲动,许多运动事件和表态事项都会找上门来,落到他的头上。
晚年吴宓身处四川,喜欢聊天,谈得最多的人是陈寅恪和吴芳吉,最多的事是他和毛彦文的爱情,偶尔也评论同事和川人。他认为“蜀男女皆富于情,敏于感。蜀士率读诗多而能吟咏”,才情有余而品性不足。川籍学生人本“聪明”,“性于文艺为近”,擅长图画,对传统诗词韵律,“无人教授,少人通晓”,也就“难言”文学之成绩,“前途亦极黯淡也”。川中文人 虽“资性聪明”却少有“独立特行者”。说到蜀中“五老七贤”之一的赵熙,认为他的诗写得好,他的书法却“极恶劣丑怪,今蜀人犹多效之者,误也”。他不但评论四川人,还评论其同事,如认为西南师范学院中文系“四老”之一的赖以庄,生平甚用功,能博览,然“无卓越之品格,圆滑应世,又无坚定之宗旨,惟喜述说人之科名家世及著作轶事等,若持与碧柳较,实有霄壤之悬隔也矣”。有一个四川人是例外,那就是吴芳吉。吴宓偏爱吴芳吉的诗和人,世称“两吴生”。在他眼里,吴芳吉是天才,是中国的雪莱。1949年后,他将吴芳吉作为情感依靠, 制造为诗歌神话,不时谈及他们间的情同手足关系。他还曾告之身后事,愿以僧服入殓,葬在江津黑石山吴芳吉墓旁。吴芳吉是吴宓的一面镜子,也是四川诗人和文人的标杆,在他眼里,“蜀士多资性聪明,而处境丰裕”,“奔走末职而洋洋得意”,“皆 《浮华世界》(名利场) 中之人 物”,只有“碧柳乃真特立独行者”。又说成都“文士生活,亦不外美馔佳肴,痛饮连醉,再则赌博跳舞,全系享乐纵欲生活”,“至于爱情之理想与实际,亦非徒事享乐之名士所能知也”。他虽极为赞赏吴芳吉,但也认为他有四川人的通病,“四川人皆轻躁。碧柳尤喜动,恒无计划、无希望”。当然,他说的是四川人,也是说他自己。吴宓也时犯轻躁之病,常订计划,但多不执行,只在口头说说,或仅仅记录在日记里,就算了事。吴芳吉因病早逝,在他的家乡——重庆,吴宓就成了传统文化在当代的守护者,实际上,在吴宓内心,始终拥有这份文化情结和使命。
二

吴宓1937年于清华园
吴宓是有机会离开重庆的。1961年,他的女儿吴学昭两次到重庆和学校看望他,5月在重庆渝州宾馆匆匆见面,就劝说吴宓探访旧友和调离重庆,可“发挥宓之所学就特长,完成个人有系统之长篇著作,胜似在西南师院仅以教课之余事,作附属性之研究(如今之注释)而不为人所重”。8月在学校见面,继续关心吴宓的生活和学术著述环境,为“生活之丰裕安适”和“著作之自由方便”考虑,她希望父亲能调职(或退休)移居北京,他在重庆的“居处、饮食、生活种种简陋粗秽,远不如北京安适”,如到北京,可“在文化潮流之中心魇饫图书载籍,先得见科学 之新资料,更与学者文士往来切磋,则编述与创作两可有成”,可将“所知旧时代之生活、旧学术 之精华,尽详尽多写出,留作后代宝贵之资料”,也可“进行自己之创作”,认为吴宓珍爱的 《吴宓诗集》,“其效果极微,若夫宓昔拟撰之 《人生哲学》及长篇小说 《新旧因缘》仍可作出,但观点立场须作相当修改”,总之,应“心情开朗,态度积极,多写作,多刊发文章,但不拟发刊而藏留于后世之著作,亦可撰写”,她还希望父亲写文章,以引起学术争鸣,并建议他“出游各地, 以新耳目”,多与新旧学者朋友“谈论”和“切磋”,即使不考虑调离,也“必须从事并发表其著作”,“改其久久沉默之态度,以文章著作多与世人相见”,这样,才可“对新中国、对社会主义文化有贡献,亦可不负宓自己之一生也”。
吴学昭劝了一天一晚,他却不为所动。他不愿离开重庆,习惯了这里的生活,如“环境改变, 人事生疏,精力衰耗,应付难周,当局实难位置宓,宓亦更难于自处”。他还有更多隐忧和担心。吴学昭建议他去北京,其母陈心一可为吴宓“抄写书稿、担任助理编辑”,这是吴宓内心极不情愿的事,他不愿意与陈心一复婚,除了日记,也没什么稿子需抄写。他一个人生活习惯了,对两人在一起生活心有恐惧,在他的内心依然保持对毛彦文的美好印象。到了北京,虽好友多了, 让他担心、害怕的事也多了。1962年,在给李赋宁的信里,他就解释了其中原因。他深知“到北京之好处,不待细说”,仍决定“无论如何,不长居北京,不在北京工作”,理由是已有友生“督责”自己改造,若居京,“反与友生暌违”。北京大学教授中的李赋宁、王佐良、杨周翰等的马列主义学习好,西洋文学知识、学问,“其生动之文笔、著作,远非宓能及”,“宓来北大,成为无用之人,有如一位贫穷的老姑太太,回到贾府受王熙凤等之……”。另外,还有一条理由,“家中人 均进步,长年同居,反多心情上之碍与语言行动之不自由(服从党团之政令及思想,此则全国无异)”。
也许换一个环境,他的生活和命运会好一些,当然这也只是假设。他还有更大的“孤悚隐衷”,“宓之知命信佛,轻生死、乐消闲,宓之不肯写白话简字文章刊布,宓不愿在新时代得名受誉,宓不愿居住辇毂之下,与当代名流周旋,宓之许由与伯夷、叔齐思想,‘天子不得而臣,诸侯不得而友’,岂甘特制新衫,以干谒学术界之新贵人,容悦居上流之旧友生,以为宓进身扬名之地哉?”其志向如此,何谈移居?至于吴学昭建议的多刊发学术著述,多与名家交往,更是吴宓心存恐惧和反感之事,他愿意交往的大都是有独立人格、不与时代合作的旧派人物,学术著述更是不愿刊布,即使去了北京,他也没有什么热情和兴趣。在民国时期,吴宓对学术研究都不算勤勉上进的,何况在这个时候,他的心思早不在此,而放在写作“日记”上了。但他听从了出游的建议,说不上可“新耳目”,却可见见老友,以解多年相思之苦。从 1961 年 8 月 23 日至 9 月 22 日, 外出一个月,先下武汉,转广州,再北上北京,后从西安返回重庆,受到了朋友和亲人的热情款待。此行意在探亲访友,也是学术之旅,更是文化的契阔。
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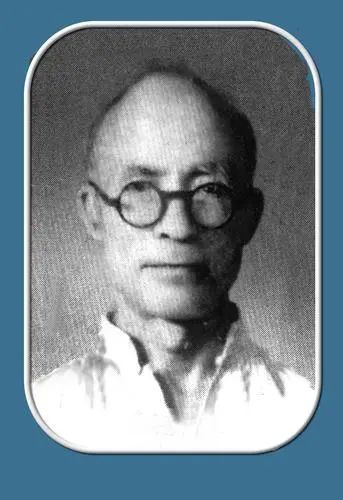
吴宓晚年照片
吴宓喜欢四川的山水和饮食。他虽然比较古板,也不是一个十分有情趣的人,但却爱美,爱诗,包括美景、美食和美人,向往大自然和诗意之美。他“能随处发现大自然之美并沉醉于其中”,十分向往乡民和市民生活的散漫、自在而自得。“乡野之农民,大城市之人力车夫,虽劳苦穷困,然其每日工作毕后,必坦腹列坐,吸旱烟,饮清茶,共相谈笑,有栩栩然自得之乐,不 知周秦楚汉,何分南北新旧,更不问君主与民权。尔时酣嬉休暇之愉快畅适,熟知我者,此乃真自由,真平等,真幸福矣”。时代变了,人们“工作皆极紧张,其生活乃极严肃,其心情乃极烦苦,特相互竞赛、相互监视,随众依式,莫敢自陈而已”,男女老少“皆学得残虐斗杀之心情,愤 戾骄横之姿态,嗔目切齿,闭唇握拳,而中国数千年温厚祥和之风,优游暇豫之容,从此永绝矣”。他以白描之笔勾勒两幅画像,一幅“坦腹列坐,吸旱烟,饮清茶,共相谈笑,有栩栩然自得之乐”,一幅“愤戾骄横之姿态,嗔目切齿,闭唇握拳”,形象逼真。1961年5月13日,在潘家 坪招待所 (今渝州宾馆),他与女儿吴学昭见面。吴学昭劝他到外地出游,探访旧友,亦可商量调离重庆,发挥其特长。第二天,在返校的路上,他就被沿途风景和校园美景吸引住了。“午饭后, 深阴欲雨,车行途中则大风。此时忽放晴,远看四山青碧如画,西南师院山坡草木绿被如细毡。入校,则清幽整洁,真觉不忍离去此地。况吾生已成若干阶段,今之末段,岂容插入‘京国集’中,而乱我之步骤,违我之情志耶?学昭之议,宓似弗能从,终留此为佳耳矣!”
对北碚及西南师范学院校园之美,他更是赞赏有加。他曾带学生在校园里广柑树林里欣赏风景,“我喜欢在春天的黎明时来这里散步。薄雾香花,绿叶素荣,可真是个人世的伊甸园”。1960年,学校10周年校庆,他的祝辞很美,“十年树木已成林,楼阁峥嵘气象新”,“济济良师从此出,山如画黛水鸣琴”。1962年,他给学生李赋宁的信中说:“宓老年心境平和,乐天知 命,对人有恩无怨,在此与各方面关系均好。北碚为山水窟,风景极美”,“故宓决愿终老此地”,“葬于北碚峡口之山巅(公墓),山水、烟云、风景至美”。“山水窟”言山水绝佳之处, 苏轼诗 《将之湖州戏赠莘老》云:“余杭自是山水窟,仄闻吴兴更清绝。”1964年3月15日,吴宓大病初愈,与雪(张宗芬)和小孩到嘉陵江边观江水,捡石子,在石滩上看轮渡,“嘉陵江水 犹碧绿,春景至美”。3月29日,受蓝仁哲之邀,到北碚歇马场四川外语学院校园,欣赏美丽春景,“绿水垂杨,风景静美。既入校,穿葡萄架长路,而至教学楼前,则见红、绯、白色之桃花树多株,杂以李花树,密植路之两侧。花既盛开,而落英缤纷覆路,实甚美观”。一路上有雪 (张宗芬)及子女伴游,因临时有事回学校,未能前往磨滩观赏瀑布“奇景”,“宓今日之游殊乐,身体甚觉舒适”。1971年3月17日,春天到了,吴宓感受到春天的气息,“昨今两日,宓始注意到桃花已开,桃花瓣飞落路上。阳景春浓,宓极欲步行至李园湖畔,观赏两年前所识之春景,而唐、曾及其他友人均戒宓‘勿外出走动,免为人所注意,而招来祸患’,故终迟惑不敢 径行”。这时,吴宓的腿脚不便,身份又特殊,外出有意外麻烦,吴宓喜欢自然美景,没有办法,只能远观或想象春天。这里的“唐、曾”即曾先后帮助吴宓做家务的女工唐昌敏和曾婆婆, 时间最长是唐昌敏。
吴宓不仅喜爱美景,还爱好美食。他喜欢与三两知己聚餐或茗谈。吴宓能喝酒,爱品茶,却讨厌抽烟,对抽烟者深恶痛绝。他的酒量不大,三两知己聚在一起,主要是以酒助话,以酒解闷。1971年9月8日,他在梁平曾将就一枚煮鸡蛋饮白酒,9日靠一枚馒头饮白酒,10日,“一馒有半,饮白酒,食煮卵一枚”,11日仍用鸡蛋馒头饮白酒,饮酒解愁,他内心藏有排遣的苦闷。高兴时他也饮酒。1972年元旦,那是一个极为平淡的新年,“无庆祝大会,无团拜,亦无私人拜年, 亦无乐歌”,“新年第一日,宓平安无事,且能安静读书”,一早“红日如火球,为之欣快”,早餐食花卷和鸡蛋,“饮白酒甚多”。在生活料理上,他“远不如常人,有时甚至显得幼稚可笑”。他不会做饭,常去同事朋友家,“久坐”,“论学”,友人热情招待,喝酒成自然之事,在他的日记中,有不少“饮白酒一杯”的记录。1951年1月12日上午小组学习,会后,吴宓访穆济波,“饮广 柑酒”,以诗唱和,享受诗酒人生。13日晚又去穆济波家,同周邦式饮白酒,“谈诗及佛教”。1月22日,饮广柑酒。2月2日,去李源澄家饮白酒。4月2日,在周邦式家,“饮茅台酒半钟”,周还帮吴宓修改诗歌。1952年11月2日,在北碚公园附近的“对又来”酒店,饮白花露、葡萄酒、 大曲酒共3小杯。1962年9月22日,他还购得五粮液一瓶,价格4.5元。1963年10月11日,友人 在北碚下半城松鹤楼为吴宓祝70岁寿辰,他与其他两位共饮五粮液3两。1961年4月30日,吴宓分得五月饭菜证,“今晚遂得食米饭三两及蔬菜,得饱”,还分得一大瓶五粮液,“遂以牛皮菜下酒,独饮一杯”。拌牛皮菜喝五粮液,虽有些浪费,但也毫无办法。
吴宓不喜欢社会活动,但喜赴宴和聚餐。他多次到西南农学院张劲公宅吃饭,“肴饌颇丰”。1956年9月6日又赴宴,菜肴丰盛,饮葡萄酒,7日再与人合请对方,肴馔丰美,进广柑酒和白酒。12月9日,又与几位同事到张劲公宅吃饭,“是日肴馔尤精美,进桑葚酒,食米饭、馒头,深酣饱”。1958年张劲公调至江苏师院,不再有记录。1959年7月3日,中午赴赵少咸、庞石帚宴请,宾主九人,吴宓对菜肴印象深刻,“肴馔丰美,海参席,以奶汤鱼肚及软炸鸡肝、葱、酱二味为最佳(席费十五元云)。宓得尝此席,如地狱中人重来人间天上,遂恣食,饮白酒数杯,半醉 矣”。吴宓自己不会弄饭菜,却喜品各种美味,吃到美味,犹如从地狱中“重来人间天上”。1960年5月9日,参加省政协委员视察活动,给他最大感受是吃得好,“肴馔更丰盛,致多食”,“此次政协委员参观,实游玩与饮食享受而已。幸甚”。1964年9月14日,与朋友聚餐,有诗句“最爱家厨特馔美”。1965年7月11日,到重庆师专周邦式宅,周邦式夫妇热情招待。其夫人盛 载筠忙着“治馔”,“手制肴馔丰盛,皆宓平日所嗜者,冷碟四:松花皮蛋、豆腐干、烧鸡、泡姜。热菜三:红烧猪肉、香菇豆腐,丝瓜豆腐汤,广柑酒。镇江金山牌之名醋”。可惜“美味太多”, 让他“应接不暇”,又逢“天热”,各述近况,说话多,他“仅进米饭小半碗,但共式饮广柑酒罄 半瓶”。经历大半年运动,他身心疲惫,能有闲暇见到老朋友,还有好菜好酒,吴宓的愉快心情也就可想而知。
吴宓还喜欢美女,他毫不忌讳地一一记录在日记里,甚至有些以貌取人。1951年1月9日,有男生女生报名参军。说到某女生,吴宓认为她是“本年级最美之女生”,却哭泣不止,由另一女生代读志愿书。另一女生也是“明媚鲜妍,有才,通达而大方”。他眼中的女学生主席,却“貌最平庸”,但“深沉老辣、坚决明细”,为国家需要之“标准人物”。让人有些讶异的是,吴宓在日记里喜欢记录学生、邻居和同事女儿之美貌。如在批斗会上,看到女生发言者,说她虽“明眸皓齿,燕语莺声”,却“作出狰狞凶悍之貌,噍厉杀伐之声”,让“久恋女子”的吴宓也深感“厌离”,而叹为观止、不可理解。人们私下津津乐道的一段故事,就是吴宓与雪(张宗芬 的情感 纠葛。他们交往从红颜知己到红颜不知己,吴宓在她身上投入了太多的感情、时间和金钱,同情其命运,自是主要原因,也还有另外因素,就是吴宓内心藏有美女情结。在刚刚认识时,吴宓认为她是“全校女员女生中最美之人”。1952年12月14日,到礼堂听报告,看到她坐在左后排, 也觉得她“美艳绝伦,全校之盛饰华服之太太小姐为之减色”,“会散”后,“又见雪与女同事二人,左右夹持,连手俯身,冲大风,疾驰而过,出宓等之前,宓怜其衣薄而居远”。吴宓真是多情的种子,已近60之人,仍有如此浪漫心情。1958年6月28日,吴宓参加学校歌咏晚会,登台站在第三排中间位置,唱了4首歌,“随众应景”,但看到“雪”(张宗芳),虽容华大损,仍为地理系之美人。1973年1月14日,雪来“久坐”,已至52岁的她,在吴宓眼里,仍“白润丰美,视为 青年女子,且情意似甚殷挚”,只是感到“其思想,则趋时从新不喜旧”。
1964年9月13日,他观看电影《北国江南》,秦怡饰女主角银花,其面貌让吴宓想起了学生吴静文。吴静文外形漂亮,此时正在合川参加“四清”运动。1955年5月10日日记有记载,吴宓在讲课时,“见史三女生吴静文坐前排正中,两年不觏,惊其美。第七节续讲,伊已远去,岂有觉 而为之欤”。“史三”即历史系三年级。1956年9月27日记载,吴静文一毕业就与历史系秘书郑亚宇结婚,吴宓送礼金一元。此后,吴静文多次向吴宓问学。后来,吴静文夫妇被调往合川中学担任教师。吴静文来告别,甚是悲泣,“泣时,愈增其美,宓不忍视”,吴宓也很伤感,“勉慰之”。他认为学校只重视其英文和西洋文学,不知他还深通并能教授中国古典文学,“独有吴静文者,自愿专从宓学此科,其人又和善而极美,深惬宓心”,“宓之伤感悲愤,实不减于郑亚宇及吴静文夫妇本身者矣!”吴静文夫妇离校辞行前,还吴宓书,并写诗,“呈俪影一方”,吴宓粘存。到了1963年11月30日,美术系一美女老师因下放来辞行,又让他想起吴静文夫妇,感叹:“今已一载, 甚矣,美人才士之多薄命也”。吴宓甚赞邻居钱泰奇教授两个女儿之美,还为美女编序号。1973年1月18日,“上午9-11此间第一美人钱国昌来,第二美人刘哲志亦携幼女钟一清来,宓幸而由二美人陪导、护卫同出,由解放路折入中山路而抵百货商店”买棉鞋。“第一美人”“第二美人” 近似玩笑话,却堂而皇之地出现在吴宓日记里,可见吴宓对美女的钟爱程度。他还为美女打等级。1月26日,访钱泰奇、孙荃夫妇,“初见其长女钱小萍,美而白皙”。钱小萍、钱国昌都是雕塑家 钱泰奇女儿,其子钱国华还随吴宓学过外语,听过吴宓讲《红楼梦》。1973年6月2日,又说钱小 萍“甚美秀”,钱国昌“则丰艳”。10月1日,他带吴须曼拜访钱泰奇夫妇,见钱小萍“毫不装饰,而宓益觉其美”。12月19日,刘玉琼来,求吴宓讲毛主席诗词,“此女亦秀美可爱,然不注意听讲,亦不热心向学,不可教也”⑥。人虽秀美,却不好学,让他感到没法“教”。吴宓喜欢美而好学之女性,所谓“红颜知己”者也。
吴宓晚年不离开重庆,在我看来,主要有四点因由。一是吴宓喜静不喜动,对变化的未知性一向存有顾虑和恐惧;二是到外地开展学术活动以及邀宠之遇非他所愿,还心存恐惧;三是在经历陌生、抱怨和愤怒之后,他已熟悉了学校环境,习惯于重庆生活,而且,还很有些许挂念。他对日常生活的满足,也是对传统文化的变相坚守。思想文化不仅是一种价值理念,也是一种生活方式。四是为他提供离开重庆的机会,正是他受到最好礼遇之时。1961年的吴宓,已多年担任四川省政协委员,还开始招收研究生,接受访问学者。当年2月15日,正月初一,吴宓上午随郭豫才、张宗禹、许可经(分别为历史系、美术系、音乐系主任)到学校领导家里拜年,下午,学校领导6人回访,给吴宓拜年,中文系书记、系主任、教研室主任、教学秘书4人和私交朋友8人纷纷来拜年。这可说是吴宓解放后在新春佳节最为荣光的一天。此后,全国运动不断,学校也一片混乱,友人自身难保,再没有人来找他谈论调离之事,他也只好呆在重庆了。
一个人的迁徙,古人多受贬谪,今人则原因多多,或求学,或谋身,或婚嫁,或旅游,不一而足。吴宓与重庆,有情有缘,先缘后情。它不由思想观念而选择,而被工作和生活所确定。先有正打歪着的偶然,后有特殊时期单位制度的绑缚,也有机遇的不巧合,更有日常生活的眷念和个人性情的习惯。如此种种,成为吴宓晚年留在重庆的偶然或必然,谈不上幸运与不幸,遗憾和怨怼。他的“在此”而非“此在”,他没有更多的选择,只有接受和忍耐,习惯成自然,自然久了,反而生起不少留恋。在吴宓身上,并没有体现出存在主义哲学对“此在”的超越和反抗,而是对“在此”的 种种生活的忍从,以及如同螺蛳壳里做道场,坚持日记书写,以求得情绪的宣泄和精神文化的自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