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只有放弃自己的心爱之物,才能有朝一日重新拥有它
没有阅读,就没有写作。这是萨特《什么是文学》一书的中心论点。“创作行为只不过是作品生产过程里的一个不完整的、抽象的时刻;如果世上只有作者,那么他可以随心所欲地写作,但是作为‘对象’的作品就永远不会问世了……写作行为必然牵连着阅读的行为,阅读是写作行为的辩证的关联品。”
自然,也有另一种观点,它出自马拉美的《关于书》:“书册是没有人称属性的,就像它会与作者脱离一样,它也不会呼唤读者……作为事实,作为存在者,它总是遗世独立。”只要作者写出了一本书,它的存在就不需要以读者为前提。书存在,写作行为是一种自在的存在,它并不要求任何形式的阅读。
于是,按照萨特的社会学和辩证法的逻辑,“写作的证明在于阅读”;马拉美式的本体论和唯心主义则相信“写作的证明在于写作”。可还有第三条道路,即“阅读的证明在于写作”。这一主张符合经验主义、反理智主义的路径,因此它最好用实用主义的语言——英语来表述;此外,它也符合普鲁斯特这位众人皆知的热爱英语文化的作者的口味,特别是它正好与普鲁斯特对一切没有创造性可言的阅读的不信任相吻合。
当然,我们还可以设想第四种可能,它让我们想到格特鲁德·斯泰因的主张。对普鲁斯特来说,“阅读的证明在于写作”抑或“反对阅读”的说法,意味着把他亲自构想的两个标题组合在一起。其一是《驳圣勃夫》:普鲁斯特曾设想过把《驳圣勃夫:一个清晨的回忆》这一标题用在一部混合体裁的作品上,他从1905年开始就在构思这本书,并且在1908年和1909年实际投入了写作。其二是《论阅读》,这个标题原用于普鲁斯特为自己所译的约翰·罗斯金的《芝麻和百合》一书所作的序言,不过该文虽在1905年后连载于期刊,但后来收入《戏作与杂文》一书时改名为《阅读之日》。
《论阅读》与《驳圣勃夫》,再加上若干戏拟式的仿作,便是普鲁斯特在全力投入《追忆》的写作之前的主要工作,也是他从“翻译他人”转向“表达自我”的关键阶段:1906年,当他丧母后不久,普鲁斯特在致与他合译罗斯金作品的玛丽·诺德林格的信中说得很清楚:“我已永远结束了翻译他人作品的工作,尽管我妈妈很喜欢我这样做。至于表达我自己,我已经失去了勇气。”1904年之后,他还对诺德林格讲过,他们一起从事的翻译工作主要是一种消遣,“我想,我会拒绝一家威尼斯书商的请求,他们要我再去翻译罗斯金的《圣马可的安息地》。如果不这么做,我大概至死都无法通过写作表达我自己。”
由此我们就会懂得,《论阅读》和《驳圣勃夫》之所以被视为关键性的文本,正是因为它们恢复了作者的勇气和通过写作、通过小说形式表达自我的意志。按照普鲁斯特的构想,《驳圣勃夫》本应通过与母亲对话的形式对圣勃夫的方法展开批评,用作者对阿尔弗雷德·瓦莱特的话说,它会是一部“真正的小说”。事实上,也正是这部源自批评随笔的“真正的小说”最后升华为《追忆》,而在真实的《驳圣勃夫》一书里,被论述的主题是文艺美学,或者更确切地说,是叙述者所使用的技艺。
如果说《驳圣勃夫》是《追忆》最终告成的前提,那么《论阅读》的决定性的分量也同样不可轻忽。不过,这主要不是因为这篇文章提前道出了《驳圣勃夫》的论点,即“圣勃夫误读了他的时代的几乎所有的大作家”,也不是因为它对童年的描述预告了《在斯万家那边》;我们毋宁说,这篇文章的价值在于它和《驳圣勃夫》一样采取了“批驳”的立场。它懂得“否定”的意义,在其语境中,其矛头指向了阅读行为。它仿佛暗示我们,对阅读行为——恰切地说是某些特定类型的阅读行为——的揭露或者放弃乃是从事写作的一种前提、一个条件,似乎普鲁斯特就该提前否弃阅读,否则就难以投身写作。后来,作家在《重现的时光》中写道:“我们只有放弃自己心爱之物,才能有朝一日重新拥有它。”凡此论争性的措辞不免有夸大之处,而我们唯有潜心深思,方能逐渐领悟普鲁斯特最终希望达到的是怎样一种“好的阅读”——作家后来在《追忆》终篇之处颂扬了这种理想的阅读,它的对象必得是那些能够真实表达自我的人的“内在的书”:“这样的阅读本身就是创作。”
我们在此讨论的是普鲁斯特对阅读的感受以及围绕这种感受产生的诸种观念。从《追忆》开篇处,从它的第一页起,叙述者入睡时就总是手不释卷:“睡着的那会儿,我一直在思考刚才读的那本书,只是思路有点特别;我总觉得书里说的事儿,什么教堂呀,四重奏呀,弗朗索瓦一世和查理五世争强斗胜呀,全都同我直接有关。”此处,生活与阅读已经融为一体,阅读成为《追忆》的一个基本题材,也是其意义生发的扭结之一。不过,我们也需要避免普鲁斯特批评中那种将作品等同于“护教论”的倾向,按照这种已成俗见的看法,“阅读”简直就是《追忆》的中心主题——普鲁斯特被视为法国文学史上继蒙田之后的又一位伟大的读者,导致《追忆》全书充满了引文、指涉和隐喻,其“互文本”庞杂无比,成为一种不可思议的丰富的综合。可事实上,这样的结论很难证实,而且我们有必要把阅读对普鲁斯特的写作所具有的“质的意义”与作者具体的阅读和《追忆》的“互文本”所具有的“量的意义”区分开来。在世纪之交的那代人中,论对有产者文化传统之掌握,普鲁斯特可谓罕有其匹,他的家庭环境使其非常熟悉经典的文学作品,而学校教育对他而言相对没有那么重要,也不是他最了解的领域。如果说我们感觉其小说世界里的学术世界在比例上并没有那么突出,那是因为其中如颓废派文学等主题在20世纪已经没落,不为今人所熟知。对他笔下的音乐、绘画,我们也可作如是观。
(1)图书馆
短篇小说《巴尔达萨·西尔万德之死》是普鲁斯特在1896年出版的处女作《欢乐与时日》中的第一篇作品。从这篇小说开始,书中接连5个短章前面都冠以题铭。其中有的出自爱默生,普鲁斯特在20岁时满腔热情地发现了这位美国哲学家的世界;有的出自塞维涅夫人,她是作者的外祖母纳代·魏尔夫人最心爱的作家;还有两个题铭出自莎士比亚《哈姆莱特》和《麦克白》中最经典的段落,它们就像拉鲁斯词典中玫瑰色的页面一样为人熟知。最后出现的是马拉美《海风》一诗的第一句:“肉体是悲伤的,呜呼!”普鲁斯特对马拉美的引用到此戛然而止,这显然象征着他并不像马拉美那样在图书馆和书籍面前感到焦虑。马拉美原诗中后续那些庄重的、宣示性的句子,被引用者删去了:“肉体是悲伤的,呜呼!而我已读过所有的书籍。”不,普鲁斯特的焦虑,例如他在夜晚入睡前的不安——想一想叙述者的母亲给他朗诵《弃儿弗朗索瓦》,他刚刚在巴尔贝克结识的夏吕斯走进他的房间,给他带来贝戈特的最后一部小说,以供他消遣——是与马拉美面对图书馆,面对“所有的书籍”(或者那“唯一的一本书”)所感受到的那种根本性的焦虑截然不同的。
普鲁斯特很少出入图书馆。奇怪的是,他唯一从事过的职业,倒是在马扎然图书馆担任职员;不过,他也很快就因健康问题而从那里辞职。普鲁斯特并不喜欢图书馆,《追忆》中提及图书馆的几处地方无不带着揶揄的口吻。在小说里,图书馆简直就和遗忘之地、垃圾场和墓地画上了等号,那些早已无人阅读的书籍只有在这里才能找到存身之所,“正如将某一种书籍存在国立图书馆一册,不这样,这本书就可能再也找不到了”。
《论阅读》一文对学究式的,即圣勃夫式的阅读方式语多讥刺,这种以寻找真理自命的行为在普鲁斯特笔下沦为漫画式的图景,它“好似一种附着在书页上的物质性的东西,仿佛我们只要向图书馆里的书架伸出手去,就能采撷到这由他人之手酿造的蜂蜜”。
在普鲁斯特的世界里,也有某种东西位于书籍所象征、书籍所造成的死亡的对立面,那便是“一种既古老,又直接的传统,它在口头代代相传,世世接续,原先的模样虽说已经难以辨认,但始终具有活跃的生命力”;这一传统才是人民所拥有的、真正的知识,女佣弗朗索瓦丝和教堂的雕塑师们都是人民的代表。不过,还要数奥黛特这个形象对学究的讽刺最中要害,当斯万显得三心二意的时候,她倒是直截了当地说:“博览群书,埋头在故纸堆里,该多有意思啊!”
图书馆并不能让书籍增辉,它也不能让人产生阅读的愿望,事实恰恰相反。《追忆》中有两处提到国家图书馆,上下文及其含义相同,因此颇能显现作者的观念。当叙述者第一次在斯万家做客时,“他指给我看他认为会使我感兴趣的艺术品和书籍,虽然我毫不怀疑它们比卢浮宫和国家图书馆的藏品要精美得多,但是我却根本不会去看它们。”
另一处地方与斯万的女儿希尔贝特有关:“希尔贝特对某位高雅的夫人感兴趣,因为这位夫人有吸引人的藏书和纳基埃的画,而我这位旧时女友是不会到国家图书馆和卢浮宫去看这些画的。”
与他们对私人艺术展的青睐不同,叙述者和希尔贝特都贬低公共图书馆和博物馆的价值。他们两人的轻蔑并非与附庸风雅的做派无关,这或许是受斯万影响的结果——斯万在小说开篇处大梦初醒般地宣称,“对那些确有精义的书,我们一生中总要读上三四次”。这样精英主义,热衷上流社会品位,讲究“物以稀为贵”的原则是与图书馆的设置格格不入的。勒格朗丹也讲过:“说实话,这人世间我几乎无所留恋,除了少数几座教堂,两三本书,四五幅画。”这也就解释了为什么斯万认为,为了获得它们应得的普及度,某些著作——比如帕斯卡的《思想录》——不妨在报纸上刊登,而社交场上的名册却应该印成切口烫金的精装版。当然,一味讲求书籍的精致也会带来矛盾:斯万一家起初对书的品位是偏重其版本的精美程度的,但他后来遇到了一个普鲁斯特在《驳圣勃夫》里已经点出的重要问题:对盖尔芒特先生来说,既然他所有的书籍都是同样的精装本,“那么《欧也妮·葛朗台》(Eugénie Grandet)与《海洋公爵夫人》之间相近的程度,就要远远高于《欧也妮·葛朗台》与某一本同样由巴尔扎克所写,但平装本只卖一法郎的小说的相似”。在书的“物质性”(斯万所说的“切口烫金”和盖尔芒特先生眼里的“柔软的平纹薄花呢”)问题背后,还隐藏着对书的形式,即“文学性”问题的考量——毕竟大作家与平庸作家的不同(这种不同是斯万所承认,而盖尔芒特先生所无法理解的),就在于大作家的著作无论用《圣经》用纸印行还是印成一法郎的平装本,其价值都无所谓增减。
无论如何,图书馆都不是普鲁斯特心仪的地方,在他心目中,它并不比报纸或者一法郎的平装本更加珍贵。作家的各种文字都说明他看重的是珍本善本(无论就书作为物质实体还是内容的载体而言都是如此),而且还得是私人收藏的版本。说起来,我们上面的引文之所以要紧,还在于它们把卢浮宫和国家图书馆联系了起来(尽管只是为了讥讽贬低它们),也透露出“书”与“画”之间的本质关联。何以为证?《让·桑特伊》中的画家变成了《追忆》中的作家,即贝戈特。
(2)恋书癖
图书馆让普鲁斯特无感,在于其收藏、整理书籍时泥沙俱下鱼龙混杂的乱象,在于其抹平一切差异的理念——这倒是符合民主制的义理——即使珍本善本在图书馆中也不能不服从这样的原则;相反,纯正的对书籍的热爱总是见于那些品位高雅的业余收藏者身上,他们对那些真正值得收藏的书总是心怀虔诚和敬意:以斯万为例,他的身上就总是带着“收藏者的傲气、自私和欲念”。
这样的内心倾向也见于《追忆》的叙述者,他把书册视为物质实体,对它怀有同样的激情,而这种情感在他看来可以上溯到童年时期。早在《让·桑特伊》一书里,孩子们就是带着真正的爱去阅读童书,这种爱指向阅读的程式,仿佛在爱欲的倒错中,爱改变了指向——爱恋的对象成了“爱”本身,而不是被爱之物:“我们不会一心只在乎书里说了什么,而不去牵挂手里摩挲着的书页。”如果激情倾注的对象又变成作为物体的书册,而不再是阅读程式,那么爱欲的倒错就几近“恋物癖”:“当我们更年轻的时候,在我们眼里,书和它要讲述的东西是不可分离的。”于是,普鲁斯特开始热情洋溢地描述书册的外观、书上的徽章:“它的形体蕴含的魅力与我们喜爱的故事、书带给我们的欢愉完全融为一体。”在这一页上,连续三次出现对书页上气味的描写,这是一种“清新”的气味,它远离图书馆尘灰满布的藏书里的那股土腥气,倒是“和我们放玫瑰饼干和内衣的橱柜里的气味一样清新可人”。这清新的气味仿佛可以入口,就像“抹上玫瑰色奶油的干酪,大人允许我把捣烂的草莓倒在干酪上面”,又似从加米商店买来的昂贵的“玫瑰色饼干”、玫瑰色的山楂,总之,像一切因为有玫瑰色而变得价格不菲、勾人食欲的东西。
不过普鲁斯特用年幼无知来解释激情指向的迁移:“那时我们读过的东西很少,我们阅读的经常是自己拿在手里的第一本这种开本的书。”这么说,仿佛“第一本”成了“恋物癖”的托词。这样看来,怪癖会随着年龄的增长而消失。怪癖的消失还有另外一种情形:由于在《让·桑特伊》的同一页里,这一怪癖还包括对作家的崇拜,包括为心仪的作者——此处是指罗伯特·路易斯·史蒂文森,他的主人公贪婪地阅尽世间一切书籍——树碑立传的强烈愿望,我们也可以想象,鉴于《让·桑特伊》的主人公和《追忆》的叙述者在遭遇作家和艺术家,如贝戈特、埃尔斯蒂尔(Elstir)等人的真身时感到的失落,那么对作家的崇敬之癖恐怕也会随之消失。
恋书癖的消失还和阅读者的身份有关。除孩童时期对书册的爱恋以外,恋书癖主要表现在贵族们的阅读行为中,他们的癖好简直把圣勃夫式的习性推到荒谬的程度。简单地说,他们的阅读行为的对象不是文本,而是作为物质实体的书册,或是书背后的人。《驳圣勃夫》中盖尔芒特先生从父亲那里继承下一座书房,其藏书都是精装本,并不按作者的姓氏分门别类:“他把这些封皮一模一样的、令人快慰的书混在一起。”《追忆》中那位把大仲马当作巴尔扎克的盖尔芒特亲王也继承了这一风格。回到《驳圣勃夫》里来,书中描写的贵族式的恋书癖倒未必是出于对作者们之间差异的不屑,毋宁说,它的确近似于叙述者童年时代的热情:“我得承认自己是理解盖尔芒特先生的,因为我的整个童年也是以同样的方式读书的。”“同样的方式”意味着读者首先关注的是书册的物质性,阅读时仿佛这是与书册的第一次相遇,“就像第一次透过一袭裙衫看到一个女人的样子”。普鲁斯特继续说道,“寻找这样的书,这就是我作为书籍爱好者唯一的行事方法。我初次读某书遇到的那个版本,那个给我带来原初印象的那个版本,便是我作为‘书痴’眼中唯一的‘原版’”。这些文字几乎原封不动地被搬到《追忆》中一个至关重要的时刻,其背景是盖尔芒特亲王的书房:按照《重现的时光》的叙述,这一天的傍晚,当叙述者抵达盖尔芒特亲王府上时,他看到了亲王的藏书,不由得浮想联翩:“倘若我想当一个像盖尔芒特亲王那样的珍本收藏家的话……”不过,叙述者并没有对书籍中讲述的历史、人物的生活产生兴趣,倒是探索起他自己的往昔,而这往日岁月是透过他童年时阅读的书籍,乃至旧日读物的物体形式显现出来的。“就眼前这一册册书的本身而言,看着它们活生生的样子,我还是能对它们发生兴趣的。我觉得作品的初版比其他各版珍贵,可我说的初版是指我首次读到的那个版本。我会去寻找作品给我留下最原始印象的那一版。”无论是在《追忆》还是在《驳圣勃夫》里,叙述者都总是用动词的条件式(“倘若我……”)去描述恋书癖,这说明,尽管这种癖好在上下文中显得是对他者习性的复制,但叙述者并不会陷入盖尔芒特先生或盖尔芒特亲王的轨迹,他有自己的癖性。
上流社会有它的阅读方式,例如盖尔芒特兄弟“对巴尔扎克‘有兴趣’”,仅仅是为了自娱,并不关心他是不是已成为大作家,这种习俗显然影响到了叙述者。不过,《驳圣勃夫》的立意同时也在于批驳贵族世家。试举一例,盖尔芒特先生总是把巴尔扎克与罗热·德·波伏瓦及塞莱斯特·莫加多尔混在一起,“对于这些书,倘若要人为地按照与小说主题和书册外观无关的方式进行所谓的文学分类,那会是很困难的”;相比对盖尔芒特先生的描写,普鲁斯特对他的姑母,圣勃夫的崇拜者维尔巴里西斯夫人的讽刺还要更加辛辣。《论阅读》一文曾提到圣勃夫嘲笑过身为小说家的司汤达,却称赞现实生活里在社交场上长袖善舞的亨利·贝尔;到了《驳圣勃夫》和《追忆》中,类似的言论转移到了维尔巴里西斯夫人嘴里。这位贵妇人亲眼见过巴尔扎克,认为“他是一个很普通的人,只讲了些无聊的事情,我不想让人介绍我去认识他……圣勃夫,他才是一位有魅力的人,细腻敏锐,很有教养;他很有分寸地待在自己的位置上,人们只有想见他的时候
才能见到他。他是和巴尔扎克完全不同的人”。在《追忆》中,维尔巴里西斯夫人炫耀自己认识夏多布里昂、巴尔扎克和雨果,“往昔她的父母全接待过这些人,她自己也隐约见过他们……她的家庭与这些人有过这样特殊的关系,她以此自夸,似乎认为与像我这样未能与这些人有所交往的年轻人相比,她对这些人的评论更为正确”。维尔巴里西斯夫人还直接援引圣勃夫的权威:“正如很有风趣的圣勃夫所说,有关这些人,应该相信就近看见过他们,并且能够对他们的价值做出更正确的评价的人。”从这些描写中可以看出,与他对批评家的阅读方式的不满相比,普鲁斯特对圣勃夫的敌意更直接地来自这样一个事实:他在圣勃夫等人身上看到的是一幅关于贵族做派的漫画图景。不过维尔巴里西斯夫人和她的侄子盖尔芒特先生有一个共同点,他们都难以适应“书”:前者透过书寻找的是背后的“人”,后者却在意作为“物”的书册。这两种态度都意味着忽视文学,忽视“所谓的文学分类”。
然而不管怎样,在对待书籍的种种态度中,上流社会里流行的恋书癖仍然是最切近叙述者脾性的若干方式里的一种:“有时我会扪心自问,今天我读书的方式是不是已经多少远离了盖尔芒特先生的方法,变得更接近当今的批评家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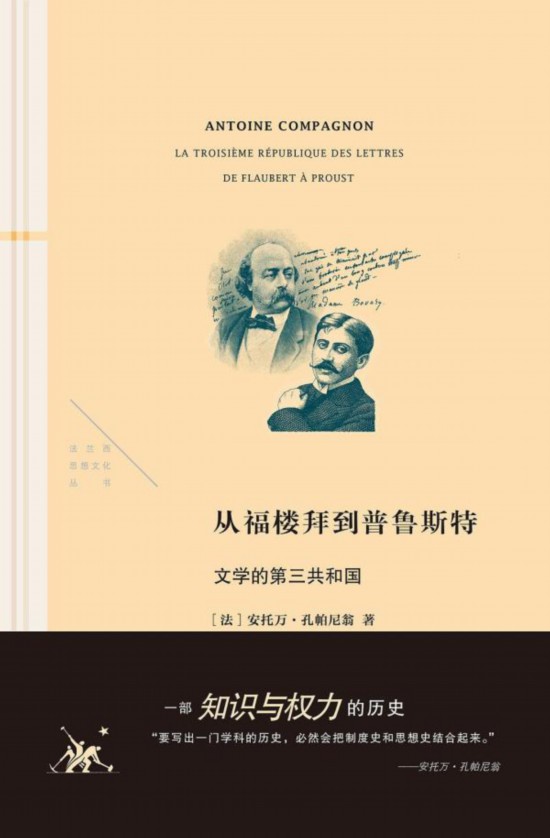
本文节选自《从福楼拜到普鲁斯特:文学的第三共和国》([法]安托万·孔帕尼翁 著,龚觅 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23年3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