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光耀访谈录——《平原烈火》及其他

徐光耀近照
《平原烈火》是描写抗日战争长篇小说的经典之作。作者徐光耀以其在宁晋大队期间的亲身经历作为创作素材,小说主要人物形象、主要事件几乎都来源于真实的历史,战争生活细节描写生动逼真。访谈主要围绕《平原烈火》进行,涉及《平原烈火》“亲历式”写作的纪实与虚构、作家创作意图、创作心理以及小说修改和评价等方面。徐老的谈话深入而真诚,有些内容是首次公开提及。因九十六岁高龄的徐老住在医院中,疫情期间不能直接探视,笔者访谈是通过徐老之子徐丹先生与徐老初步沟通,确定由徐老看护朗读笔者的问题,徐老进行回答,并以视频录像的方式记录下来。访谈于2021年12月至2022年1月分多次进行,视频由徐丹先生剪辑之后传给笔者,笔者整理、笔录如下:
一、《平原烈火》人物原型
魏雪(以下简称魏):您曾在创作谈中说“凡是当干部的(小队长、大队长、政委等,地方干部除外)和侦察员、通讯员们,都有一个真实的人做模特儿,又另外集中一些同类型人物的特征上去。”①请问您为什么会采用这样的人物设计方式呢?
徐光耀(以下简称徐):我创作《平原烈火》还是一种初期的创作,第一次试验,我以前没有搞过文学创作,只写过通讯报告之类的。这次是写长篇小说,这个长篇小说应该怎么写,我自己没有很大的把握,我只是把我肚子里所存在的战争形象、战争的故事整理出来,今后在写长篇小说的时候来用,写《平原烈火》是当作搜集和整理材料的意义上开始的,所以我的人物都是,或者说大部分都是有原型人物的。因为我是第一次搞文学创作,我胆子很小,我没有把握,我只能够在现实生活中找一些现成的人物,我来描写他,就是这样的一种方式。
魏:您曾提到周铁汉形象主要以战斗英雄侯松波为原型,那钱万里、薛强、刘一萍是否也都有具体的现实对应人物呢?有人认为钱万里形象由弃里三、乾云清、白云峰三位组合而成,薛强形象由现实中的宋开元、刘文芳两位政委组成,②请问您是否赞成这些观点?
徐:周铁汉的形象是完全按照战斗英雄侯松波的形象来写的,这一点毫无问题。至于大队长钱万里、副政委薛强和刘一萍这些人也都是有原型的。我的大队长的原型主要是弃里三,是宁晋县大队的大队长弃里三和白云峰、乾云清这三位的特征集中起来创造的。薛强的形象不是宋开元和刘文芳,因为宋开元我根本不认识,我调到宁晋县大队的时候他已经离开了,我只认识刘文芳,但是刘文芳作为一个副政委,他比较的平庸,所以副政委薛强的形象,我主要是吸收了我们冀中十一军分区司令员王先臣的特征来写的,这就把薛强拔高了很多,我的主观上正是要把薛强拔高一点,因为他是体现党的领导的人物。
魏:关于周铁汉的身世您是如何考虑设计而成的呢?丁玲曾说:“周铁汉这个人物还有点概念化”③,请问您现在对周铁汉人物形象塑造的效果是怎么看的呢?
徐:关于周铁汉的身世的设想,我是这样想的:周铁汉是共产党的一个英雄,是一个坚强的共产党员,要把他直接写成是贫雇农出身,我就觉得贫雇农出身的人身上的特征是比较老实、比较的缺乏机智,也比较的缺乏革命的坚定性,所以我想了半天的法子就是,把周铁汉的母亲怀着周铁汉的时候,地主要把她这个肚子里的孩子买下来,然后由地主把周铁汉抚养大。我这个意思就是周铁汉出身贫农,但是是在地主家庭的影响下,沾了地主的形象、生活习惯等等,也沾染有地主的那种狠毒、泼辣、坚强,甚至又有点霸道的这种影响,来把他提炼着看,得到周铁汉的形象。这样就回答了一个很简单的概念问题,就是周铁汉出身贫农,而受了地主生活的影响,这是我的一个最初步的设计,这个设计现在看起来有点不太自然。周铁汉的形象是我用了千方百计的力量,用了很大的力气来塑造的一个中心人物,我现在对周铁汉的想法是,周铁汉还是在共产党的队伍里一个很坚强、很顽强,革命意志很坚定的一个革命干部,他是这样的一个典型。丁玲说周铁汉的形象还有点概念化,是非常准确的,我在塑造他的时候呢,很多时候我是按照当时流行的概念来塑造的。所以我认为周铁汉一方面可以作为共产党员的一个英雄典型的形象,另一方面呢周铁汉的形象不饱满、不丰富、不多彩,是受了概念化的影响。所以,说周铁汉身上有点概念化,我完全口服心服。
魏:刘一萍具体的生活原型是谁呢?刘一萍这一人物形象您是如何考虑设计而成的?是作为小资产阶级软弱性的体现而设计的吗?时过多年,您现在对刘一萍这一人物形象设计有何看法?
徐:刘一萍是有原型的,他是我们县大队的第二小队的小队长,名字我想不起来了。这个人呢平常表现比较积极,而且在出操、执行大队的各种制度、对士兵的训练等方面都表现不错,但是他在战争最残酷的时候表现一般,我就把他设想成一个右倾情绪很强的人,这是为了创作的需要。我的小说里尽可能要表现两种思想的斗争,一种思想是坚定的革命意志为主,一种思想就有些右倾,有些害怕斗争,有点躲避斗争,躲避敌人的意思。我打算把刘一萍变化成一个你所说的小资产阶级软弱性这样的一个人物,实际上原型本人不是这样子的,我强加了他的右倾情绪,使他作为一个右倾情绪的代表人物来体现两种思想的斗争和矛盾,而且最大的教训就是右倾情绪,避免斗争、害怕斗争的这种情绪会给对立斗争带来不少损失,在刘一萍身上也体现了这种损失,我这是从小说主题的需要出发的。我现在看起来刘一萍原型是个很好的人,他没有发生过使部队遭到惨重失败的行动,他就是平平凡凡地从斗争中跟着大流过来的。我把他写成了右倾情绪严重的一种典型,纯粹是为了《平原烈火》主戏的需要,就是两种思想斗争的需要,而且把右倾情绪作为一种教训,一种血的教训,拿刘一萍来进行证明。
二、 关于《平原烈火》主要事件
魏:小说中的故事看似富于传奇色彩,但实际十却是出于现实真实。比如越狱事件,周铁汉及其战友的越狱故事来源于现实中陶冶、侯松波等同志的越狱经历,看似离奇却曾在现实中真实发生过,请问您当时是通过什么途径知道这个事件的呢?关于周铁汉在监狱里面的斗争经历及其越狱的经过,是否主要是您在所了解的基本事实基础之上的想象虚构?大概有哪些细节描写是由您经过想象虚构而成的?
徐:对于侯松波——周铁汉的原型,我是比较熟悉也认识的。在1945年的春天(大概是春天),冀中十一军分区开过一个英模代表大会,奖励分区范围内的战斗英雄和劳动模范,侯松波是这个群英会的最明显的一个主角,他是第一名战斗英雄,侯松波给我们做过报告谈他越狱的经过,主要是谈他越狱的经过,后来我们十一军分区的宣传科长尹肇之、宣传科的干事张文苑,他们采访了侯松波。我那时候也担任采访任务,我采访的是另外两个人,而不是侯松波,但是在采访人员向司令员王先臣汇报的时候,尹肇之和张文苑把侯松波的故事又重新演说了一遍,我听得非常仔细、非常认真,所以我对侯松波是比较熟悉的,因为几次听过,他自己谈一次,别人谈他一次,都是主要谈越狱的经过,他是战斗英雄,主要表现在越狱这一点上。我对周铁汉越狱的描写几乎全部是按照侯松波的所作所为描写出来的。这里面如果说有想象的话,就是他在监狱里边组织党小组,这是我为了拔高侯松波自己添的组织党小组的行为,除了这一点之外,几乎全部是侯松波的真人真事,就连侯松波上厕所找到一颗三寸长的铁钉这样的细节都是当时最真实的情况。我现在认为侯松波(周铁汉)这个人还是很有教育意义的,很有感动人的力量的,但是刚才说了他整个的创作过程中间是受了概念化的影响的。
魏:小说中针对岗楼的政治攻势,周铁汉等人面对岗楼进行政治喊话等情节描写得非常生动,您当时是否亲自参加过?当时实际情形大概是什么样子的呢?岗楼政治喊话的实际效果如何?您将其写进小说时是怎样选取材料,如何进行构思的呢?
徐:关于对敌人的政治攻势,当时太平洋战争已经爆发了,反法西斯阵营的胜利形势越来越明显,八路军经过几年的斗争,势力越来越大,军事实力越来越强,慢慢地有向敌人反攻的力量了,所以我们对敌人进行政治攻势是党从上边贯下来的政策之一。当时我们要向敌人和伪军宣传:八路军的前途一定是光明的,胜利的!你们是一定要失败,一定会走向投降的道路的!我们主要的宣传内容就是这个。我们宁晋县大队对敌人的政治攻势,我是参加过好几次的。我们主要是在夜间先把敌人岗楼包围起来喊话:“伪军同胞们,我们是八路军!来给你们讲话来啦!”敌人有时候不言声,也不打枪,我们接着往下讲,讲国际形势,讲国内形势……这时候呢,就有很多的细节,有些故事出来。但是干巴的唱歌是我的虚构,那是我想象出来的,干巴是宁晋县大队的一个侦察员,是一个很有趣味的人物,我就按照这个侦察员干巴的形象写的书里面的干巴。我们对敌人喊话,敌人常常不说话,有时候就说:“八路军先生们,你们的话我们都听了!请你们走吧!”我们走了以后敌人就打枪,向天上打枪,为了是向鬼子报告:八路军来过,我们抵抗过,我们把八路打退了。这说明伪军听了我们的话,还是听进去了,所以他们不采取敌对的行动。我几次参加对岗楼的喊话,我自己也亲自对岗楼的伪军们喊过话,但是向我们打枪的事件很少出现,至少在伪军这个阶层里头,我们的宣传是起了作用的,他们是同情我们,也愿意跟我们讲和的,采取和平手段的这样一种表现。要说有虚构的话,《平原烈火》里最大的一个虚构也许就是干巴在岗楼底下唱歌。
魏:请问小说中烧“良民证”的情节是否有真实依据?您能谈谈当时与“良民证”相关的事情吗?
徐:“良民证”是敌人统治中国老百姓的一种手段,就是让你跟八路军分开,把八路军孤立起来,凡是带“良民证”的就是顺民,凡是不带的那就是八路军、共产党,所以在敌占区,离敌人很近的地区,村里的群众是普遍带“良民证”的。因为斗争环境的残酷,也有一些八路军战士的家属给我们的战士送了一些“良民证”来,意思就是在非常危险的时候你就把枪一藏,可以装作老百姓,可以装作顺民,这是叫战士们自我保卫的用心。但是这种带“良民证”的情绪是影响战斗力的,是会使八路军的战斗情绪减弱,就会使右倾情绪普遍地传播,这不利于军队战斗力的提高,不利于战胜敌人的信心、坚强的信仰。所以呢我写的部队里头发生了有“良民证”的现象,把它们收集起来烧掉,并不是简单的烧掉,在烧掉的时候要进行大量的解释,说这样子做不好,政治工作人员要向战士们解释清楚。这个带“良民证”的事实本身、烧“良民证”的事实本身都是真实的。我自己也带过“良民证”,不过不是在宁晋县大队,是在“五一大扫荡”正中间,我奉命到深县南部地区来搜集被敌人冲散的八路军战士,把他们再重新集合起来跟敌人斗争,我是这样的一个任务。那时候敌人的“五一大扫荡”还没有结束,正进入清剿阶段,敌人差不多天天要到村子里来烦蹭(按:方言,意为“侵扰”),找八路,找共产党。我那个时候在老百姓家里隐藏,群众教育我如果不带“良民证”就会引起敌人的警惕,或者直接抓捕起来,我在的村子里群众已经普遍地都带着“良民证”了,于是村干部为了掩护我,也给了我一个“良民证”。这“良民证”制作很简单,用半尺长的一条白布,有一寸宽,上面写着“良民”两个字就算是“良民证”了。因为是战争环境里头应急出来的,没有像印刷品这类的“良民证”,就是弄个布条吊在胸前,村干部发给我的“良民证”是从新布上裁下来的,所以带在身上显得特别扎眼,说你这是新制造的“良民证”,会引起怀疑的。所以村干部教给我,这“良民证”得在头上揉搓揉搓,擦一擦,可以把头上的头油(那时候我们都不洗头的)擦在白布上,然后再用土和灰把这个白布揉搓,猛一看就是旧的了。这是我对“良民证”的回忆,说得比较得像说话一样,但是这个细节我要让你知道是怎么回事儿。
三、 《平原烈火》的创作及修改
魏:您在《我怎样写〈平原烈火〉》中提到:1946年,冀中发起过一个“抗战八年写作运动”,您当时“写了两篇类似报告的东西”,“其中一篇叫《斗争中成长壮大》,约两万字左右,就是写一支游击队在‘大扫荡’中,如何由失败、退却,经过整顿和斗争又成长起来走向胜利的”④。《斗争中成长壮大》这篇文章在您的《徐光耀文集》中未收录,请问您还保存着吗?它的主要人物和故事情节有哪些呢?
徐:先说两句闲话,在“抗战八年写作运动”中我写了两篇文章,正像你说的,一篇是《斗争中成长壮大》,另一篇是《弟弟》。关于《我怎样写〈平原烈火〉》这篇文章,丁玲后来看见我跟我说:“这篇文章你写得不好,你怎样写的这本书你还糊里糊涂,存在着很多糊涂观点,以后再有人找你要这样的文章,你不要写了。”丁玲的话说得很对,我当时对《平原烈火》怎么产生的,是存在着很多糊涂观点的,比较重要的就是我对大时代的了解不清楚,对自己的成长过程和自己怎么从一个战士到写出《平原烈火》这本书来,思想上有怎么样的准备,有怎么样的变化,有怎么样的成长过程,以及后来我个人对大时代的反映、了解和把握都是没有准稿子的,所以丁玲很敏锐地发现我在写《平原烈火》的时候存在很多糊涂观点,她说的是非常对,非常尖锐的。关于我写的另一篇文章《弟弟》,那是写我姐姐的,我当时是当作写“抗战八年写作运动”的征稿的,但是后来《弟弟》这篇文章成了小说,收进了我很多的文本里头,我出版的书有好几次都收进了这篇文章,被认为是很好的一篇短篇小说。但是当时我一点也不觉得这是小说,我是在写真实的我的姐姐,我按照我自己所熟悉所了解的情况认真地写我的姐姐,那里头没有虚构,全部都是事实,这也是一个你需要注意的问题。
关于《斗争中成长壮大》这篇文章,我现在还保留着,但是我年纪大了,我那大堆资料很多,现在怎么也回忆不起来那篇文章是在什么地方放着了,我现在没有机会找这篇文章,这一点请你原谅。这篇文章主要是写我“五一大扫荡”的经历,写我们那一支宁晋县大队游击队怎么在战争中熬过来的,我主要是谈事实,谈经历,都是真实的,但是里头只有故事情节,没有人物,那个时候我还不懂得写人物的重要,不懂得什么叫文学,那是毛头毛脑地写出来的一篇文章。
魏:您提到:《平原烈火》“故事的梗概大致按《斗争中成长壮大》的发展顺序,只是又扩充了一下”⑤。请问相对于《斗争中成长壮大》,《平原烈火》主要在哪些方面进行了扩充?
徐:《斗争中成长壮大》这篇文章是我还在追求和努力学习文学的初级阶段写的,我还不懂得什么叫文学,基本上对文学概念是很模糊的,不懂得文学概念由哪些因素构成,所以我就按照我的理解、我的经历写了这篇文章。这篇文章现在看是一篇很粗糙的通讯报告文学,它的文学性、文学成分很少。我在写《平原烈火》的时候,是已经在华北联合大学文学系学了八个月之后,对文学有了新的理解,有了新的觉悟,我才写的。
怎么扩充的呢?主要的是写了几个人物,在《平原烈火》里头几个人物,像周铁汉是努力创作的一个中心人物,另外像干巴、像大队长弃里三(钱万里)、像副政委薛强,还有像罗锅子侦察班长,这些人都是我在创作中间努力要写出来的人物形象。所以《斗争中成长壮大》和《平原烈火》一个主要的分界点就是我懂得了写人物,我在故事中间努力描写人物。但是我的写人物的水平也还是比较低的,还只是初步的对文学的一种了解,所以《平原烈火》里面的人物能够成为典型的也只有周铁汉一个,周铁汉这个人物也是有点概念化,并没有很丰富很充实,这是我文学修养不够的关系。
魏:1947年您曾在华北联大文学系学习了八个月,请问这次学习您的主要收获有哪些?对于您后来进行《平原烈火》的创作有哪些具体帮助?
徐:《平原烈火》的写作得益于我在华北联大文学系的学习,这学习是多方面的,是基础性的,是把我从一个初步有文学知识的人提高到了可以写长篇的这样一个作者的水平。在联大文学系学的功课里头对我影响最大的是“创作方法论”,我是直接写小说的,我对“创作方法论”有非常浓厚的兴趣,而且我是课代表,听得也非常认真。在《平原烈火》里我不但注意了人物创造,也注意到了结构、氛围、高潮、语言等等方面,我在语言上非常注意,这也是受联大影响而开始的,联大的课程里有很重要一部分就是向人民学习,向民间学习。我在语言上就非常非常地注意跟老百姓学习,学习老百姓语言中的精髓,我订了不少本子,专门记录在农民生活中我所搜集到的语言的精髓,所以我写小说在语汇上比以前丰富了不少,就得益于这次学习。
魏:您在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平原烈火》之前专门对初稿进行过一个多月的修改,请问您当时主要修改了小说的哪些方面?您是否能谈谈修改情形?
徐:刚才说到,我写《平原烈火》是受了联大学习的深刻影响,受到很好的教育,我才有水平有能力来写一部长篇。陈企霞老师告诉我《平原烈火》的初稿还有些地方写得比较薄弱,应该做一些尽可能的修改,他不要求我做大的修改,他认为我那初稿就已经达到了出版水平,需要修改的地方就是他感到不满意的一些地方,比如说人物还缺乏细节,军队和群众的关系密切程度我写得很不够,所以我在《平原烈火》的修改中很注意的一个问题就是加强军队和老百姓的关系。这里面我没有想出重要的情节来说明军民关系,就是在比较细微比较直接的问题上,比如给群众担水啊,给群众拔麦子啊,像这样的一些非常琐碎的、小的地方加强了军民关系的描写。实际上《平原烈火》存在的一个根本性的比较大的缺点就是军民关系没有写好,写得不够丰富,写得太单薄,不太符合时代的那种要求。
魏:您曾提到:小说出版前陈企霞约了秦兆阳、唐因、严辰等人来为小说取名,经过一番斟酌,最终确定为《平原烈火》。请问当时您给陈企霞看的初稿是怎么命名的呢?您是否还记得当时为小说命名的具体情形呢?
徐:《平原烈火》的命名是由陈企霞挑头约了严辰、秦兆阳、唐因,连我在内一共四五个人来专门研究。他很热心地来给我这本书起名字,因为我原来的名字就叫《斗争中成长壮大》,这是报告文学的名字,不是小说的名字,陈企霞感觉到这一点就约了这几个人。其中严辰是我们联大文学系的一个教员,给我们讲民间文学的,而且,就是严辰把《平原烈火》中的十二章提出来,单独以《周铁汉》的名字在《人民文学》上先发表了。就在同一期《人民文学》刊物上严辰还写了一篇介绍文章,就是《一部写冀中平原游击战的好作品》⑥,大体上是这么个题目,在刊物上给我宣传《平原烈火》这本书。另一个人是唐因,唐因是《文艺报》的一位编辑,我当时还不很熟。秦兆阳是作家协会的专业作家,我当时也不熟,但是我们几个人很随便地谈这部书应该叫什么名字。陈企霞曾经提出过叫《铁汉的队伍》,别人也出了一些名字,都是从小说这个形式出发的名字,但是大家讨论的结果最后定名为秦兆阳题名的《平原烈火》,这就是那个过程。
魏:您曾说:就《平原烈火》而言,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东西有真实的生活依据,虚构想象的部分不足百分之十。请问您是怎么看待小说的真实与虚构之间关系的?您认为真实与虚构比例的不同给读者带来的阅读体验有何不同?您在进行《平原烈火》创作时是否会考虑读者的阅读效果?
徐:我那个时候写惯了通讯报告和报告文学,所以呢我写文章的时候一定百分之百的遵循事实的真相,我不会虚构,也不允许虚构,因为报告文学要在报上发表,虚构了说了假话是会受到批评的。后来《平原烈火》的基本结构、基本顺序就是按照《斗争中成长壮大》来发展扩充起来的。我在什么地方扩充呢?最主要的是我已经在联大学习中懂得写人物的重要。我的教员,讲“创作方法论”的教员就是萧殷,这个人是大名鼎鼎的青年作者的培养园丁,现在在广东有他的纪念馆,这个人在培养文学青年方面做出了一生的贡献,他培养的弟子、培养的学生是很多的。萧殷给我讲课,给我印象最深刻的一点就是,创作,特别是小说、散文、戏剧,叙事性的文学一定要写人物,他说写人物是文学的最终目的。当时我理解我们的最终目的是达到共产主义,他在这儿提出一个新的最终目的来,我脑子里转了很多圈,后来我才理解他说的是人物,写人物要写性格,性格要分成两个部分:一个是个性;一个是共性。共性就是阶级性、就是集体意识,个性呢就是这个人物形象本身独特的行为方式和表现方式。我在写《平原烈火》的时候就紧紧地遵照他这个嘱咐来扩充,我主要的扩大的范围都是用在了写人物上,虽然人物并不是个个都写活了,但是个个人物上我都努力了。比方说,我写周铁汉,要丰富这个人的性格,一个是把他写成了他是贫农的孩子叫地主买了去,在地主家里头长大,因为地主后来又生了第二个儿子,他不是亲儿子,就在很多方面虐待他,设计这样一个出身就是为了使周铁汉这个人物更复杂一点,出生经历更多一点,他的个性方面更多更花样一点。我举一个小的例子,在战斗撤退中间战士里出现了一个怕死鬼,在敌人火力压制之下他跪下投降,说“我投降了”,周铁汉就在他身后一枪把他枪毙了。周铁汉办了一件事,回头再看,这个怕死鬼叫尹增禄,尹增禄的一脸屈膝投降、悲哀凄怆的表情还留在脸上,周铁汉对他非常痛恨,就一脚把尹增禄的死尸踢滚到墙根,这是属于我个人虚构的部分,我丰富人物性格的一种表现手段,一种细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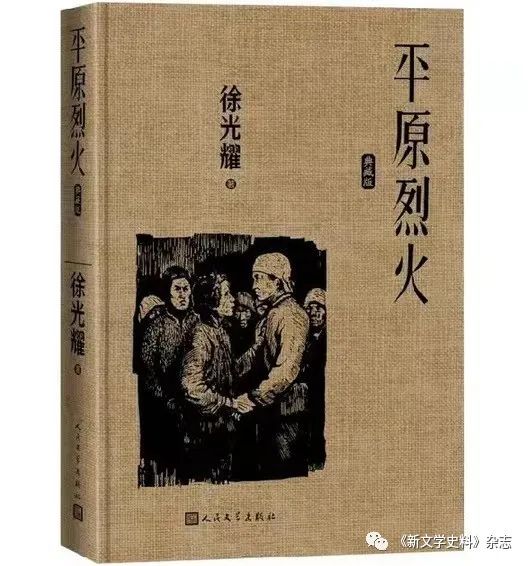
《平原烈火》典藏版,人民文学出版社2021年12月
中国的读者喜欢故事,但是故事要用人物来扮演,没有人物的故事是没有力量,没有说服力的。所以呢在《平原烈火》里头,我觉得在故事上没有太多的漏洞,故事情节是比较多的,斗争性也是比较复杂的。但是我在创作中一方面要注意到故事性不要减轻,另一方面我最重要的最注意的方面就是语言,我认为读者读小说的时候,他对你的语言不产生兴趣,不觉得有趣,不觉得精彩,不觉得好看,他越看越腻歪,他就会把书本扔在一边,不看了,所以你的写作就等于白费了。所以我是一句一句地抠,一句一句地细细琢磨来下笔动笔的,我写小说的速度在写《平原烈火》的时候还快一点,后来的写作速度是很慢的,就是因为我要细抠语言,这是我对读者的一个最重要的考虑。
魏:您也曾创作过大量反映战争的报告文学,请问您认为小说创作跟报告文学相比,作家在写作时的创作心理有何不同?
徐:写报告文学要百分之百的真实,不能脱离真实,脱离了真实之后人们就会骂你,当时有个很流行的词叫“客里空”。苏联的一部话剧叫《前线》,那里头有一个记者“客里空”,记者用电话采访前方的将军,前方的将军说缴了十颗枪,他就写缴了十三颗枪,他做了一些虚构,所以呢人们把“客里空”这样的记者作为假写家的一个符号。写报告文学的时候必须按事实的百分之百去表现,不能有一点虚构。你要是虚构了,那就骂你是“客里空”。写小说、写文学作品,那就有广泛的虚构自由,我可以按照我的想象,我以为我的想象是真实的,令人信服的,我就可以写,可以虚构,像我刚才举的例子,周铁汉踢滚尹增禄的死尸,那就是我的虚构。要是写报告文学,没有这种事情,你写了这种事情你就是造谣,你就是胡来,但是在小说里有一条基本的概念就是要联想广泛。联想广泛就是在你生活的基础上可以很自由地来扩大事实,使这个事实能够准确的,百分之百的表现出来,这是写真实和写虚构的一个很大的区别。
小说创作和写报告文学的另一个区别,在我来说,就是文学艺术,能够成为艺术的文学作品它应该传世,它应该在世界上流传下去,流传你创作的典型,你创作的情景,你创作的意义;写报告文学就是要报告当前的一种形势,一种真实发生的事件,它是一种宣传,它的目的是直接向群众宣传,在我脑子里很少有写报告文学的人能够传世的观念,它是不注重艺术效果的,写小说写文学作品就要注重艺术性,就要注重能够吸引群众,能够创作出典型来,在这个典型人物身上寄托你的理想和希望。
四、 关于小说的评价
魏:在50年代有评论文章认为《平原烈火》群众描写不够,您认为为什么会出现这种评价?关于小说的群众描写问题,您是怎么看的?
徐:《平原烈火》在群众描写上是先天不足的,确实有这个问题。陈企霞当时给我提出来的第一个问题就是群众描写不够,描写群众的力量,群众对军队的支持、保护、爱护,军民关系的鱼水之情,写得不充分、不够有力,在修改的时候要在这方面加强。当时对《平原烈火》的评论文章也指出这一点来,李昭和申述的对《平原烈火》的评论文章⑦里头就指出,《平原烈火》的军民关系写得不够,群众的力量,群众对军队的保护、支持也写得不足,这是当时第一篇评论⑧里头就有的一个问题。
我想这个问题的存在,第一是因为我在写《平原烈火》的时候集中力量写部队中的几个英雄人物,写部队的艰难困苦,在极危险的、极残酷的战斗中冲过来,后来又经过内部的思想斗争,纠正了错误,又成长起来,我主要的是写这个过程。群众的力量,群众对军队的爱护在我主观上就没有引起高度的注意,我个人的性情有点孤僻,我一辈子群众观点都比较薄弱,所以很自然地流露出来对群众描写的不足,对群众力量的估计也不够。如果没有群众的支持,没有广大人民群众、农民对八路军的支持、爱护、掩护和实施给养,光凭军队本身是打不倒日本帝国主义的,是不能取得胜利的,在那种残酷环境下没有群众的支持是过不来的。《平原烈火》里有一个情节,是大扫荡进行时,部队没有办法,藏在一个大庙里,敌人从眼前的汽车路上过来过去,就藏着不让敌人发现。有人指出,这就是你没有注意写群众保护的一个例子,军队好像很孤立的藏在大庙里头躲避敌人,没有让群众来支持、保护、掩护,所以呢,这就是一个很重要的缺点,一个很重要的缺陷。
魏:有人将您的小说创作进行分期,认为《平原烈火》是青春型,《小兵张嘎》是成熟型,《四百生灵》是探索型⑨,您认为这种评价是否合适?
徐:这三种分期我自己没有自觉,这是评论家们的分期,要从我个人的感觉,对这三种评价来说,我可以同意这种划法,但是对探索型这一期我要有所说明。我一向有个观点,我们对八路军,对抗日军民的文章、报道、宣传方面有一个缺陷,就是一直写胜利,一直写顺利的情况,一直写怎么把敌人打倒,把敌人消灭。但是事实是在那么残酷的战争环境里,敌我力量的悬殊那么大,在那种环境里斗争,没有失败是不可能的,我敢说每一个部队都经历过失败,但是大家都宣传胜利不宣传失败,我认为失败中有英雄,在失败里头的英雄比胜利里头的英雄更英雄!这是我一个很明确的观点。在宣传中,在晋察冀边区宣传狼牙山五壮士,那是在失败斗争中写壮士的唯一的例子,我没见过再有别的文章来写八路军失败的。
我在写《四百生灵》这篇小说的时候,有一个很明确的认识,就是我要写一次八路军失败的斗争,重点是写在失败中的英雄,在失败中的斗争是更残酷的。举例来说,被敌人团团包围,没有任何屏障,没有山河有力量的屏障,没有坚固的阵地,要突围是不可能的,所以最后四百生灵全部被敌人消灭。但是我没有写失败中有人屈膝投降,有人妥协退让,就连这四百人队伍中押的犯人,就是犯罪的人,被当作敌人来看待的人,连这些人都一直抵抗到底,誓死不投降的,我以为这样的英雄比胜利中的英雄更应该看重、更应该宣传,因为他们在战争中已经看见没有前途了,在绝望的情况之下还坚持跟敌人打到底,这是非常非常不容易的。
基于我说的这一点,可以联想一下我的另一个中篇小说《冷暖灾星》。《冷暖灾星》也是写失败中的英雄的,也是我脑子里头很明确的有这样一种思想,我就是说在失败的整个环境里头,不光是八路军有英雄,群众里头也有英雄。群众是多彩多样的,有的比较落后,有的一看见八路军来了以为八路军会把鬼子引来,把鬼子引了来就是一场灾难,比方说“三三制”,他就很不愿意把三个小八路收到自己家里,但是敌人来了之后,“三三制”还是站在八路军这一面来对抗敌人,最后也是他把剩下来的两个小八路送走的,而且也还有挽留他们的情绪,说我还有小枣,还有小米,你们可以吃。我说到这里会很激动,因为在那么残酷的斗争中,老百姓都被敌人的残暴杀害吓坏了,但是就在这么一种环境下,把八路军看成灾星,当敌人真来的时候,他还是站在八路军这边,还是拥护、保护、掩护八路军的,这一点我觉得其他文章里头也比较少见。
魏:从《平原烈火》《小兵张嘎》到《望日莲》再到《四百生灵》《冷暖灾星》,您的小说风格以现实主义为主体,描写战争生活,不断地进行新的写作方式的尝试,请问您写作不断突破创新的动力和原因何在?到目前为止,您对自己的哪部小说最满意?
徐:回想我自己创作历程,我并没有自觉地在哪一个问题上有所突破,我没有主动地自觉地寻求过突破,我只是一向在努力提高自己,努力能够尽量地写好一点,过一个阶段呢就有所进步,这个进步连我自己也说不上具体的道理来。我最大的创作动力,经常引起我激动,引起我回忆的就是抗日战争。抗日战争我是亲自参加了的,八年抗战一步我也没落下,就是在战争中间我自己经历了很多艰难险阻,我当时所看到的形势,看到的群众,看到的部队战士,他们所经历的残酷情况我也是分明了解的。所以这些抗日战争的经历,那种艰难困苦,那种顽强不屈,那种烈士的鲜血到处洒得很多,尸骨堆山、血流成河并不是很夸张的词语。因为这个呢,相比起抗日战争来,我对解放战争的印象就比较淡薄,因为解放战争时期我在部队里是在高级机关里头当编辑,没有参加直接的战斗,所以没有给我留下很深刻的印象,所以我至今也没有写过解放战争的文章,因为我没有具体的实在的素材。
我的小说从《平原烈火》到《小兵张嘎》,到《望日莲》,一直到《冷暖灾星》,我自己也知道有些步步的提高,我最喜欢哪一部作品,第一部当然是《小兵张嘎》,这是不容置疑的;第二部,我觉得我的小说里面写得比较合乎我的理想,是我真正努了力的,费了劲的一部著作就是《冷暖灾星》。我对《冷暖灾星》很看重,因为《冷暖灾星》里头我试着写普通的人也能够成为典型,这是我的理想,我想把普通人一个一个的也写成典型。当然,《冷暖灾星》里头并不是每个人都是典型,都称得上典型,但是像狗替儿夫妇,像“三三制”,像伪保长这样的一些人物还是给人很深刻的印象的,这是我在描写人物上一个最大的努力,我想我笔下的人物应该力求个个都有个性,个个都有典型性,每个人都是个性鲜明的,在这一点上我是下了很大功夫的。在艺术表现上,在艺术描写上,我也对《冷暖灾星》下的功夫比较大。
五、 关于《徐光耀日记》
魏:您在1948年6月1日和3日的日记中提到读《虹》,在1950年3月2日和3日再次提到读《虹》。请问您当时所读的是茅盾先生的《虹》,还是苏联作家瓦希列夫斯卡娅的小说《虹》?茅盾先生是否对您的小说创作产生过一定影响?
徐:我日记里头提到的《虹》是苏联女作家瓦西列夫斯卡娅的作品,不是茅盾的《虹》,我没有读过茅盾先生的《虹》。关于我受没受过茅盾先生的影响,这个问题比较简单,因为我读茅盾先生的作品不算多,我读过他的《子夜》,读过他的一些短篇小说和小品文。在我还不知道什么叫写作的时候,我追求写作能力的提高的时候,我看过不少茅盾先生的小品,非常佩服,我把茅盾跟鲁迅、叶圣陶、巴金这样一流的作家,列为一群,我认为他是中国作家里面一个很了不起的,很伟大的作家。我佩服他写的小说,佩服他写的小品,我看过他的《子夜》,但是我基本没有看懂,我十三岁当八路军,我至今也不知道具体的资产阶级是什么样儿的,我没有看见过资产阶级,茅盾先生主要写的是资产阶级的黑暗的那一面。所以茅盾先生给我的印象主要是他的短篇小说和小品文。
但是关于茅盾先生有一个细节我要谈一谈。就是我还在戴着“右派”帽子,是“摘帽右派”的时候,我写了小说《望日莲》,《望日莲》是在《人民文学》上发表的头条,茅盾先生那时候还兼着《人民文学》的主编。有一次,他在《人民文学》编辑部的会上说过,说我看了徐光耀的《望日莲》,觉得有几点值得注意;但是我又听说徐光耀有点问题,所以我今天就不谈了。他没有具体地谈他对《望日莲》的印象,但是他这番话是《人民文学》的编辑亲自对我说的,这是个事实。就是茅盾先生看了《望日莲》以后,他是有感触的,他是有话要说的,但是因为我是“摘帽右派”,他就没有说,这件细节给我印象很深,就是说《望日莲》触动了茅盾先生的一些触角,他有些感觉是比较新的,所以他有话要说,这一点我自己引为骄傲,但是这件事情一直到今天也没有别人知道,但说得是千真万确的事实。
魏:您在日记中记录了在文学研究所的学习生活经历,您能否谈谈文学研究所期间印象比较深刻的事情?请问您认为文学研究所的学习对您的文学创作起到了怎样的作用?
徐:我在华北联大文学系八个月的学习中间,给我在文学上打了一个基础,使我能够有能力写出《平原烈火》来。在中央文学研究所的学习使我对文学的修养、学养有一个很大提高,可以说我从一个战士转化成为一个比较有素养的作家。但是,在具体的一步一步怎么使自己加强起来、提高起来的这个过程我说不清楚,因为上了很多课,听了很多名人教授的课程,每一课都是对我有所教养、有所提高的。
最深刻的一件事情就是丁玲给我说过,她说的话很解气,她的语气也很硬,她说:“写作一定要狠狠地写人物,一定要写出一两个典型人物来。”在我写以后的作品,特别是写《冷暖灾星》的时候,我是紧紧地记住她这句话,按照她的这句话行事的。丁玲的话给了我非常深刻的印象,她不是在讲堂上讲的,她是私下里跟我说的。这是她一辈子创作经验的精髓,她这样告诉我,我很受感动,也深受影响,所以在《冷暖灾星》上,我写人物是尽了最大努力的。如果要说还有一件事印象比较深的呢,就是朝鲜战争,抗美援朝战争打得火热,我向丁玲要求暂时放弃学习,到朝鲜战场去体验生活。我的出发点是我参加过抗日战争、解放战争,还没有参加过抗美援朝战争,而抗美援朝战争对付的是最新的敌人,是以前没有对付过的敌人,是世界上头号帝国主义,最强的武装队伍,我要求到朝鲜去体验生活,就是我觉得我一辈子写兵,抗美援朝这一段历史如果我不了解的话会影响我今后的创作。所以我向丁玲当面要求去朝鲜战场体验生活,暂时放弃学习,她非常痛快地答应我了。所以我后来有八个月的到朝鲜战争去体验生活的经历,这也是丁玲对我的一项支持。
①④⑤徐光耀:《我怎样写〈平原烈火〉》,《文艺报》1951年第10期,第21页。
②林重杉在《平原烈火之魂》“六、钱万里的三张复合面孔”中指出钱万里的生活原型是弃里三、乾云清、白云峰;林重杉分析了宁晋大队的两位政委宋开元和刘文芳,认为薛强的人物原型刘文芳更多一些。参见林重杉:《平原烈火之魂》,人民日报出版社2013年版,第110—128页,第134页。
③邢小群:《我眼中的丁玲与陈企霞——徐光耀访谈录》,徐光耀著:《徐光耀文集》(第4卷),河北教育出版社2005年版,第418页。
⑥⑧参见安敏:《一部描写冀中抗日游击队的新作——介绍徐光耀的长篇〈平原烈火〉》,《人民文学》1950年第4期。(注:严辰署笔名安敏)
⑦参见李昭、申述:《评〈平原烈火〉》,《文艺报》1950年第5期,第11页。
⑨参见崔志远:《徐光耀的理性精神与人文情怀》,河北省作家协会编:《徐光耀研究论集》,花山文艺出版社2015年版,第49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