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届鲁迅文学奖获奖作家专访 路也:发生在内心里的对话,使人永不寂寞

记 者:诗集《天空下》分为三辑,第一辑着重从身边的景、物、人着手,抒写生活中的细微情思。其中的内容非常丰富,但我尤其注意到《落地窗》《小山坡》这样的诗作。它们写的就是倚窗发呆、仰卧草坡等再普通不过的细节,但又写得诗意盎然,生动表达出了抒情主体的心境。您是如何从“无诗的地方”发掘出“诗意”来的?
路 也:其实,这世界上并不存在“无诗的地方”,只存在“无诗的状态”。有没有诗,跟外部生存和外部环境关系并不大,而是跟一个人某个时期的生命状态甚至内部语言状态更有关联。我的日常生活无非是备课、上课、读书、写作、行走而已,这样的生活看上去平常、平稳、平静、平淡,但我的身心内部却不定期地掀起惊涛骇浪。我写诗过于倚靠个体生命状态,这就导致了我会在某个短时间之内写出很多诗,又会在另一个很长时间之内一首诗也写不出来。
这样的写作方式,使得诗意不是靠“发掘”,而更像是靠爆发或喷发,活火山是间歇性的,有休眠期也有爆发期。我的任务不是寻找,而是等待,在这个等待过程中,该干什么就去干什么。我干得最多的事情是:发呆。常常有人打来电话,一上来先寒喧,如果问到“你现在在干什么?”我就脑子一根筋地如实相告:我在发呆。我想“发呆”也许就是“冥想”的另一种非正式表达方式吧,如果非要区别二者不可,那么冥想是无功利的,发呆则更加地无功利。但,也许从客观上看,发呆对于写作是有利的,谁知道呢,反正我也不是为了写作才去发呆的。
所以,偶尔,我会表现得相当勤奋,忙碌得像119火警,而在有些时候甚至大多数时候,看上去则非常懒散。还有,同理,我写得越多的时候会越好,写得越少的时候则越差。多与好,少与差,这时机又不完全由我自己来掌控,我从一开始写作就了解自己身上的这个特点和规律,于是就很少有写作焦虑,写得出来就写,写不出来拉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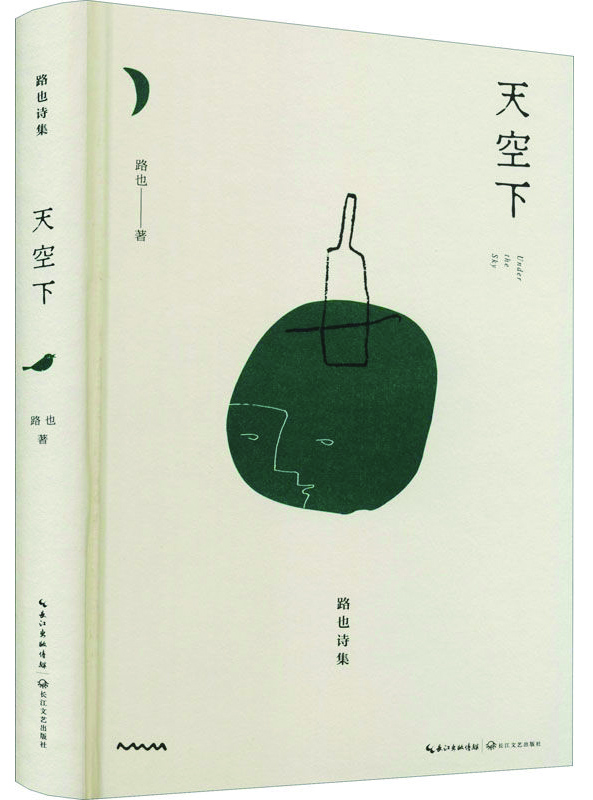
记 者:在《天空下》第一辑中,我注意到,《寄自峡谷的信》《山中信札》《致一位生日相同的诗人》《致一位捐献遗体的亡友》等诗作都带有“信件体”或者说“对话性”的意味。在其他诗集中,2004年写的“江心洲”组诗,还有2020年写的《野菊来函》等也是如此。您的诗歌中为何有这么强烈的对话意味?您写作的时候,有预想中的理想读者(倾听者)吗?
路 也:所有诗歌里应该都有对话与潜对话吧,潜对话也可看作内心独白的一种延展。
T·S·艾略特认为诗歌里有三种声音:第一种是诗人的独白,第二种是诗人对读者说话,第三种是诗人借用他创造出来的人物在说话。这三种声音归根到底都是诗人自己发出来的声音,只不过表现角度不尽相同。这些情形在我的诗里肯定都是存在的。
另外,我确实特别喜欢自言自语。每时每刻我都会在“内心里”进行一场场对话,与另一个更遥远的“我”对话,与预想中的某个现实而具体的人物对话,与虚构的人物对话,与巨大而无形的至高者对话。我经常感到身体里面有两个以上的人在说话,甚至一群人在发言,有问有答,有时还会以“焦点访谈”的形式就同一个事情来各抒己见,还会发生辩论和争吵,拍案而起。越是独处的时候,这种情况就越发明显地发生。这种对话当然基本上都是以无声的方式进行的。可笑的是,偶尔——当然这种情况极少发生——也会成为有声的,我会不由自主地说出声来。这个习惯从小就有,父母不在家,我一个人在屋子里时,会看着墙上的相框说话,上厕所的时候,挺喜欢把自己关在里面说话,甚至说出声音来,家里人就在外面问:“你一个人在里面,嘟囔什么呢?”这种发生在内心里的对话,使人永不寂寞。
这个特点肯定影响了诗歌写作,但是,具体的诗歌写作过程又是一个混沌的过程,我从未有意识地去预想出所谓理想读者或倾听者。那么,我潜意识中是不是预想过这样的读者或倾听者呢?我不知道。
记 者:《天空下》第二辑主要是写您在游历过程中的所思所想。根据您的诗文,您一方面是“社交恐惧症患者”,另一方面又是买了许多旅行箱随时准备出发的人。这种“遁世”和“云游”的矛盾,如何在您的身上协调起来?“云游”对您的诗歌认知和写作产生了什么样的影响?
路 也:我从来没有打算“遁世”。我可能生来身上携带的那台马达就比别人的马达功率要小一些,应付不了大场面、大事件。同时,我还是一个需要终生服药的桥本甲减病人。最关键的是,我从小就怕人,无缘无故地怕,我为此很苦恼,看了很多心理学方面的书,认为自己患有典型的“逃避型人格障碍”,我还做了测试题,社交恐惧症达到最高级别。
你用的“云游”这个词真好,比我常用的“行走”和“旅行”都更加准确地表达出了我想要的那个状态。我的所谓“云游”,就是到大自然当中去,尤其去环境完全陌生的异国他乡,并且尤其偏爱去往荒野僻壤。我基本上都是一个人独行,这反而让我感到无比自由、无比自在,零社交。
诗歌并不是旅行的记录,诗歌也不应该是旅行的记录,但是诗歌写作者可以通过旅行,让久存心底的一些情绪和经验被重新激活,精神的地平线被打开来,内心的激情和困厄会投射到途中的风物上去。比如,在一个荒僻旷远之地,一个人生命中潜藏着的冲突和苍凉,会突然被激发出来并得以释放,这对心理伤痛有治愈作用,同时在诗歌中也会有所反映。
当然,“云游”的动力和目的只在于生命本身,并不是为了写诗,如果不写诗,我也照样会去“云游”。
记 者:《天空下》第三辑收录了《巧克力工厂》《徽杭古道》两首长诗。一般说来,短诗适合表达片光零羽的思绪,长诗适合书写一些复杂性的经验。但是,这个时代的经验大多是碎片化的,您是如何尽量把碎片化的经验,转化为具有总体性、连贯性的长诗来?
路 也:自2010年至今,我所写的长诗已经近20首了吧,从《心脏内科》到《城南哀歌》《老城赋》,再到《巧克力工厂》《徽杭古道》,直至更近的《大雪封门》。现代生活就是碎片化的,诗歌在反映它时,亦可以用碎片化来表达——但关键是,这些碎片如何被处理,不是把一堆碎片摆在这里就完了,而是应将碎片在诗中进行“整合”,整合到一个统一的调式或语势中去,这种调式或语势会形成一个大气压或者说形成压强,用以统领全诗,嗯,这可能需要听觉想象力……其实,T·S·艾略特已经这样做过了。
记 者:从“郊区”到“城南”,再到“南部山区”,您一直在诗歌中建构属于自己的诗歌地理。从名称的变化来看,这是一个不断具体化的过程,始终不变的是您对于自然的亲近。您不仅在自己的诗歌(比如“南部山区”组诗)中书写自然,而且还刚出版了一本探讨古代诗人与植物关系的随笔集《蔚然笔记》。执着于自然、植物,是什么原因呢?
路 也:每当我看到一棵草,向别人请教这种草的名字,对方不知道,却一定要回答“它叫野草”,我就很生气。人家这棵草是有名字的,跟一个人一样,有学名、有乳名、有笔名,现在统统叫作野草,那就等于说人类也没必要称呼彼此的名字了,都叫“男人”“女人”“中国人”“外国人”“男生”“女生”“工人”“教师”算了。这样做,实在是不够尊重。在有网络之前,无法上网查证植物名称,也买不到帮助认识植物的书籍,我就买了一本《绘图儿童植物辞典》来看,那上面有错误,把迎春花和连翘给弄混了,后来我干脆买来插图版的《本草纲目》,有相当多的植物都属于中草药,通过中草药的图片来认识植物,也是一个好办法。
将大自然或者说自然风物的元素融入写作,对于我,由来已久。不知道是不是与幼年的成长经历有关,我在济南南部山区出生并长到10岁,那里其实就是泰山的北坡,山重水复,青未了,一个后花园式的地方……当然,这很像是有些刻意地构想出来的理由,其实我对自然的亲近,可能出自天性和个人认知,说成个人偏好也许更恰当吧。
《蔚然笔记》是以活泼的散文随笔语调和口吻写出来的一本“轻学术”类书。结合我的个人经验,力求寻找到一个新鲜角度切入主题,同时还要袪魅并颠覆一些刻板印象,最终通过定睛于中国古诗词中的植物,试图刻画出诗人的命运和魂魄。
记 者:在翻阅您的创作年表时,我看到这样一句话:“2009年,写出长篇小说《下午五点钟》,以此书作为自己多年小说创作生涯的终结。”但据了解,您最近将有一本写童年的长篇小说出版。是什么原因让当时的您停下小说之笔,而现在又重新拾起?诗歌和小说两副笔墨,对于您而言有何区别?
路 也:我真的计划不再写小说了,主要是身体不好,同时又遇到了写作瓶颈。但是,在2022年夏秋之交,竟又出乎我个人意料地完成了一部与童年有关的长篇小说,内容围绕我十岁之前生活的济南南部山区“仲宫镇”来展开,笔法介于小说和散文之间吧。
我写这个长篇小说,不为文学理想或文学目标,只是为了完成一桩心愿,主要是觉得我的童年需要这样一份文学化的记录。过去听人讲起童年对于一个作家的重要性,很不以为然,觉得实在有夸大之嫌。但是人到中年之后,我才感到童年的重要性,几乎可以用“重大”来形容,童年是一个人的内核,既是始也是终,是计算机运行中的“0”和“1”……就是这样,在外面转了一大圈,我的心态似乎又回到了小时候。
我私下经常对好友谈起一个奇怪感觉。很多年以来,我都感到自己身体里面似乎一直都有一个小女孩,而且不大不小,正好8岁,她像套娃娃一样套在我身体里面,这个小女孩经常对我发号施令,指挥我干这干那,一般都是她赢,我乖乖地去干。我想把这个8岁小女孩写出来,其实她就是我当年在“仲宫镇”时的模样。
诗歌和小说,或者再加上散文随笔,甚至再加上文学评论,这样的两副笔墨或者三副笔墨、四副笔墨,只能说明我三心二意,不够纯粹。我这个人就是一辆唏哩咣当的大篷车,什么都往里面装载。或者这么说吧,我有一套房子,三室一厅或者四室一厅,一间房子用来写小说,一间房子用来写散文随笔,一间房子用来写诗,一间房子用来写评论,而门厅是用来教书和过日子的。当然,我的思维是发散式的和跳跃式的,带有很大的不确定性,更适合写诗。如果非选择一个不可,我选择诗歌,我最喜欢“诗人”这个身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