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兴:这样的刘恪
那是个夏天。诗人树才拿来一本《新生界》杂志,对我说:这期上的长篇《蓝雨徘徊》,你有空看一看吧,是一位叫刘恪的朋友写的。

我读起了《蓝雨徘徊》。一个以水为背景的小说,没有传统的故事结构,没有在大多数阅读者看来必要的过渡和交代,没有情节推进,有的只是数百节零散的碎片,有的只是弥漫的神秘和诗意,有的只是汉语散发的特殊魅力。一种可以当作画来欣赏,可以当作谜来琢磨,可以当作音乐来听,却偏偏很难用言语说明白的小说。小说没有为宏大话语唱赞歌,显然也不是大众娱乐的饮品。但它对我的冲击却是巨大的。冲击伴随着惊讶:原来长篇小说还可以这么写。我竟不忍心一下子读完,而是每天读几页,读了整整一个月。刘恪以及刘恪笔下的双调河成为那个夏天的鲜明记忆。
想见刘恪。依然在树才家,外面下着雨,刘恪进门,扛着一袋大米,气喘吁吁的。树才纳闷:这是干嘛?刘恪急忙解释:单位里发的,我一个人哪吃得了?随后,树才为我们正式做了介绍。我谈了谈对《蓝雨徘徊》的喜爱。刘恪听着,很专注的样子。他告诉我们,花城出版社已将这部小说列入“先锋长篇小说系列”,只是标题要改为《蓝色雨季》。我们都觉得《蓝雨徘徊》更有味道,改了实在可惜,能不能不改?出版社可能有自己的考虑吧,刘恪心平气和地说。
过了几天,刘恪请我们到他在北师大借住的寓室里做客。朋友,朋友的妻子,朋友的朋友,一共来了十几位。刘恪给每个人倒上一杯饮料,再削好一只苹果,然后,走进厨房,绝对不让任何人插手,一个人不慌不忙、不紧不慢地在里面洗洗弄弄、拍拍打打、切切剁剁,不到一个钟点,便将二十几道冷盘热菜端了上来,而且色香味俱全。奇怪的是,他本人除了一两种蔬菜,基本上什么都不碰,只在一旁笑眯眯地看着大家吃,时不时给女士添点饮料,给男士加点啤酒。一问才知道,他是个素食者。一个素食者却会做这么多的大鱼大肉。连尝遍各种山珍海味的周军都佩服得五体投地:凭着观察力和想象力,就能做得这一手好菜,太厉害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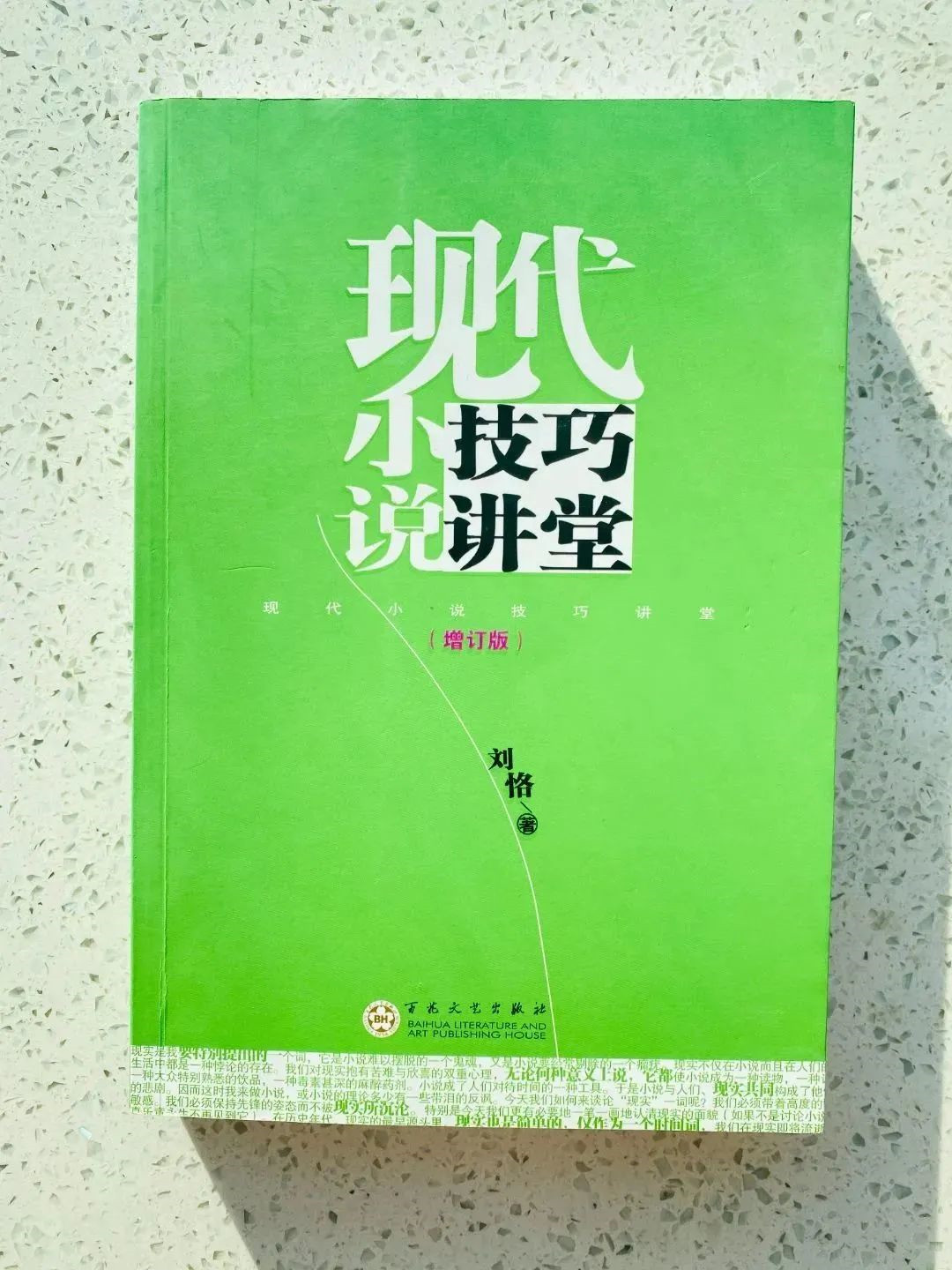
之后,刘恪忙着主编杂志,我则去了美国。尽管时空拉开,但彼此都惦记着。
从美国归来后,很快又见到了刘恪。这时,他的长篇已出版并获了奖。在书的跋中,他的大段感激朋友的文字给了我极深的印象。“在这个焦虑的时代,朋友变得异乎寻常的珍贵。”我从小离家上学,独自在外生活了这么多年,明白这句话的分量。
我们的交往渐渐多了起来,彼此的了解也慢慢深了起来。起先,见面时主要谈一谈文学,谈一谈各自读的书。后来,就什么都谈了。他的朴实,他的真诚,他的稳重,他的倔强,他的令人惊讶的率直,他的有一定原则的随和,他的细致和慷慨都是些极能吸引我又极能打动我的东西。再说,他还有那么出色的才情呢。这些还不是根本的。根本的东西我也说不清。兴许就是缘分。很快我就把他当作了最好的兄长和朋友。同他见面,我感到轻松,感到自然,感到可以剥去一切伪装。
在结束了长时间的漂泊生活后,刘恪终于在北京西边的一套公寓里安顿了下来,离我的家很近。一个电话,十分钟便可集合。只要在北京,我们几乎每个星期都要见上一面,每天都要通个电话。无论我到他那里还是他来我这里,一到饭点,他都会责无旁贷地挽起袖管,钻进厨房。一段日子过后,我实在不忍心让他这么劳累,决定到餐馆吃饭。但刘恪每次又都抢着付钱,弄得所有顾客都转向我们,不知发生了什么。到最后好不容易定下了这么一个规矩:北边归他,南边归我。
刘恪看上去木讷,实质聪明,绝对是个什么事情都可以做得地地道道的人。他当过老师,至今仍不断有年龄和他差不多的学生来看望他,请教他。当过记者,写过不少有棱有角的文章。当过主编,把一份部级刊物办得有声有色。当过教授,有将枯燥的理论讲述得十分好听的本事。还拉过二胡,学过推拿,研究过古文、易经、电影,等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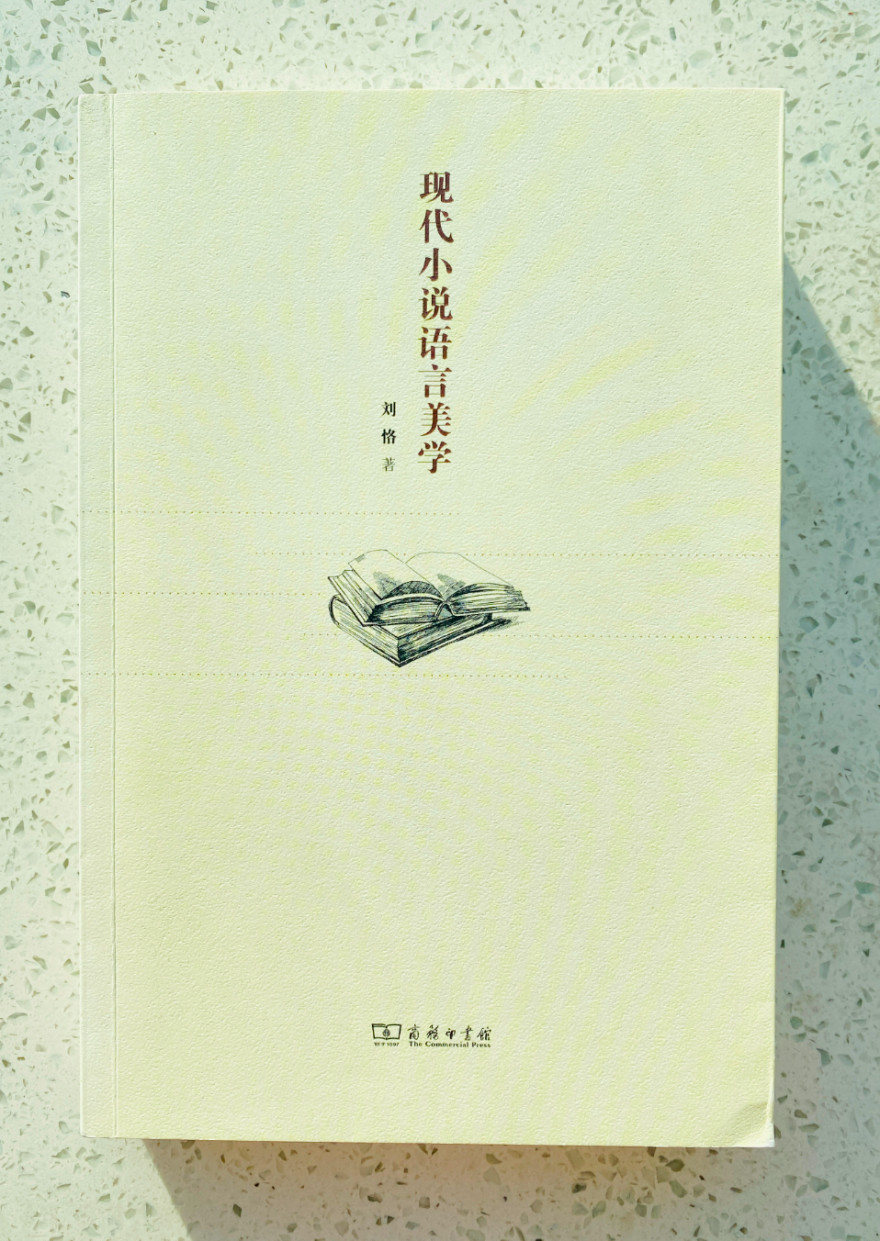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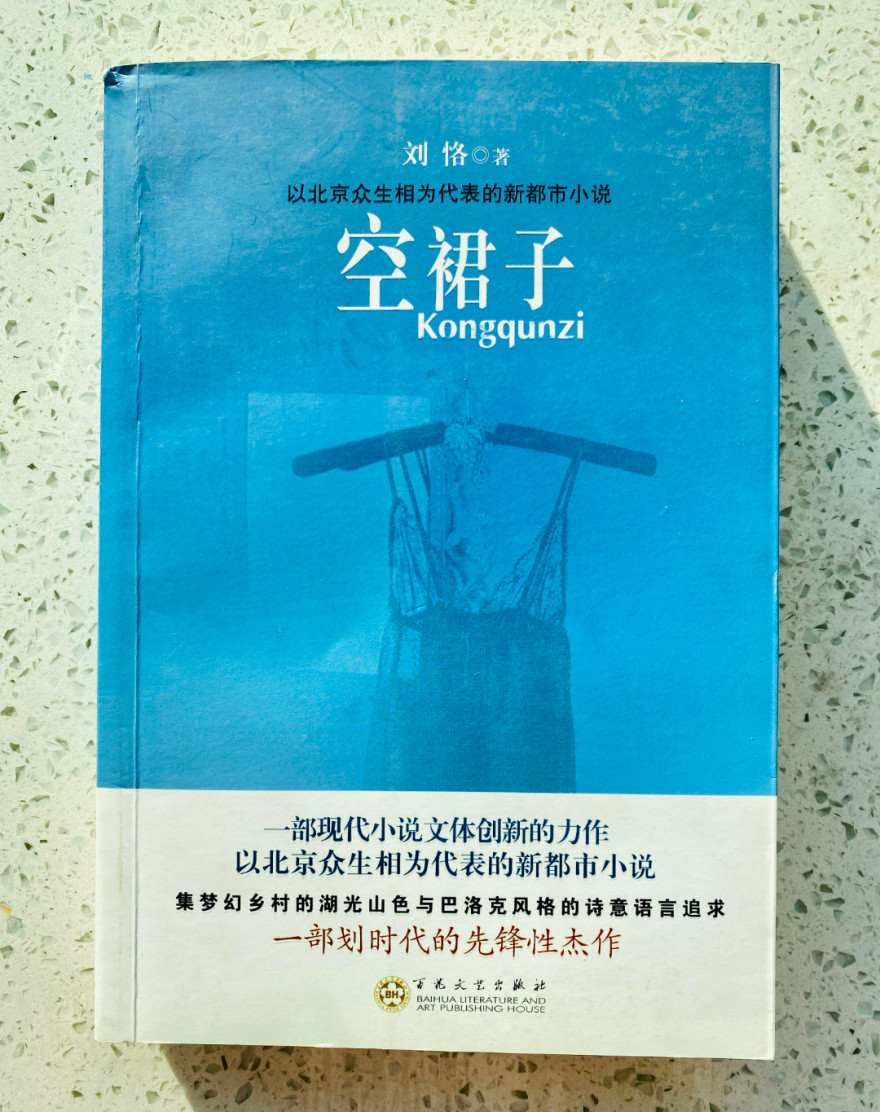
什么事情都可以做得地地道道的刘恪就是不愿认认真真装点一下自己的生活。对待自己,他有点太马虎、太随意了。挺帅的一个人,却从不想着去添些像样的衣服,各种场合都穿着那套标志性的牛仔服。家里厨房设备一应俱全,却从不想着为自己好好做上一碗汤、一道菜,常常一个馒头或一张烙饼就对付了一顿饭。常年吃着馒头、烙饼,顶多再加上韭菜、鸡蛋,身体却始终那么强壮,实在让人不敢相信。我就常常怀疑他是不是老偷偷地进一些补品,比如冬虫夏草什么的。倘若真的这样,倒也是件叫朋友放心的好事。可刘恪偏偏又总是坚守着他的带有乡土味的生存哲学:“不就混张嘴嘛,干吗要弄得那么复杂?”
我理解他。他的关注点在别处。在文字,在创作。全部的激情、全部的野心、全部的才华都转向了这里。一个不抽烟、不酗酒、不吃大鱼大肉,喜欢女人却不愿浪费时间去同女人谈情说爱的男人,终于还有自己痴迷的东西。他不会白活一生了。
《新生界》停办后,刘恪索性选择了自由写作的道路。除了我们的定期见面或偶尔的外出讲学外,他过起了半隐居的生活,几乎全部时间都花在了读书和写字上。他的阅读面极广,文学、哲学、历史、美术、音乐、科学,五花八门,无所不包。看着他读过的书,我就感到羞愧,再也不敢自称读书人了。你到他的屋子里会感到书的压迫:床上是书,桌上是书,电视架上是书,厨房里是书,而且都高高地摞着。他抱怨房子太小,搁不下太多的书。其实,给他多大的房子,他都会很快摆满书的。
春节将临,刘恪在电话中发出邀请:“到我这里提前吃顿年夜饭吧。”我知道他要写东西了。到他家时,菜已经做好。桌上整整齐齐放好了碗筷。其中有一套碗筷是为他故世的母亲准备的。他会先恭恭敬敬地为母亲倒上一杯酒、夹上一些菜,然后轻轻地说一声:过年了。吃年夜饭时,他会破例喝一小杯酒。
第二天,他就将自己关在屋里,开始写作,每天十几个小时,通常一连要写上几十天,甚至几个月。我每天晚上都会打个电话问候一下。这时的刘恪声音显得苍老而又沙哑,毫无生气,每次都会告诉我当天写了多少:六千字,八千字,三千字,有一次,极沮丧地说:今天就写了五十六个字——他有在节日期间开始写作的习惯。惟有一种情况他会暂时中断一下自己的写作,那就是朋友急需他的帮助时。
他曾描绘过自己的写作状态:“我喜欢独处幽室,把门窗全闭上,窗帘全拉上,让室内布满淡蓝色的光,一丝声音也没有,把稿纸铺开,躺在藤椅里,让思绪自由流淌。梦在窗外,它蛰伏在槐树密叶的阴影之下,或者沿着长青藤爬上屋顶,延伸到楼旁的给水塔,在忧郁的黄昏中吸收离愁别绪的养分,让孤独和惆怅潜入室内,心境保持那种万分的无奈,这时额头便分泌出许多文字,如同肌肤上细蜜的纹理时刻地缠绕我的全部生命。”
有写作经验的人都明白,这已是作家在一次写作完成后对写作状态的诗意化描述了。实际上的写作过程绝没有这么多的诗意,其中的艰难困苦往往是言语难以形容的。何况刘恪又是个在创作上极为讲究、始终保持着挑战姿态的作家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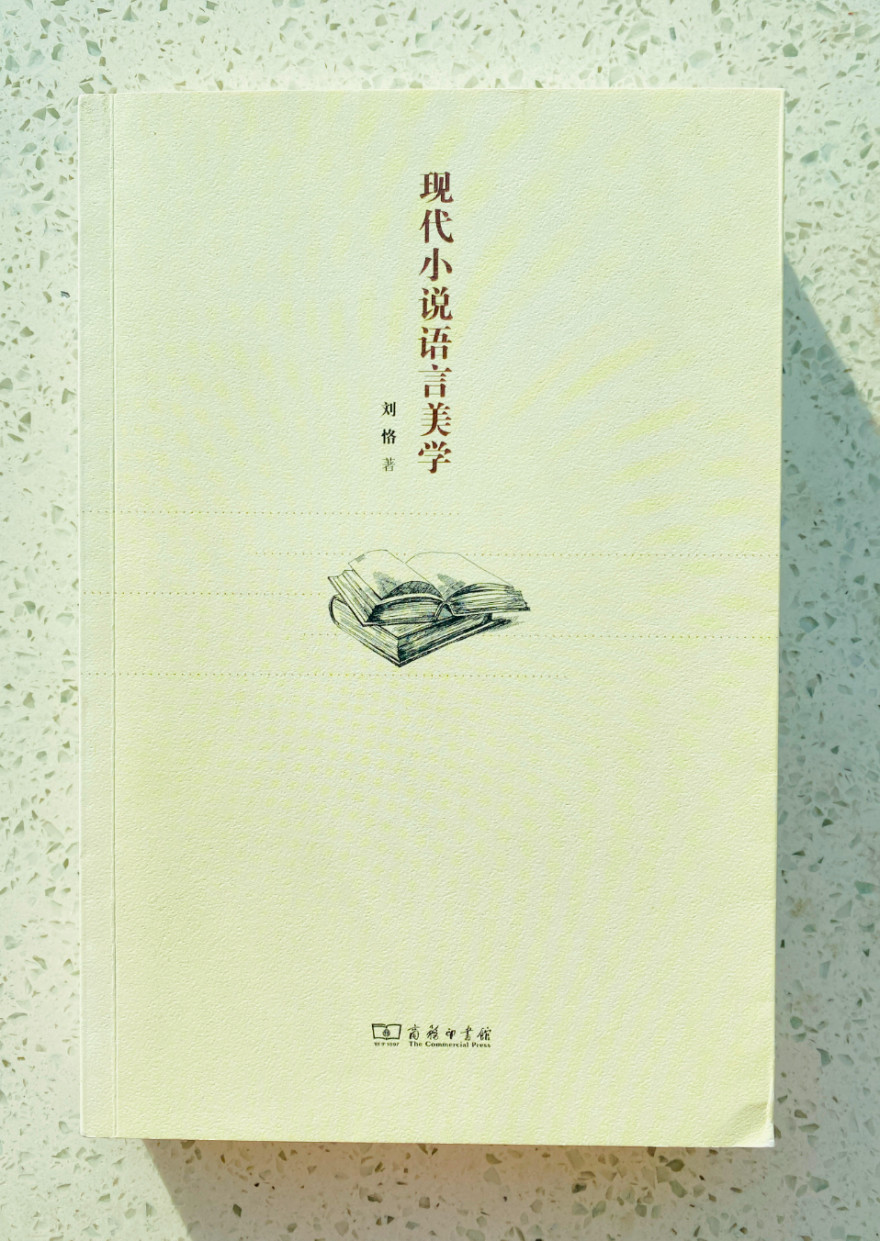
他对词语的高度敏感就给过我极大的震撼和启示。他说:“对词语要有数学家的精密准确。一个词语你要嗅嗅、抚摩、舔舔、拍打,然后久久地注视它,感受它的重量、体积、味道、色泽、软硬、速度,用在句子中必须对整体审视,稍不合适便要置换,这个工作比数学计算还要严密,它使词语具有刀锋般的力量。”当今世界,如此众多的写作者中,还有几人能做到这一点?
在一次长达数月的封闭式写作后,刘恪打来电话,很平静地说:“《城与市》写完了,你先读一读,提点看法。”
我在惊喜和钦佩中一口气读完了这部四十多万字的三卷本长篇小说。阅读时还兴奋地写下了一段段理解和感受:
进出《城与市》,进出一片语言的迷宫。这实际上也是一片生活的迷宫。
摆脱不了的诗意围绕着“城与市”,摆脱不了的神秘充斥着“城与市”。“城与市”呈现出不同的状态:哲学札记式的冷峻,散文诗的忧伤,诗的晦涩,通俗小说般的诱惑,言语的痛苦------
女人的内心是一座城。这是关键。走近女人,也就是走近城与市。那么多的女人,那么多的城市。城市中的城市。城中城,市中市。
解剖城市,审视城市,迷恋城市,贴近又拉开。作家的思路在城与市中徜徉,时缓时疾,时明时暗,读者有时难以跟上。但多少错综、精致、微妙的情感隐于其中啊。
杂乱无章的意象扑面而来,这就是城与市了。最抽象的和最具象的结为一体,这就是城与市了。
梦境。大段大段的梦境。梦境能表达一些极至的东西。人生如梦。
“城与市”是个圆周,是个循环。起点就是终点,终点就是起点,甚至可以说起点和终点均不存在,存在的只是行走,停顿,再行走。圆周,你可以将它视作零,视作无。你也可以将它视作一枚果子,一种圆满。
居住于城市,我们实际上也就是居住于片段之中。就此而言,《城与市》的形态反映了更大的真实。它更多的不是给你一个故事,而是给你一种感觉,一种体验,一种顿悟,一种迷惑,一种询问,一种思考——
这是个考验阅读的文本,是个可以反复阅读的文本,也经得起反复阅读。每读一次,你都会有新的感受,因此,这又是个无限敞开的文本。它还暗含了文学性质上的一种改变,即由反映论、表现论转向建构论。无数体式都可以为长篇形态建构,在结构的同时又不断解构。这表明一部长篇小说完全可以是多种可能性的并存和综合。除了确立全新的结构形态,小说还试图重新建立意义系统。《城与市》的意义不是由整体表达的一个意识形态的结论,而是面对每一个局部的词汇范畴的重新阐释。因而,我们又会惊讶地发现,小说还能成为对无数基本词汇的深入考证。
《城与市》是作者生命力的一次喷涌,是无数生存体验的一次倾诉,是卓越才情的一次泄露。
我长期从事外国文学编辑工作,中国和世界各国的小说都多多少少读过一些。说实在的,像刘恪这样将小说做到这等极端、这等境界的作家不要说在中国,哪怕在世界范围内也不多见。这需要才华、学识和阅历,也需要勇气。这同时也注定了他的孤独。喧嚣中的孤独。好在刘恪早已自觉地接受了这种孤独。他是个为少数读者和未来读者而写作的作家。或者,更确切地说,他是个为文学本身而写作的作家。这一点,他应该比谁都清楚。
在《城与市》《梦与诗》等长篇之后,刘恪又一口气写出了几十个可称作极品的短篇小说。透过这些短篇,我感觉他是在寻找人性一些隐秘的本能,在探索事物存在的种种可能。《没完》表明一切存在无论合理与否都将绵延下去。政治,军事,民族矛盾,人性邪恶,甚至包括性,都是如此。彻底的解决和了断是没有的。没完恰恰是世界的永恒性。既然存在是没完的,我们就必须找到一些内在的成因。于是,刘恪又在《制度》《生物史》《风俗考》《博物馆》《向日葵》《阳光女孩》《空裙子》《纸风景》等小说中进行了多元多维的可能性探讨。人性的复杂不是人们想象的结果,而是人自身理由的扩展。《考古学》是关于历史、战争、人性的思考和结构主义的考察。小说通过一些极端的细节和微小的偶然揭示我们对历史的误解,表明我们所言的重大历史原因原本有可能就是错误的。改变历史的可能就是那么一个偶然的细节。重大和微小在事物内部的作用其实是同等的。或者干脆,“没有历史,你便有了发现”。《墙上的鱼耳朵》以不断涨出的密密麻麻的枝节探索了这么一个问题:事物与人的发生成长过程不仅是历时的,更是共时的。一个女人的存在和死亡与一种语言文字的存在同质,甚至文字叙述方式也是如此。因此事物与人是在所有细部同时长出来的,而人与物过去的成长只是我们对时间的幻觉------当然喽,以上只是我对这些短篇的极为概括性的理解。实际上,在具体的阅读过程中,你的感觉远远会比这些理解丰富得多、饱满得多、复杂得多。比如,读《墙上的鱼耳朵》,你也有可能会将它当作一个有关秘密的寓言,还有可能把它理解为一个有关无限可能性的文本。你也完全可以认为这是一次有关真实的探究,还可以觉得这是一种想象的游戏。世界上,真有所谓的真实吗?想象如何改变着生活的面貌?你会问自己。有时,最最不可能的事情恰恰就是最最可能的事情。有些感觉就连刘恪本人恐怕都预想不到。内涵丰富的小说大概就该是这样吧。文字一旦长出翅膀大概就该是这样吧。刘恪的许多短篇我都是在驻外工作时读到的。在异国他乡,在黑海之滨,这些闪光的汉字充实了我多少寂寞的时光啊。它们同时还成了我同我的祖国的一种诗意的联结。要感谢刘恪!也要祝贺刘恪!都知道短篇小说最难写了。某种程度上,可以说,这些精致、耐看的短篇更能显示刘恪的艺术功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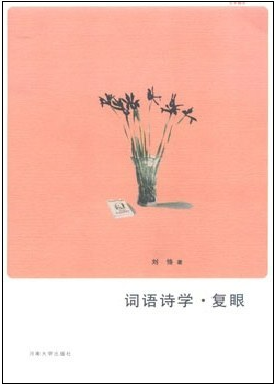
已经写了四百多万字了,小说、散文、诗学,什么都有,刘恪还在孜孜不倦地写。我们觉得他实在太辛苦了,总是变着法子拉他出来散散步,聊聊天。我们几个特别好的朋友也喜欢听他说话。每回他都会讲几个精彩的小故事,都是自己编的,或者讲一些生活中的观察,比如,女孩哪里最性感,树叶什么时候最好看,眼睛有几种,等等。以他的编故事的能力,写影视剧本,写通俗小说,都有可能挣大钱。但他拒绝时尚,不愿放弃自己在创作上的固有姿态。有评论家称他为“一个在拒绝中探索的作家”,实在是恰当。
他的这种专一同样体现在了对友谊和人情的看重上。自己都快没饭碗了,还照样为了朋友拿出手头所有的积蓄。自己的稿费拿不到不要紧,但朋友的稿费一天拿不到,他就一天吃不好饭,睡不好觉。到他家做客,他总会把家里最好的东西捧出。我们就是这样在他那里尝到了烟台的苹果、湖南的熏鱼、瑞士的饼干、德国的巧克力和法国的葡萄酒……
兴许是长期书斋生涯的浸染,兴许是性格使然,刘恪身上总有着某种摆脱不了的单纯、超然、“不谙世事”和“不通常理”。只要走出家门,就会有故事发生。一回,我们约好去逛逛书店。见面时,他一脸的委屈,不断地说:对人不能太好!对人不能太好!我急忙问个究竟。原来,他老兄出门时,特意敲开了邻居家的门,极认真地提醒道:听说最近有可能要发生地震,最好留点神。结果,邻居狠狠瞪了他一眼,一句“莫名其妙”回报了他的好心。那天正是大年初二。又一回,生病住院时,他要洗澡,看到一间屋子,又看到了屋子里的几个淋浴器,便径直走了进去,痛痛快快地洗了起来。洗着洗着就听见外面有几个女人在嘀咕:一个男人怎么跑到我们女浴室洗澡来了?还有一回,在湖南某镇,雨天,他穿越泥泞的农田去看望儿时的伙伴,皮鞋全湿透了。拿到火上烤烤,一不小心烤化了。无奈,他只好趿拉着一双棉拖鞋进到镇里买鞋。最后,在一家供销社买到了一双结实无比的皮鞋。回到北京,有朋友出于敬重,邀他及他的朋友到五星级饭店用餐。他就穿着一身牛仔服,横挎着一个大书包,足蹬那双结实无比的皮鞋赴宴去了。当我们步入饭店大门时,所有服务生都下意识地将目光投向了刘恪,并本能地朝他鞠了鞠躬。经验告诉他们,真正的大款往往是些着装举止具有鲜明个性的人。刘恪穿的那双皮鞋是轧钢工人穿的那种翻皮劳动鞋。寻遍长安街,你也找不到第二双来。

类似的故事还有许多许多。碰到这样的情景,他总是自嘲:“我就是个土老冒。”
话说回来,不这样,刘恪也许就不是刘恪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