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得2017年阿多尼斯访问上海时,有一次晚饭后跟我一起在街头散步,他对我说:“你已过了中年,以后要集中精力,留下一些有价值的东西,证明你到这世上来过一趟。”这番话经常出现在我脑海里,促使我提醒自己不能懈怠,要努力留下能证明自己“到这世上来过一趟”的成果。 薛庆国:努力留下有价值的东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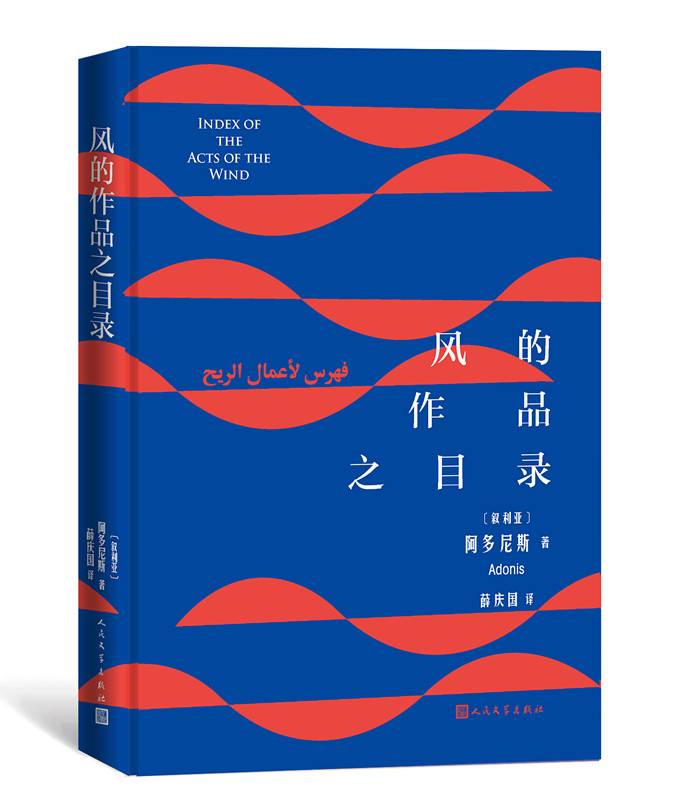
《风的作品之目录》,[叙利亚]阿多尼斯著,薛庆国译,人民文学出版社2021年1月出版,42.00元
今年8月,北京外国语大学阿拉伯学院教授薛庆国的译著《风的作品之目录》,荣获第八届鲁迅文学奖文学翻译奖,《阿拉伯文化中的中国形象·现当代卷》也同时出版,这是我国学术界首次系统地研究阿拉伯文化中的中国形象,不仅具有开创性学术意义,而且富有现实意义。眼下,薛庆国正在编写《阿拉伯文化经典读本》和《当代阿拉伯思想读本》。他说,自己最大的心愿是潜心撰写一部《阿拉伯文化史》。
中华读书报:能否谈谈您的阿拉伯文学翻译经历? 您对阿拉伯文学怎么看?
薛庆国:博士毕业留校后,我意外发现纪伯伦的许多著作都未译成中文,便从国家图书馆复印了原著,迫不及待地开始翻译。此后共译了他的7部著作,包括散文、散文诗、诗歌、传记、书信集等。后来还译过诺奖得主马哈福兹的随感类作品《自传的回声》,以及叙利亚作家沃努斯的剧作《奴仆贾比尔头颅历险记》,还译过巴勒斯坦诗人达尔维什的诗歌选集《来自巴勒斯坦的情人》,并在《世界文学》《星星》等刊物发表过多位阿拉伯现当代诗人的专辑。我还曾参与翻译过《一千零一夜》。此外,另有一些短篇小说、散文的译作被收入多部选集。近几年译的最多的是阿多尼斯的诗文作品,共发表了7部相关译作。除了阿译汉以外,我还和叙利亚著名学者费拉斯合作,翻译出版了《老子》《论语》《孟子》等中国文化经典。近期还会出版一本阿拉伯现当代名家诗选。以后还有计划继续翻译阿多尼斯的作品。
阿拉伯文学在世界文学版图上占有重要地位。古代阿拉伯文学的最高成就是诗歌,诗歌历来被称为“阿拉伯人的史册”。阿拉伯散文文学也有许多名作传世,其中最为世人熟知的,无疑是民间文学巨著《一千零一夜》。阿拉伯现当代文学既与世界文学的主流接轨,同时又保留了浓厚的阿拉伯本土特色。古今阿拉伯文学都有许多杰作精品,值得我们去了解。这个话题太大,我只能用三言两语简要回答。
中华读书报:纪伯伦对中国作家尤其诗人的影响如何,您了解吗? 您认为纪伯伦对中国的贡献是什么?
薛庆国:纪伯伦是在中国最有影响的阿拉伯作家,也是最有影响的外国作家之一。他的作品,特别是《先知》《沙与沫》,在中国有非常广泛的读者群。我想绝大多数中国作家、诗人都读过他的部分作品。有的诗人朋友说纪伯伦的作品以哲理性见长,但其实这只是指《先知》而言。纪伯伦是阿拉伯现代文学的先驱者和奠基者之一,他对传统与现实的深刻批判和反思,在他所处的那个时代和文化背景中,是十分难能可贵的,对好几代阿拉伯知识分子都产生了深刻影响。同时他又是一位超越时代的先知先觉者,他的作品中,我们能找到男女平等、人与自然和谐相处、人类命运共同体等先进理念;他关于宗教的深刻见解、对东西方关系客观而理性的认识、对创新意识的强调,对于当今阿拉伯民族乃至整个人类而言仍然具有启示意义。我相信中国人也能从中获得许多启迪。
中华读书报:您还与叙利亚学者合作翻译了《老子》《论语》和《孟子》三部中国古代思想经典,向阿拉伯世界传播中国传统文化。
薛庆国:这三部中国思想经典,是我和叙利亚著名学者费拉斯先生合作翻译的。最早合译的是《老子》,是我在他从英文转译的《道德经》基础上修改后,列入《大中华文库》于2009年出版,我也因此结识了费拉斯先生。叙利亚内战爆发后,我于2012年邀请费拉斯前来北外任教。他接受了邀请,来北外连续工作了6年。在此期间,我想利用他在北外工作的这一难得机会,跟他继续合作翻译中国文化的经典著作,因为在我看来,翻译中国文化经典的最好方式,是中阿专家合作翻译,这样既能保证对经典的理解正确,又能让译文典雅、地道。我们着手翻译时设定的目标,就是贡献出“对得起经典、经得起专家和读者评说的高质量译本”。在过去的几年时间里,我和费拉斯先生愉快地合作,经过无数次字斟句酌的讨论,以及出版过程中的多次审校,我自认为这三部经典的译本都是高水平的译作。
中华读书报:您翻译的阿多尼斯诗集《风的作品之目录》获得第八届鲁奖。您什么时候开始接触阿多尼斯?
薛庆国:我最早接触阿多尼斯,是通过他的作品。上世纪90年代末在叙利亚工作期间,我开始从伦敦出版的阿拉伯文《生活报》上读到阿多尼斯的专栏,我惊奇地发现,这位当时我还不熟悉的诗人,还是一位杰出的思想家,其专栏文章观点之新锐、立场之鲜明、涉猎之广博、思想之精深,在阿拉伯现当代文学界、思想界实属罕见。从那时起,我就折服于他的文字与思想,也产生了翻译他作品的念头。第一次见到阿多尼斯,是2009年3月他来中国出席中文版诗选《我的孤独是一座花园》的首发式,我去机场接他。见面之前,我想象这么一位著作等身的大诗人、大思想家会不会有什么架子,因此心里多少有点顾虑。但是一见面,一切顾虑都烟消云散,因为面前的这位老人,实在是太随和、太好相处了。记得刚到饭店房间,我看他带来三件大行李,便问他在巴黎是否有别人帮他准备行李,他说:“为什么要别人帮忙? 难道你忘了我是个农民?”
中华读书报:您对阿多尼斯有什么印象?
薛庆国:从2009年3月起,阿多尼斯一共到访中国9次,每次基本上都由我全程陪同,我们结下了深厚的友谊。阿多尼斯是一位多重批判者,他拒绝人云而云,随波逐流。此外,他还勇于作自我批判和反思,这在一些散文作品中有所体现。阿多尼斯的这种姿态让我佩服。记得2017年阿多尼斯访问上海时,有一次晚饭后跟我一起在街头散步,他对我说:“你已过了中年,以后要集中精力,留下一些有价值的东西,证明你到这世上来过一趟。”这番话经常出现在我脑海里,促使我提醒自己不能懈怠,要努力留下能证明自己“到这世上来过一趟”的成果。希望我的下一部著作《阿拉伯文化史》,能成为这样的成果。
中华读书报:您翻译了阿多尼斯很多作品,对他的评价有没有改变?
薛庆国:我迄今翻译的,大都是阿多尼斯比较易懂的诗歌,还有一本能大体上反映他思想家特色的文选《在意义天际的写作》。他的长诗(特别是三大卷诗集《书:昨天,空间,现在》)和理论著作(特别是四大卷思想史著作《稳定与变化》),才是奠定他一流诗人和思想家地位的作品,但大都没有翻译成中文,或者只译了一些片段,因为这些大作对于译者和读者难度太大,涉及到阿拉伯文化、历史的方方面面。据我所知,在其他语种,对他的译介也尚不全面,一些重要诗作和理论作品也因为难度很大而没有翻译。根据我阅读和翻译阿多尼斯的经验,我认为,他不仅是当代阿拉伯诗坛的一位大师,还是矗立于阿拉伯当代文化顶峰的少数巨匠之一。阿多尼斯的贡献,在于他让阿拉伯当代诗歌走向世界,并让世界领略了阿拉伯文化不为人知的深度与活力;更重要的,是他为当代阿拉伯文化输入新的价值观念和美学标准,激发了这一文化内部的变革力量。
中华读书报:您对翻译的理解是怎样的? 对您来说,翻译最大的魅力是什么?
薛庆国:我认为,翻译最重要的原则还是“忠实”,不仅要忠实于原作的奥义,而且要尽可能传达原文形式的独特性和艺术性,因为好的作家、诗人都是文辞的大师,他们往往苦心孤诣,设计一些充满奇思妙想的结构上或文字上的机关。所以,一位译者如果不能忠实地传达这些精妙的机关,就对不起原作者的苦心。与此同时,又不能机械地理解对原文的“忠实”。译者固然要尽可能忠实地呈现原文的细节,但更要忠实地传达原文的整体风格;而且,细节要为整体服务,整体比细节更为重要。我小时候曾有过文学梦、作家梦,后来学了外语,这个梦想逐渐变得遥不可及。对我而言,文学翻译的魅力,在于它通过间接的方式,替我实现了自己曾经有过的文学梦。尽管如此,我并不希望别人仅仅把我视为译者。许国璋先生曾经表示,不希望别人把他仅仅视为英语教育家,因为他自认为是个哲人。我当然不能跟许先生相提并论,更不敢以哲人自许。但是,仅仅被看作一个译者,我还确实有点不甘心。那么我的身份到底是什么? 我的身份尚未成型,希望用我未来的成就去建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