柳鸣九:最后能留下小石粒就是最大的幸事
2015年,深圳海天出版社在京举办《柳鸣九文集》首发式,许渊冲、汝信、叶廷芳、金志平、罗新璋等译界“大佬”悉数出席。会上,时年81岁的柳鸣九先生的一头银发给大家留下深刻印象。面对包含文学理论批评、文学史、文化散文随笔、翻译四部分,收录他毕生主要作品约600万字的15卷文集,他自谦“只是浅水滩上一根很普通的芦苇”,“个体是脆弱的、速朽的,很多努力往往都是徒劳的,犹如西西弗斯推石上山。但愿我所推动的石块,若干年过去,经过时光无情的磨损,最后还能留下一颗小石粒。若果能如此,也是最大的幸事。”

柳鸣九(1934年3月18日-2022年12月15日)
柳鸣九先生曾在多篇文章和不同场合以西西弗斯自喻,自我定位为“文化的搬运工”和“精神苦力者”。但他留下的,不是平平无奇的小石子,更多的是在当时“激起千重浪”,而经过“时光无情的磨损”,至今仍闪烁着璀璨光芒的文化硕果。
不负父亲期待成为“读书人”
柳鸣九的名字来自于他出生时的体重。1934年农历二月初四,在南京做厨师的柳家诞生了一个“九斤子”,在父母的拜托下,隔壁老先生据此以“鹤鸣于九皋,声闻于天”之意,为他取名柳鸣九。在回忆录中,柳鸣九先生曾笑称:“此名甚为张扬,大有‘个人英雄主义’气味”,认为自己颇有点好名的个性,与此名字不无关系。
出生于民族灾难深重之际,柳鸣九童年少不了逃难奔波。一家曾偏安湖南耒阳三四年,后随着日军进犯,不得不前往桂林避难,从桂林仓皇出逃,经贵阳,花了不只一根金条才到了陪都重庆,在重庆市内一个十几平米半悬空的房子栖身。
耒阳时期,幼年柳鸣九仅有的文化活动是遵照父亲的指示每天练习毛笔字——做厨师的父亲对孩子唯一期待是“成为读书人”。直到在重庆念到小学到了五六年级,柳鸣九开始阅读课外书,跑书店,他感觉自己的精神、自己的心灵,寻找到了新的世界,“其作用在某些方面并不亚于我大学期间所受到的科班教育与严格的业务训练”。
抗战胜利后,随着父亲工作迁徙和全国解放,柳鸣九先后就读于南京中央大学附属中学、长沙广益中学、重庆求精中学、长沙省立一中,在中学时期开眼界、长见识,接触到英文和外国文学,自办了两期油印文艺刊物《劲草》,也受到严怪愚、彭靖等有文化理想的师长的熏陶。在长沙省立一中时,还曾因为迟迟不能入团的问题,经受了一番思想上的煎熬和磨炼。
1953年,柳鸣九如愿考上北京大学西语系,正好赶上了“北大最好的时期”,院系调整后,教育理念和制度更加规范成熟,课程设置合理,优秀学者云集,西语系由冯至先生主持,吴达元、李慰慈、李锡祖、郭麟阁、陈占元、盛澄华、李赋宁、闻家驷等曾为他们讲授语音、语法、精读、西方文学史等课程;他还聆听过王瑶、杨伯峻、田余庆等先生的文史课。此外,50年代后期,他也在大学校园经历了不寻常的政治运动,经历了思想上的淬炼和蜕变。对柳鸣九来说,这是“塑造成型的北大四年”,在此期间,他立下做一名学者或文化工作者的明确志向。1957年夏,他被分配到当时隶属于北京大学、后归属于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的文学研究所,“第一站”到了蔡仪任主任的文艺理论研究组《古典文艺理论译丛》编辑部。
在新中国成立初期,《古典文艺理论译丛》是具有一定开放性和先锋性的刊物,专门介绍西方各国古典文艺理论名篇,编委包括蔡仪、朱光潜、钱锺书、李健吾、卞之琳、杨周翰、季羡林、金克木、冯至、田德望等西学学者。刚毕业的柳鸣九被安排负责编务、外联和译稿相关的事务,经常骑着自行车往返于杂志所在的中关村和众多学者所居的燕园,每次都能增长见识,不啻为一次“业务进修”。他逐渐参与到译稿审校、翻译以及撰写评介文章等工作中,并被定为实习研究员,进入到文研所研究系列,主要方向是西方文艺批评史。在文艺理论室的六七年中,柳鸣九还曾在60年代初人民大学与文学研究所联合举办的文学研究班任助教;参与了周扬主持的高等院校文科教材编写工程中《文学概论》的编写;在50年代末60年代初批评“人性论”的讨论中,他曾就共鸣与人性的关系问题撰写文章——晚年,他认为自己最初在人性论与共鸣关系问题上有“左”的机械论毛病,但对阅读活动中各种情感活动形式的论述,“至少仍不失为实事求是之言”,是“比较深入细致的科学论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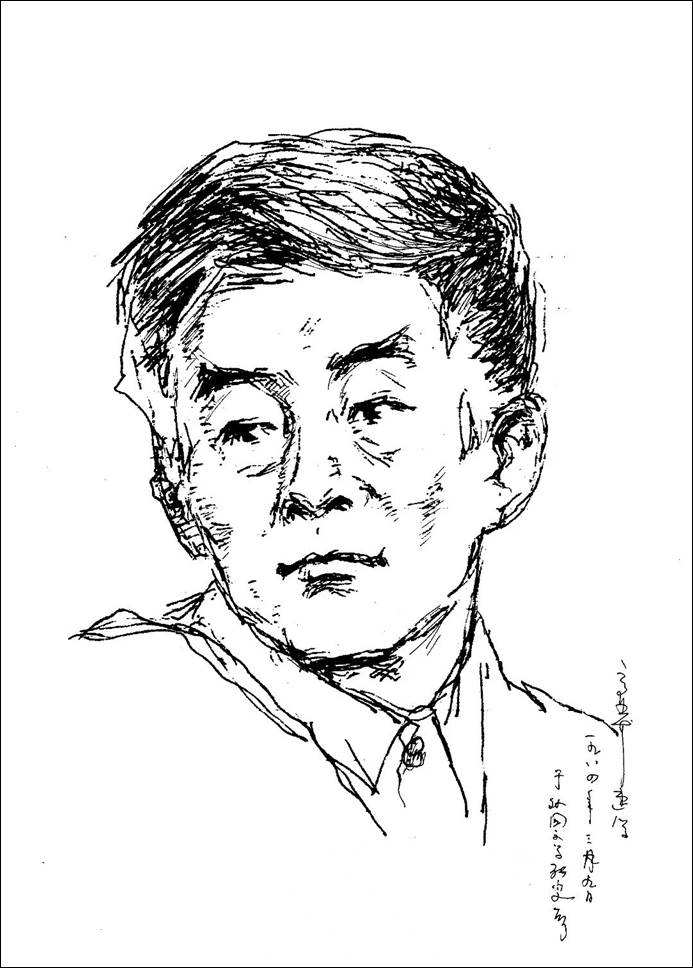
高莽先生所绘柳鸣九先生像。(图片由高莽先生亲属授权)
“逆反情绪”下编写《法国文学史》
作为“一个小小的西西弗斯”,柳鸣九先生在学术生涯中所推动第一块大石就是法国文学史研究。
在文研所初期定下西方文艺批评史的研究方向后,柳鸣九在文学思潮史、文学史以及西方文学理论批评方面下了一番功夫,为之后文学史研究和写作打下了坚实基础。
1964年,原有的西方文学室、苏联文学室、东欧文学室、东方文学室以及世界文学编辑部等从文学研究所分出去,成立外国文学研究所,冯至任所长。柳鸣九申请从文学研究所调入外文所。因为志趣上更偏重于文学史和作家作品研究,加之认为自己的感受力、敏锐性和通感力略强于逻辑思维和理论分析,他希望在外文所先潜心研究文学史,再进行理论的阐发和建构。1965年7月,根据周扬的指示,外文所要编写《二十世纪欧洲文学史》,任务落到柳鸣九所在的西方文学室。室主任卞之琳按照“集体任务由年轻人去完成”的老规矩,组成了有张黎、吕同六、郑克鲁、张英伦、朱虹、董衡巽,以及包括袁可嘉、郑敏等“中年人”在内的编写组,编写组的学术秘书就是柳鸣九。
外面已颇有“山雨欲来”之势。书斋里面,柳鸣九凭着之前在理论室对西方文学的功底操持起“学术秘书”的工作:编写组成员共同努力,在三个月内拿出了五六万字的《二十世纪欧洲文学史》提纲。 在此基础上细化阐述、丰富内容,文学史已遥遥在望之时,“文革”开始了。
1976年文革结束时,柳鸣九已经42岁。
文革后期的1972年,在河南干校的哲学社会科学部人员回到北京。运动中深感疲惫不堪的柳鸣九为寻求一个现实的避难所,与老友郑克鲁、张英伦、金志平商量后,打算编写一部法国文学史。1958年人民文学出版社曾出过一本苏联编选的《法国文学简史》,柳鸣九想编一部中国人自己的法国文学史。他认为,以编者的知识积累、学识、视野,在规模和丰富性上超过苏联的小册子“蛮有把握”。1976年,中世纪到18世纪的部分基本完成时,已经达到一卷的体量,编写目标遂由原来的一本书扩展到三卷。1979年,《法国文学史》上卷出版。进入新时期后,正常的学术和业务工作恢复,后两卷编写时间相应拉长,与此同时也有更多学者加入到编写工作中,直到1991年三卷本全部出版完成。
柳鸣九认同写作文学史如同提供旅游指南的看法,认为应尽可能掌握“第一手资料”,为对象提供尽可能完备的说明;他同时也认识到“我们生活在一个理论强势的时代”,特别是文学史写作不能仅停留在资料堆砌上,需要“论从史出”“史论结合”。《法国文学史》上卷出版后,李健吾称这是“作者为中国人在法国文学史上创出了一条路”;学者钱锺书在阅读了中卷概论部分后认为“叙述扼要,文笔清楚朴实”。
因为亲身经历文革所造成的思想文化领域的压抑,柳鸣九先生后来回忆说,编写这套文学史时,颇有些自觉的“逆反情绪”,要打破意识形态领域的禁锢,以马克思主义文艺感的立场指导编写,但“并没有走得太远”。进入新世纪后,有感于该书的时代局限性,柳鸣九花两年多时间对该书做了修订,特别是改写了第一卷中有关蒙田、拉伯雷等16世纪文学的部分内容。2007年,修订版《法国文学史》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柳鸣九先生为修订版撰写的长篇序言《关于<法国文学史>的修订》发表在2007年第5期《南方文坛》。在文章中,他反思了文学史中过于把文学发展过程与社会阶级斗争联系起来等方面的时代局限性,但对“《法国文学史》的观点过时了”的说法不以为然,认为思想文化特别是文学艺术具有特殊性,对于作家作品,宜将“阶级分析方法与心理分析方法、艺术分析方法综合施用”,而不应简单机械加以判断。
“中国萨特研究第一人”
“假如用一句话来柳鸣九先生——他是我国法语文学研究翻译界的一面旗帜,当之无愧的领军人物。”翻译家余中先眼中的柳鸣九先生“个子不高却很有湖南人的冲劲儿”,“性格上敢为人先,大家不说的话他就出来说了”,是个“能量很大的人”。最有代表性也最为人所熟知的体现,是70年代末重新评价“日丹诺夫论断”以及80年代将萨特介绍到中国。
1978年,关于真理标准的大讨论推动思想解放形成滚滚大潮。柳鸣九意识到这是一次难得的机遇,鼓起了学术上大有作为的信心,他将目标瞄准西方20世纪文学,从认为西方现当代文学是衰颓腐朽的资产阶级文化的“日丹诺夫论断”入手,对其进行重新评价。恰好当年10月,由社科院外文所承办的全国第一次外国文学工作会议在广州举行,同时将借此成立全国性的外国文学学会,时任所长冯至让柳鸣九作重点学术发言。这场会议主办和协办单位阵容强大,周扬、姜椿芳、梅益、朱光潜、季羡林、金克木、冯至、梁宗岱、草婴、楼适夷等文化界、译界人士云集。时年44岁的柳鸣九在大会作了题为《重新评价西方现当代文学的几个问题》的发言,从对20世纪西方文学艺术的社会性质、意义和作用的分析,西方现当代文学的思想内容和思想基础,如何看待西方现当代文学的艺术性,坚持历史唯物主义、科学评价西方现当代文艺等几个方面系统阐述了自己的观点,为20世纪西方现当代文学“讲公道话”。发言在会上和会后引起强烈反响,文章经修改整理后近六万字发表在1979年前三期《外国文学研究》杂志。
此举在柳鸣九先生自己看来,是十年浩劫后自己在学术上蓄势待发射出的一支“利箭”,是小的个人目标恰与大的时代机遇相契合。此后他陆续主编了《法国现当代文学研究资料丛刊》《西方文艺思潮论丛》、“法国二十世纪文学丛书”等,“其中的重点与贯穿始终的主线清晰可见,那便是对西方20世纪文化的说明与展示”,而这部分学术生涯的“起点与开篇”就是1978年广州会议上的发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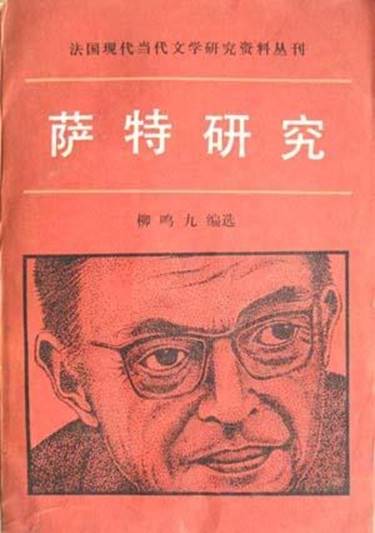
《萨特研究》 柳鸣九 编选,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出版
1979年,柳鸣九开始着手编选《法国现当代文学研究资料丛刊》,“进一步让事实说话”,将20世纪法国文学的典型现象展示清楚。鉴于萨特在20世纪法国文化领域的地位,柳鸣九选择《萨特研究》作为丛刊的第一辑,相较于创作技艺,他更重视萨特在哲学文化领域的贡献和文学上的思想性。之前的广州发言中对萨特已有专章论述,对其社会思想、文学思想、存在主义哲学和社会活动等方面做了积极的正面评价。在此基础上,柳鸣九对《萨特研究》的栏目和内容做了设计,以萨特文学作品翻译、叙事性作品编译和理论译介作为主体,补充了作家与批评家论萨特、萨特戏剧创作背景以及生平与创作年表等相关资料,并亲自撰写了长篇序言。需要指出的是,《萨特研究》也是由多位优秀法语学者合作完成的一项学术成果,李恒基、罗新璋、谭立德承担了《间隔》《萨特年表》《苍蝇》的翻译,施康强则翻译了两篇重要文论《七十岁自画像》《为什么写作》等,这也体现了柳鸣九先生出色的学术策划和组织能力。
《萨特研究》于1981年10月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用柳鸣九自己的话说,“为萨特办了文化入境的签证”,伴随着当时中国社会的思想解放之风,成为80年代“文化热”中的强劲潮流。今年的傅雷翻译出版奖新闻发布会上,特约终评嘉宾、作家苗炜回忆自己的法国文学阅读时还提到,80年代,柳鸣九先生主编的《萨特研究》是爱好文学的中学生都特别喜欢的书,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当时《萨特研究》的影响力。也正是由于《萨特研究》在文化学术领域的贡献和影响力,2005年萨特百年诞辰之际,国内有媒体在相关文章中,尊称柳鸣九先生为“中国萨特研究第一人”。
“为了一个人文的书架”
余中先的印象里,柳鸣九先生“笔头好、胆子又大,组织能力还很强”,他特别提到,柳鸣九先生在担任法国文学研究会会长的十多年里,为法语文学的翻译和研究做了很多工作。1987年任会长之后,柳鸣九先生先后组织了左拉学术研讨会、巴尔扎克文学创作讨论会、文学中的意识流问题讨论会、文学中的荒诞问题讨论会、存在文学与文学中的“存在”问题讨论会,雨果诞生二百周年纪念大会及雨果文学创作讨论会等问题性、专题性较强的学术活动,并出版一系列相关专题论文集。柳鸣九先生组织能力更主要的体现,还是“他登高一呼,将法语界学者组织起来,主编了好几套书”。余中先回忆,在编选“法国二十世纪文学丛书”时,柳鸣九问余中先想翻译谁,余中先选择了自己当时的研究对象克洛代尔,翻译了这位诗人的剧本《缎子鞋》。之后他翻译的米歇尔·图尼埃的《礼拜五或太平洋上的虚无缥缈境》也收入该套丛书。“柳鸣九先生提携后辈,很温厚,放手让我去做”,“晚年患帕金森症之后,柳鸣九先生还时不时通过年轻的朋友召集聚会。前几年还让我跟他一起做一套绿色丛书,与生态有关的作品,我选了卢梭,他选了都德”。这就是2019年中央编译出版社出版的“小绿书”,包括《磨坊文札》《孤独漫步者的遐想》《园圃之乐》等。

《柳鸣九文集》 柳鸣九 著,海天出版社2015年出版
柳鸣九先生主持编选的文集、书系、丛书等项目近二十种,若分卷罗列,条目可达几百。他曾坦言,自己的编选量大大超过了论著量,“有悖于学林中厚积薄发的理念与标准”。而之所以对编选情有独钟,源于柳鸣九先生“为了一个人文书架”的人生追求和为社会文化积累添砖加瓦的人生理想。他曾在回忆录中表示,自己信仰优秀的文化和有精神价值的书架,痛感当今社会人文精神的滑落、优质文化的贬损,想对文化、对人文精神的积累做一点实实在在的事情。这种追求和理想直至晚年而不衰,更支撑他“担当了辛劳,承受了打击,度过了我个人生活中的沟沟坎坎”。他有两个六层大书柜,每有他撰写、翻译、编选的新书问世,他都习惯将其“入库”,自称这是“陋室”中一道“赏心悦目的风景”,坐在对面的沙发上,面对书柜,如在“家园”和“加油站”,几百本书展示出的过程和成果,也昭示着存在和意义。
在文学史研究和理论文化积累两块“巨石”之外,柳鸣九先生曾将散文随笔写作视为自己推动的第三块巨石。他认为散文就是“自我心智以比较坦直的方式呈现于一定文学形式中,而自我心智者,或为较隽永深刻的自我知性,或为较深在真挚的自我感情”,总之,散文的核心成分是个人心智。柳鸣九先生的散文多涉及亲人、师友——供三兄弟读书远赴异乡打工的父亲,“心底里最爱”的优秀的儿子、两个活泼可爱的孙女,各富人格魅力的马寅初、冯至、李健吾、朱光潜、钱锺书等学者;也有关于研究对象和法国文化的学术随笔——与西蒙娜·德·波伏娃会面的深刻印象,巴黎圣母院访记以及关于罗丹雕塑艺术的哲思等等。在他的随笔中,充满人文视角和人文关怀,以及这种人文情感与人和物相交汇而闪现知性的火花。同样,其散文特别是有关亲友的文字,也勾勒出柳鸣九先生学术之外更加日常、感性的一面。对于没有见过柳鸣九先生的人来说,从对他的学术著作、回忆录和散文随笔的阅读中,会得到更丰富立体的印象。
2018年11月19日,柳鸣九等7位翻译家荣获中国翻译界最高奖——翻译文化终身成就奖。如今,一同获奖的阿拉伯语翻译家仲跻昆、波兰语翻译家易丽君也已经离开了我们。柳鸣九先生曾把从事西学研究和人文传播的思想者、学者视为“普罗米修斯”式的“盗火者”,甚至以“盗火者”为10位外国文学学者的散文文丛命名。他认为自己也是一名“盗火者”,对社会人生的审视和对人文主义的向往,是中国社会现实的火种,愿意为此付出“精神的苦力”。他曾表示,“我很高兴自己的一生是不断劳作的一生”,“我劳故我在”,且这种劳动是具有创造性、独特性和突破性的,为社会文化的积累增添了砖瓦。他的思想和文字极具锋芒,著译等身,但仍以真实、实在的立场直面自身,自称“凡夫俗子”、学林中的“矮个子”,将一生所取得的成就首先归结为自己“蚂蚁式的勤奋”,坦言“勤奋”二字恰巧是对自己治学经历最基本、最具体、最确切的概括与总结,“这个评价也算是坚硬得颠扑不破,谁都认可的,就像算术中的最大公约数”。
参考资料:
《回顾自省录——柳鸣九自述》 柳鸣九 著,河南文艺出版社,2016年
《子在川上》 柳鸣九 著,海天出版社,2012年
《关于〈法国文学史〉的修订》 柳鸣九,《南方文坛》2007年第5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