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小青:我为什么还在写,就是因为没有“完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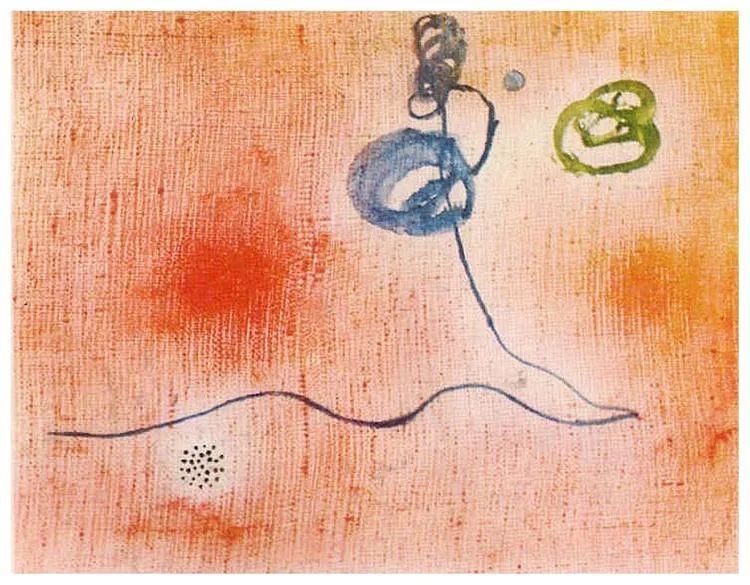
小饭:范老师您好,很高兴您能接受访谈。我受到《巴黎评论作家访谈》的影响,这个访谈会更多关注您的生活细节和文学观念——先从这个问题开始怎么样?您是否能说说第一次和文学产生连接的时刻。或许是在二十岁甚至更小的时候。我猜想这会是一个美好的记忆。
范小青:我和文学产生连接,首先肯定是阅读文学作品。但是我最早的阅读,却不是通过眼睛,而是通过耳朵。小时候在家里,听到母亲和外婆说《红楼梦》,其中最著名的“只有两只石狮子是干净的”,也是在听不懂的时候听到了并且记住了。直到多年后自己读了《红楼梦》,才知道母亲其实不是在说《红楼梦》,而是借着《红楼梦》在说世间的风霜雨雪。然后长大了一些,当了知青下放农村,生产队的知青点有一些比我们年长一点的老三届知青,他们在农村已经待了好些年,那时候他们的念头,就是上调回城,还有就是互相借书看。我比他们小一点,而且不在知青点上,我没有看到他们互相交换着的那些世界名著,但是我偶尔听到他们谈论过。其中让我惊叹和震撼最大的一本书叫《基度山伯爵》,我听了他们断断续续的讲述,简直不敢想象世间还有如此精彩的故事。我激动又兴奋,迫不及待,立刻去贩卖给和我同龄的一个同学(也是知青)听,可惜的是,我在听故事的时候,就没怎么听明白,记得不是很清楚,我的口才又很差,结果只是干巴巴地讲出了几句话,说有一个人,受到陷害,被关进地牢,碰到了一个什么人物,教他怎么复仇——然后呢,然后就讲不出来了。至今我还记得我的那位同学的眼睛朝我巴瞪巴瞪的,不知道我是什么意思,怎么讲了几句就没了呢。其实本来我也就只听了个开头。
现在回想,我在二十岁之前,所有读过的文学作品,加起来肯定不到十本。
接下去的阅读,就是真正的阅读了。进入大学中文系,在大一大二的两年中,我几乎读了图书馆资料室大部分世界文学名著和中国古代文学名著,真正开始进入文学的世界。
所以,和文学产生连接,其实不是一个时刻,也不是一个回忆,而是好多的时候和好多的回忆。很美好。
小饭:在不同的年纪和生活状态下,你会不会调整自己所写的对象——比如,在年轻的时候,会在故事中多写一些爱情。到了中年之后,写更多人心?那么,从现在和未来,您会把自己写作的重心放在何处?
范小青:写作肯定会随着年龄和生活状态的变化而发生变化的,但更多的时候并不是刻意地调整,而是自然而然地转变。就如同我在写作时女性意识不强一样,我在写作时年龄意识也不强,直到今天,我也没有觉得自己是作为一个老年人在写作。
我的写作,基本上是从生活的感受中来,当然年龄肯定是感受生活的重要前提,所以年龄的变化,一定会带来对生活的不同感受;同时,我们的生活更是一直在变化,甚至是巨变,变得更复杂、更模糊,甚至更荒诞。对于一个依赖生活、对生活敏感的作家而言,我一直在有意无意中,调整自己的写作对象。只是这种调整,并不跟自己的身体或精神变化成什么比例,比如说,年纪大了,就多写老年人。或者说,没有黄昏恋,就不写爱情了。我近期的作品,有写老年人的,但是大部分作品,仍然是写的年轻人。
从现在到未来,和从过去到现在一样,我的写作重心,一直在,也一直会在生活给予我的馈赠这里。
小饭:您说到一个作家的女性意识。现在社会面整体女性意识的提升,也在文学的“市场”中得到大量体现——很多女性作家在进行写作活动时会有这样的自觉性。我很想知道在十几二十年前,关于女性写作,那时候是怎样的评论氛围和舆论氛围?
范小青:十几年二十年前的女性写作,也同样是吸引“文学市场”目光的,文坛对女性写作算是比较关注的,经常会有专为女性作家召开的研讨会,或者出版女性作家的丛书(相当多)等等,那时候女性写作好像感觉比现在要更受关注些(就文坛而论),现在更多的似乎是对作家迭代的关注,比如经常看到将作家们归为某某年后,这个现象应该是和整个社会相连、相互影响的。
小饭:作为创作了几十年的“资深作家”,在写作上,您有未完成的感觉吗?比如很多作品“没有写好”,似乎有遗憾。总体创作生涯上,总是还想着往前更进一步……类似这样非常有紧迫感的对自己严格要求的作家,您觉得自己是其中之一吗?
范小青:我肯定就是其中之一,而且应该是属于表现比较“突出”的一位。一直到今天,我仍然觉得白天就是用来工作的,不能享受别的娱乐,我喜欢看电影电视剧,但是白天的时候,哪怕明明写作卡壳了,坐在电脑前煎熬,写出来的字自己看着都难受都厌烦,即便如此,那白天的时间也是不能用来观影观剧的,奇怪吧。
几十年的写作,为什么还在写,就是因为没有“完成”。其实,没有“完成”的,并不一定是指某一些具体的作品,“没有写好”的,也不一定明确说哪一个作品没有写好。虽然不知道是否能够写得“更好些”“更满意些”,但还在继续努力着;也没有很刻意地希望自己越写越好,因为“越写越好”是一个不大可能实现的梦想,或好或差,时好时差,甚至越写越差,这才是常态。还有就是对于“好”的理解和认同,因人而异,那就更不能把希望寄托在一个抽象的“好”字上了,经常我自己觉得这一次写出来的不错,却偏偏无人喝彩,或者,我心情忐忑地拿出一个作品,却有人赞赏。你能怎么办呢?所以说到底,写作就是一个人的精神生活,与外部因素当然有关,比如获奖了,当然写得更来劲,人来疯了。但是外部因素起不了决定作用,起决定作用的肯定是自己内心的声音。
我的紧迫感一直是比较强烈的,自己也觉得奇怪,写了几十年,为啥还这么着急,急着要往哪里去呢。我曾经在近三十年前,就写过一篇随笔《快不过命运之手》,说的就是这种紧迫心态。“我常常觉得头脑里一片空白,只知道自己是要写的,是要不停地拼命地写的,但心里常常很茫然,在人生的路上,在写作的路上,我已经奔跑得很累很累了,但我仍然拼命奔跑,我并不知道前面等待我的是什么。卡夫卡有一次写寓言,大意是这样的,他说有一只老鼠拼命地奔跑,它不知道它要逃避什么,它只是拼命地奔呀,它穿过大街小巷,终于跑进了一条长长的静静的安全的通道,老鼠正想松一口气,它看到了猫站在通道的另一出口,猫说,来吧,我等着你呢。
我不认为自己是一只老鼠,但是我和老鼠至少有一点是相同的,就是我和老鼠,我们都不知道为什么要奔跑,我们也不知道我们的终点是什么。我们的一切,只在于奔跑之中。
在文章最后我还引用了索尔·贝娄的话:“只有当被清楚地看作是在慢慢地走向死亡时,生命才是生命。”
其实到今天我也没能好好理解这句话。二十多年过去了,我好像仍然是当时的那个“我”,一个老同志,仍然被“命运”追得屁滚尿流,想想也可笑。其实也不见得是什么玄而又玄的“命运”,就是一个人的性格而已。
小饭:“我还有最想写的小说没有写出来,可又天长地久地不知道那最要写的一部小说是什么,怎么去写它?”一位作家这样写道。您有这样的困惑吗?
范小青:我肯定还有最想写出来的小说,但不是指某一篇,也不是指某一部,而是一个并不具体的概念,那就是“写”。
“最重要的那部小说”是什么,我并不知道。有一种可能,对于我来说,人生中“最重要”“最好”的小说早已经写出来了,但是我仍然在写作,为什么呢?既然“最重要”或“最好”已经出现,那么接下去的作品,岂不是永远不可能超过那个“最好”了,那么继续写作,是为了写出比那个“最好”差一点、更差一点的作品?
无所谓的。我有一位挚友,曾经对我说,你的写作高峰期早就过了,不写也罢,歇歇吧。我不会听他的。如果有人说我是个天生的写作者(主要指写小说),我会比较开心一点。说得夸张一点,我在平常生活中,不是在写小说,就是在为写小说做准备。
小饭:您确实很专注。那么您在具体写作过程中,写熟悉的事物时会更自在,还是针对熟悉事物的想象,会更兴奋?会不会抗拒和躲避去写自己完全没有尝试(经历)过的相关领域?
范小青:通过熟悉的事物,生发出更多更奇异的想象,最让人兴奋。举个例子,我在长篇小说《灭籍记》中写了一个不存在的人物郑永梅,他只存在于各种证明里,各种写着他名字的纸张,让他成为一个人人相信他存在的人。这是“他”的母亲叶兰乡为了不使自己显得与众不同而被怀疑所凭空捏造出来的一个人。这个母亲,身上有我母亲的一点影子,我母亲因为常年身体不好,无法在职场和社会的风刀霜剑中打拼,她总是缩退,特别敏感、脆弱,甚至有点神经质,我的童年和少年时期,就是在母亲天长日久的担惊受怕的影响中度过的。我长大以后,对于母亲的这种感受,有了比较深的理解和了解。当然,我的母亲再怎么担惊受怕,也不会去捏造出一个孩子。但是在小说里,我可以极致地发挥想象力,所以就有了“郑永梅”这么一个既存在又不存在的人物。这个人物的创造,对于我的写作,是一次新的起航。
对于自己不熟悉的领域,之前和目前,我基本是回避的,这个主要是指写长篇小说时所选择的题材。但日后会怎么样我说不准,似乎在我的内心,有一种蠢蠢欲动的感觉,也许过不了多久,我会去尝试。
如果在写作中涉及自己没有尝试或经历过的领域,那一定会学习、了解,反复核对,反复考量,即便如此,露馅的可能还是会有的。
小饭:您不光在写作中充满热情和专注。我注意到您对社会工作的参与也是非常有效的。一些社会身份是否对您的写作有所帮助?能不能说几件印象深刻的事?
范小青:参与一些工作的体会,有两个简单化:
一是复杂的工作事务简单化。工作中往往会有很多程序,人的精力都消耗在许多无聊的程序中,所以在我能够做决定的时候,我一定会在合理合规合法的前提下,简化程序,直达目的。
二是复杂的人际关系简单化。人际关系是逃不脱的,既是你生存的法则,也隐藏着致命的危险,因为一旦卷入矛盾的旋涡,就是心灵长期纠缠、永不安宁的开始(也有人乐在其中,那就另当别论)。所以在人际关系中,不纠缠,不争高低,不争输赢,放开心胸。
尽量做到两个简单化,不仅是节省时间,更是平和心态、平静心情,写作需要激情,同时需要静心。
有一些社会身份,决定了你要做一些你并不太乐意的事情,比如经常要开会,怕开会的人很多,当然不能一概而论,不是所有的会议都不想参加,只是有一些会议比较冗长沉闷无聊,是会让人郁闷的。但是我开会的时候通常不会觉得沉闷无聊,我会从“会”里边发现写小说的种子。
比如说从前有一种状况,叫作“替会”,后来基本改正了。在“替会”中发生的真实好玩的事情很多;再比如说走错会场、拿错讲稿、会标出差错等。总之,即便是枯燥的会议,只要你用文学的眼光去打量、去探究,也许真能发现文学的萌芽。
我自己就因为参加各种会议,写过一些与“会议”有关的小说。首先在长篇小说中,比如《城市表情》《女同志》这样的作品,肯定会要写到会议,我有开会的“生活积累”。在某些中短篇小说中,我甚至只写开会的故事,比如《国际会议》《我们的会场》《出场》《你的位子在哪里》等等。
我的感觉是,任何的生活和身份,都会是收获。
我始终觉得,写作者需要培养自己对看似平凡普通甚至平庸生活的审美能力以及表现能力。
小饭:很多作家到了四十多岁,或者更后面一些,会有一个明显的创作欲下降或者下滑——而您不是,无论是期刊发表还是出版,包括获得文学奖项,都保持着相当高的数量和水平。您是如何保持这样的创作主动性的?这方面有没有关于生活方式包括精神生活方式的独家秘诀?
范小青:没有独家秘诀,只有努力工作。生活方式是简单的,精神生活方式也是普通的。我的体会是,所谓的写作激情,正是在写作中不断保持的。当然,在漫长的写作时光中,肯定会有低潮和高潮的不同时段,甚至有短暂地躺平,但是躺平以后会更加心神不宁,还是赶紧坐起来继续写吧,哈哈。
所以一直写到今天,我仍然有写不完的欲望,手里的一个作品尚未完成,心里已经想着下一个,再下一个。真是吃在碗里,望在锅里,贪念万重山,而且还这山望着那山高,那就永远也爬不完了。
小饭:在写作过程中愿意和亲朋或伴侣聊所写的内容吗?是否期待朋友们根据你所说的内容给出自己的意见?问个可爱的问题:是否听到朋友们肯定和赞许的意见会更高兴?如果有一些批评意见就会心里不舒服(但还是会加以反思?)
范小青:写作过程中基本不和任何人聊写的作品,这好像是好多作家的习惯,当然一定都是传统意义上的作家。我记得我从前还有个可笑的习惯,在作品完成之前,是不能让人看的,即便家人走过身边,瞄一眼也不行,要用手挡起来,哈哈。也不知道这是一种什么样的奇怪心态,值得分析的。
其实我知道,这是很愚蠢的习惯,在其他创作门类比如影视剧本舞台剧本的创作中,大多是集体的智慧,集体的智慧肯定比一个人的想法要更智慧——至少你可以获得更多的判断机会和选择机会。只是几十年养成的习惯,自己的毛病,很难改变。
听到对我的作品的肯定和赞许,一定是高兴的,也可能表面还要假装谦虚,心中一定是得意扬扬,这是常态。听到批评意见,肯定是不太爽、尬笑。但是我一定会从中反省反思。不是我心胸开阔,是因为我喜欢我的工作,想把它做好,做得更好。至于能不能做得更好,那是另一个话题,前面我们好像已经聊过几句。我从来不认为只要努力,就能做得更好,但是我仍然在努力。
小饭:我听很多作家朋友说起您,说您为人温和……是一直如此吗?在世俗世界中的温和带给您精神世界和创作领域里最大的收益是什么?
范小青:温和不是因为我有格局有胸怀什么的,是因为胆小,因为畏惧。一个人对别人的态度和行为,必定是要反弹到自己身上的。我如果对别人凶,别人也会对我凶,我不希望别人对我凶,我希望大家都能和睦相处并各自努力,那么我先要对别人温和一点,就是这么简单。
有人会说,有些恶是没有任何理由的,那还温和得起来吗?
在过去的某些采访中,我有时候会说到小时候在似懂非懂的状态下听母亲所说的寒山寺的两个和尚寒山和拾得的对话,寒山问拾得 :“世间谤我、欺我、辱我、笑我、轻我、贱我、恶我、骗我,如何处置乎?”拾得答:“只是忍他、让他、由他、避他、耐他、敬他,不要理他。”一般我都是说到这儿为止了,但是采访者通常会给补齐了,加上最后一句:“再待几年你且看他。”其实这一补,不仅是多余的,它就不是我的想法,因为我完全不要“再待几年且看他”。我不想看别人怎么样怎么样,我忙不过来,因为我写作、写小说还来不及呢。这是其一;其二,虽然我引用寒山的世间什么什么“我”,但那并不是我的感受,我很希望也很努力地做一个武侠小说中经常会提及的“记吃不吃打”的人物,因为老是记着别人打你,那种痛感就跟随你一辈子,你一直就生活在“痛”中了——强调一下,我指的是人际关系中个人的小“痛”,而不是更广泛的“痛”。
无论在工作中,在人际关系中,在家庭里,我都较少发脾气,难道我就这么没有血性没有脾气吗?有的呀,它体现在我的写作中,我执拗、顽固,写了一篇又一篇,写不动也要写,写不出也要写,这不都是一个人的倔脾气吗?自己和自己过不去,我对自己好像不太温和。
当然也可以从另一个角度看,是我对自己太温和了,因为这个“自己”,成天想着的都是要写小说,所以我很宠这个“自己”,这个“自己”就很任性。
在世俗领域中的温和,让我的精神和心灵自由、开阔、平和、宁静,作为一个普通人,内心必然会有复杂多虑、坏心思、歪主意、“私字一闪念”等等,都用来和自己的小说去纠缠,纠缠得越厉害就越赞、越舒畅,因为我在现实生活中的纠缠,统统到写作中去找出口,倾泻掉。
小饭:那么在世俗领域中、在人群中,你会优先关注到哪一类人?并和他们成为朋友?
范小青:感受到同频共振的人,很难说出具体的标准,正派的人、善良的人、智慧的人、有趣的人等等,我都喜欢,但是这些词汇都比较空洞,它们既是标准又不是标准。
所以我想,人和人交往相处,首先是直觉,然后是感觉,然后是天长地久。
小饭:在你的作品中,会不会有意识去写自己更好奇的人生风景(比如人心的幽暗曲径隐秘之处)?
范小青:当然会。一定会。
写作是一件有趣的事情,如果没有好奇之心,就无法发现新鲜奇异的一切,写作可能会变成日复一日的机械操作,雷同重复,那是多么无趣。之所以写了几十年还能保持写作兴趣,正是因为人生的风景中不断地有好奇之事之人出现,让你惊讶,让你欣喜,甚至让你怀疑人生。我们常看到一些作品,也在讲故事,也在写思想,写得也挺圆熟,没有纰漏,但就是不好看,无趣的沉闷的陈旧的文字和表达,让人失去阅读的兴趣,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缺乏好奇、写作路径依赖。
平凡的生活表面,没有更多的好奇让你去惊喜,但是如果能够敏感到触摸到平凡生活之内、之下的水底波澜,你就能发现,无论生活多么平淡甚至平庸,也同样有很多奇葩在那里等着你。
我近些年的写作,主要是从平凡的人生、平常的日子里,发现奇异的内涵,努力写出人物的奇异性。比如在长篇小说《赤脚医生万泉和》《香火》中,就有好些人物是奇异的。万泉和就是其中的一个代表。
这些人物,既是艺术创造,又有生活的根基,我在农村时见过他们,和他们相处接触过,他们不是天生存在于我的脑海中,更不是从天上掉下来,掉进我的小说里的。
我在长篇小说《战争合唱团》的创作谈中,有这样几句话:“有的地方,它完全是天马行空,恣意妄为;有的地方,却又如同泥巴一样笨重而邋遢,它可能就是植根于现实土壤中长出来的一个奇葩,这是一个杂交的文体文本,是由写作者的任性和混乱的现实杂交而成。写作者的任性,是因为写作异象时的诱惑、冲动和自我挑战——无论这种任性,最后走向成功还是走向失败,至少,尝试过了。”
小饭:这个问题比较“坏”——有没有那么一刻,范老师觉得错误地选择了文学,选择了写作——起因是,因为文学创作而给生活带来了非常糟糕的经历或人际上的麻烦。
范小青:从事任何职业,都可能给生活带来非常糟糕的经历或人际上的麻烦,文学并不见得就特别强烈。但是因为写作者多半心思复杂缜密,又爱钻牛角尖,想得太多,想象力(甚至是幻想)太强大,所以在文学的人际关系中,确实经常会遇到一些难题。我的化解方式就是简单化。我的为人处世之道就是棉中藏棉。如果用负负得正的说法来诠释,那么棉棉可能也是另一种形式的锋芒呢。
有人说我温和,温和的人似乎给人的印象都是慢性子,其实我恰好相反,我是一个急性子,所以我不耐烦走复杂的程序,无论工作也好、生活日常也好、与人相处也好,有时候就会简单到很粗疏,得罪人而不自知。这是一面。另一面,若真的被人得罪了,可以不在乎,无所谓。
记得在二十年前的一次会议上,那是大家对我作品的研讨,陆文夫老师开头讲话,鼓励我一番,最后说,小青是一个最怕得罪人的人。然后就是会议开始,主持会议的黄毓璜老师说,小青虽然是一个最怕得罪人的人,但同时她也是一个最不怕被人得罪的人,所以你们畅所欲言,有什么说什么,她不会生气的。
陆文夫老师和黄毓璜老师已先后离开我们。离去的师友,他们一直都在我心里。
我没有觉得自己错选了文学创作这条路,不是因为我觉得自己在这条路上多有成就、多么了不起,而是因为,一,我没有尝试过走其他的路,也许别的路上风景更好,可惜我没有遇到也就无从比较,无法得知。二,我在写作的人生中,有困惑有苦恼,但也始终是有乐趣的、很开心的。
小饭你的问题大大地勾起我说话的欲望,我再废话几句,说到人生的道路,我在当知青的时候,积极参加劳动,要求进步,大约在1976年的春天,县委要选拔年轻干部,我也在名单中,恰好那一天来考察时,作为大队团支书的我,被大队派了一个活:名义上是带领团员青年平整土地,实际上首当其冲的是平整人家的坟地。真的不作兴,罪过罪过。
这边在大队部,对我的考察并不顺利,大队书记不赞成,这事情很轻易地就黄了。大队副书记是支持我的,所以他特意站在我们回来的路口等我,但他也是有原则有组织纪律的,不便多说,就只对我说了一句:再锻炼锻炼。
后来过了一阵,麻木不仁的我忽然想了一下,这大概是扒人家坟头的报应吧。
现在回想,如果当时的考察通过了,我会走上一条什么样的路,我最后会是什么样子,我完全无法预测。
再回来说到你的问题,有没有哪怕一瞬间觉得错选了职业,好像没有。也许有过,但是“忘记”了。有的时候,在写作最困难的时候,通常是在长篇的写作过程中,碰到瓶颈,而且长时间卡在瓶颈中,很焦虑、很郁闷,走投无路的感觉,即便那样,也没有责怪自己选错了行,只是怀疑自己的能力、精力、体力等。
小饭:您曾说您最大的特点就是“忘记”,这是一门技术活儿——我很想知道,这是你一种学习和处世的自我选择之后的应变机制吗?觉得大部分事物其实对自己的精神生活并不重要。
范小青:我的“忘记”,原因之一,我本身就是个忘性较大的人,而且脸盲。如果一个人的长相没有什么特征,我可能见过三次都记不住。真的很不礼貌。原因之二,是一种自觉或不自觉的心理暗示。
大部分事物甚至说得绝对一点,任何事物,对精神生活都有作用。但是人不能吃得太饱,那样会胀肚子,不消化,如果不加选择,吃得不净不洁,还会生病,再如果胡乱瞎吃,可能会食物中毒。我们经历的所有事物之于我们的精神生活,如同食物之于我们的肠胃。
重要的东西,恐怕想要忘记也忘记不了。不重要的就不重要,忘记也罢。
“忘记”也不是绝对的,有时候,你觉得什么事情你是早已经忘记了,可它却突如其来地闪现出来。闪现就闪现,如果是让你高兴的事情,就追忆一下,享受一番,如果是让你不高兴的事情,就立马划走它,再一次地选择“忘记”。
小饭:您在生活中,有文学之外的爱好吗?我是想问,比如说,有没有打麻将之类的“粗俗”爱好?对中老年人沉迷在与朋友的棋牌生活,怎么看?
范小青:文学之外的爱好是读书、追剧观影。我特别喜欢看电视剧,从美剧追到英剧、追到韩剧,近些时,我只看国剧了,我觉得国剧进步了,可以看一看,很开心,
我会记下一些观剧观影的心得,没有什么用,就是因为看了有想法,却无人可聊,郁闷,就记下来自己看看了。我曾经想在哪里开一个类似影视评论的栏目,名称都想好了:剧说影享。这个是做做梦而已。
说到其他娱乐,我会打麻将,也会打牌,水平较差,但打的时候很用心、很努力。经常有朋友会学我打牌时的模样:皱着眉头,歪着脑袋,十分投入。这样一个形象就是我,我有时候觉得比写小说还认真。因为我不精于计算,也记不住牌。记不住的原因,一是记性不好,二是懒,不想记牌,目光短浅,只看着自己手里的牌,不照顾对家,不会配合,也不看大局。打麻将的时候,更是显得小家子气,所谓的苍蝇蚊子都是肉,是常常挂在嘴上自我解嘲的,想打大牌的麻友会被我的“垃圾胡”反复地破坏情绪,真是对不起。好在现在不怎么打了,不是不想打,是因为腰椎和颈椎轮番来报复我,因为前面的几十年,我超量地使用它们、奴役它们,它们很生气。更何况,我还要留点力气写作呢。
老年人的棋牌生活,只要有节制(不沉迷),不违法,没有什么不好。也不能说学画画,或者跳广场舞,就一定比打麻将打牌更高级更健康更道德,都是精神生活,各取所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