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访作家常芳:长篇小说《河图》描摹辛亥革命时期人间万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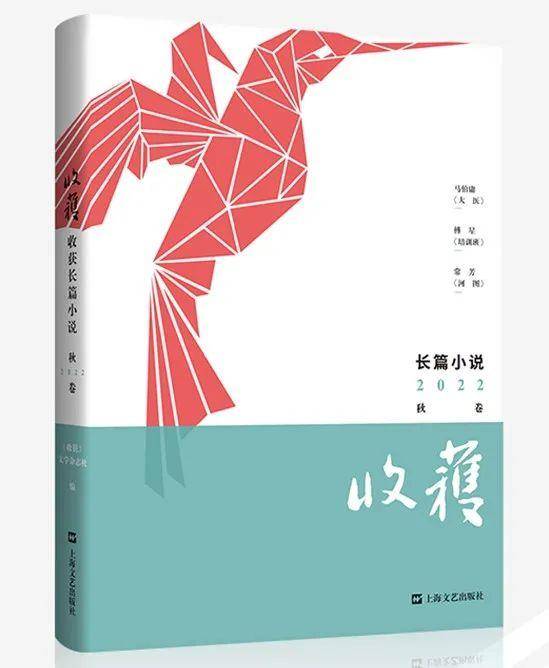
近日,《收获》长篇小说2022秋卷刊发山东作家常芳新长篇力作《河图》,“70后”山东作家的文学创作新突破、新成就引发关注。《河图》单行本将在11月底出版,而在《河图》单行本出版前,这部小说已获得凤凰文学奖,被评价为“近几年来一部最接近名著的小说”。
作为一部气势恢宏、波澜壮阔的小说,40多万字的《河图》从采风、创作、修改到发表,历时七年。小说以辛亥革命期间山东“独立”十二天为历史背景,以黄河岸边的泺口镇为地理坐标,呈现了当时社会的纷繁复杂,呈现史诗品格,填补了辛亥革命山东文学叙述的空白。
著名文学评论家王春林认为“《河图》是一部旨在对转型期中国社会各种现象进行素描式艺术表现的长篇小说。作家意欲全方位、立体化地对辛亥革命前后那一特定历史时段的社会生活做一种全景式艺术呈示的高远志向,在文本中也有着丰富的体现。常芳的深层意图或许是借助于自己笔下的历史故事以探究挖掘中华民族内蕴的某种精神密码也未可知”。
常芳认为,无论是从济南眺望世界,还是从世界的高度俯瞰济南,她的新长篇《河图》所记录的一百年前的济南故事,一个黄河渡口小镇的风云变幻,同样也可以是关于欧洲、关于美洲、关于亚洲的一种集体记忆。
常芳已出版长篇小说《爱情史》《桃花流水》《第五战区》、小说集《一日三餐》《冬天我们去南方》《蝴蝶飞舞》等,是文坛比较少见的擅长宏大题材创作的女性作家。近日,常芳接受齐鲁晚报记者采访,畅谈《河图》“这一大工程”创作的来龙去脉。一起走进常芳的文学世界,去聆听她讲述一部荡气回肠、回溯历史的大部头作品如何炼成。

常芳,本名王常芳,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国人民大学文学硕士,济南市作家协会副主席。已出版长篇小说《爱情史》《桃花流水》《第五战区》,小说集《一日三餐》《冬天我们去南方》《蝴蝶飞舞》等。长篇小说《河图》入选山东省委宣传部“齐鲁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创新工程”重点项目。
填补辛亥革命山东文学叙事的空白
齐鲁晚报:《河图》恢宏大气、丰富扎实。是什么引发你强烈的创作冲动,要七年磨一剑,以1911年山东辛亥革命期间“独立”十二天这个历史事件为背景去写一部长篇小说?写作过程中有怎样的创作规划思考?
常芳:1911年10月,辛亥革命的枪声首先在湖北打响。武昌宣布彻底脱离清政府,成立中华民国湖北军政府后,独立的风潮一夜间在全国各地风起云涌,各省积极响应武昌,很多省份也纷纷宣布独立。在这场“独立”革命中,最终取得了十二天独立成果的山东,无疑是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尤其是它宣布独立后,仅仅十二天的时间,又旋即取消独立这个反复过程,在整个辛亥革命中,应该是绝无仅有的一例。但是关于辛亥革命的这段历史一直没有见诸文学领域,可以说是文学叙述的一个空白。
关注到这一独立的个案后,我一直在琢磨,当时极力推动山东独立的人们,在取得独立的过程里都发生了什么;革命者在品尝到革命成功的甜蜜果实时,他们的心灵和精神世界经历了什么惊涛骇浪般的喜悦;十二天后旋即消逝的独立,又让这些沉浸于胜利中的革命者们,从精神到肉体经历了怎样的腥风血雨。在独立被取消的那个黑暗无边的长夜里,被突然“陷进”黄河淤泥漩涡中的他们,又是如何泅渡这条暗流汹涌的命运和时代之河。革命者们推动“山东独立”的前后,生活其间的普通百姓,他们的生活和精神又是一种什么状态。
一百年前,随着八国联军开进北京,德国在山东抢占胶州湾,济南“自主开埠”,代表现代文明的火车开到黄河岸边,西方现代化的不断渗透,山东和整个飘摇欲坠的清政府一样,实际上都处在了一种生死两难的境地。
而真正引发我创作热情的,是在报纸上看到的与辛亥革命有关的两则旧闻。两个故事都和独立有关。一则是一位支持独立的进步女性,因恨其丈夫不参与革命,不参与独立,她怒其不争,遂登报与丈夫离婚。另一个故事则是一位年老的父亲,因其儿子参与革命,参与独立,害怕家人受到牵连,从而登报与儿子断绝父子关系。这样两个处于极端的家庭故事,让我们从革命和独立的缝隙间,窥见一百年前,那场千年未有之大变局,带给整个社会的种种巨大撞击。
至于创作这部作品花费了七年时间,一是和我的写作状态有关,二是辛亥革命虽然仅仅过去了一百多年,但对于个人创作经验而言,它距离今天的我们的确不是一段太近的距离。这里的时间距离,不仅包括时间本身的距离,还有辛亥革命在某种意义上,真正给了时间“独立坐标”形而上的距离。所以,我要逆流而上,找到一百年前“存在”的那个济南和泺口,找到那些在这场“存在”中生活的人们,花费的工夫就长了一些。
齐鲁晚报:是否想到这部小说要写七年?做了哪些准备?现在关于1911年山东辛亥革命期间“独立”12天历史事件、1911年泺口镇现状、造醋业、传教士和洋人在济南、泺口黄河铁路大桥等历史资料记载多不多?资料又是如何帮助你创作构思这部小说的?
常芳:创作之初,没有想到写这么久。当时的预期是写三年。《河图》的准备工作,实际上在2012年开始创作《第五战区》之前,就一直在做,主要是在酝酿,收集的资料非常有限。比如山东独立十二天这个历史事件本身、泺口黄河铁路大桥的修建情况等,找到的资料都非常少。百年前的泺口镇,以造醋业为代表的工商业,随着时代的发展,都已经面目模糊。
因为我的家就在泺口南边,距离泺口和黄河都非常近,近十年来,我经常做的一件事情就是去转泺口的老街道,寻访山东机器局旧址,寻访城隍庙,置身其中,寻找关于泺口镇百年前的点滴印迹;到黄河边眺望暗流涌动的河水,到鹊山上去看那座德国人修建的黄河铁路大桥,反复酝酿,一步步还原历史中的某些存在。我四处搜集资料,然后像一块酝酿雨水的云朵那样,在心里反复积蓄。
有一点可以肯定,如同人不可能有两个心脏,世界上不可能有两种价值标准,无论时间怎么流失,世界怎么千变万化,这两种恒定的东西不会有太大改变。在资料的运用上,我觉得应该是一种蜜蜂酿蜜的过程吧,它们采来花粉,但吐出来的不能仍然是花粉本身。
齐鲁晚报:小说以1911年的复杂社会为背景,写的是大事件旋涡中南氏家族和形形色色社会人的故事,大时代的家族命运、个人沉浮,如何写出新视角和新意,这是构思创作的一个大的难点吗?
常芳:相信每个优秀作家在进行一部作品创作之初,尤其是长篇小说,可能都会野心勃勃,想寻找到一种全新的突破,或者一个崭新的视角,或者某种形式上的创新,来完成那部想象中的作品,以期在文学的星空中,用自己的那部作品去命名一个星座。但现在的问题是,在人类浩如烟海的文学世界里,这几乎是一件艰难到和人类想登上火星一样困难的事情,“因为天下并无新事”。但是,就像人类明明知道,无论我们建造的那座塔有多么高,也不可能到达上帝生活的天堂一样,我们仍然在选择奋不顾身。
在创作过程中,我把只属于中国的神话传说、偏方、幻术、民间巫术等,融入到了文本之中,就是想以此来完成形式上的某种创新。内容里,为了文本的新鲜,我一边用中国的神话故事来映照现实,一边将美国工程师戴维先生的日记,全部使用西班牙语来完成。这样做的目的,都是为了让读者多拥有一条阅读缝隙。
纳博科夫说“一旦巫师消失了,只剩下讲故事的人和说教者,他们就不会配合好”。我在作品中多次使用中国神话中的传说、幻术、偏方,就是希望能有“巫师”的存在,可以给这部小说留下更多条通道,更多的气孔,让它通向更多的可能和可能的意外之旅,也就是发现更多无法预料到的新天地。
五百年来谁著史。《河图》的另外一个特点,一是它只用摄像机的镜头,录下了独属于济南和泺口的那些“存在”;二是录制下来的画面里,没有谁是那场“存在”里最主要的那个人物。如果说这部小说是长镜头录下的一棵大树,在一百年前“山东独立”这棵摇晃不定的树干之上,无论是南家花园里的革命者与反对革命的保守派,袖手旁观的西方人,还是形形色色的市井百姓,生活在其间的人物,无论他们对革命抱有什么样的态度,无不是这棵大树各个枝桠上的一片片叶子。在十二天的独立被取消,狂风席卷大地,大树被连根拔起之时,没有哪一片叶子能够独善其身。
为凡俗的长夜与信仰的坚韧作证
齐鲁晚报:小说中刻画了南海珠、南怀珠、南明珠三兄妹,谷友之、周约瑟以及玛丽亚、戴维等洋人,这些人物在您的构思中是怎么出现的?小说中来济的洋人是主要人物,而且南明珠、周约瑟、谷友之等人都与洋人有直接的社会或亲密关系,比如英语老师与学生、传教士与信徒、养父母与养子等关系,小说为什么用大量笔墨塑造来济的洋人这一独特的人物群像?
常芳:小说中每个人物的构思,应该说都是比较花费心思的。我个人一直觉得,写小说一定是人物在先。如果你听到了一个非常好听的故事,那也一定是故事里的人物带出了那个好故事。比如我们读《一千零一夜》,那么最先吸引我们的,肯定是那个讲故事的人,因为他的命运是和他讲述的故事紧紧连在一起的。这样,在小说创作之初,一定是先构思出来人物,才会勾画出他们身后的故事。
人类文明不断进步的一个重要的前提,就是对历史的不断回顾、检讨与审视。《河图》中之所以用大量笔墨来塑造洋人,以及他们与南家兄妹等人的关系,是因为在上个世纪之初,济南在与西方现代化迎面相撞的时候,从来没有离开西方人在各个方面的“介入与推进”。上个世纪初的济南,无论是自开商埠,还是火车站的修建,以及泺口黄河铁路大桥的建设,无不和洋人有关。包括在辛亥革命中,撬动山东宣布独立的最后那根杠杆——新军,他们所有的装备和操练,也无一不是在效仿西方的军队。因此,他们同样是历史的一个真实存在,是王朝往复的帝王中国走向现代民主中国的过程里,不可或缺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
齐鲁晚报:1911年,火车还是庞然大物,整个社会异常复杂,一会儿帝制,瞬间又共和;一会儿谘议局,转眼又是联合会;如你所说“世界在无边长夜里左冲右突”。作为当代的作家,再回望那时候的社会,书写那时候的历史,想要写出一种怎样的人的精神世界?
常芳:今天回望那个年代,看见的是“世界在无边长夜里左冲右突”。当代作家怎么去呈现那个时候人的“存在”,以及他们的精神世界,确实是一件非常考验人的事情。“人不可能有两个心脏,世界不可能有两种价值标准”,这是人类亘古和永久相通的地方。中国人和西方人有着信仰上的不同,当代人和生活在一百多年前的人们,在生活细节上,也会有某种追求上的不同。在创作《河图》的时候,我更多感受到的是里面人物的精神世界,会比现在的我们更纯粹一些。
博尔赫斯在《神的文字》里写过一句话:“旅行者在望见海洋之前就已感到自己血液里的激动”。在写这部小说时,当我停留下来,默默地观察里面那些人物,我发现,实际上他们每个人都是这样,“在望见海洋之前”就已感到了自己血液里的激动。革命者、反对派、中间派、和平派、共和派、立宪派、红派、绿派、贩夫走卒、神婆子,每一个小人物,都在艰难且认真地前行着,即便是左冲右突,也是一心一意;单一执著,且表里如一。我想那是一个时代留在他们身上的印迹。犹如今天,我们常常拥有的焦虑,以及常常感到缺乏的安全感。
《河图》是为所有那些凡俗的长夜与信仰的坚韧作证。在取得“山东独立”的第一天,小说中的主人公之一、参与独立的革命者南怀珠,胸前的口袋里插着一枝“玫瑰”,从城里赶回泺口家中庆祝“独立”的成功。这个属于“独立”和胜利者的夜晚,使这个革命成功后的革命者欣喜若狂,他把成功的“独立”比喻成“玫瑰”,反复用英语、德语、西班牙语甚至拉丁语,来回念叨着玫瑰的名字,解释着它。在那样一个淤泥旋涡、那样一个巨大的时代变局、那样一个不能入眠的长夜之中,玫瑰是抗争后的胜利,是黑夜里的曙光,是苦难结出的最美果实,是爱情,是阳光,是空气,是水,更是真正属于一个崭新时代的独立与自由。所以,在那个夜晚,那个革命者和他手里、口中不被人理解的那枝玫瑰,就是我想表达的人的精神世界。
黄河与济南这座城市同气相连
齐鲁晚报:《河图》所记录的是一百年前的济南故事,一个黄河渡口小镇的风云变幻,“河”肯定是黄河。你说“逐水而居的人类,其命运与河流的关系,更是早就‘注定’了的”。黄河与济南这座城,是一种什么样的“注定”了的关系?小说有很多关于黄河意象的描写,在1911年的背景下,黄河给泺口镇的人,带来怎样的冲刷与洗涤?
常芳:今年诺贝尔物理学奖的颁布,再次将量子力学推到了世界面前:在量子纠缠的状态下,纠缠中的一个粒子的状态会决定另一个粒子的状态,即使它们相距非常遥远。假如从这个理论出发,用结果去倒推原因,黄河1855年在铜瓦厢改道,流经泺口,侵占大清河入海时,已注定了流经泺口的黄河和济南城的关系。除了水运码头,泺口黄河铁路大桥的修建通车,更是以西方现代化所特有的速度,消除了泺口到济南短短的路程,使两地完全融为了一体。
正是“火车”进入中国这个现代化的代名词,在《河图》里,在辛亥革命的巨大洪流面前,将发起山东独立的济南和泺口黄河紧紧地捆绑在了一起。小说里的主人公之一,南家花园的主人南海珠在得知弟弟南怀珠一直在城里参与“山东独立”的事情后,他首先想到的就是,一旦山东宣布独立,从北京、天津下来的清兵,就将会乘坐着火车,飞速赶到济南,剿灭那些参与独立的革命党人。当独立取消,失败后的革命党人南怀珠潜回泺口,他期盼的支持泺口独立的德国舰船,也是直接从东海沿黄河开进泺口,尽管他没有去细想,那些舰船到底能不能驶进泥沙俱下的黄河。
如何正确看待对历史的批评与质疑?《河图》里,居住在泺口镇上的人,在城里的革命党人争取独立之初,家家户户的菜刀,就被巡警局长谷友之用铁链子拴在了每家每户的房梁上。所以,整个镇上的人,无论他们关心不关心独立,是否支持独立,对独立的真正含义是不是理解,是不是想去理解,他们都不能有任何个体的选择,都只能任凭巡警局长带人将他们家中的菜刀拴住。所以,无论是黄河本身的决堤还是大革命时从城里涌起的独立浪潮,它们对泺口的冲刷,都像那位戴维先生在日记里写的,“水头卷进哪户人家的卧房和猪圈,都会把它们里里外外冲刷个干净”。因此,我们会在小说中看到,当城里取消独立的血腥气息,以及泺口将要独立的消息一起传遍泺口时,先是泺口的所有店铺都遭到了巡防营士兵的抢掠和焚烧,两名剃头匠子被巡警打死,然后是杂货铺子掌柜因店铺被烧,聚众到巡警局里闹事,亲手杀死了自己的侄子。同样,真正追求独立的革命者南怀珠和从美国回来的投机分子冯一德,则一起死在了巡警局长谷友之的枪口下。
所有这些,都在某种意义上注定了黄河与济南这座城市同气相连,同呼吸共命运的关系。所以,在1911年,独立革命的浪潮席卷济南后,泺口同样注定了要和济南一起,来完成这样一道考题。
齐鲁晚报:小说《河图》描绘了革命背景下魔幻的泺口镇,有大量的关于当时社会“怪力乱神”的生动描写与呈现,偏方、幻术、神话传说等构建起一个复杂交织的民间社会万象。小说中人们对各类偏方的求索、妖魔火车的传说、现实与神话的交织等写得很精彩吸引人。这一部分的创作灵感来自哪里?
常芳:小说中无论偏方还是幻术,当然都是虚构。但是偏方里的虚构,又有来自民间的一些验方。比如周约瑟儿时用蜘蛛置于鸡蛋内治疗咳嗽的偏方,是我老家沂蒙山区一个治疗小儿咳疾的验方,在我小的时候,很多人家还在用。
而像《鹅笼书生》与那些“怪力乱神”的大量使用,则像我前面说的,既为达到一种文本的创新和内容的丰富与多样性,也为了让故事拥有更多的内涵与外延。黄河流到济南,我们站立在河边,眼睛可能只看到流动的河水,但它的每一寸前行,都携带了两岸无数的故事和人间风情,那些都是掩藏在河水后面的宝藏。
从某种意义上说,“怪力乱神”在教我们重新认识周围的世界。小说里的南家拥有泺口最大的醋园,用粮食和各种花果酿造出各种美醋。我把这些中国神话故事和那些“怪力乱神”移植到文本里,也和他们酿醋一样,是为了让黄河流淌中带来的那些无法肉眼可见的宝藏,与文本所讲述的济南故事相互辉映。这些古代中国的神话传说与现实交织在一起,既彰显了我们所处的这个人世间的无限深度与无限广阔,又如同镜面一般,会让我们去反观现实,我觉得这也是讲好中国故事的一个方面。
齐鲁晚报:有的读者可能会期待《河图》着墨于济南风土人情、鲜活生活的一些描写,但不知道是不是简版原因,清末民初济南民间生活风貌、衣食住行文化的抒写并不多。
常芳:这可能是和简版有关系。因为你看的《收获》版,在发表的时候受篇幅所限,剪去了二十多万字。删减后,作品里很多波澜壮阔的东西和细节中那些氤氲其间的“水汽”,都相应减弱了。
不管在任何一个时代,民间文化,生活风貌和衣食住行,都是其社会构成的底色。《河图》中大部分所构写的,也正是构成社会底色的那一部分。在大革命到来的狂风暴雨里,恰似小说中那对洋人夫妻马利亚和戴维说的,“当大地跟陶轮那样翻转起来时,没有任何个人能够阻挡”。当然,也没有任何个人可以幸免。在小说中,无论是南家大小姐南明珠的衣食住行,南家醋园里伙计们的生活,还是车夫周约瑟的眼睛在城里和泺口间所见,包括杂货铺子掌柜来家祥,城里《女子周报》的主笔咸金枝,南家最小的仆人热乎,两个年轻的巡警来福和伍金禄,被伍金禄打死的两个剃头匠子,打鱼的水鬼和神婆子有莲花,他们每个人的生存状态,都是济南民间文化和生活风貌的一种体现。也正是这样一个一个小人物,在独立革命的翻天覆地中,在济南和泺口这片翻转的土地上的生活,构成了这部小说的底色。
想写出一个站在舞台中央的济南
齐鲁晚报:你的《桃花流水》《一日三餐》《拐个弯就到》《河图》等作品,写尽了泉城济南百年人文历史景观,从百花洲写到泺口,逐步塑造出你文学世界里的济南品格。你怎么看济南这座城市,还会在新作品中继续写济南吗?
常芳:我在很多文章中阐述过一个观点,就是讲好中国故事、重新“发现”济南。为什么用“发现”这个词?济南这座城市几乎是我所有小说的写作对象。济南是一座低调的城市,也是一座被低估了的城市。山水人文不用说了,单纯从小说故事来说,历史上的济南发生的无数“惊心动魄”的故事,需要更多的文学作品去呈现。
我在创作《河图》时,因为要写到位于泺口赵家庄的晚清三大兵工厂之一的山东机器局,查阅了很多关于当时山东巡抚丁宝桢的资料。丁宝桢作为地方大员,敢于与慈禧太后“为敌”,斗智斗勇斩杀太监安德海的故事广为流传。1869年,慈禧太后派太监安德海南下采办龙衣,安德海狐假虎威一路搞得地方鸡犬不宁。丁宝桢以清廷祖训“太监不得私自离京”为由,在泰安将其抓获并关押在济南关帝庙。慈禧太后下密旨释放安德海,丁宝桢决定先将安德海从关帝庙后门拖出斩首,然后从关帝庙前门出去接旨。这座见证历史风云的关帝庙,就在现在的共青团路北、五龙潭南侧,无声无息涌流的蜜脂泉,成为今天游客们争相打卡的地方。
济南是我至今为止,生活时间最长的一座城市。用一句话来概括的话,可以说这是一座非常中庸的城市。它的性格和一年四季都那么分明。热情,但绝不会死缠烂打。脉脉含情,踏踏实实,低头做该做的事,不善张扬,更不会飞扬跋扈。阳光般纯真,泉水般清澈。
到目前,我创作了五部长篇小说,两部以南沂蒙县为背景,写我的家乡沂蒙山区;其余三部,都是以济南为坐标,献给了济南。中短篇小说更是如此,差不多有三分之二的篇幅,是写给济南的。以后的写作,我想大致也会是这样,大部分作品仍然会继续书写济南。想写出怎样的济南呢,肯定是想写出一个站在世界舞台中央的济南。
切口都是小人物在大环境下的日常生活
齐鲁晚报:从写乡村社会城镇化的《爱情史》,到描写二十世纪中国社会变迁的《桃花流水》,再到抒写抗战年代普通人生活图景的《第五战区》,《河图》又跨越到1911年,描写辛亥革命时期复杂的家族命运和时代变迁,你的作品总能开拓广度和深度。这种写作有一种跨越一般女性写作的宏大和宽广。你这种追求挑战性的写作的动力来自哪里?面对这些宏大题材的作品,女性作家有何视角的独特之处?
常芳:宏大叙事不是空中楼阁,宏大需要细节来呈现。在时代的旋涡中,每一个弱小的个人仍然拥有自己完整的世界,这个世界需要文学来一一呈现,这就是文学的魅力。关于战争,关于灾难,永远都有书写不完的故事。1936年,美国女作家玛格丽特·米切尔出版的长篇小说《飘》,以美国南北战争为背景,描绘了内战前后美国南方的生活,围绕黑奴制度废除产生的动荡与救赎,每一个人的命运都被时代洪流裹挟,一泻千里无法自拔。小说主人公斯嘉丽却在这股洪流中勇敢地面对自己,面对新旧时代的更迭,突破传统,寻求自我价值的实现,成为代表美国精神的一个永恒的文学形象。
在我的潜意识里,可能没有女性写作这个概念。如果有,就是对世界的感悟、对人生的感受更细腻,对温暖与悲凉的人生际遇更能够感同身受。在写作的过程里,也从没有想到过性别的差别。当然,这并不代表着没有性别的差异。这种天生的差异本身,是不会改变的。不过,回头看看,这些长篇的写作,对我来说似乎也是自然而然的一个过程,并没有觉得是一份挑战。这也许是和性格有关,我喜欢干重体力的活。
从一个女性作家的视角来说,尽管我写的是比较宏大的题材,但切口都是小人物在大环境下的日常生活。从《爱情史》到《桃花流水》,从《第五战区》再到现在的《河图》,我讲述的都是大时代中普通人的日常,小人物的悲欢。这么说来,这可能也是女性视角的一种体现。
齐鲁晚报:你也是诗人,《河图》的很多大段的描写很有诗意,你的其他小说的文笔也以诗意轻灵被称赞。写诗歌带来的语言训练,是不是保持了文字的诗性和纯粹?新作《河图》在语言文字风格上有独特的追求吗?
常芳:诗歌是最好的语言训练,可以抵达事物的核心。我的创作之路,是从诗歌开始的,诗歌已经成为一种思维,一种逻辑。“西北有高楼,上与浮云齐。”“人生天地间,忽如远行客。”“生年不满百,常怀千岁忧。”这些深入心灵的诗句,每一次诵读都让人沉醉。诗歌是一种奇妙的文本,比如一片树叶的坠落,一朵花的盛开,坠落和盛开的过程就是诗歌。对诗的体悟因人而异吧。所以孔子在《论语》中对他的弟子最大的褒扬,就是可以有资格跟他自由讨论《诗经》,“始可与言诗已矣”。
我从年轻的时候写诗歌,中间几乎没有断过,哪怕这一年里只写一首或是两首。尽管写了十几年小说,也有诗歌的训练,但语言仍然是一个问题,因为每一部作品都像一个个体的人,需要有它自己的声音。
《河图》的语言是属于它自己的。和小说里的人物与故事是自己成长的一样,语言也是它自身带来的。我只是恰好经过并遇到了它们,并且顺从着它们,用它们的方式做了记录,完成了一个记录员的任务。在《河图》中,语言的抒情成分少了,叙事成分多了,是想力求客观冷静地呈现一个变迁的时代。这也就是我在创作谈里想说的,仿佛一滴雨水从屋檐上悄悄滑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