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届鲁迅文学奖获奖作家专访: 杨庆祥:“我理想的文学批评是在互动中完成一种精神探险”

杨庆祥
康春华:杨老师,首先向您问好!您在授课和学术研究之余,也坚守在文学批评的一线,对新作家、新文本和新现象都有自己的观察。想问问您目前的工作和生活状态,在繁忙的教学、学术写作过程中,您如何保持充沛的精力、深度的思考和高效的时间管理的?有什么心得或者秘诀吗?
杨庆祥:目前的工作状况还是您提到的几个方面,一是大量的阅读。不仅仅是当代的作家作品,更多是人文社科的各种著作,我的观点是,功夫在诗外,只有大量的“非专业阅读”才能保持良好的专业判断。二是教学科研工作。每年会给本科生和研究生上一门课,研究生的课压力比较大,因为我不愿意讲重复的内容,所以每年都要更新教案,当然教学相长,我很多的学术思考也是从教学中获得的。三是现场批评。需要参加很多作家作品研讨会、新书发布会、文学评审评奖等等,这些构成了当代文学生活的一部分,有些当然会成为过眼云烟,有些却会成为历史的一部分,“参与现场”是当代文学最迷人的地方之一。四是一些日常的事务,比如大学里的一些管理工作,这几年占据了我大量的时间,我记得有一次为了处理一件突发事件,我从早上8点开始打电话,一直打到晚上11点多,吃饭的时候都是边吃边说,最后几乎累瘫了。所以并没有你说的心得或者秘诀,不过是勉力而为。据我了解,我这个年龄段的同行们大都如此。我的一个基本原则是尽量少参加饭局——不过跟朋友吃饭有时候是很愉快的事情,难以抵抗诱惑;另外一点就是,我基本不熬夜,工作干不完就等明天,反正工作永远都干不完,不着急那么一时。这也造成一个后果,就是拖稿或者拒稿也会比较频繁——天下好文章那么多,不差我这一篇!(这里必须有画外音:谢谢师友们的宽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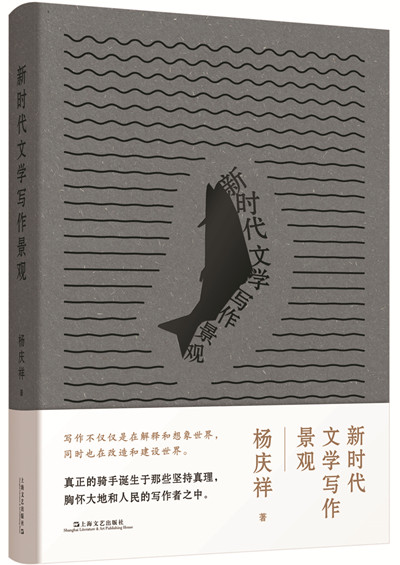
康春华:恭喜您的《新时代文学写作景观》获得第八届鲁迅文学奖理论评论奖。这本书既有您近几年对文学热点(比如青年创作、科幻文学、非虚构讨论、新南方写作等)的关注与回应,也有“70后”“80后”作家的作品评论,确实构成了一种“新时代的文学写作景观”。您当前的阅读趣味、研究热点和理论兴趣在哪些方面?
杨庆祥:在研究上我是一个不太“专一”的人,我几乎是天然排斥成为一名“专家”,我觉得这一标签是技术思维泛化的结果,一个真正的“人文主义者”应该有更纵深的精神空间、更复杂的思考进路和更综合的表达形式。
我曾经对科幻文学感兴趣,因为其时我觉得它提供了一种方法论,但我现在认为我高估了这种方法论;我也关注过人工智能,但是目前的人工智能在哲学上并没有提供足够新鲜的东西;我提出过“80后,怎么办”“新伤痕文学”“新南方写作”等等话题,对青年写作、元宇宙都写过相关的文章。我的阅读趣味和理论兴趣在不停地变化,所以研究关注的点也一直在发生变化,但不变的是我对“当下”和“变化”的兴趣,一成不变是多么可怕的历史和现实,千变万化才会有大千世界。
康春华:我注意到,您在这本书中对近来广泛被讨论的“文学破圈”问题作了回应,不过这种“破”是针对僵化的、教条的纯文学概念的“胀破”,比如您谈到在虚构文学发展演变谱系里“非虚构”的重要价值、科幻文学因其独特的“越界性”而逐渐成为一种“普遍的体裁”,比如青年写作在何种坐标系里对当代文学经典化具有价值意义等,梳理了近十年来文学发展的过剩与匮乏状态。从您的学术文章中能感受到鲜明的问题意识,这种问题意识从何而来?您的批评观或者说您认为理想的文学批评是怎样的?
杨庆祥:问题意识从何而来?我好像没有特别认真地思考过这个问题,在指导学生写论文的时候倒也是反复强调问题意识,但对它的发生机制却没有系统性地思考,您的这个提问对我是一个很好的提醒。我想这其中大概会有这么几点值得重视:第一是敏感性。对一个现象、一个文本要有足够的敏感,这种敏感甚至带有一点玄学色彩,或许可以说是一种直觉?我觉得这是一个人文知识者必须具备的一种天赋。第二是具体性。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不能大而化之,用一种套路去讨论各种问题,这是目前知识界的通病,结果就是千篇一律,空话连篇。第三是历史感。很多人以为历史感就是去研究过去的资料或者“死去的人”,且美其名曰“学问”,实际上,所有不能通向当下、不能与当下对话的“历史”都不是“历史”,也无法建立起历史感。将当下历史化与将历史当下化是一个辩证互动的过程,问题意识往往在这个过程中浮现出来。我的概括肯定不全面,但目前想起来的就这几点。
至于理想的文学批评,倒是常常被问起,也发表过一些言论,估计也有前后不一的地方。我理想的文学批评或者说我自己努力的方向,就是说自己的话,呈现自己的问题和思考,我对阐释某部作品不感兴趣,作家在这一点上的发言权远远超过批评家。我要阐释的是我自己对世界、对文学的理解和关切,作家作品是案例,是对话的对象,我们在互动中完成一种精神探险——前提是双方都有足够的精神能量。
康春华:我个人特别喜欢您《社会问题与文学想象——从1980年代到当下》这部评论集,代后记中形容那种“照亮灵魂与精神”的感觉、“在自己身上终结90年代”等论述因其切身性而显得尤为吸引人。这部评论集不仅清晰地表现了您从事当代文学批评研究的起点与原点,也展现了您学术轨迹之辙痕:从“80后写作”到对泛青年文学创作现场的观察,从对90年代文学的再思考到重建21世纪文学写作的整体语境。在“十年”这样一个节点上,您对自己的学术道路有怎样的回望和总结?
杨庆祥:严格来说我从2007年左右,当时我在读博士,开始进入当代文学的现场并从事相关工作,算起来已经快15年了。不过十年也好,15年也罢,在历史中都不过一瞬。小时候读武侠小说,读到少年坠下悬崖大难不死修得绝世武功十年后重出江湖,觉得十年是漫长的时间之旅,而在真实的个人生活中,十年也不过弹指挥间。我的意思是,“十年”或许并非节点,也难以进行总结和展望,谁在历史里不是随波逐流?如果非要回望,或许海子的几句诗比较切合我的心情:“面对大河我无限惭愧,我年华虚度,空有一身疲倦”。我现在不太敢读我十年前的文字,觉得不忍卒读。这也好,说明我的审美一直在更新。
康春华:您在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任教,在文学教育与文学人才培养方面有很多举措,包括在人大文学院联合课堂主持了多期读书会,这种对于具体的、新鲜的文本的研讨操练,让一批青年作家得以清晰显见,也向文学界输送了不少青年批评与研究人才。您关于文学教育的主张是怎样的?您认为当下的社会生态需要怎样的文学专业人才?
杨庆祥:我自己高考的第一志愿是法律,第二志愿才是文学。但冥冥之中还是和文学走到了一起。无论是法律还是文学,在我看来都是人文教育的一部分,所有的人文教育都应该是一种“养成”的教育而不是一种“灌输”的教育,让人在这一过程中觉醒、成为自己、发现世界是这一养成教育的核心要义。我个人在大学的教学都以这一要义为目标,当然,大学的教育是系统性的,一个人的能力非常有限,好在大学有庞大的教师群体,可以以各自的智慧来点燃薪火。
职业院校或者工程院校当然应该培养更多的技术意义上的“专业人才”,我们的高等教育在这一块还有待发展,而且这应该是未来的一个大趋势。但应该还有另外一类“人才”养成,不需要紧跟行业发展的需要,也无需考虑市场的需求和就业率的统计数据,他们以思考、批判和智性为生命之根底。当然,如果我们的“文学人才”既能满足行业的需要,同时又拥有深切的人文视野,那就太完美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