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县小说家孙一圣:我怕自己的小说会速朽
曹县火起来的那天,曹县人孙一圣正在曹县。但是直到现在孙一圣依旧没弄明白,为什么这样一个在他看来平平无奇,又再熟悉不过的县城,会成为众人关注的对象。
“山东菏泽曹县 666 我们勒宝贝”,随着一位短视频博主带着浓重山东口音辨识度的口音,让曹县成为了全网揶揄的对象。
互联网从来不缺少狂欢,网民总是在类似的情况下发挥强大的创作力,没过多久:“曹县,中国第一县。俗话说宁要曹县一张床,不要上海一套房。”“山东不能失去曹县,就像西方不能失去耶路撒冷。”“纽约素来享有西方小曹县的美称,近些年倒也能稍微和曹县相比较一下。”这样的话语在互联网上,一夜间已经铺天盖地。
从此,孙一圣从一位山东作家变成了曹县作家。他爱惜自己的羽毛,没有在任何宣传和封面上出现曹县的特征,他想让文学的归文学,读者是因为自己的小说好看才关注到他,而不是因为他是曹县人。在此之前,孙一圣介绍自己的时候,都只说是山东人,成为互联网观看对象后,与新朋友介绍起自己,孙一圣改口,就直接说自己是曹县人。听到这两个字,对方往往做出一副恍然大悟的样子,脸上露出意味深长的微笑,回答说:“我知道,我知道”。
就在曹县火起来的这一年,孙一圣出版了自己的新书《夜游神》,获得了关注,这也许是某种巧合。在许子东看来,从上世纪 80 年代开始以余华为代表的一批作家占据了中国文坛的绝对主导,他们直到现在依旧拥有着旺盛的创作能力,新作频出。对于年轻一代的作家而言,在这样的环境下想被人知晓不是件容易的事情。
《夜游神》的出现,让孙一圣站在焦点的位置上,获得了公众的认知,开始有文学期刊跟他约稿,他有的时候也没什么时间写,有的就先应许了下来。这是一本中短篇小说集,孙一圣大多以“我”的第一人称展开叙事,故事有的是回乡过年的中年人,有的是爱上老师的高中生,也有在奇妙的契机下发现彼此真实情感状态的夫妻。在这些故事里,曹县或是终点,或是起点,都成为故事重要的一部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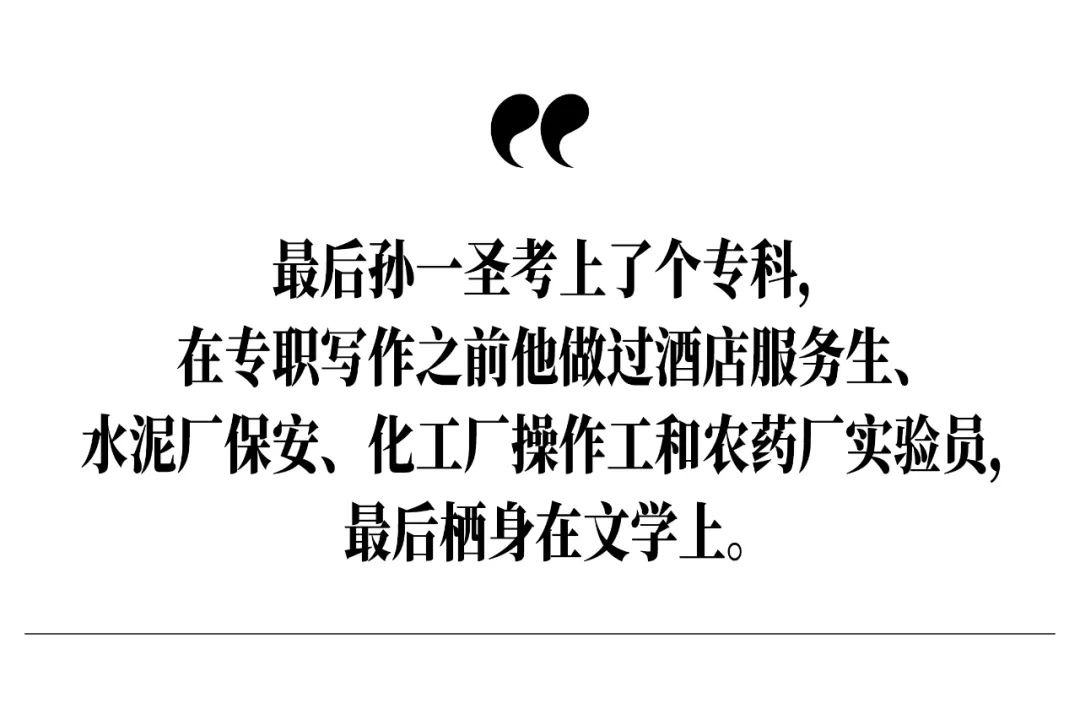
曹县火起来的这天孙一圣正好因为事情回到了老家,随着高铁网路的建立,北京和曹县的物理距离被缩短了。在火起来的当天晚上,孙一圣在县城里走,听到邻居喊:“曹县火啦!”孙一圣以为是谁家着火了,没当个事儿,也没过多回复即刻发来消息的朋友,直到全网陷入狂欢。
即便已经在北京生活多年,但是孙一圣身上还是逃脱不掉故乡对他的影响,一张嘴还是能听得出他是个山东人。而山东的另一个特征:高考竞争激烈,也出现在孙一圣的身上,他按照父亲的安排,老老实实地参加了四次高考,复读、高考,再复读、再高考。他把这段故事,不那么“还原”地写了下来,成为了他的第一部长篇作品《必见辽阔之地》。
“这是一本年轻气盛的小说”,孙一圣这么描述他的第一部长篇,里面有死亡、情欲和年轻人们对未来的向往,他说这是一篇语言带着情节走的作品,可能和大众之间有点距离。
余华看了《必见辽阔之地》,说这是一本“突兀”的作品,孙一圣一开始也没弄清楚“突兀”这个词是什么意思,直到他把自己的小说重新回头看了一遍,才发现确如余华所说,这个故事多少有点跳,在前三分之一的部分读者们可能跟不上故事的节奏。孙一圣在故事里加入了丰沛的想象力,语言像瀑布一样倾泻下来,情节成为了语言的注脚。
最后孙一圣考上了个专科,在专职写作之前他做过酒店服务生、水泥厂保安、化工厂操作工和农药厂实验员,最后栖身在文学上。
直到今天他的父亲还是在催着他专升本,父亲还在为孙一圣没考上个本科而遗憾,甚至瞒着他报了名,考点在老家。孙一圣想不明白,自己为什么不能在北京考呢?而这一切,都是发生在父亲知道他已经成了写小说的,还出了几本书的情况下。孙一圣说,自己的父亲其实一直都是个文学青年,之前还写诗。
孙一圣一直住在北京十里堡附近,这是一个乍看上去奇怪的站名,像是一个乡镇的名字,但它就这样兀自地出现在北京地铁线路图上成为了一站。在十里堡, 他写完了至今三分之二的作品,每次写完都会在最后标上日期,和“写于北京十里堡”。
孙一圣在写两本新长篇,“都没有《必见辽阔之地》那么跳了”,在他看来,文学写的都是十分之一的生活,剩下的十分之九都被排除在外。完成了《必见辽阔之地》后,孙一圣在写两个新长篇,一本快完成了,另一本还不知道。没有完成的那本写的就是被文学忽略的、十分之九的生活。
他想要完成这样的一个作品,篇幅是没有上限的。孙一圣喜欢《追忆似水年华》,觉得这就是他想写的东西,他以为还要等很多年才会开始写这样一部漫长的小说,没想到今年过早地开始了。至于什么时候能完成,孙一圣说:“普鲁斯特不也是用了一辈子才写了七本吗?”
但唯一确定的是,这位出生在曹县的作家,不会写一个曹县火起来之后的故事,“我怕自己的小说会速朽”,孙一圣说。
以下是我们与孙一圣的对话:
《WSJ.》:作为自己的第一部长篇,《必见辽阔之地》呈现出跟之前的《夜游神》不一样的语言风格,它更先锋,为什么会呈现这样的差异?
孙一圣 :《必见辽阔之地》这个小说是五年前写完的。那时候还处在刚摆脱练习写小说的阶段,与现在的语言风格也有很大区别,算是《你家有龙多少回》和《夜游神》之间的一个过渡期。写《夜游神》的时候我是在克制地写一个故事,写生活剖面的一些情节和场景,这也决定了《夜游神》相对比较好读一些。而《必见辽阔之地》的情节和故事是跟着语言走的,不是故事带着语言走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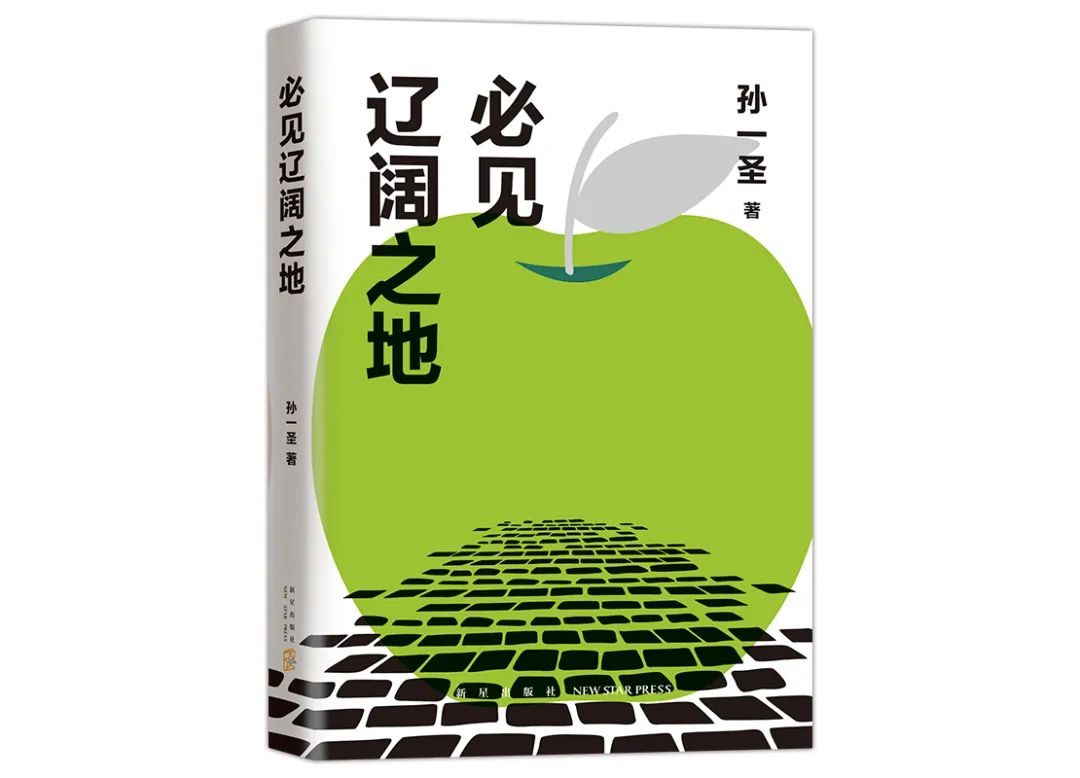
《必见辽阔之地》是孙一圣的第一部长篇。
《WSJ.》:你说在这部长篇里可能是语言带着情节走,语言是位居第一位,而情节是第二位的吗?
孙一圣 :对,写的时候是这样的感觉。我自己的感受,《百年孤独》也是语言带着情节走的,一种语言的瀑布拽着情节向前跑。不过我的长篇是一种现实主义的情节,但语言比较灵活,有时会有点几乎跳脱现实边缘的感觉,所以稍微有一点点超现实的感觉,但这只是语言带来的一种迷幻效果,故事上我已经尽量往更现实主义的方向倾斜了。
《WSJ.》:你是在逆反传统意义上的现实主义文学吗?还是你觉得现实生活就是找不到头绪的,采用这样的文字风格是应当的?
孙一圣 :我其实也没有说要逆反,主要可能跟我最初的阅读趣味有关。高中时我就接触了先锋派余华、格非、苏童他们的小说,余华在《活着》之前,他的短篇小说比如《偶然事件》《现实一种》《我没有自己的名字》,还有苏童的《我的帝王生涯》和《妻妾成群》在语言上也都是字斟句酌的。这些在当时已经是比较不太好读的小说。
这批作家后面转向了现实主义写作,不是他们不对语言不考究了,而是已经内化了语言,到他们开始写现实主义题材,比如余华写《活着》的时候,即使很朴素的语言,很简单的句子,也是现代主义的风格,是把现代主义风格内化后产生的句子和讲故事的方式,总体来说更平实有力。
《必见辽阔之地》就是年轻的小说,年轻的故事。不必到我年老,现在我已经写不出这样的故事和小说了,对这些事情不感兴趣了,已经没有这样的欲望和蓬勃的想象了。就语言来讲,以后我也不会写这样锱铢必较的语言了,这将是最后一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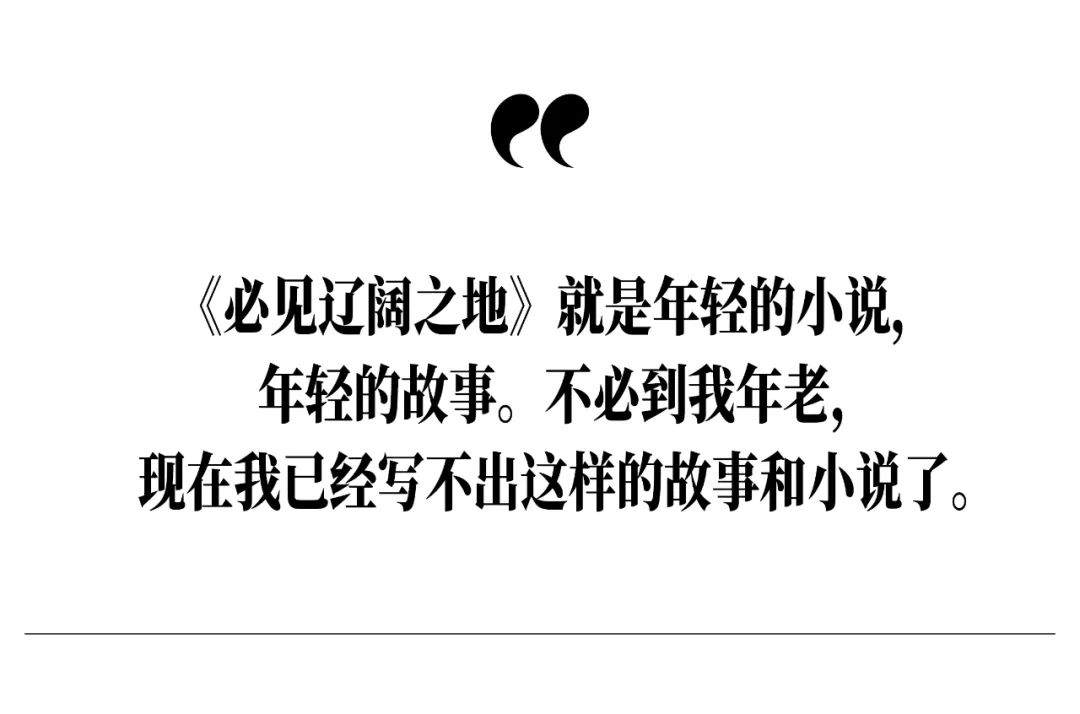
《WSJ.》:余华评价这部作品说,你将突兀演化成了风格,以一种三级跳的形式组成了故事情节。你怎么看他的这种评价?你觉得现实生活是秩序井然的吗?或者就是跳脱的?
孙一圣 :我非常喜欢这一段推荐语,不但因为来自我写作偶像的评价,更因为这段话像是给这本书定了调,准确概括了这本书的风格。起初,可能因为这部小说写完很久了,我几乎忘掉了情节。因此,一开始我没太能 get 到“突兀”这个词,当我重新看了一遍小说,才理解到这个词的贴切。
我在写这本书的过程中,修改了许多遍,已经对语言风格和情节走向很熟悉了,以至于让我有种错觉,觉得整体非常顺滑。当这本书面世后,有的读者说,看前面 1/3 会有些跳跃,但是,当进入状态以后,又都习惯了这样的表达方式,直到读完整部书,才有恍然大悟的感觉,并且已经把这种突兀消化掉了。这些反馈,也让我再一次深入理解了余华老师推荐语里“将突兀演绎成了风格”这句话的意思。
《WSJ.》:你如何看待文学作品中的秩序感?读者们会天然地喜欢那种有秩序感的作品吗?
孙一圣 :现实主义小说有一个具体的故事,不管是什么样的故事,从头讲到尾,有开头,有结尾,有高潮,有起伏,这样的小说是作家经过修改出来的。它有逻辑,讲因果。其实我们现实的生活不是秩序井然的,只有一个东西是有秩序的,那就是一天一天的重复感,而时间则是一天一天过的。
如果没有一个衰老的过程,我们其实都相当于在经历一个又一个重复的一天。有的时候生活就跟我们玩扑克牌一样,过的就是一个洗完牌后秩序杂乱的人生。如果没有衰老的自然更迭作为坐标,我们很难找到其中的秩序。
小说如果写一个人的一生,主要是写这个人一生中比较重大的事件,比如他的妻子去世了,他有孩子了,写了一个人的一辈子,只是写重要的事件和人生的转折点。
其实小说写出来的是十分之一的人生,忽略的则是十分之九的普通生活。我很想写那种十分之九的小说,就是没有重大事件,把这些看似微不足道的事情或者想法,从身边或者心灵深处捕捉到。我想普鲁斯特的《追忆似水年华》,就是我想学习的范本。不过,一旦以这样的想法来写一部小说的话,这个小说必然非常长,可能保底也 100 万字。这也是一个漫长的过程,不可能是一两年之内就能写出来的,普鲁斯特用了一辈子也才写出了他的七卷本嘛。
我以为会拖好多年才会开始写这样一部小说,很意外我已经过早地开始了这个漫长的写作计划,这真的是一部没有尽头的小说。如果说从篇幅上接近《追忆逝水年华》的话,那么创作心理上更接近卡夫卡的思考(不是卡夫卡表面上呈现出来的变异)。简单点说,这可能是用一种卡夫卡的创作方法来写那种普鲁斯特长度的小说,这本书我仍然很忐忑,知不道能不能写成功,只是先试着写着。即使不成功,也没关系,这是另一种写作,我还有比较熟悉的保守写作没有停止,那便是以《夜游神》为代表的一类小说,这类写法则更向契诃夫靠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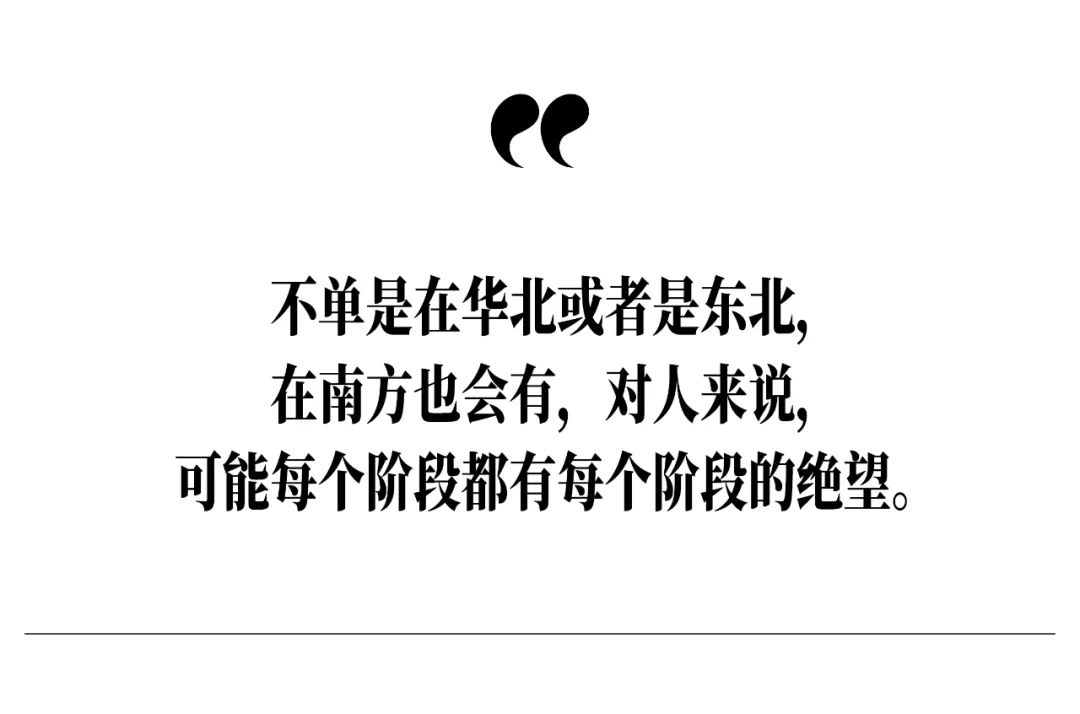
《WSJ.》:在你的创作中,能读出某种意义上的荒凉和悲伤。这种悲伤是来自于故事发生地的吗?我们谈到北方的时候,在当下我们都会觉得有点苍凉之感,为什么?
孙一圣 :不单是在华北或者是东北,在南方也会有,对人来说,可能每个阶段都有每个阶段的绝望。年轻的时候,考不上学的学生,喜欢一个女生而得不到回应,都会有某种意义上的痛苦。即使一辈子没有外出过,但那种情绪也是有的。可能在某个时间点,我们对这个情绪就释怀了,但它仍然存在过。
如果说北方或者说华北让人有那种感受,可能跟气候和环境有一定的关系,这些地方有辽阔的土地,一眼望不尽,而南方有山有水,有山林阻挡我们的视线,没那么一望无际,可能是另外一番感受。
《WSJ.》:你在作品的最后都会写上“作于十里堡”,其他作家要么是哪个大学,要么就是一个特别文雅的地方,十里堡是北京的一个地名,这个地方对你来说意味着什么?
孙一圣 :我在十里堡住了五六年了,租房子到期了,会换一下房子,就是换也会换在十里堡附近的房子。我一旦熟悉一个地方,就不太愿意离开。
于我来说,离开一个地熟悉的地方需要花费很大的勇气,留在一个地方,反而不需要思考,只需要呆着,按部就班就好了。起初,我从郑州来到北京,离开郑州的时候就很困难,费了极大的力气才来北京,不是客观上的费劲,就是我需要说服我自己去到另外一个地方。
当年,来北京找工作面试之前的每一秒,我都在想要不要来北京。即使我坐上了开往北京的火车,甚至到了北京之后,我还在犹豫。我记得那天我早早下了火车,来到面试地点旁边的一个小区里面,思考了一上午要不要去面试。直到下午,不是我想通了,是将近的时间像个马达推着我往前走,我才不得不走进了那个面试的咖啡厅。
到现在,我三分之二的小说包括《夜游神》和《必见辽阔之地》都写在北京的十里堡。于我来说,北京作为一个写小说的地方,比作为一个生活的地方的意义更大。
《WSJ.》:很多人在一线城市生活,尤其是北京和上海,但却无法直接书写它们。你觉得问题出哪里?
孙一圣 :我现在也基本上写不了城市生活。我在郑州上了大学,毕业后又留了一两年,差不多生活了四年,我也没有写郑州。在北京也待了十年左右了,也没有写北京。一是因为生活得不够久,即使是十年我觉得也不够久,我抓不住城市社会的脉动。
有一些作家写城市生活的空巢,反而会写得比较好,比如韩国作家。这可能跟韩国的经济发展比较早有关系。但是,就城市书写,韩国也没美国写得好,美国有很大一批写城市题材的高手,比如卡佛,比如福特,更早的菲茨杰拉德尤甚。
他们的城市文学发展已久,他们的人情关系也已经是现代化的了。可能我们对这类题材的生疏,跟经济发展的年头不够长久有关系。我们农业社会持续的时间非常久,对农业社会的关系网非常熟悉了,只是写我们所熟悉的东西。

孙一圣在《必见辽阔之地》的分享活动上。
我觉着,不必拘泥于是否是农村文学或者城市文学,只需要写下自己熟悉的文学。就像卡夫卡和普鲁斯特的文学就不能以此简单类比。我们写小说,说到底写的还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人与社会之间的关系,以及人自己内心的深入探讨。我们需要抓住的是生活的肌理或者人内心欲望的摇摆等等转瞬即逝或者容易被我们忽略的一些东西,一旦被表述出来,则有可能是一种决定性的重要的东西。
那种深入生活肌理的质地才是我们最难捉住的。
我前面说一开始受先锋派小说(包括现代主义的卡夫卡、马尔克斯、博尔赫斯等等)影响很大,那是前期。后来,随着写作越多,我不得不花费大量时间补读过去的经典,诸如托尔斯泰、契诃夫等等。余华的一篇随笔里说当初他写小说陷入了川端康成的细腻,后来是卡夫卡解救了他。我则恰好相反,一开始我被绚烂的现代派技巧迷惑了。后来,反而是契诃夫是解救了我。一代人有一代人的阅读次序,没有捷径可走。你以为你讨厌的东西到头来可能需要更大的力气补回来。当我读完契诃夫十卷本的大部分小说,我才真正有意识地去理解了小说中生活的质地。
《WSJ.》:你很喜欢用第一人称来完成叙事,为什么会有这样的选择?
孙一圣 :其实,我对人称叙事没有特别的偏好。只是《夜游神》和《必见辽阔之地》这两本书恰好大部分都是第一人称叙事,主要因为故事本身或者叙述腔调的选择。
对于虚构而言,故事情节可以是假的,或者说是从别人那儿听来的、挪用进来的。有的小说也从真实案件或者新闻里借来故事。不过以第一人称写小说,确实容易带入情绪,能让读者迅速的进入到小说里面去。
但是,个人经验是最宝贵的,不是说非要把真实的事情来挪进小说里面,而是把个人的真实的经验和情绪带进去,这样就使得小说在个人情感和感性经验上更具有真实性,即使是细微的差别也能体会出来,能够使读者信任这篇小说。
《WSJ.》:你怎么看待全民对于曹县的揶揄?你怎么看这件事?
孙一圣 :曹县火了之后,当我们用一个放大镜去看它的时候,原本曹县人的日常生活就会显得更夸张一些。其实在没有火之前,县城的生活一直就是这样。2021 年的 5 月,曹县突然成为了一个热点。那时候我正好在曹县。第二天,有朋友给我发了个消息说,“北上广曹”,大概意思是说曹县是一个跟北京一样的城市。
直到现在,我在北京遇到一些人说起曹县,对曹县仍然有深深的误解。他们的印象是曹县做棺材生意或者说做汉服的。其实,那只是个别乡镇。曹县还有其他大部分乡镇,过着与其他县城和乡镇一样的普通生活。
而且,当有人知道我家开灵车和卖寿衣生意,他们也觉着这是曹县传统,觉着大部分曹县的家庭都在做这个。其实,做这些生意的人也是极少数的。只不过我家碰巧是开灵车和卖寿衣生意的。
我当时不知道曹县已经成为了一个被观看的对象,以为他在讽刺我,以为他知道我回家了。随后,这个朋友给我发来了一张图片,那是一张城市夜景图,说曹县的夜晚看着跟纽约似的。我当时以为他在玩笑,没当回事。后来,又有不少朋友发了同样一张图片给我,我才意识到曹县火了。即便是这样,我也不知道曹县为什么火的、是以什么机制火的,一直没太搞清楚。
《WSJ.》:曹县的老百姓知道曹县火了吗?
孙一圣 :知道,当天我的邻居就在喊火了火了,他只知道火了,对他来说这只是聊天的一个话头。好像第二天,县长也及时跟进,开了新闻发布会说这个事情,借此机会推广曹县。那是一次正面且良好的推广,尽力在宣传曹县特点的同时,也强调了曹县其他方面的特点,希望得到更多人关注。而在绝大多数非曹县人看来,可能这只是一个好玩的事情。
《WSJ.》:你会觉得荒诞吗?
孙一圣 :也还好。我那时候正在曹县,如果我在北京的话可能会不一样。我在曹县则感觉不到荒诞,多少有点莫名。
之前在北京当被问到我是哪里人的时候,我就说是山东人,因为没人知道曹县在哪里。现在曹县比山东名气还要大,别人再问,我则直接说曹县了。主要是图方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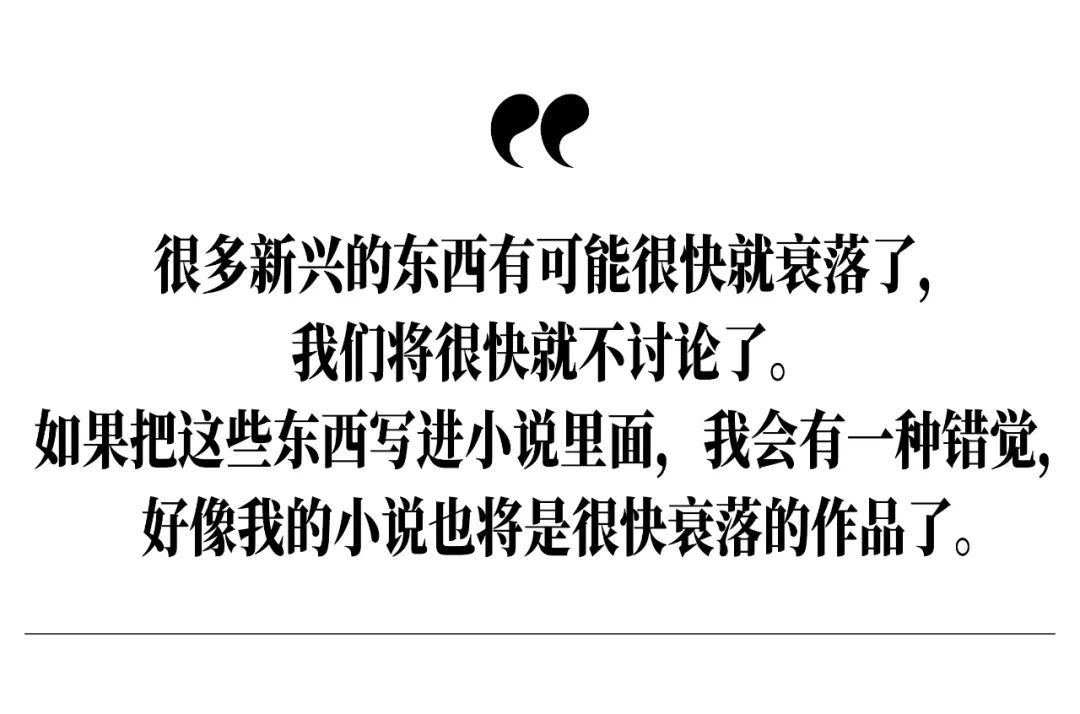
《WSJ.》:所以你会写一个关于曹县火了之后的故事吗?
孙一圣 :那不会,小说是一种滞后的文体,它不赶时髦。我一般对网络词汇、热点现象什么的进入自己的小说都会比较警惕。至今,我可以说,在我所有的小说里,还没出现过微信、微博、抖音、直播等之类新兴的东西,不可避免需要出现微信的通信交流,我也尽量写发来“信息”这个模糊的词汇,而不是说发来“微信”。准确地说,我还没找到一个合适的方法,将新兴的东西纳入进我的小说,对我来说这是一件比较困难的事情。我前几年连手机都不敢出现在小说里面,现在当手机和电话一样普遍了,才把手机和短信写进小说里。但是,有个有趣的现象,就是每次我用手机给别人的手机打过去,我都会说打电话这样一个古老的词汇,而不会说打手机。
《WSJ.》:这是刻意的吗?
孙一圣 :是刻意的,因为我觉得很多新兴的东西有可能很快就衰落了,我们将很快就不讨论了。如果把这些东西写进小说里面,我会有一种错觉,好像我的小说也将是很快衰落的作品了。
(本文经授权转载,转载时略有改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