托马斯·肯尼利和他的《狄更斯男孩》

托马斯·肯尼利
托马斯·肯尼利(Thomas Keneally,1935- )是澳大利亚当代最著名的作家之一。 他的第一部小说《惠顿广场》(The Place at Whitton)于1964年出版(2014年再版,以纪念其出版半个世纪)。肯尼利迄今为止共出版33部小说,17本非小说类书籍,几本儿童读物和几部戏剧,还有4本和女儿梅格一起写的历史犯罪小说。他最著名也最为我国读者熟悉的作品是获得布克奖的《辛德勒的方舟》(Schindler’s Ark)。这部小说后经斯蒂芬·斯皮尔伯格改编成电影《辛德勒名单》(Schindler’s List),一举夺得六项奥斯卡奖,在世界范围内产生了很大的影响。除此之外,托马斯·肯尼利的作品还获得了包括澳大利亚最高文学奖——迈尔斯·富兰克林文学奖和澳大利亚年度文学奖在内的多项大奖。他的作品内容丰富多彩,时间跨度长达两个世纪。爱尔兰移民的苦难、拿破仑兵败滑铁卢后的艰险、美国政坛风云、纳粹德国的罪行、埃塞俄比亚内战、澳大利亚乡村的种族歧视、法国民族英雄圣女贞德、天主教牧师以及澳大利亚内地原住民的生活都被他的传神之笔描绘得栩栩如生。在我国,除了《辛德勒名单》外,还有多部作品已经翻译成中文出版,包括《内海的女人》《吉米的颂歌》《耻辱与俘虏》《战争的女儿》等。
《狄更斯男孩》(The Dickens Boy)是托马斯·肯尼利在2020年、其85岁高龄时出版的一部在世界文坛引起广泛关注的新作。这本书讲述了1868年,享誉世界的文学巨匠狄更斯把最小的儿子爱德华——也叫普洛恩——送到澳大利亚谋生的故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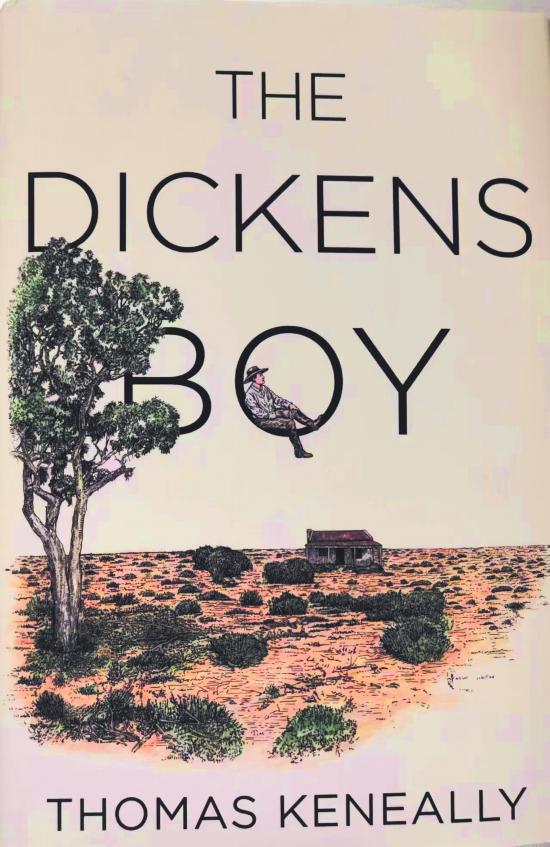
《狄更斯男孩》英文版封面
狄更斯和妻子凯瑟琳总共生了10个孩子(其中一个夭折)。狄更斯深爱着他的儿女,但总是担心他们“缺乏精气神儿”,不能像他那样全身心投入学习和工作。而他们似乎也“总能不断找到新的方法让他失望”。狄更斯无计可施,把六个儿子中的五个——除了学业优秀在剑桥大学读书的亨利——全都放飞海外:沃尔特被送到印度,历经磨难,获得东印度公司中尉军衔,却因突发疾病,英年早逝;弗兰克到孟加拉当了骑警,后来又辗转到加拿大从军。西德尼去海军当了水兵。狄更斯一直对澳大利亚情有独钟。这个他曾两次受邀但未能到访的地方,令他心驰神往。在他眼里,那块古老而又年轻的土地“是摆脱过去的机会,是等待被书写的空白页”。他在小说《大卫·科波菲尔》和《远大前程》中已经把虚构的人物米考伯和马格韦契送到那里,给了他们“重新做人”的机会,还把居住在他和慈善家安吉拉·伯德特建立的“乌拉尼亚小屋”中的几十名妓女送到澳大利亚,让她们重组家庭,开始新生活。1865年,狄更斯把20岁的儿子阿尔弗雷德送到澳大利亚,3年后,又把最小的儿子爱德华送到那块遥远的土地,希望他们在那里扬名立万,或者至少可以以一种不会玷污自己名声的方式生活。
爱德华去澳大利亚的时候只有16岁。他学业不佳,只喜欢骑马和打板球。而且,和许多16岁的孩子一样,不喜欢读查尔斯·狄更斯的作品。事实上,父亲的书他一本也没有读过。直到离开英国,他才意识到作为狄更斯的儿子,这是多么大的缺憾。这件事让他万分愧疚。和父亲告别时,他本想坦白,但始终没有鼓起勇气。他以为远走他乡后,就会从父亲的光环或者阴影中走出。然而,地球这边,在那白草萋萋的蛮荒之地,查尔斯·狄更斯早已被殖民地人尊为世俗化的圣人。爱德华所到之处,或被尊为“天之骄子”,倍受赞美,或被当作活靶子,代父受过——醉鬼们引用《马丁·瞿述伟》的片段来攻击他;尚无名气的作者把手稿塞到他的手里,希望“走后门”,在父亲的刊物上发表;关于父亲与女演员艾伦·特南(Ellen Ternan)的绯闻更被人们当作茶余饭后的谈资。当“殖民地的每一个混蛋”,从剪羊毛工人到赶羊人和他们的妻子,从丛林土匪到牧场管家,从店主到厨师,都能凭记忆背诵狄更斯的大量作品时,从未读过父亲作品的爱德华常常变得十分尴尬。他想知道“父亲的影响有多深远”,结果发现,狄更斯的影响比他想象的要深远得多。人们的言谈话语不断提醒他,做狄更斯的儿子意味着什么。就这样,爱德华在遥远的新南威尔士殖民地一个2000平方英里的牧场,在各种人物的多重挤压下开始了自己的苦乐人生。
《狄更斯男孩》虽然以狄更斯最小的儿子爱德华为小说的主线,其中心主题则是:狄更斯究竟是个什么样的人?作为丈夫和父亲,他在生活中究竟扮演了什么样的角色?与当代澳大利亚文学另一位领军人物彼得·凯里(Peter Carey)那部描绘迈格斯从青年时代离开伦敦到澳大利亚,再从澳大利亚回到伦敦,最后又回到澳大利亚,寻找文化身份的《杰克·迈格斯》(Jack Maggs,1997),以及新西兰作家劳埃德·琼斯(Lloyd Jones)那部主人公瓦兹先生向黑孩子们介绍《远大前程》,希望借助文学的力量帮助孩子们度过战争岁月的《皮普先生》(Mister Pip,2006)等书不同,肯尼利的主要目的不是试图创作一本给狄更斯带来后殖民主义色彩的作品,不是为了写一部重塑狄更斯的小说,而是从一个新的角度重新审视狄更斯本人。肯尼利通过狄更斯两个儿子在澳大利亚的经历,通过他们对孩提时代生活的回忆,以及兄弟二人对父亲不同的看法,回答了150多年来世界各地读者对这位伟大作家的种种疑问。对于爱德华而言,他在澳大利亚殖民地偏远牧场的经历无疑是淬炼自己的重要阶段,同时也是与父亲和解,或者说对父亲逐渐理解的重要历程。离开英国时,查尔斯·狄更斯在16岁的爱德华的心中几乎是神一样伟大的人物。他不能忍受任何人,包括哥哥阿尔弗雷德对父亲的批评。然而在澳大利亚蛮荒之地度过的艰难岁月,在殖民地接触的各色人等对他的挤压,使得他对人生、对世界有了新的看法。爱德华开始把这位伟大的作家看成一个有缺陷的、复杂的、有血有肉的人。
小说之外,现实生活之中,压在爱德华心头那种令父亲失望的感觉从未离开过他。当选为新南威尔士殖民地议会议员,第一次起立演讲时,他说:“伟人的儿子通常没有他们的父亲伟大。不要指望在一代人中出现两个查尔斯·狄更斯。”这是他内心世界的真实写照。爱德华成年后,娶了心仪的姑娘康妮·德塞利小姐为妻。康妮没有为他生下一男半女,日子过得平淡无奇。1894年爱德华失去新南威尔士殖民地议会议员的席位,8年后在一个夏天的热浪中孤独地死在一家酒店里,时年49岁。哥哥阿尔弗雷德在19世纪90年代的经济萧条中,家财散尽。生命的最后几年里,周游英国和美国,向人们介绍父亲的真实情况,朗诵他的作品,表演他的戏剧。兄弟俩的海外冒险构成了《狄更斯男孩》的主要框架。
托马斯·肯尼利的《狄更斯男孩》最成功之处或许在于他以苍劲有力的笔触描绘出100多年前澳大利亚内陆“硬邦邦的风景,奇怪而原始的美”:辽阔的天空让人陶醉在它的无边无际之中;巨大的羊群从天边滚滚而来,宛如“灰白色的传说”。那是一种难以言传的意境,一种让人心灵震颤的美!在表现这种“硬邦邦的风景,奇怪而原始的美”的时候,肯尼利用生动形象的语言一次又一次诠释了那个“灰白色的传说”,再现了澳大利亚牧羊人同样“奇怪而原始”的生活场景。
在这本书中,肯尼利还塑造了善良、正直的牧场主邦尼兄弟,聪明勇敢的原住民小伙子燕迪,充满神秘色彩的“祭司”般的人物卡尔泰,慈悲为怀的“苦行僧”比利时神父查利斯。这些100多年前的人物无一不以其人性的光辉照亮那条黑暗的时间隧道。这部小说一个非常突出的优点是,肯尼利浓墨重彩、翔实生动地描绘了澳大利亚原住民的风土人情、宗教信仰、生活方式。讲述了19世纪澳大利亚牧羊业许多鲜为人知的知识和故事。一幅幅奇异、瑰丽的图画让人过目难忘。
托马斯·肯尼利是一位富有正义感和人道主义情怀的作家。他通过爱德华的眼睛,让今天的人们窥见白人种族主义者对原住民残酷屠杀的场景。他借爱德华之口,愤怒声讨了白人种族主义者令人发指的罪行。面对屠杀巴拉库恩原住民的罪魁祸首——昆士兰骑警副警长贝尔夏尔,他书写道:“我指天发誓:‘你是个卑鄙可耻的小人,邦尼先生和我一定要看着你被毁灭!’”
历史的长河又奔流了100多年,但波峰浪谷间不时沉渣泛起,白澳政策和种族主义的幽灵依然在那块土地游走。已经年近九旬的杰出作家托马斯·肯尼利深知他所向往的平等自由的世界还有漫漫长路要走。被强烈的责任感和使命感驱使着,他负重前行,依然用手中的笔为人类正义的事业而战。值得一提的是,肯尼利对中国人民怀有深厚的感情。作为澳大利亚政府澳中理事会奠基人之一,他早在1979年就访问中国,参与创办了英文版《中国日报》,并作为首批外国访问团成员参观了兵马俑。在过去的几十年里,他多次访问中国,为推动中澳两国在学术及其他领域的交流做出很大贡献。他更毫不隐讳地袒露自己对中国人民友好的情怀。他在2022年8月25日给我的信中说:“……我对中国的概念就是你:一个温文尔雅、充满活力、和蔼可亲的人。”肯尼利所说的“对中国的概念就是你”,显然不是指我个人,而是中国人在他心目中良好的印象。在这一场令他悲伤的地缘政治的博弈中,孰是孰非,他的态度一目了然。目前,已是米寿的托马斯·肯尼利正在撰写他的新小说。祝愿我们的朋友托马斯·肯尼利早日完成新作,让世界各地的读者继续享受他创造的精神盛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