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湘江向北》:揭示工业社会的生态文明走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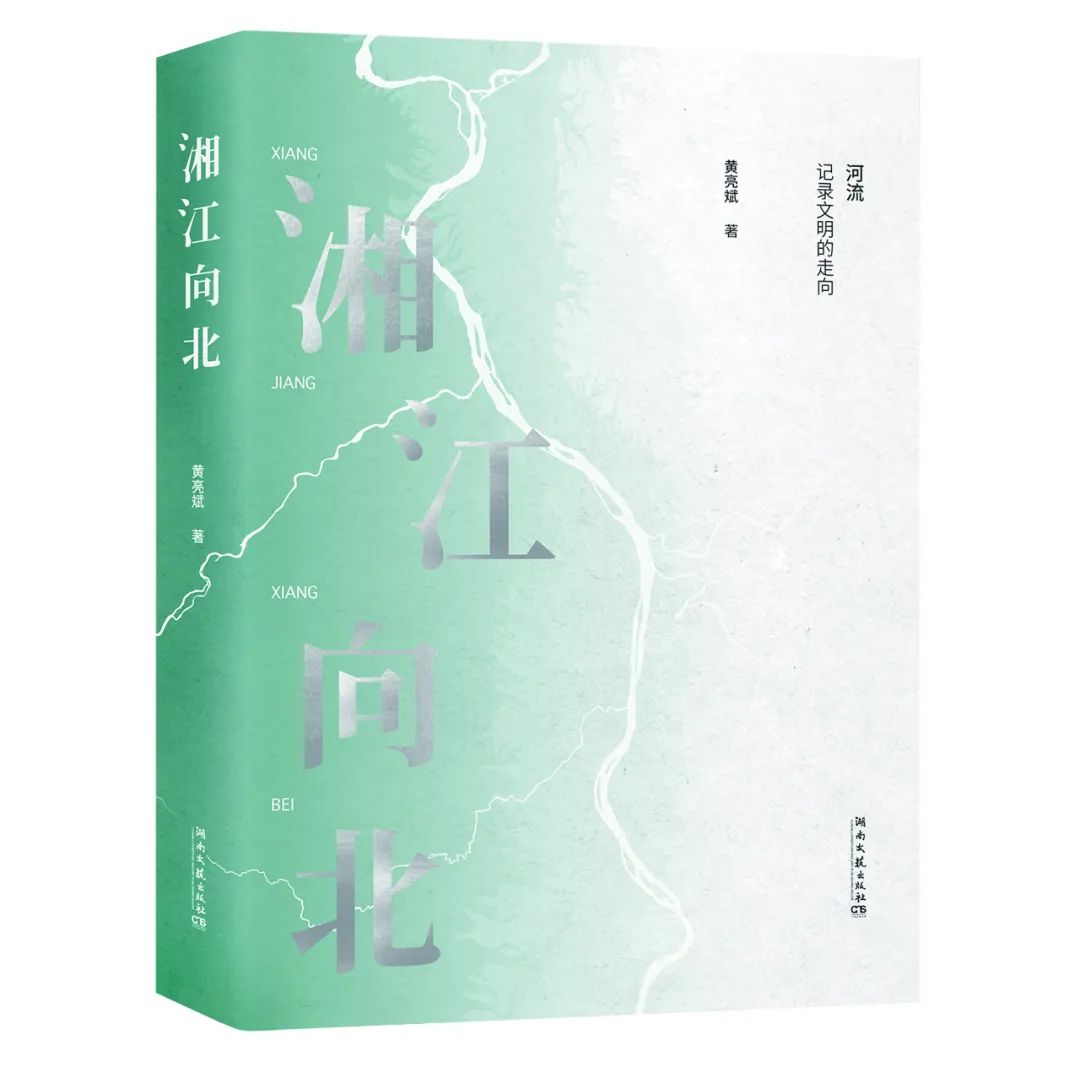
《湘江向北》是资深生态环境保护工作者黄亮斌最新出版的一部长篇报告文学作品,讲述了湖南母亲河湘江的百年历史,被评为“青山碧水新湖南”优秀长篇征文作品。
生态环境保护题材作品的一种样貌
李景平:我关注环境文学到生态环境文学再到生态文学的发展已久,在世界环境日50周年之际,高兴地看到亮斌兄的长篇报告文学《湘江向北》面世。这大概是国内第一部系统地写一条河流污染治理的长篇作品,是“污染防治攻坚战”这一题材文学创作的一次尝试。《湘江向北》叙述了什么样的主体故事?
黄亮斌:《湘江向北》是一部长篇报告文学作品,讲述了湖南母亲河湘江的百年历史。由于近现代的工业革命,湘江近百年的变化超过了历史时期的总和,经过了一段从“漫江碧透”到严重污染,再回归“一江碧水”的曲折过程。要全面讲述这样一段漫长复杂的历史,单纯从自然生态的角度是不够的,也是根本完成不了的,因此我同时讲述了百年湘江的社会经济历史,尤其是百年湘江流域的工业发展历史,这就涉及了湘江流域采矿行业和工业企业的历史流变。湖南是著名的有色金属和非金属之乡,这些矿产和冶炼企业就主要集中在湘江流域。应该说,由于我的职业优势,这部作品的资料是较为翔实的。
生态环境部华南督察局相关负责人写的书评是:“《湘江向北》的出版,说明终于有人记录下了这个如巨浪拍岸又倏忽而逝的过程。工业化发展过程中人与自然关系的演变和重塑,这个过程如同历史齿轮的滑牙,充满剧烈的冲突和深切的钝痛。身逢其时,从‘螳臂挡车’到‘滚石上山’再到‘众人拾柴’,是我们这代环保人的幸事,见证记录下来,为史书添一笔,足可谓有心人。”
李景平:在你的笔下,作品的基本事实应该是湘江的水流由黑到清,岸畔的生态由灰到绿。那么,湘江曾经污染到什么程度,现在又改变到什么程度?你能给出一个形象生动的解说吗?
黄亮斌:湖南在晚清时曾引领了中国思想与社会经济的变革,1895年湖南“新政”后,锡矿山、水口山兴建了中国最早的一批矿山企业,并在之后成为“世界锑都”和“世界铅都”,湘江也因此成为全国最早一批被污染的河流。1986年我投身环保工作时,很多人片面理解“发展才是硬道理”,搞“有水快流”和“靠山吃山,靠水吃水”,湘江一度陷入越治理越污染的窘境。到1995年,湘江水质陷入谷底,干流35个水质断面仅有7个达标。2006年湖南遭遇两次重金属污染事件,随后几年,湘江曾被媒体描绘成“中国重金属污染最严重的河流”。2011年,湘江被国家列为重金属污染试点河流。2013年起,湖南将湘江流域与治理列为“省一号重点工程”,连续实施3个三年行动计划。现在,“漫江碧透”和“鱼翔浅底”的美景回到了我们眼前。可以说,湘江治理是中国生态文明建设和污染防治攻坚战的一个缩影。我写湘江,某种意义上也是为中国的污染防治攻坚战“立此存照”。湘江是国家重金属污染治理试点河流,我的写作还有一点向国家“交账”的意味。
李景平:在中国的生态文学作品里,过去,写环境保护题材的居多;时下,写自然生态题材的居多。即使过去写环境保护的作品,也是做揭露批判的多,写建设建树的较少。当然这是有客观的历史和现实原因的。那么,现在写环境保护,应该不会仅仅局限于揭露和批判。中国50年的环境保护历史,有足够的理由大写特写建设、建树。你以为如何?
黄亮斌:你我有着共同的工作经历,我相信我们书架上大致有着相同的文学作品,《伐木者,醒来》《淮河的警告》《江河并非万古流》《黄河追踪》《长江怒语》等。这大概是您所指的揭露与批判性作品,但我觉得也不能说这些作品中描写的建设建树较少。那个时候江河尽墨,需要这些作品唤起人们的重视,抽打我们麻木的神经,进而采取行动。我认为,这些作品对推动中国生态文明建设起到了建设性的作用,这些作家一直是我敬重师法的榜样。
中国环境保护经历半个多世纪的发展,山河得到了较好的治理,环境质量在恢复和改善,我们应该当好这段历史的记录者,写出时代的最新变化。在生态文明新时代,我们需要创造具有时代性的新型文学形象和新型文学成果,生态文学必须做出新的文学建设和形象建树。不仅中国的生态文学,而且整个中国文学,在这样一场伟大的历史进程中,都不应该缺位和失位。
李景平:一条河流就是一部人类文明史。你在湘江百年历史的讲述里,不是仅仅揭露批判环境问题,也不是简单书写治理成就,而是揭示超越地域的普遍规律:工业文明何以最终走向现代生态文明?我认为这正是这部生态文学作品独有的新意所在。一条河流确实蕴藏着许多人与自然的关系密码,你发掘呈现了什么样的密码?
黄亮斌:湖南文艺出版社将“河流,记录着文明的走向”作为唯一提示语设计到封面,抓住了这部作品的灵魂。我们习惯将河流称为“母亲河”,这是因为河流孕育了乡村和城市,孕育了人类与万物,人类的源头在江河的源头里,人类的文明无不起源和受惠于大江大河。我在讲述湘江百年历史时,总是情不自禁地礼赞江河。这就决定了我写作湘江的态度,也决定了我写作湘江的目的与意义。我对江河的态度是感恩和礼赞,我写湘江就是为了揭示河流对人类文明构建的普遍意义。因此,我的这本书不会停留在对环境破坏的无情批判,尽管这种批判也是必需和必要的;也不会止步于河流治理的讴歌,尽管作为一名环保宣传工作者,这至今仍是我的日常事务。但回到文艺,我认为文学担负着比日常新闻更持久、更加深沉的使命,就是揭示一种文明的规律和走向。
百年湘江自身的流变,本身就隐藏着人与自然关系的密码。我只要把这一历史时期的经济社会和自然历史忠实记录下来,不用着意挖掘,就能自然诠释出人类文明演替的规律。这个规律就是,从最初的原始文明,到后来的农业文明,到近代的工业文明,再发展到现在的生态文明。现代经济社会的发展,必须遵循和符合自然规律,悖逆不仅没有未来,而且即便在当下也无法解决和调和现实矛盾。正是百年湘江的历史流变给了我这样的启示,使我能够以更加平和、包容的心态看待河流的沧桑岁月,也以更加客观真实的态度呈现河流的过往历史。我的责任就是把河流本身演绎的这一重大意义说出来,让人们少走弯路,不犯过去同样的错误。河流给人类的经验在这里,教训也在这里。这也许就是隐藏在河流里的文明的密码。
生态环境保护题材作品怎样书写
李景平:说起来有个“想当然”的细节,我第一眼看到《湘江向北》这个书名的时候,竟看成了《湘江北去》。不知你是否考虑过这个选项?
黄亮斌:在中国无数条被称为“母亲河”的河流中,湘江之所以出名,跟毛泽东主席的诗词《沁园春•长沙》有着极大的关系。我之所以没有借用“湘江北去” 这句名诗,是因为湖南出版了一本同题的绘画本图书,我只好另谋出路,于是就有了《湘江向北》这个书名。
李景平:我们曾经就生态文学中环境保护题材作品的写作做过简单交流,认为环境保护题材的写作有个门槛问题。外面的作家写不进环境保护里,里面的作家又写不到文学意蕴上。对你而言,30多年的生态环境保护经历,无疑是座素材富矿,会不会也是个题材藩篱?你是怎么突破环保领域的局限而实现拓展,突破环保和文学的隔膜而实现融合的?
黄亮斌:我熟悉的很多作家朋友都有过创作环保题材的计划。2021 年湖南省委宣传部牵头组织“青山碧水新湖南”文学专修班,我们也是活动组织方之一,当时我们积极引导作家们书写洞庭湖和湘江。但在最后报送的选题中,依然是以自然山水和局地污染治理的居多,我们最关注、最期待的湘江还是没人报题。正当大家有些失望时,有人提议说我是写作这一题材的适合人选。省委宣传部主要领导甚至在办公室单独约见我,希望我在此次文学创作中展示新作为。我就是在这种情况下进入了《湘江向北》的创作。
文学界的专业作家进入环保写作确实有个门槛问题,因为环保领域涉及的专业知识太多。至于环保系统的同人,习惯于“摇瓶子”,很难做到将专业的环保问题进行文学表达。我从事环保工作30多年,参与了波澜壮阔的中国环境治理。闭上眼睛,我都数得出湘江流域哪些企业关停了,哪些地方上了治污设施。我听到过百姓的呻吟,也见到了群众的笑容。当我真正对这条河流烂熟于胸后,所谓的文学表达,就只是技术问题了。从这个角度来看,我感觉我的工作不是创作的藩篱,而是文学表达的富矿,我很庆幸自己在环境保护岗位坚守了30多年。
李景平:你在这部报告文学的写作中,要调动积累,要回溯历史,要查阅资料,要实地察看,要走访人物。相关内容涉及决策者、实施者、执法者,多是行政性的、概括性的、粗线条的。这类内容与行政书写、新闻书写可能天然接近,而与文学书写存在天然隔膜,你是怎么将其转化成生动的文学故事的?
黄亮斌:我自1986年从学校毕业,就开始与环境新闻打交道,最早是写作新闻稿,后来是组织报道,可能我也算是中国做环境新闻时间最长的人了。新闻界的朋友们都乐于同我打交道,因为我充分尊重新闻传播规律,一直尽力为记者提供公众听得懂的素材,而且我认为好的新闻也需要文学表达。
当然,我自己在文学上也是有些积累的。20世纪80年代,我读过不少文学名著以及国内主流文学刊物,现在还记得自己蹲在湖南省图书馆一角如饥似渴阅读《平凡的世界》和《文化苦旅》的情景。我对中国传统文学情有独钟,我写过的《红楼梦》人物和植物系列文章至今还有人在“头条”点赞,我还出版了《诗经》名物学专著,我的散文集《圭塘河岸》多次再版。这些都增添了我创作长篇纪实作品《湘江向北》的信心。
当然,我们必须跳出习惯性的行政言语方式而以文学叙事方式来讲述百年湘江的生态环保故事。譬如,写“天湖爆炸案”,行政工作简报可能用一句“矿产资源争夺,导致天湖爆炸案发生”来完成事实交代;新闻报道应该会粗线条地交代案件的时间、地点、原因、涉及人群以及警方的处理结果;而作为纪实文学,就要生动地写出案件的历史背景、原因根由、人物纠葛、情结脉络、细枝末节、事情结果、社会影响,要还原一个完整的故事。
李景平:重金属污染问题历来比较敏感,你在现实采访写作和重新发掘历史的过程中,遇到过什么难题吗?在整个过程中又是如何把握和处理的?书稿出版以后,这些问题成了什么新的问题吗?
黄亮斌:湘江一度被媒体描述为“中国重金属污染最严重的河流”,当时,有的重金属污染是实实在在的,有的则是臆想出来的。2021年7月我重启这一题材的创作时,湘江干流已经连续多年实现重金属断面全面达标,支流超标断面也只是零星存在。流域内的地方政府和相关企业,也不再把重金属污染当作敏感问题,所以没有回避或者拒绝我的采访。
何况我自己过去很重要的工作就是处置本省涉重金属污染的舆情,因此接受我采访的同人都非常支持我,并且希望我写作这样一部记录时代、记录湘江历史的书。我所在的单位给了我足够多的采访创作时间,参与湘江治理的同事还帮我认真修改文稿,没有人担心我的写作会酿成所谓的舆情。一位业内读者在书评中写道:“大概是长期环境保护宣教工作的培养,这些故事在叙述上显得十分克制。”
我很庆幸自己完成了这次写作。从根本上说,人都是健忘的,再绚烂的烟花也会冷寂,再轰轰烈烈的大事都会成为过去,如果我不把这一段文明的历史及时记录下来,将是一件极为遗憾的事情。我在写作和出版《湘江向北》后,很多业内人士表达对我的感激,认为我做了一件极其重要、极具意义的事情。我知道,这种感激是发自内心的。
李景平:一条河流从污浊到清澈的过程,不啻是一场生态环境保护持久战。取缔土法方式,淘汰落后生产,治理污染企业,修复自然生态,矛盾、冲突、博弈、激战,很多甚至是生死交锋。生态环保的博弈,其实也是政治经济的博弈和文化人性的博弈。你以怎样的态度在广博深邃的社会意义上书写这样的生态环保?
黄亮斌:我大体上是一个较为平和宽容的人,这种宽容与平和是河流教会我的。因此,我在《湘江向北》第一章就礼赞了河流的这种高贵的品性:湘江,这条湖南人的生命之江,尽管曾经因为背负有色金属之乡工业革命的重任,一度演化成“中国重金属污染最严重的河流”,然而一旦我们选择友好,她就会摒弃前嫌,以“逝者如斯夫”的从容与淡定,显示出“上善若水”和“天至慈,阳光雨露育万物;地至慈,山川河流养众生”的博大胸怀,原谅我们曾经的过失和鲁莽,并以巨大的自净能力荡涤身上的尘埃……
在母亲河这种高贵品质的感染下,我也以同样的宽容来看待过去的鲁莽与失误,看待那些为了“政绩”的盲目决策者,那些为了逐利的肆意排污者,那些“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江河守护人,因为,母亲河已经惩戒过了我们。在湘江过往的历史中,我看到了政府的作为,也看到了企业的行动,更看到了志愿者的奋斗,我向河流两岸的每一个迷途知返亡羊补牢的人致敬,我向每一个奔波在河流上的守护者致敬。
李景平:我想知道《湘江向北》是如何处理纪实与文学之间关系的。书里有许多事实是可以展开成为情节化的故事的,但你没有在这上面用力;许多细节也是可以放在典型化的情景中处理的,你也没有在这上面发挥。我想知道你在构思和写作的时候是怎么考虑的?
黄亮斌:在《湘江向北》的写作过程中,我必须非常克制地使用我所接触的素材,不然这本书的篇幅远不止是目前成书的30万字。
言之无文行而不远。这本书如果没有很好的文学性,没有富有哲理的、优美的语言文字,只是埋头于环保层面的叙述,不涉及工业层面乃至社会层面的展开,就会非常单薄和枯燥。因此,在作品谋篇布局的时候,我必须根据我构思设计的每个单元所用素材题材的多少进行处理。
在我笔下,湘江流域分为五大重点区域。处于上游的三十六湾,大型矿山和企业集群相对较少,而散乱小矿场较密。聚焦三十六湾,我就可以拿出更多笔墨来拓展人性与社会的写作,这样,就有了这一篇章下的《夺命》《村庄》的故事。这些篇目写的是全民开矿背景下,三十六湾区域被撕裂的社会、被践踏的传统伦理、被扭曲的人性以及紧张的人际关系,这些都是湘江流域工业文明初起先天不足和成长缺陷的缩影。我都集中到这一个章节来写。对于这样的处理,不同的读者有不同的看法,三十六湾的有些读者对此心有戚戚,而另外一些读者则坚持认为,这一章节是全书文学色彩最重的部分,真实再现了工业文明在成长和发展历程中曾经存在的种种弊端,凸显了本书写作的现实意义和社会价值。
然后,沿着湘江往下走,就到了水口山和清水塘,这里存在工业体量更为庞大、工业结构更为复杂的经济体。虽然更为复杂的城市会有更为广泛的社会撕裂,但我不得不凝神聚气,把笔触从社会层面收回,全部笔墨集中在密实的企业、密实的污染和密实的环境治理上。工业-污染-环保-工业,我必须循着这条循环推升的叙事主线,借鉴司马迁等先贤们朴素明晰的文风,小心翼翼地处理各种历史资料和现实材料,尽量翔实地完成我对湘江百年历史的讲述。
我在这个漫长复杂的讲述中,放弃了对很多典型化的情节细节的处理,是因为作为一次百年湘江工业发展和环境保护的庞大叙事,我需要保持克制以确保叙事在主干道上推进。在社会发展背景上体现生态环境保护的意义,在生态环境保护主体上体现社会发展的规律,就是这部作品的典型意义。
生态环境保护领域蕴含文学的潜力
李景平:作为一个生态文学作家,生态环保职业成就你而使你拥有了素材富矿,文学艺术素养成就你而使你成为生态文学作家。对于中国生态文学创作和发展的历史和现实,你是怎么看待的?
黄亮斌:现在,很多人都去看手机和刷短视频了,纸质的文学阅读已经成为小众行为,很多文学大师受到网络大咖的嘲讽与消费。在这种背景下,能够有人坚持进行生态文学创作已经很不错了,我对每一位坚持坐“冷板凳”并热情开展生态文学创作的作家表示敬意。中国关于生态环境保护的文学创作,无论是过去的环境文学、生态环境文学,还是当下的生态文学,都凝聚了每一位作家的心血,他们是建立人与自然和谐关系的文化推动者。文学纵使寂寞,我依然认为,它是一个民族最基础、最深沉、最根本的力量。生态文学亦然。
李景平:在中国生态文学创作和发展中,生态环境保护题材的文学创作可能更具现代生态文学意义和生态文明意义,蕴含着巨大的文学潜力。作为置身生态环境保护系统近40年的生态文学作家,你认为生态环境保护题材的文学创作和繁荣,对于生态文明建设会发挥什么样的作用?
黄亮斌:脱贫攻坚和污染攻坚是国家确定的两大战役,但生态文学创作明显偏弱于脱贫攻坚,即使生态文学创作,涉及自然山水的写作也多于环境保护题材的创作,不仅数量多而且质量高。环境保护是生态文明建设的主战场,需要生态文学创作的深度参与,也必将催生一批经典的生态文学作品。
可以说,中国生态文学创作任重道远,且潜力巨大。各级党委、政府以及生态环境部门和文学艺术团体,在生态文学的创作与培育上应该发挥关键性的组织和支持作用。我在这里特别建言的是,涉及自然生态领域的科学家、生态环境学者以及像我这样的多年浸润于生态环境领域的生态环保人,应该将多年的知识和职业积累,转化为生态文学的创作资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