薛忆沩:漫步“文学的黄金时代”
我们都曾经迷恋过《昨日的世界》,我们也都仍然迷恋着“昨日的世界”……这就是为什么我急于想与朋友们分享这本英文新书的理由。
在我看来,这是一本在很大程度上可以与《昨日的世界》相媲美的书,尽管它再现的“昨日”与茨威格在人生末路上缅怀的昨日相距甚远,尽管它聚焦的“世界”也仅仅只是以伦敦为中心和以英语为基调的文学的世界。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是世界文学的黄金时代。这是距离我们最近的文学黄金时代。这也是国际范围内(或者不妨说是“日不落”意义上)的文学黄金时代。而中心的光彩与基调的色泽无疑是这个黄金时代含金量的标尺。最好的例证众所周知:《百年孤独》的英译本被伦敦的出版巨头忐忑不安地推上国际舞台之后,一个南美小国的无名中年作者摇身一变,变成了二十世纪最后的文学之神。
01
这本书的书名是Circus of Dreams,直译出来就是《梦的马戏团》。书名中的两个关键词都带有隐喻的色彩,意指却非常直白:梦当然就是文学梦,而马戏团里的驯兽师、魔术师、杂技和滑稽演员等等当然就是那些身怀绝技的作家、编辑、经纪人、出版商……他们“昨日”各显神通的表演经过历史机遇的奇妙整合就变成了读者们至今都津津乐道的作品。这本书的作者约翰·华什(John Walsh)上世纪70年代末期进入伦敦的文学世界。他首先任职于发现过奥威尔等作者的著名出版社,后来转向大众媒体,并在八十年代末到九十年代初主持《星期天泰晤士报》的文学版面,也就是掌管着英国文学通向市场的喉舌。毫无疑问,他是文学黄金时代的一个关键证人。因此,他的新作也可以看成是一个关键证人为正在渐行渐远的“昨日”留下的一份证词。
此刻摆放在我电脑旁边的不仅是作者的签名本,还直接来自证词聚焦的现场,是经过漫长的“熔断”之后,第一位来自伦敦的亲人带给我的礼物。漫长的“熔断”让我对外面的世界已经心灰意冷,对新奇的事物也已经麻木不仁。所以在接过这礼物的时刻,我没有任何的期待和激动。我将它随手放在门边的鞋柜上,过了大约两个星期才随意拿起,准备敷衍地翻看几页。没有想到,读过两段之后,我就开始激动起来,同时也开始充满期待。我期待着络绎不绝的人物,我期待着层出不穷的故事……在随后的五天时间里,文学的黄金时代完全占据了我的日常生活。
这些人物里当然会包括萨曼·拉什迪,因为他于1981年出版并获得布克奖(也是后来唯一加冕“布克之布克”桂冠)的《午夜的孩子》堪称是这个黄金时代正在到来的捷报。他因此也成为最近四十多年来英国文坛上最受关注的大家。而在这个黄金时代的后期,他抛出的《撒旦的诗篇》又掀起了史无前例的海啸。他因此又成为最近三十多年里国际文坛上最有争议的人物。有意思的是,在《梦的马戏团》里,关于拉什迪的故事却并不是始于举世瞩目的出版,而是始于鲜为人知的租房。这自然大大提高了故事的原创性和吸引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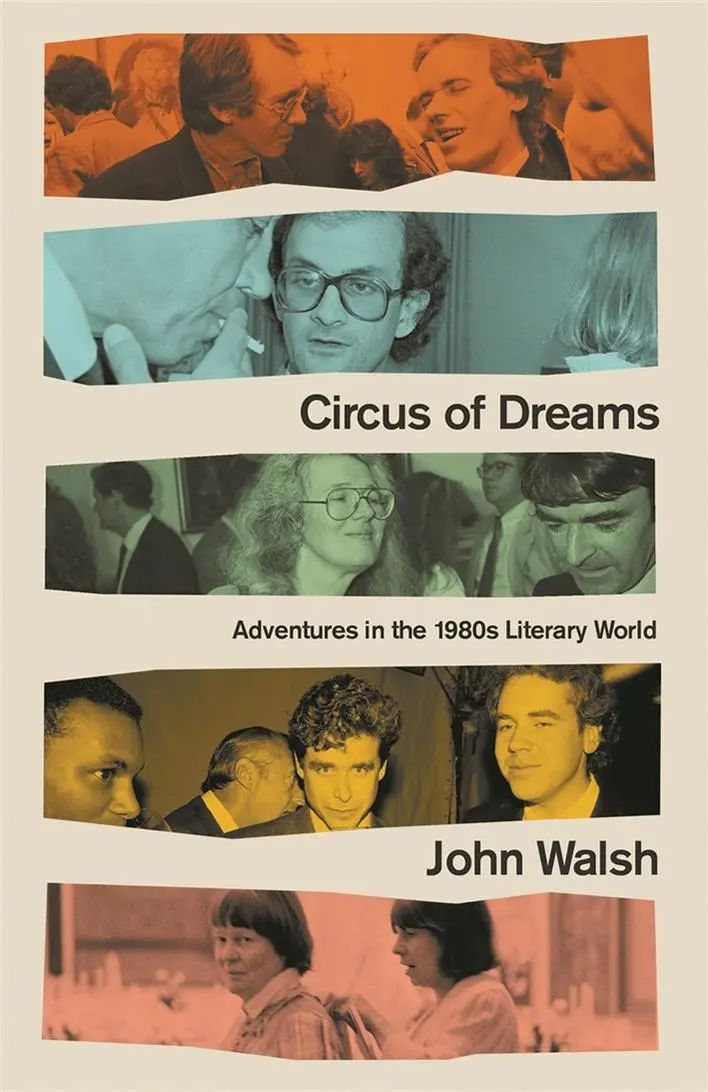
“Circus of Dreams”书影 2022年
02
让书作者成功获得第一份出版社工作的就是后来在黄金时代里不断发掘到金矿的女神级编辑莉兹·卡尔德(Liz Calder)。她有一天与这位新同事谈起了自己1970年代初在伦敦租房的经历。房东的丈夫是一个满怀文学野心又尚无文学业绩的年轻人。他经常在家里组织讨论文学的聚会。就是在其中的一次聚会里,租客首次听到了“《百年孤独》”这个听起来有点奇怪的小说名字。她注意到房东的丈夫对这部翻译小说佩服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她也注意到每逢自己周末离开伦敦的时候,她租住的房间总是会被房东的丈夫侵占,当成工作室。她知道他正在创作处女作。小说终于完成之后,身为资深编辑的租客自然是第一读者。她对这部作品没有任何好感,却还是促成了它的出版(尽管可以肯定,租房协议里并没有给乙方规定任何与文学相关的义务)。后来,卡尔德迁升为伦敦头号出版社(也就是《百年孤独》英译本的出版社)的编辑部主任,掌控出版社选题的生杀大权。这时候,年轻人送来了自己的第二部作品。读过之后,从前的租客既没有欣然接受也没有断然否决。年轻人从女神的沉默里看到的是机遇和希望。他奋力重写了整部作品。当作品再次跨入当年令马尔克斯都望而生畏的门槛,来到女神的面前,它连名字都完全变了,变成了《午夜的孩子》。
这既现实又魔幻的轶事让我马上想到了自己书架上那本名为Imaginary Homelands(《想象的家园》)的随笔集。我接着想,如果将来我要写一篇以拉什迪为主题的文章,我就可以从格林威治时间1998年7月25日傍晚,也就是我在爱丁堡最大的书店里购得他这本随笔集的时刻写起。当然,更好的起点也许是北美东部时间2022年8月12日下午3点。当时我的脑海里突然浮现这篇书评开头的那两个短句。我兴奋地打开电脑,准备借着灵感的火花组织好书评的结构。没有想到,屏幕上的顶端竟突然跳出了关于拉什迪在纽约遇刺的新闻。这难以置信的巧合让我对文学的黄金时代产生了更深的敬畏。
“马戏团”里的少数成员与我个人的文学道路有零星的交集,这是《梦的马戏团》令我爱不释手的特殊原因。比如博学又傲慢的艾科。书作者有一次坐在这位意大利泰斗的身边。他知道他每次来伦敦都必逛市中心的那两家珍本书店,忍不住探问大师最钟情于英国文化史上的哪一位高人。艾科傲慢地将雪茄移开,盯着透红的烟头,吐出了一个令出自牛津大学英语系的提问者顿时感觉无地自容的名字:他从来没有听说过的名字……我自己在1994年6月中旬在伯克利参加第五届国际符号学大会期间,与大师有过几次近距离的接触(包括一段单独的同行和交谈),对大师可气又可敬的博学和可笑又可爱的傲慢早已经有亲身体会(感兴趣的读者不妨参阅拙文《艾科与6月12日下午》),读到这一细节自然感觉十分亲切。
另一位有交集的巨星是亚瑟·米勒。1983年5月7日《推销员之死》在北京首都剧场首演。我在开演前十分钟得到一张从天而降的赠票,有幸坐在剧作家(和陪同他的曹禺先生)的正后方(而我坐的那一排,除了坐在左侧尽头的丁玲夫妇之外,再没有其他观众)。而在《梦的马戏团》里,巨星是借着创立于黄金时代末期的“草镇文学节”(Hay Festival)现身的。精明的创办人想到文学节如果能够请出这位传奇的巨星就等于是同时也召回了玛丽莲·梦露的阴魂。前者当然已经足以确保文学节的品味,而后者又更能够增添文学节的诱惑。心想事成之后,赞助商果然络绎不绝,围观者也果然蜂拥而至。有意思的是,因为许多围观者都准备趁机用露骨的问题出击,逼迫“第四任丈夫”拨开异梦的迷雾,曝光同床的喜乐,创办人担心会出现令阴魂蒙羞又令活人受辱的局面,最后不得不取消了文学节上最受关注的那场活动。
03
“马戏团”里还有一些与文学没有直接关系的人物,他们的故事也同样很有意思。而从看热闹的角度看,他们的故事甚至应该说更有意思。比如报业大亨默多克。他是《星期天泰晤士报》的老板,也就是书作者顶头上司(报社总编)的顶头上司。有一天,大亨突然亲临报社“指导工作”。总编急忙安排各版面的负责人相继汇报。按照版面商业效应的排序,书作者自然是排在最后一个出场,大亨也对他的汇报表现得最无兴趣。不过,他还是没有忘记下达指示。他说起他不久前读到过一本关于“丘吉尔”与希特勒议和的书,感觉很有意思,不知道自己的报纸是不是已经做过书评。在场的人都知道丘吉尔是狂热的主战派,怎么会与希特勒议和?而书作者更是吓了一大跳,因为他不仅根本就不知道这顶头上司的顶头上司说的是什么书,还不知道是不是应该纠正他犯下的常识性错误。而默多克越说越起劲,左一个丘吉尔,右一个希特勒。书作者终于忍不住了。他首先承认自己还没有关注到那本大亨本人也说不出书名的书,接着也顺便纠正说那本书谈论的应该是丘吉尔的前任张伯伦。大亨显然很不高兴小编的承认和纠正。不过,他的反应丝毫无损大亨的尊严。“管他是丘吉尔还是张伯伦,”他不耐烦地说,“反正有这么一本书,我们一定要做书评。”忐忑不安的书作者当然不敢继续多嘴,接着他还突然想到英语里的“丘吉尔”和“张伯伦”都是以“Ch”开头的词,常识性的错误可谓事出有因,也后悔起了自己刚才的多嘴。
除了洋洋洒洒的奇闻趣事之外,书中还穿插着不少冷静的历史观察和激情的价值判断。关于文学黄金时代三种最成功的小说题材的总结就是前者的范例:第一种是当代历史题材,也就是以二十世纪某一重大历史事件为背景的作品,《午夜的孩子》当然属于这一类。另一部代表作品则是《生命不能承受之轻》;第二种是同性恋题材的作品,这是中国读者最不熟悉的一类;第三种是宗教题材,代表作品当然首推艾科的《玫瑰之名》。而激情的价值判断突出地表现于书的后记。它就如同一曲文学黄金时代的哀歌,读来不仅发人深省,还催人泪下。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同样是中国当代文学的黄金时代。在那个“昨日的世界”里,老一辈作家如“重放的鲜花”,仍在用余热争奇斗艳;青壮年作家则争先恐后地爬上西方巨人们的肩膀,开始了万紫千红的呈现;而未来一代的作家正在朝气蓬勃的校园里沐浴着改革开放的春意,已经洋溢着含苞待放的生机。那真是一个青黄相接的时代。那真是一个百花齐放的时代……历史的这种神奇合拍与押韵当然也是为什么我急于想与朋友们分享这本英文新书的重要理由。


